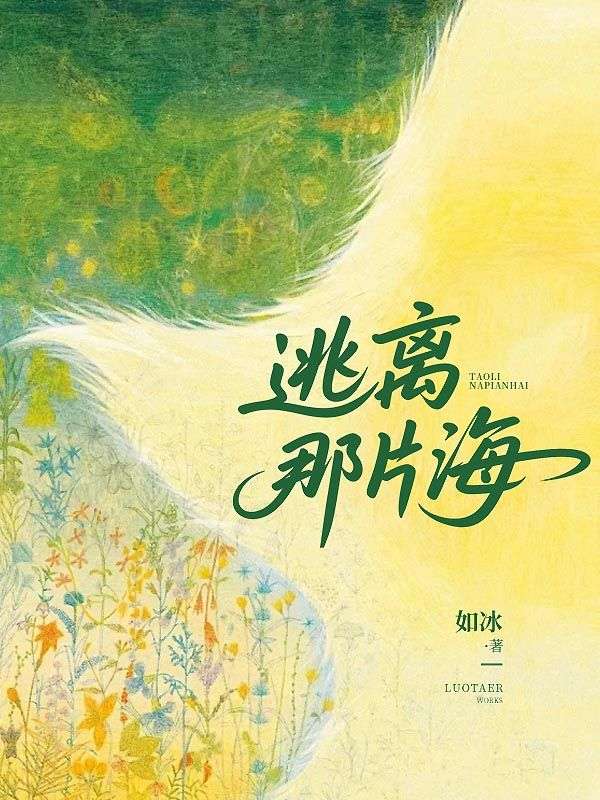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3
第二天,教練來接人。
看到的是滿地的碎片,和拿著掃把守在門口、滿身是血如同惡鬼的我。
教練被嚇跑了。
林海哭得撕心裂肺。
她跪在地上,拚湊著那件泳衣。
“為什麼!你為什麼見不得我好!”
“你是啞巴,你就要我也變啞巴嗎?”
“你嫉妒我!你嫉妒我有出路!”
“我恨你!我這輩子都恨你!”
那天,我當著全村人的麵,拽著她的頭發,把她拖回了屋裏。
扔給她一本《新華字典》。
那是阿寧生前最想買的書。
我把門鎖死。
任憑她在裏麵哭暈過去,任憑老林在外麵踹門罵娘。
我坐在門口,守了一夜。
聽著海浪聲。
我想,恨吧。
恨著恨著,你就長大了。
長大了,你就遠走高飛了。
隻要不碰水,你恨我入骨也沒關係。
初中三年,她沒再回過一次家。
她住校。
拚了命地讀書,像是為了報複我。
每次考試都是第一。
老師誇她,同學羨慕她。
隻有我知道,她是想逃。
想逃離這個瘋子母親,逃離這個充滿魚腥味的家。
老林賭輸了錢,欠了一屁股債。
要把林海賣給隔壁村的瘸子換彩禮。
“讀個屁的書!讀到現在也沒見拿回一分錢!”
“瘸子出八萬!有了這八萬,我就能翻本!”
那天,我正在碼頭給人撬生蠔。
十塊錢一筐。
手在冰水裏泡得發白、腫脹、潰爛。
聽到這個消息,我瘋了一樣跑去學校。
老林正拽著林海往外拖。
“跟你老子回家!嫁人生娃才是女人的命!”
林海死死扒著校門,眼神絕望。
“我不回!我要考高中!我要上大學!”
周圍圍滿了看熱鬧的人。
“這老林也是作孽,不過女娃娃讀書確實沒用。”
“就是,那啞巴婆娘供了這麼多年,也該盡頭了。”
我衝過去。
一口咬在老林的手腕上。
死死咬住,直到嘴裏滿是鐵鏽味。
老林慘叫一聲,鬆開了手。
反手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
“臭啞巴!你敢咬我!”
他抄起旁邊的磚頭就要砸。
我爬起來,一把推開林海。
“啊!!”
我用盡全身力氣,把她推進了學校大門。
然後轉身,抱住了老林的腿。
磚頭落下來。
砸在背上,砸在肩上。
我聽見骨頭斷裂的聲音。
但我沒鬆手。
我看著門內的林海,滿臉是血,卻對她露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
我想說:別怕。
媽在。
媽這輩子是個廢人,是個啞巴,是個瘋子。
但媽絕不會讓你走阿寧的老路,也絕不會讓你走我的老路。
那天之後。
全縣都知道了,那個瘋啞巴為了讓女兒讀書,差點被打死。
林海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我。
眼神複雜。
沒有感激,隻有深深的恐懼和厭惡。
“你能不能別這麼極端?”
“你知不知道同學們都怎麼看我?”
“他們說我是瘋子生的女兒,說我以後也會瘋。”
她背過身去,冷冷地說:
“這筆錢我會還你的。等我考上大學,我就再也不回來了。”
我看著她的背影,點了點頭。
好。
隻要你走。
隻要你活在陽光下。
如今,她真的做到了。
她是著名的設計師,她住在北京,有體麵的生活。
公交車到站了。
我拖著病體,回到了那個破舊的漁村。
老房子已經被噴上了大大的“拆”字。
老林幾年前喝醉酒,掉進海裏淹死了。
報應。
都是報應。
我走進屋裏,翻出一個生鏽的鐵皮盒子。
那是我的寶貝。
裏麵有阿寧的一張黑白照片。
有林海小時候剪碎的那件泳衣碎片,被我一片片縫起來了,雖然很醜。
還有一張張彙款單。
這幾年,她雖然恨我,但每個月都會打錢。
備注永遠隻有兩個字:活著。
我知道,她是用錢在買斷我們也就不剩多少的母女情分。
突然。
門口傳來一陣急促的刹車聲。
緊接著,是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聲音。
很急,很亂。
門被推開。
逆著光,我看到了林海。
她不是走了嗎?
她氣喘籲籲,頭發有些淩亂,眼睛通紅。
手裏死死攥著一張紙。
那是......王嬸給我的診斷書?
我下意識地想把鐵皮盒子藏到身後。
“藏什麼?”
她聲音顫抖,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哭腔。
“肺癌晚期?三個月?”
“你寧願死在個破屋子裏,也不肯告訴我?”
她大步走過來,一把搶過那個鐵皮盒子。
“這是什麼?”
林海的聲音在發抖。
鐵盒蓋子被掀開,一股陳舊的黴味混合著鐵鏽氣撲麵而來。
沒有她以為的臟東西。
沒有她以為的屬於瘋子的垃圾。
最上麵,是一遝厚厚的彙款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