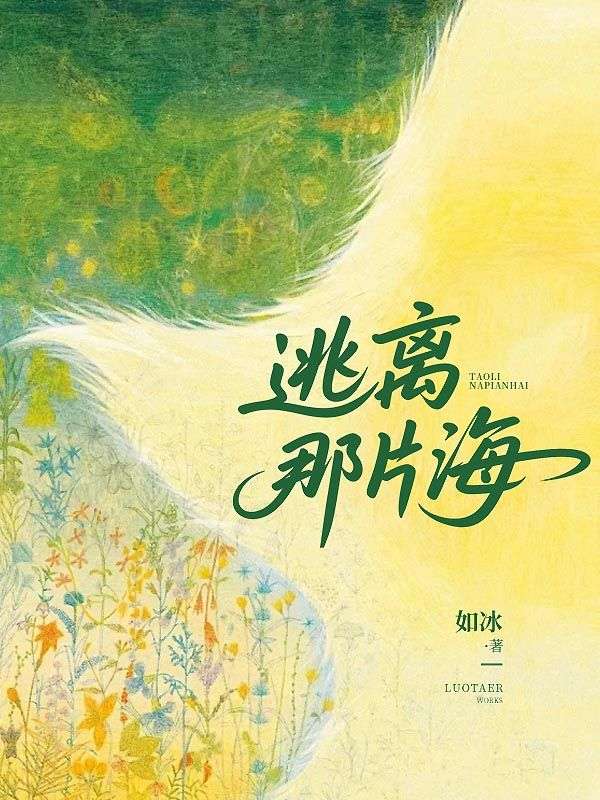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2
公交車晃晃悠悠,開往那個我守了一輩子的漁村。
窗外是漫無邊際的灰藍色大海。
“阿婆,你也去趕海嗎?”
鄰座的小姑娘背著書包,手裏拿著個塑料小桶,笑得燦爛。
“我媽答應我,隻要期末考雙百,就帶我去潛水!”
“海裏可漂亮了,有珊瑚,有小醜魚。”
我看著她,身子控製不住地發抖。
我想吼她,想奪過她的桶扔出窗外。
想告訴她:海裏沒有珊瑚,隻有吃人的漩渦和回不來的屍骨!
但我發不出聲音。
我隻能死死抓著扶手,指甲幾乎嵌進肉裏。
記憶像潮水一樣湧上來。
那個年代,漁村窮得叮當響。
女娃娃不值錢,要麼嫁給船老大當填房,要麼就下海當“海女”。
不帶氧氣瓶,赤身跳進十幾米深的海裏挖珍珠、撈海膽。
那是拿命換錢。
我最好的姐妹阿寧。
她是我們村水性最好的姑娘。
她說:“阿月,等我攢夠了珍珠,我就帶你坐大船,去海那邊的城市。”
“那裏有高樓,有汽車,不用天天喝鹹水。”
那天風很大。
村長說不能下海。
可阿寧想走,她太想走了。
她為了多湊那最後一點路費,偷偷潛了下去。
我在岸上等啊等。
等到天黑,等到漲潮。
隻等到了一具被礁石撞得麵目全非的屍體,還有那隻死死攥在手裏的珍珠網兜。
阿寧的肺炸了。
七竅流血。
村裏人說,這是海神的懲罰,是因為她想逃。
我抱著她冰冷的屍體,哭啞了嗓子,發了一場高燒。
醒來後,我就成了啞巴。
後來,我嫁給了村裏的爛賭鬼老林。
生下了女兒,取名林海。
多麼諷刺的名字。
老林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這丫頭以後也是個當海女的好料子。
林海三歲那年,就能在水裏閉氣兩分鐘。
她有著驚人的天賦,那是刻在骨子裏的、屬於大海的詛咒。
老林高興壞了,逢人就吹噓:“我家要出個金鳳凰,以後撈鮑魚能發大財!”
隻有我。
在這個被魚腥味籠罩的家裏,像個瘋子一樣把她從水缸裏提出來。
狠狠地打。
拿著竹條,抽得她滿身紅痕。
“啊!啊!!”
我指著書本,指著遠處的大路。
我要告訴她:讀書!
隻有讀書,才能坐車走,不用遊過去!
隻有讀書,才不會像阿寧一樣,肺炸開,死在冰冷的水底!
可她不懂。
她哭著喊:“媽,我疼!我喜歡水!為什麼別的孩子能玩,我不行!”
老林喝醉了酒,一腳踹在我心窩上。
“死啞巴!瘋婆子!你斷我財路!”
“她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你讓她讀書?讀書能當飯吃嗎?”
老林的拳頭雨點般落下來。
我護著頭,護著懷裏的課本。
我不怕疼。
我怕我的女兒,變成下一個阿寧。
林海十歲那年,村裏來了個省隊的遊泳教練。
他在海邊看到了像條魚一樣穿梭在浪裏的林海。
教練眼睛都亮了。
“天才!這是百年難遇的天才!”
“大嫂,讓你女兒跟我走,進省隊,以後能拿金牌,能為國爭光!”
老林樂瘋了。
因為教練說,隻要簽了約,有一筆不菲的簽字費。
林海也樂瘋了。
她看著那個教練,像看著救世主。
“媽,我想去!我真的想去!”
“教練說我能遊得比誰都快,我能去奧運會!”
那晚,家裏像是過年。
老林買了燒酒,林海收拾著她的小包袱,眼睛裏閃著從未有過的光。
隻有我坐在角落裏,磨著一把生蠔刀。
刀刃在磨刀石上蹭出刺耳的聲響。
“滋啦,滋啦”
半夜。
趁著他們熟睡。
我拿著剪刀,把林海那件珍貴的、教練送的連體泳衣,剪成了碎片。
我把她的泳鏡砸得稀爛。
然後,我做了一件更瘋狂的事。
我拿著那把生蠔刀,衝進了老林的房間。
我沒殺他。
我隻是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因為用力,血順著脖頸往下流。
我死死盯著被驚醒的老林,喉嚨裏發出野獸般的低吼。
“啊!!!”
我不許。
誰敢帶她下水,我就死在誰麵前。
老林嚇傻了。
“瘋子......你這個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