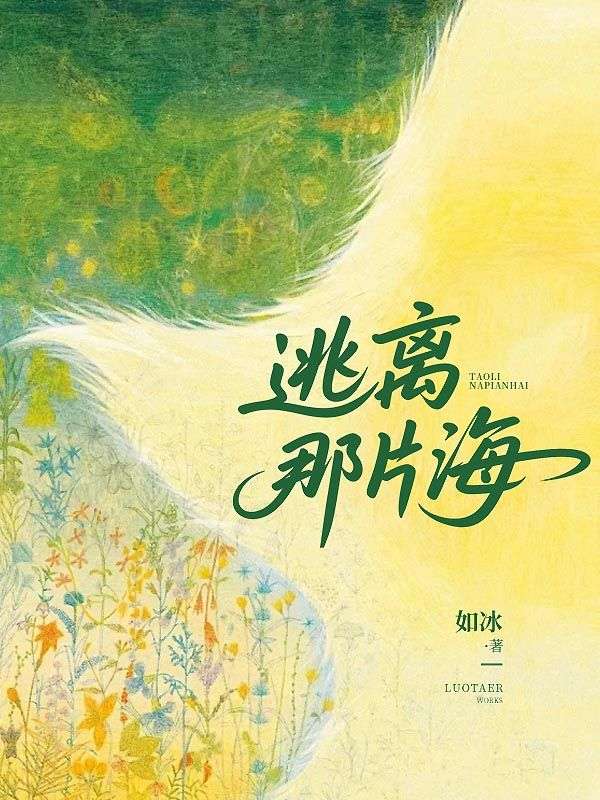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1
拿到斷絕關係判決書的那天。
外麵下著瓢潑大雨,女兒站在法院門口,沒打傘。
她把那張薄薄的紙折好,放進那萬把塊錢的皮包裏。
我想伸手給她擋擋雨,嘴裏發出“阿......阿......”的嘶吼。
手伸到半空,卻又觸電般縮了回來。
怕她嫌臟。
也怕她嫌我這個啞巴丟人。
她回頭看了我一眼,眼神冰冷。
“以後別來找我。”
“也別讓人知道,著名的跨海大橋設計師,有個瘋子當媽。”
我張了張嘴,拚命點頭。
雨水順著我臉上溝壑般的皺紋流進嘴裏,鹹澀得厲害。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所以我按了手印,我放你走。
隻要你不上那艘船,隻要你不下那片海。
去哪都好。
......
三年後。
一輛黑色的豪車停在滿是魚腥味的巷口。
車窗搖下,那是張經常出現在電視新聞裏的臉。
精致、冷豔,早已沒了當年那個在泥灘裏摸爬滾打的野丫頭的影子。
女兒手指修長,遞出一張卡。
“這裏有五十萬。”
“老房子拆遷的事我知道了,這錢你拿著,去養老院。”
我局促地搓著衣角,手上全是長年累月撬生蠔留下的傷疤和洗不掉的腥氣。
我擺手。
嗓子裏發出急促的“啊啊”聲。
把卡推回去。
我有錢。
我撬了一輩子生蠔,織了一輩子漁網,我有錢。
她眉頭皺起,像是看著一堆不可回收的垃圾。
“拿著!”
“別讓我欠你的。”
“我不希望以後有人挖我的底,說我虐待殘疾老人。”
那張卡硬生生砸在我臉上。
棱角劃過顴骨,有點疼。
但我沒躲。
她看著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諷的笑。
“你還是老樣子。”
“除了像個瘋狗一樣亂叫,除了用蠻力,你什麼都不會。”
“小時候你打我、關我、燒我的泳衣,現在你還想用這種可憐姿態來綁架我嗎?”
“省省吧,啞巴。”
車窗升起。
豪車卷起地上的臟水,噴了我一褲腿,揚長而去。
我彎腰撿起那張卡。
擦了擦上麵的泥點。
五十萬啊。
夠買好多好多書,夠交好多好多學費了。
我把卡揣進貼身的兜裏。
轉身上了去往縣醫院的公交車。
車上人擠人,都是帶著鹹魚味兒的漁民。
電視裏正放著她的專訪。
主持人問她:“林工,聽說您的設計靈感都來源於對海洋的熱愛?”
屏幕裏的她,笑得得體又自信。
“不,是因為征服。”
“我從小就發誓,我要把海踩在腳下,我要造出最堅固的橋,讓所有人都能逃離那片深淵。”
“我不想讓任何人,再被困在孤島上。”
我看著屏幕,渾濁的老眼突然就模糊了。
逃離好啊。
逃離了,就不用死了。
我摸了摸口袋裏的診斷書。
肺癌晚期。
長期的海風侵蝕,加上年輕時為了供她讀書,沒日沒夜在冰水裏幹活。
身子早就透支了。
隔壁的王嬸給我打來電話。
她是這世上唯一知道我秘密的人。
電話那頭,她哭得喘不上氣。
“阿月,你個死啞巴,你是不是又沒告訴她?”
“你都要死了!你就讓她恨著你送終嗎?”
我拿著手機,輕輕搖了搖頭。
對著話筒,艱難地敲擊了兩下外殼。
這是我們約定的暗號。
別說。
說了,她會愧疚。
她是造大橋的人,心裏不能有裂縫。
那些陰暗的、潮濕的、帶著血腥味的過去。
就讓我這個瘋婆子,帶進棺材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