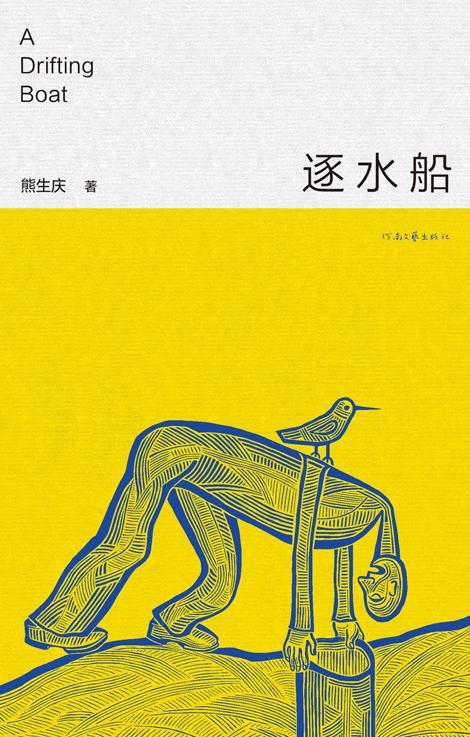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八
年關前夕,每家每戶都要熏臘肉、做臘腸,正是豬肉旺銷好時節。三叔終日魂不守舍,清早用板車把肉拉到肉鋪,賣肉的活便交給夥計小吳,轉眼就沒了蹤影。三嬸嗔怪我爸,不該在這節骨眼上出這餿主意。我爸說,這是為十九好,北方大漢一看就是練家子,動起手來,傷到誰都不好。那些天,漢子神出鬼沒,我們都摸不準他什麼時候出門,什麼時候回來。
除夕早上,吃過湯圓,我媽著手準備年夜飯,我爸帶著我打掃衛生。收拾後院,我特意看了看那塊梨木案板,中間凹下去倆拳頭那麼深,像個木盆。打掃完衛生,我爸帶我上街,買了春聯、燈籠、炮仗、香蠟紙燭,還買了兩箱煙花,準備吃過年夜飯後放。到家後,我爸攪了糨糊,帶著我貼春聯,掛燈籠。三嬸把洗衣機搬到院子裏,把家裏的臟衣服全收集起來堆在旁邊,開始洗衣服。臟衣服堆得小山似的,鐵頭在衣服堆裏打滾,樂得嘿嘿傻笑,邊笑邊流口水。
下午,街上刮起風。我爸說,春風吹,又一春。年還沒過呢,我說。我媽說,鐵蛋,你又長大一歲。我心裏歡喜莫名,楊柳街的時間太漫長,我希望自己快些長大。三嬸說,過不幾年,鐵蛋就要娶媳婦啦。我爸媽笑起來。我本想說到時也要娶個像三嬸這麼漂亮的媳婦,沒好意思。從廚房裏飄來血豆腐的香味,我正要衝進廚房,街麵上傳來高亢的歡呼聲。
人群洪水般湧來,打頭的是獨眼龍和三叔,他們簇擁著北方大漢,漢子胸前戴著大紅花,極不自然地笑著,朝我們家走來。葉屠夫和李大耳不知從哪兒弄來兩麵軍鼓,捶得震天響。人群很快擁到門前,有人在院門上拉了條幅,上麵寫著個大字:“勇擒劫匪,為民除害。”不一會兒,廠領導和派出所老黎也來了。老黎激動地對北方大漢說,劫匪已解送市裏,你耐心等待,爭取為你開個表彰大會。漢子憋紅了臉,他把胸前的紅花摘下,順手掛在院門上,湊到三叔耳邊說了幾句話。三叔接過李大耳手中的鼓棒,重敲幾下,人群安靜下來,他說,劫匪逮了,天也要黑了,各回各家,年夜飯我們家不管。
有消息傳出來,說劫匪是一九九二年冬天私賣廢鐵被抓的那兩個,這案件當年廠子內外盡人皆知,倆人被抓後,吃了幾年牢飯,受了不少苦,出獄後懷恨在心,又沒了飯碗,便鋌而走險,盯著水鋼作案。我爸問漢子,你是怎麼找到劫匪的?漢子指著鼻子說,一個字——嗅。這事湊巧,通過周密工作,警察終於查到劫匪落腳處,選在那天中午動手抓人。倆劫匪力氣大,掙脫警察奪路便逃。北方大漢撿了個便宜,堵住劫匪,和警察一道把人給逮了。
年夜飯已經備好,有豬肘子、辣子雞、蒸鱸魚、老水鋼烤鴨子等,我數了兩遍,一共十六道菜。我爸從櫃子裏摸出兩瓶老酒,滿滿當當倒出四碗,又給我媽勻了幾滴,屋子裏溢滿酒香。燒過紙錢,供過祖宗,正式開始吃年夜飯。老水鋼的春節,數這頓年夜飯最隆重、最講究。街麵上陸陸續續響起炮仗聲,年夜飯吃得早的人家,已經開始放煙花。人坐齊,北方大漢率先端起酒碗,朗聲說,這碗酒敬你們。言罷,漢子一仰頭,酒入喉嚨,碗已見底。他站起身,退到一側,兩手一拱說,多有打擾,見諒,我這就告辭。三叔攥住他,嗔怪道,這是鬧哪一出?漢子握住三叔手說,我一個浪蕩子,不喜歡團聚。三叔坐下,悠悠說,你不是想看我的刀嗎?漢子一愣,想,他說。
三叔正襟危坐,道出了刀法淵源。
清朝初年,平西王吳三桂征剿水西,水西宣慰使安坤節節敗退,引兵據守水城阿紮屯。安坤憑借阿紮屯四周天險,緊扼山門要道,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平西王久攻不下,戰事陷入膠著。
這一晚,三更時分,平西王近侍奢那沙接到密令,要他連夜啟程,潛往烏撒衛尋找一個叫熊希野的私塾先生。此人熟諳水西地形,頗有謀略,且曾被安坤驅逐,或有破敵之策。奢那沙原是蜀人,練得一身好武藝,使一口威武的斬馬刀,一刀在手,勢大力沉,威風赫赫,雖百十人亦不能近身。哪知奢那沙行至阿佐,突然風雨大作,電閃雷鳴之際,馬失前蹄,跌到深溝中,被安坤手下先前衝散的一股散兵拋網困住,抓了個現成。
探知安坤被困,那股散兵就近遁入深山,按兵不動,一連躲了五日。奢那沙暗自尋思,期限已過,就算找到熊希野,也免不了受罰,一旦平西王撤圍,這股散兵勢必去尋安坤,那時候,隻怕性命不保。左右不是辦法,他想到了第三條路——逃。趁守兵換防之際,他掙斷繩索,連滾帶爬梭進密林之中。
逃離險境的奢那沙找來本地土人服裝穿上,扮作收藥材的商人一路往北走。不知走了多久,在一個叫也裏古的村子裏,他終於聽到人們說起那場戰事的結局。不出所料,平西王大獲全勝,安坤兵敗被俘。這並不是什麼好消息。如果安坤得勝,他大可逃回蜀中,重新開始生活,而今平西王掃平水西,固守西南、放馬蜀中之勢已成,中原也盡是其耳目,他無路可走了。奢那沙萬般絕望之際,十萬烏蒙大山張開無私懷抱,將這個無路可走的人藏進深山。
那個戰亂頻仍的年代,山裏也不太平,匪盜四起,打家劫舍之事時有發生。為防暴露身份,大刀斷然不能再使,奢那沙從山裏人用的手鐮得到啟發,打造了兩把鷹爪刀,采眾家所長,糅合所學武藝,自創了一套攻守兼備的近身刀法,這便是這套刀的由來。
奢那沙娶了個當地女人,在山裏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慢慢斷了回蜀地的念想,後半生過得還算平穩。臨死,他把兩個徒弟叫到跟前,專門交代要把刀法傳下去。他規定,每一代隻傳兩人,傳男不傳女。念及當年逃亡時的艱難困苦,老人特意交代,對身逢絕境、天資聰穎的後輩,要優待一分,高看一眼。後人恪守奢那沙遺命,於十萬大山之中,茂林掩映之下,秘密傳承著這套獨門刀法。到老嘎姆這裏,已經是第九代。
奢那沙創刀之初,並未給刀法命名,傳到第四代,因翁達老師祖是苗族人,後人方便起見,就把這套刀稱作苗刀。到老嘎姆這一代,師兄染上暴疾,還未及傳刀便英年早逝,因此,培養苗刀第十代傳人的任務落到了老嘎姆頭上。天可憐見,西郊觀音山上,正在采藥的老嘎姆遇到準備跳崖自盡的三叔。老嘎姆說,三叔手準,是學刀的好料子。另一個傳人,是他的兒子阿雕。
這刀法創立之初,其意便不在攻,而在守,守護亂世中的生靈,守護妻兒老小,守護手裏的飯碗,守護沉默的群山……
三叔眼中有淚光閃過,劈裏啪啦的炮仗聲陡然傳來,喝完最後一碗酒,北方大漢起身告辭。他對三叔說,我的刀,和你不同。言罷微微欠身,消失在夜色中。
三叔跟了出去。夜漸深,細細的雪花稀稀疏疏灑落。
三叔直到午夜才回來。他撣掉身上的雪,問我爸要了根煙。那是我第一次見三叔吸煙。吸完煙,三叔說,北方的刀,霸道。說完他回屋睡了。
第二天,三叔告訴我們,漢子名叫宮延武,人稱宮一刀,沈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