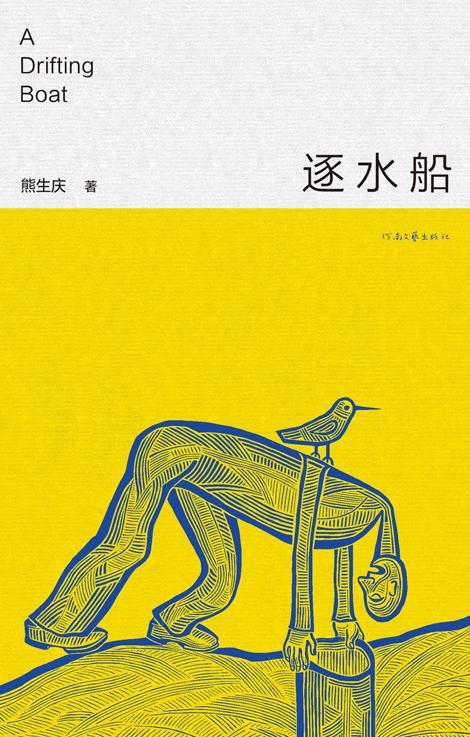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七
這年冬天比較暖和。一個日光和煦的下午,我們家來了位特殊客人。當時我正在院子裏幫我媽擇菜,每個月我媽都要做酸菜,這次做的酸菜是要吃到第二年的,很快要過元旦了。電視上說,今年的元旦叫跨世紀,我沒弄明白,隻是感覺要比往年熱鬧,廠子裏早早掛起燈籠,街上慶祝元旦的大紅條幅也比往年更多。水城人愛吃酸,吃那種漚得黏噠噠、水汪汪的清湯酸菜,或是用番茄酵成紅彤彤的紅酸湯,把菜或肉下在裏頭煮著吃。做酸菜需要酸本,即把上次吃剩下的酸菜勻一缽出來,待新酸菜做好裝壇,再將那缽酸菜淋在上麵,以幫助新酸菜發酵。我媽舀了一大缽酸本放在方桌上,整個院子裏彌漫著濃鬱的酸味。一道修長的身影從大門裏飄進來,我抬頭,一個頭戴狗皮大棉帽、身穿軍綠色齊膝羊皮襖的漢子踏進來。那人奇高,手裏提著條手腕粗的火棘棍子。漢子吸吸氣,用手捂住鼻子,打了個響亮的噴嚏。他指著方桌上的酸本說,咋這麼臭?漢子說的是普通話。我媽從屋裏出來,上下打量漢子一番,問他,你找誰?熊十九,漢子說。我媽說,你是十九的朋友吧?漢子不說話,在花池邊坐下來。十九一家進城買東西,得傍晚才回來,我媽說。漢子說,我等著。
我繼續擇菜,我媽把我爸從床上叫起來,我爸沏了壺茶,和漢子並排坐在花池邊喝。漢子摘下頭上的棉帽,一顆圓圓的大腦袋鋥光瓦亮。我爸問他,你是外地人吧?漢子點頭。我爸說,從哪兒來?北方。漢子的回答異常簡潔。我媽把他們叫進屋,她已經焙好一海碗蛋炒飯,盛了缽素瓜豆,擺在我們家餐桌上。漢子憨笑,說聲謝謝,埋頭便刨。眨眼工夫,那碗飯就見了底。漢子喝完湯,問,還有嗎?飯是沒了,我媽又下了碗麵條,外加兩顆煎蛋。吃完,漢子滿足地抹抹嘴,說,南方的麵條。我爸說,南方麵條怎麼了?漢子說,沒事兒。說完,倒在我們家沙發上閉眼就睡。我爸對我說,去,找你叔。
黃昏時分,三叔和北方漢子見麵了。我和三叔回來時,漢子已經候在院裏。漢子上下看了看三叔,說,你是熊十九?你是哪位?三叔問。原來他們並不相識。漢子走到院門前,輕輕關上門,轉過身說,我走南闖北,啥也不愛,就愛玩個刀,聽說你使刀利索,咱比畫比畫。漢子輕輕摩挲手掌,補充說,不耽擱時間,我看這兒挺好。三叔鬆了口氣,嗔怪道,大白天你闖進我家來,我還尋思是不是得罪人了。說著,三叔走到院門邊,打開院門。漢子說,聽說你使苗刀。三叔說,你可以走了。漢子說,看不上我?三叔說,我隻是個殺豬的。漢子朗聲一笑,火棘棍子往前一戳,說,不鬥狠,不傷人,分了輸贏馬上走。三叔說,你使長刀,一板一眼有個說法,我使的是巴掌大小的玩意兒,入不了眼,出了門,你就說我輸給你了。漢子一愣,說,你不是使苗刀嗎?此苗刀非彼苗刀,三叔說。漢子歎一聲,收起拐杖。
本以為漢子第二天會離開,可早晨我起床,發現他已經在後院幫三叔幹活了。他們用板車裝好新鮮的豬肉,正出門往肉鋪送。早飯時,我媽問我爸,要不要報警。我爸說,看樣子那人沒惡意。三嬸說,報警幹嗎,如果想動手,大不了跟他幹一仗。
漢子住了下來。他幫三叔殺豬賣肉,把這兒當自己家。每天清晨,他們並排走在楊柳街上,一高一矮的兩個背影看起來十分滑稽。後來,彭二先生對楊柳街的人說,看到三叔和北方大漢一高一矮走在街麵上,他就已經算到會發生什麼。不過,彭二先生說,他從派出所出來後,身體垮了,整日躺在床上,沒來得及告訴大家。花伯娘罵他,臭不要臉的東西,既然你終日躺在床上,是怎麼看到人家在街上走的?
過了小年,年味越來越濃。這天晚飯時,三叔問北方大漢,你不回家過春節?漢子說,沒家,老爹老娘走得早,有個哥哥,前些年進山給木材老板當保鏢,進去便沒出來。三叔夾了塊肉,仔細嚼著,吃完那塊肉,他說,你這意思,要長住?漢子放下碗筷,笑說,你啥時候跟我比刀,我啥時候走。三叔把碗一扔,說,刀法早忘了,你怎麼不信呢?漢子笑,你讓我怎麼信?三叔說,你想怎樣?漢子說,本來我快信了,見你家後院剁肉末那塊老梨木案板,見你賣肉從不用秤,沒法信。三叔說,你上街問問,我這估斤兩的本事老早就會。漢子說,使刀講究穩準狠快,你身子骨瘦小,速度快,賣肉不過秤,這是準;據我所知,你賣肉沒幾年時間,那塊老梨木案板,正常情況十年以上才能砍那麼深的凹痕,說明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剁的不是肉末。三叔額頭上滲出汗粒,癡癡盯著漢子。漢子說,還要我繼續說嗎?
當啷,我爸的飯碗掉到地上,碎了。啊呀,我爸說,隻顧聽你們聊天,碗都掉了。我媽趕緊找來掃帚,打掃地上的碎碗。三嬸放下碗筷,把鐵頭叫回了屋。我爸對漢子說,你知道前段時間出的事吧?漢子搖頭。我爸重新盛了碗飯,把連環搶劫案給漢子說了一遍。漢子怒目圓睜,有這種人渣?三叔咬牙切齒說,最好別落我手上,否則我非剮了這倆畜生。我爸放下碗筷,緩緩說道,你們練了一身武藝,依我看,比刀沒趣,要能把這倆禍害逮出來,那才算本事。啪,漢子一掌拍在桌上,湯水四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