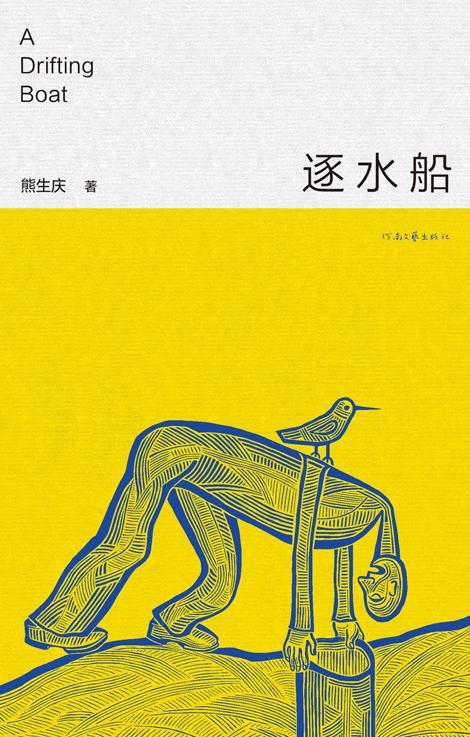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三
黃昏,黑雲密布。
獨眼龍一聲吆喝,十八家肉鋪早早收攤,集中到叔肉鋪前。獨眼龍走到三叔跟前,往他口袋裏塞了幾張票子,說:贏了,這是入行開張紅錢;輸了,是打發你的盤纏,打哪兒來,回哪兒去。人群中掌聲響亮。李大耳說,十九,這是肉行最高禮遇啦。三叔雙手拱起,朗聲說,講究。李大耳朝肉鋪努嘴,兩個後生近前來,把鋪子裏的豬肉抬走。
也不知是哪朝哪代傳下來的規矩,肉行比刀,是在豬白條上拚功夫,誰在最短的時間內漂漂亮亮解好豬白條,就算誰贏。此前獨眼龍說比刀,三叔還以為要打架,因此有所顧忌,李大耳講解後他才明白原來是解豬白條。我問三叔,你解過豬白條嗎?三叔說,算不上。我說,那你還敢答應?三叔抬起他油乎乎的手,又想拍我的頭,我趕緊躲開。
解豬白條有講究,說的是“骨歸骨,肉歸肉,五臟六腑得鑽透;一刀富,一刀窮,不砍不剁不沾油”。“骨歸骨,肉歸肉”,即肉和骨頭要分開,考校剔骨頭的功夫。“五臟六腑得鑽透”,說的是切開豬白條後,豬肚子裏的五臟六腑不僅要完整刨出來,還得把心肝肚肺腸等分門別類拆開,交給學徒或者夥計清理。“一刀富,一刀窮”,說的是切肉的本事。會切肉的人,一刀下去,幹淨利落、圓潤飽滿,沒有半點餘肉,客人能全買光;不會切肉,刀子拖泥帶水,刀口橫七豎八,顧客挑來揀去,最後留下一堆“爛肉”沒人要。“不砍不剁”,是說解豬時全程不能用刀剁,也不能硬砍,隻能用刀拆。“不沾油”,是說豬板油要剔幹淨,不能殘留在內臟及胸腔肉上,還有一層意思是說殺豬的人不沾油,要讓屠夫看起來不像殺豬的。這有些玄乎。
四個漢子扛來兩頭鼓囊囊的豬白條,獨眼龍挽起袖子,走到三叔跟前說,湊彩頭吧。三叔一愣,沒聽明白。屠夫們哄堂大笑。李大耳湊到三叔身旁,快速解釋一通,三叔這才掏出錢,塞到豬嘴巴裏。原來,肉行比刀要先掏錢,豬白條的錢。比贏了,豬嘴巴裏塞的錢和肉都是自己的;輸了,不光錢拿不回,肉也得不到。
獨眼龍那把明晃晃的剔刀已攥在手裏,他用刀背輕拍豬屁股,幽幽地說,肉行比刀,都怕打頭陣被人瞧走刀法,我不怕,讓你一手,免得大夥笑我欺你手新。說罷,他朝人群中掃一眼:誰來計時?慢著,三叔說。他站到肉案子前,拱手道,馮大哥,我先來。獨眼龍似笑非笑,你確定?三叔點頭。
起風了。
涼風過處,卷起陣陣煙塵。
三叔彎腰,手裏多了兩把黑黝黝的鷹爪小刀,刀尖如刺,刀身極窄,隻巴掌長短。那刀攥在手裏,不細看,很難察覺。我離得近,看清了,正是削掉葉屠夫和李大耳頭發的那兩把刀。三叔縮手,連掌帶刀退回袖子裏,朝獨眼龍側身,低聲說,見笑。“笑”字出口,他朝豬肚子閃電般揮出個“十”字,眨眼之間,他已收刀回袖,側立一旁。
獨眼龍眨巴著左眼,有些犯迷糊。他催促,動手啊。說話間,豬肚子上滲出兩條細細的十字紅線。獨眼龍湊近看,淡紅色的血水緩緩流出來。獨眼龍伸出兩根手指頭,往十字紅線交叉處輕輕一戳,露出白生生的肥肉。再一掰,豬肚子已順著十字紅線切開,連肚子裏那層白色的油脂都切開了。獨眼龍又掰了掰,大腸小腸現出來。刀口齊齊整整,深度恰好,內臟並未損傷分毫。
獨眼龍張大嘴巴,盯著被剖開的豬肚子。良久,他抬頭,傻愣愣看著三叔。三叔搓手說,來吧,我接著忙活。獨眼龍站在肉案前,挪不動步。三叔靠過去,輕輕推他:馮大哥?這一聲把獨眼龍叫醒了。他揮手,將剔刀扔給身邊人,一言不發,消失在街頭。
閃電刺破黃昏,雷聲滾過,轟隆不止。
人群聚得快,散得也快。空蕩蕩的街上隻剩下我和三叔。他鐵青著臉,不說話,雙手顫抖不已。長大以後,當我又一次問及那次比刀,三叔說,鋌而走險唬人罷了,要來真的,我必輸無疑。說這話時,三叔的肉鋪已歇了好些年。
出了風頭,廠子裏外都知道三叔回來了,肉鋪一炮而紅。三叔每天守在肉鋪前,也不多話,割肉收錢,找零送客。賴著手上估斤兩的本事,他的肉鋪不怎麼用秤,隻消過手一掂,隻多不少。為此,市電視台專門來楊柳街采訪三叔,給他做了期節目。漂亮的女主持人拿三叔和庖丁做比較,說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十九解豬,讓三叔火了一陣。市中心有不少人專門來楊柳街買肉,就為看一眼三叔切肉,看他掂斤兩。
甭管生意多火爆,三叔堅持每天隻賣兩頭豬,多一斤也沒有。夥計小吳不解,說,看看獨眼龍,每天賣那麼多。三叔搖頭:肉行就一碗飯,得分著吃,吃獨食容易噎著。三叔的話傳出去,不少人豎大拇指,人們重新接納了他。
當上屠夫,三叔不揮刀了,他請街東頭甑鐵匠打了兩把笨重的剁肉刀,在後院柴堆旁支了塊厚厚的老梨木墩子,每天早晨在上麵剁肉末。每次五斤,剁得極細,半斤留家裏吃,剩下四斤半給街脖子周三包子鋪。周三為人老實,老婆跟人跑了後,一個人開包子鋪供倆娃讀書。用了三叔的肉末,原本冷清的包子鋪紅紅火火,周三那張苦大仇深的皺皮臉上綻開笑容。
我問三叔,為啥每天剁五斤?三叔隻是笑。後來,不光我問,我爸我媽以及楊柳街知道三叔剁肉末的人都在問。一天早晨,我起床尿尿,三叔突然叫住我說,想不想剁肉末?我走到三叔跟前,認真看了會兒,他剁得並不快,刀子剁在豬肉上,吃進案板裏,拔出,舉過眉頭再剁,如此循環往複。我搖頭說,不想,不好玩。三叔額角鼓起青筋,猛一揮手,雙刀飛出,哢嚓,兩把刀齊刷刷釘在院子中間的木架上。你不是想知道我為什麼每天剁五斤肉末嗎?三叔說。我被嚇傻了。他說,每天四千下,不多也不少。說罷,他從木架上抽出刀子,自言自語道,沒有肉末,隻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