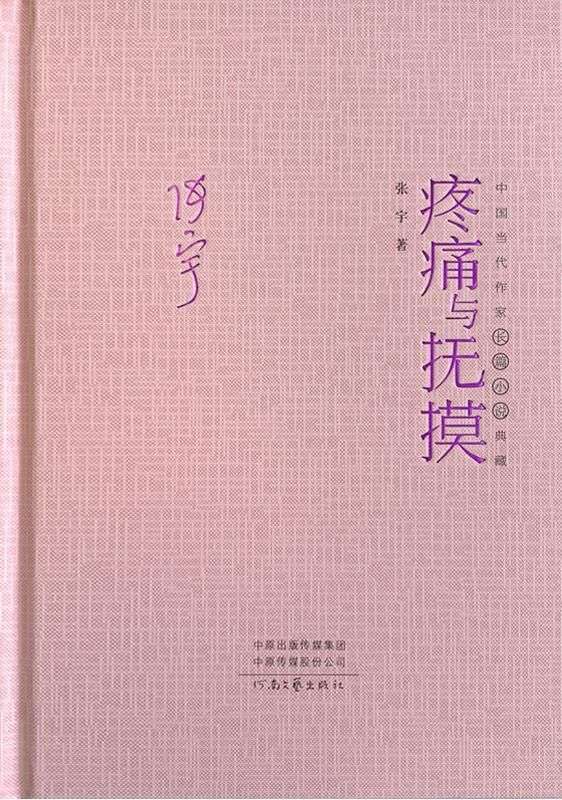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六
水秀難以忘記的那個夜晚,是黃家族長敲響她的窗框。作為一族之長,族人楷模和道德的化身,能在深夜裏走到水秀窗前,他該邁過多麼遠的心理路程。他本來讓人感到古板和腐朽,像一具會移動的道德死屍。但是,自從他舉手敲響窗框起,就顯出了豐富和鮮活。一個活生生的男人,從族長的殼子裏掙脫出來。
現在我比較能理解了,族長隻是這男人在人麵前表演的一個角色。他當族長就像演員演戲,說族長的話辦族長的事,隻是淪陷進族長的劇情裏在操作法則。盡管他迷戀這個角色,卻不能永遠生活在舞台上,那會把人累死。他需要經常走出這個套子,回到生活的真實之中。就像生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也要經常去進入許多角色一樣,永遠生活在真實裏不去表演任何角色,也會把人累死。現在他趁著黑夜的掩護,悄悄溜出那個套子,舉起手輕輕把窗框敲響。
那晚上沒有星光,天陰著卻沒有落雨,隻把雨霧灑下來,夜晚就彌漫著濕潤潤的溫情。
水秀已經洗罷身子躺在床上,洗去白天勞動留在身上的汗味兒,使她覺得清爽和舒適。心裏想著些細碎事情,像一個一個數著罐裏的雞蛋。她準備就這麼入睡。有人把窗框敲響。她起初懶著身子遲疑著不想起身。這遲疑差點丟失這個夜晚。後來她想了想才披衣下床,摸火柴點燈。接待客人時,她一直堅持先點亮燈,好像點亮燈就光明正大一樣。
她去開門,先把人讓進來,回身又把門閂推上。沒看清黑暗中來人的模樣,隻看到既陌生又熟悉的輪廓。她跟著這男人走進裏屋,看到他把錢放在桌子上,同時吹滅了燈。水秀在燈光消失時捕捉到族長的側影,隻是她不敢相信,確實是族長來到了她的床前。族長和嫖客,這兩者相距太遠,就像天南海北,她無法穿針引線把它們縫在一起,就感到不真實。
長期以來,水秀隻把他當成族長,忘記了他還是一個男人。就如家廟裏的神像來到她眼前,使她覺得突兀,看著麵前黑暗裏恍惚的身影,就像看到一團飄來的夢幻。
兩個人站在黑暗中,水秀覺得像站在自己的夢裏。她伸手擋住他,不讓他往她身上靠。他把腳步停住,如一根黑乎乎的樹樁栽在那裏。
“我得知道你是誰。”
他不回答她。說慣了族長的話,他丟失了自己的話語。人回到真實中,語言還飄揚在遠處。
“真的是你嗎?”
族長點了點頭。
水秀看著眼前這個腦袋向著她低下,仿佛看到一座廟宇轟然倒塌在眼前。她這才走出剛才的夢幻,回到現實生活裏。族長又欺過來時,她心裏忽然慌亂如生長出一大把茅草。不再阻攔,也沒有反抗。並非他放了錢,就不能夠拒絕,而是沒想到要拒絕。就讓他把她弄到床上,脫光了衣裳,輕輕地摟進懷裏。那時刻她覺得自己發輕,輕如一把棉花在他手裏掂來掂去。
他不像別的男人那樣粗俗和野蠻。就像縫紉一件絲綢衣裳,做得很精細。她沒想到族長看去那麼呆板,卻這麼會疼女人。更沒想到做完後不起身走,而是像夫妻那樣躺下來歇息。
這就給了水秀一個整理慌亂思緒的機會。剛才像在半空中,如今落到實地上。水秀就覺得自己很冤。他讓人用鞭子抽打她,又讓她遊街示眾,如今又騎到她身上找快活,就覺得自己太窩囊,太賤太不值錢。她想把這份冤找回來,又不知從何處做起。
如果族長留心,就會感受到水秀的情緒有了變化,可惜他沒有。他也在整理自己的思緒,正一點點恢複著理智,逐漸冷靜下來。他一下子覺得這一步邁得很遠,有些荒唐。想到族長的身份,他有些不安,他必須想辦法把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掩蓋起來,永遠不被別人知道。說穿了他是想占有這個女人,又要讓這個女人維護他的形象保護他的名聲。
這使我們發現,在對待性愛的態度上,男人永遠比女人要虛偽和軟弱。他們總是最先想到後果,安排善後工作,甚至做好背叛的準備。
“我知道你恨我。”
“我不恨你。”
“其實恨我也沒有道理。我由不得自己,那是規矩。我心裏可想你,總想來看你。”
族長用很少的話語,表述他全部的虛偽。他想用這話語,給自己修一條退路,沿著這條路從真實生活裏返回族長的角色的套子裏。就像狐狸把偷來的東西埋在雪地裏,用尾巴掃著雪退著把自己的腳印掩埋。
但是,水秀不讓他這麼做。族長說什麼,她都應聲,心裏卻在想著別的主意。她拿定心思要出出這口窩囊氣。如今他在她床上,就等於在她手心裏,她也要讓他窩囊窩囊,最好窩囊到心裏頭。
她甚至想到了最惡毒的主意,翻身騎到他身上,騎驢騎馬騎豬騎狗那樣,把他騎一騎。你玩弄我,我也玩弄玩弄你。然後把錢給他,這錢不是那錢,那錢是你買我,這錢是我買你。最後一口痰吐到他臉上,把他趕出去。讓他也受受女人的氣,嘗嘗受侮辱受欺淩的滋味。但是她沒有這麼做,並不是沒有勇氣,而是覺得那樣做自己就太賤太潑太壞,真正成了一個壞女人。不管別人如何看她,她自己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好女人。
這是人的普遍心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好人。如果自己也認為自己是壞人,就不去辦壞事,就不做壞人。無論做再壞的事,他都能找到理由去做。好人永遠是自己,隻有別人才是壞人,這才是人們區別好壞人的普遍方法和統一標準。
水秀最後才想到族長的小旱煙袋,她放族長走時,留下了他的小旱煙袋,就像放走狐狸時割下了它的尾巴一樣。水秀做得很聰明,她留下了信物,也就留下了一切。但是我在想,水秀留下這信物是為了以防萬一之外,是否還有另一種暗示呢?那就是暗示著她不拒絕族長再次來敲她的窗框。我想連水秀自己也不會明白,這種下意識裏還有更豐富的內容。起碼族長沒有悟到這個暗示,丟掉了旱煙袋,他像丟了魂一樣,回家去就躺了三天不出門。再出門見人時,別人發現他害過病似的老了許多。
水秀抓住這個旱煙袋,就抓牢一個可能性,隨時可以憑證物出門去吆喝,使族長出醜。當然,她要真這麼做,就沒有了味道。她不這麼做,隻握著這麼做的可能性,就抓緊了對族長的威脅。可能性比肯定性容易產生恐怖,把族長的精神折磨。他忍受著這種折磨,永遠等待著大禍臨頭一樣,再也想不到去把水秀的窗框敲響。
剛開始,水秀摸著族長的旱煙袋,還有點高興,時間一長安靜下來,她也覺得沒了多大意思。族長害怕她找事,遠遠看見她像看見蛇一樣繞著她走,使她心裏感到別扭。她甚至覺得老拿著旱煙袋嚇他,還有點難為他。平心而論,過往這麼多男人,還就是族長讓她動心。她雖然厭惡白天裏人麵前那個族長,卻喜歡夜晚黑暗裏那個族長。她在這時才發現拿著他旱煙袋的另一層含義,在內心深處,她不拒絕他再來找她,多少還有一點渴望。說到底她是一個多情女子,走不出溫柔。女人永遠是情感的羔羊。
這以後幾年間,她的家庭生活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再沒有人找她的麻煩,又有人送錢花,她不再替人紡花織布。經常帶兩個女兒上街趕集,讓孩子們吃糖豆和肉包子,回家時還割肉買豆腐。生活好起來,想盡辦法讓孩子們吃好穿好,把兩個女兒養得兩朵鮮花樣豔麗。
水草和水蓮年幼不懂世事,不知道媽媽作難受苦,傻嗬嗬高興。出門去和別人發生爭吵,感覺不到自卑和膽怯。隨著年齡增長,懂事以後就不行了,終於明白了媽媽在夜裏做的事情,揭開了家裏的秘密。出門去再站不到人臉前,感到丟人敗興低別人一頭。
在一個有雨的傍晚,兩個女兒圍著媽媽做針線,再也承受不住壓抑和痛苦,開口向媽媽發問。那時候姐妹兩人擠眉弄眼,相互推讓,最後還是水草先開了口。她看著媽媽的臉,看了許久,才怯怯地說:“媽,外邊好多人說你。”
水秀抬起頭,並沒有停下手中活計,對女兒的話語沒有設防,她的神誌還纏繞在針線上。
“媽,外邊人都說你不正經。”
先是針紮傷了水秀的手,就有血流出來立在手指上。她心裏疼了一下,就明白孩子們要說什麼了。她早知道有這麼一天,早晚要麵對自己的孩子,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突然這麼快。她一時答不出話來,感到孩子們已經長大成人了。
“媽,是真的嗎?”
“媽,這不是真的。”
兩個孩子不放棄這種追問,又抱著幻想,希望出現奇跡,等待媽媽否定這一切並給予解釋,最好把她們說服。在她們印象中,媽媽最會說服她們。
孩子們錯了。承認這一切雖然艱難,但媽媽從來不對她們說謊。雖然她們的問話如刀子剜心使媽媽疼痛,媽媽還是向她們點頭默認了。
當媽媽的腦袋向她們低下來又低下來時,她們明白媽媽承認了自己是不正經的女人。她們受不了這種最終的打擊,姐妹兩人哇地哭起來。
水秀不勸她們,就讓她們這麼哭,哭出來好受,憋在心裏容易傷身子。等到她們哭了一陣子,她才認真地說:“當媽有當媽的難處。現在你們還小,不明白事理。等你們長大,就明白了。別嫌媽丟人,媽可是清白人,媽有給你們說清楚那一天。”
孩子們年幼,聽不出這話的分量。她們開始找破舊衣裳穿,不再穿新衣裳,她們開始輕視她們的母親。水秀無力改變這一切,隻有承受這痛苦。但她無論如何沒想到水草會為此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