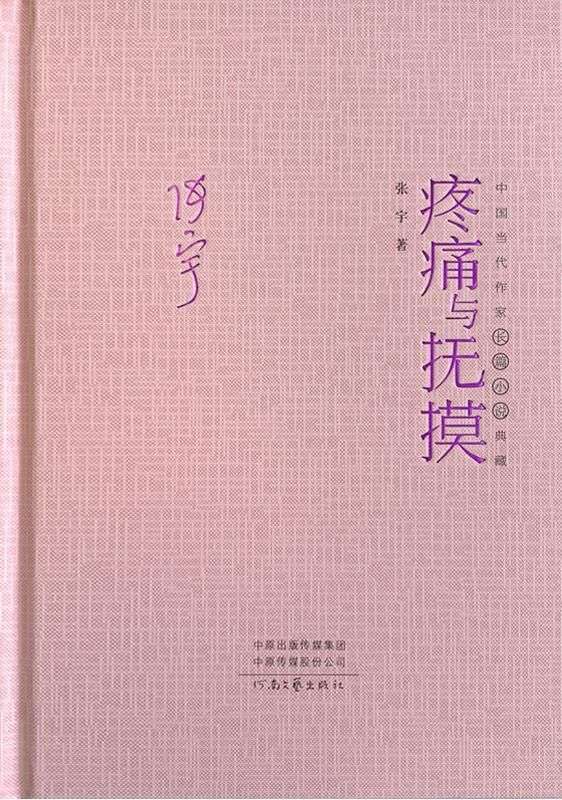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五
在懲罰水秀之前,黃家的人為了保護臉麵,先放了黃鐵鎖。
這樣就把水秀弄成勾引良家子弟敗壞門風的淫婦,讓她把罪惡承包下來。雖然是為了迫害水秀,無疑也是對黃鐵鎖的一種偏袒。不想這偏袒,卻害了黃鐵鎖。回家以後,黃鐵鎖一下覺得垮了,垮得全身心感到一種虛弱。無論如何他還是一個年輕的血性漢子,雖然被捉住關在家廟院裏,丟人歸丟人,有水秀為伴,共赴災難,他心裏還有一種悲壯感。這種事,不為別人發現更好,既然事發也就撕破臉皮破罐破摔,甚至有一種豁出去的快感。
那時候他被關在家廟院裏,心裏就橫下來,出醜就出醜,受罰就受罰,不過是皮肉受些苦。這樣也好,索性把事情挑明,過後經人說說就和嫂子過日月。兄弟娶嫂子這種事雖然少,也不是沒有發生過。族裏能同意更好,不同意就和嫂子脫離黃家另過日月。有嫂子做伴,他也不虧做回人。如果再生個一男半女,自己這輩子也不可憐。這就使鐵鎖反而有一種慶幸,對前景充滿了樂觀。隻是他什麼都想到了,沒想到先把他放了。盡管他掙紮反抗一再說怨他不怪嫂子,還是硬把他押著出了家廟院,送回到家裏來。又派人看管,不準他出門去亂攪和。
往床上一躺,鐵鎖全身都軟了。放他回來,這就把責任全推給嫂子一個人。他覺得族裏人逼著他出賣了嫂子一樣,在關鍵時刻自己離開了嫂子,離開了自己的心上人,成了無恥的小人一個。無論嫂子如何看他,怪不怪他,他都扔下了嫂子,讓她一個人去承擔罪過。從這裏出發,他走進了自己聯想的恥辱之中。
捉奸捉雙,自己被當場捉住,再無話說,往後也就再無臉去見族裏人和另姓旁人。自己走到哪裏,都會有人指著他的脊梁骨罵他不要臉,找嫂子睡覺。由於關鍵時刻逃脫懲罰,加重了嫂子的罪過,嫂子也不會原諒他,過後也會不理他,輕視和小看他。就是嫂子寬容,不計較這些,作為一個男人,他再也無臉麵去見嫂子,去見自己的心上人。這樣,前後路都斷了,他感到了往後無處逃遁。
有自己在場,無論打罵,那懲罰有多重,總覺得可以忍受和闖過去。現在隻剩下嫂子一個人,他們將如何迫害和折磨她?他想不出來。越想不出來越想,越想就越痛苦。想象的痛苦永遠比行為痛苦更加痛苦,這種痛苦由於看不見摸不著,就如無邊無際一樣折磨著他。他心疼嫂子,他心疼他的心上人。
這是一種思維怪圈,任何人都會有這種思維體驗,凡事隻要你一開始往壞處想,就越想越壞,往好處想就越想越好,這時候思維過程和思維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出發選擇的思維角度和路線。就像水秀在遊街示眾時她想到自己冤枉一樣,越想越冤枉,竟理直氣壯罵著跳起來。鐵鎖一開始就覺得自己無恥,就走進了自己恥辱的深淵。
如果鐵鎖一開始往別處想,就會沿著另一條思路展開聯想,就不會輕易想到絕路上。他選擇了自責這種思維方向,就越走越遠,想到了絕路上。
他先是把道德這條路想斷了,今後無法生活在族人和鄉人之間。又把愛情這條路想斷了,今後無法再麵見心上人。就感到了走投無路,走到了人生盡頭,想到了自殺。
實際上,他想到無法再生活在村裏和無法再見心上人,還都是表象,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此刻糾纏在心裏的死結是他自己無法再麵對自己。也就是說,他更重要的,是他今後看不起自己。沒臉再見自己。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就自己判處了自己死刑。
我覺得黃家族人放了他隻是幫助他找到了自殺理由,真正殺死他的,還是他自己的心靈。
這使我再一次覺得自殺這個詞語很準確,自殺的人都是自己找到死亡理由的。找到理由就去實現它,這都是些勇敢的人。這使我對所有自殺的人,無論什麼理由自殺,都懷著深刻的理解和尊敬。
自殺,絕不是什麼輕生。那是些把人生看得比什麼都重的人,才敢想到並實現自殺。
黃鐵鎖是七天之後自殺的。這七天裏,白天他都待在家裏關上門吃飯和睡覺,不見任何人。夜裏就出門來幹活兒,他把自家的糞都挑到水秀家的地裏,為水秀家的莊稼追了一遍肥。又摸黑把水秀家的地邊都刨了刨,還給坡地挑了一道崖,以便存住水來養莊稼。嫂子帶兩個女兒過日月,這些活兒她幹起來太吃力。
這些情況別人不知道,水秀是發現了的,也想到是鐵鎖幹的活兒,隻是想他心裏難受,沒往別處去想,也就沒有理他。她不會想到,這是有人走到了人生盡頭,要上路了,用這種方式來向自己的心上人告別。
真正要自殺的人,是很少公開和人告別的,這時候自殺成了他最後的秘密,他要守住自己的秘密,不被人知道。一直到鐵鎖吊死在墳裏柏樹枝上,水秀才想明白了鐵鎖的心思,但是已經晚了,舌頭已吐出一尺來長,那顆心已經不跳了。
鐵鎖一死,水秀才開始傷心。雖然讓她遊街示眾,受盡鞭打和苦刑,那隻是外傷,鐵鎖的死才使水秀受到了內傷,傷碎了心。如果說遊街示眾沒有征服水秀,在某種程度上,那是還有鐵鎖的愛情在墊底。隻讓她一個人受兩份罪,把鐵鎖放了,正合她的願望。她開始就說怨自己不怪鐵鎖,就透出來她希望保護鐵鎖不受折磨。放過鐵鎖,隻迫害她一個人,她覺得保護了鐵鎖一樣,反而心裏踏實一點。她一直覺得鐵鎖比她小,像她的弟弟和兒子一樣,她渴望像母親那樣保護他,傳達一種情感。如今鐵鎖一死,才把她打垮了。特別是鐵鎖臨死還想著她,為她幹了七夜晚的活兒,這份情一刀一刀剜著她的心。女人不害怕苦難,在苦難麵前,女人和男人相比永遠是強者。女人最要命的,就是受到來自情感方麵的傷害。女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活的是情感。
鐵鎖死後,水秀覺得天才真正塌下來。脫光衣裳把她趕上大街,她沒有放聲哭過,如今她跑到鐵鎖墳頭放聲痛哭。山裏女人,喜歡一邊哭一邊訴說,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水秀就跪在墳頭,撲在墳上哭著叫喚:
“鐵鎖,是我把你害死了,你死得冤呀。”
“好兄弟,嫂子害死了你啦——”
如果不是兩個孩子牽掛著她,她很可能以死來報答鐵鎖對她的情義,和他一塊兒走。除了孩子,這世上沒有什麼讓她留戀的。
鐵鎖死後,水秀變了一個人,她忽然不說不笑不搭理別人。她認定了自己沒有錯,她看透了這個社會的肮臟和黑暗,就不理會別人態度,反而拔起來一份孤傲。
這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對峙現象。別人看不起她,不搭理她,如果她上趕著去討好別人,別人就會越來越看不起她,她就永遠站在做人的低處,抬不起頭來。但是她先不搭理別人,就居高臨下抵抗住別人的輕視,守住自己的尊嚴,保護了自己的人格。這裏邊的關鍵是,別人看不起自己,自己要看得起自己,甚至要尊敬自己。
水秀賣淫就是從這以後開始的。雖然叫喊著要賣淫,但是等到真有人來敲響她的窗框,還是讓她心驚肉跳。雖然接過鐵鎖塊錢,但她一直不承認這就是賣淫。在五塊錢之外,他們敘述過那麼多情感。於是,第一次真正賣淫以後她大哭了一場。她覺得她的清白這一次才失去了。哭過之後是咬碎牙的仇恨。現在她終於徹底站在了這個社會和傳統道德的對麵,開始報複和瓦解它。
這種事大都在夜晚進行,不是水秀白天不敢接客,而是男人們白天不敢來嫖。他們像鬼一樣,隻有等天黑下來才敢溜出家門,來做他們自己也認為見不得人的事情。去做見不得人的事情,永遠對人們是一種誘惑。
由於孩子們小,水秀怕臟了孩子們的眼,就把另外一間房收拾收拾,另支一張床,作為她賣淫的地方。她讓倆姑娘睡在原來的屋裏,放上尿盆,一入夜就把她們反鎖進老屋裏。好像她要去打狼鬥虎,害怕傷到孩子們一樣。好像她要跳到茅坑裏淘糞,害怕屎尿濺到孩子們身上一樣。孩子這時成了她活著的希望,成了她的命。
剛開始人少,偶爾有男人半夜偷偷摸進院子裏,將她的窗戶敲響。她把人悄悄領進屋,先接過錢,再脫衣裳上床。第一次就找到了和鐵鎖私通時不一樣的感覺,一切隨男人的便,他愛怎麼就怎麼,她隻是為了掙錢,投入不了感情。那樣子像替人紡線和織布一樣,隻感到在幹活兒,感受不到燃燒,感受不到要死要活的瘋狂。
接著,人逐漸多起來。有時候屋裏已經有人了,外邊還有人敲窗戶,她就沒好氣地說,屋裏有人,趕明兒個吧。她說這些話時不再不好意思,臉不紅心不跳,完全是生意人一個。那樣子就像誰找她幹活兒,她已經接下了別人的活兒,就回絕人家一樣。
她越來越看不起這些找她的男人,平時在陽光下看他們一個一個正經君子模樣,隻要天黑下來,摸到她床上,就低三下四像孫子。隻要脫光衣裳,馬上就換了一個人,豬狗那樣不要臉,沒有一個好人。
起初做這種事,水秀覺得收了人家的錢,替人家幹活兒一樣。後來感覺發生了變化,不僅僅要掙錢幹活兒,同時要使用牲口那般使用這些男人。就像借用別人家的驢拉磨,小鞭子抽打著它,累得驢一身汗水,把她的糧食磨成了麵。
她逐漸學會打發和戲弄這些嫖客。沒心情便罷,收了錢一由他們自己折騰。心情好起來時,她就讓他們侍候她,享受性行為的快活。然後再把他們趕下床,轟蒼蠅那樣趕他們出去。有時候洗罷身子幹幹淨淨往床上躺下,回想這些臭男人,她覺得自己成了戲台上的君主,這些人成了她的奴隸,她的狗。
有時候夜深人靜,她也覺得自己很壞,成了壞女人。隻要回到世俗觀念裏,她就感到不安,不明白這鬼日月還要過多久。想到再不能在人前當好女人,就覺得傷心,就害怕這日月。這種意識來回流動,常常使水秀感到進退兩難。
其實,人都生活在兩難之中,沒有人能夠逃脫。
這大概就是生的苦惱。
有人叫苦海無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