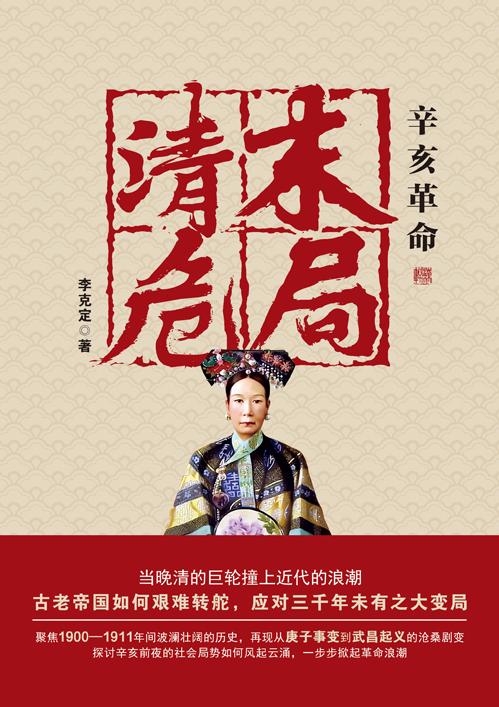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兩宮回鑾
一、災害頻仍 苦難深重
兩宮抵達西安不久,即下明詔以西安為行在。行在就是行宮所在。行宮設在陝甘總督府。總督駐地在省城,稱為北院,左宗棠任陝督時駐紮於此,後來為了收複新疆,他將總督駐地移至蘭州。閑置多年的北院,驀然見到佛光照臨,冥冥中若有天意垂顧。太後老佛爺入住三堂,她的兒皇帝住在二堂東三間,皇後住在後三間,還在三堂西屋安置了大阿哥。紫禁城中莊重森嚴的“天家”,在北院成了大戶人家,距離一下子近了許多。
行宮右門內,軍機處和六部九卿朝房,排列起按部就班的朝廷場麵。軍機處現有三位大臣:榮祿、王文韶、鹿傳霖。榮祿頂替禮王做領班,成為軍機處的主心骨。可他陰柔的毛病沒有改,入值時若無上頭垂詢,總是塌著眼皮不哼不哈。加上王文韶年老耳聾,常打瞌睡,幾乎要引發旁人的嗬欠。鹿傳霖新近入樞,心性好強,但他自知資淺,不敢造次多言。所以麵對這班軍機,慈禧往往想起年輕時日,恭王和文祥等那班樞臣,生出一蟹不如一蟹之歎。
好在當今朝政,遠不像往常之繁重,平日君臣所議,全為議和事體,說到底是應付洋人的勒索。僅為“懲凶”一件事,便反複糾纏好多回合,眼下仍在拉鋸中。然而結局早已定下,被洋人指控的肇禍諸臣,逃不脫誅殺貶斥的命運。所爭的不過是朝廷體麵,還有體麵後頭的要命內容:洋人在懲處了反洋臣子後,會不會追究到太後頭上?畢竟,對外宣戰出於太後的旨意,臣子們不過是替她頂缸。隻要和約未定,洋軍未撤,慈禧的擔憂就無藥可解,難得安寧。
榮祿懷著同樣的心事。在一般人看來,身非王爺而做軍機領班,這在近世唯此一人,該是何等榮耀!不知他身陷危疑之中:他是武衛軍的首領,被洋人視為中國軍方首腦,而攻打使館這項“重罪”,理所當然由他負責,所以洋人對他緊咬不放。議和大臣為他辯解,南方督撫替他求情,都無法澆滅洋人的怒火。外患難解,內憂更深,京城的宅邸遭受聯軍焚毀,幾代積蓄毀於一旦;妻女在流亡途中病死,淪為難以入土的孤魂野鬼;更叫榮祿憂心的是獨子綸厚,他在顛沛流離中身染重病,接到西安後仍未減輕。此子若有三長兩短,豈不斷了榮氏血脈!這是求天天不應告地地不靈的事情,榮祿為此常常走神,在麵君奏對時也會瞬間失語,令他自責以至於淚下。
正處在興頭上的達官,唯有陝西巡撫岑春煊。他在甘肅藩司任上提兵救主,護衛兩宮一路西巡,被慈禧倚為“守護神”,以至於官界和民間流傳佳話稱,慈禧夜寢中受驚啼哭,岑春煊在窗外執戈高叫:“臣岑春煊在此保駕,請太後不要怕!”不過也有人指摘說,這是岑家人編造出來的,他要用忠心報國的神話,洗刷康梁死黨的罪名。不管怎麼說,岑春煊升授陝撫,顯示其聖眷優隆,非尋常臣子可比。你想想,整個小朝廷都坐落在岑三的地盤上,這要有多大骨力,才能承擔得起!
因此,陝撫的最大政事,就是伺候好慈禧。慈禧此行受盡了苦難,剛出京的那一段不用說,即使到了太原局麵改觀,皇差供應也難周全。每餐禦膳,下頭進奉兩桌席麵,慈禧自享一席,待老人家進餐畢,再由皇帝皇後食用。另一席賞總管太監李蓮英,開始是因他正生病,後來便形成慣例了。岑春煊要改變這種窘境,他把兩桌改為三桌,每一餐都費盡心思,要讓上頭吃得高興。可惜秦地苦寒,物產以黍粟為大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天幸上頭體恤下情,從未在筷子頭上挑三揀四。
隻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晚膳時,慈禧向膳桌掃了一眼,移開了眼光,懨懨地坐著。往常慣例,老人家見到中意的菜肴,注目示意,伺候的太監便將食皿挪近,用湯匙往上布菜。這次顯然食欲不佳,太監們哪敢吱聲,但若一直僵著,那可如何是好?四格格立在旁邊侍應。這是慶王奕劻的女兒,生性八麵玲瓏,頗得太後歡心。她輕微地變換站姿,以引起太後注意,趁機笑著言說:“老佛爺,今日這膳,奴婢以為少了一味。”
慈禧還沒回過神來:“嗯?什麼一味?”
四格格回道:“食全五穀,天賜五福。席上稻、黍、稷、麥具備,獨少一菽。請老佛爺開恩,讓奴婢下去做個豆腐。”
慈禧開顏一笑:“花言巧語半天,隻為一個豆腐?好了,你去。”
四格格身手伶俐,去不多時,雙手捧上一個香氣四溢的青花大盤。但見盤中薑黃蔥綠,蒜青椒紫,紅豔豔醬汁滋潤著白生生的嫩豆腐,讓人見了饞涎欲滴。慈禧瞟一眼四格格:“鬼靈精妮子,該你誇嘴了吧?”
四格格蹲身做戲台上的萬福禮:“是,小妮子遵聖命。話說這菜備料,要豆腐一斤,牛肉二兩,蔥、薑、蒜、麻椒粉、五香粉、澱粉、油、鹽各一份。先將豆腐切成三分見方的小塊,牛肉切碎如米粒,蔥薑蒜切末,熱鍋下油,放入少許蔥薑熗鍋,放入牛肉粒翻炒變色,放入豆瓣和一半麻椒粉,炒出紅油,放入豆腐,旺火翻炒後加水放鹽撒五香粉,紅燒移時,傾入水澱粉炒勻勾芡,然後出鍋入盤,在表麵勻撒蔥薑蒜末麻椒粉粒,再以一勺熱油澆淋完工。此菜名為陳麻婆豆腐,有詩為證:麻婆陳氏尚傳名,豆腐烘來味最精。萬福橋邊簾影動,合沽春酒醉先生。”
慈禧笑吟吟地說:“陳麻婆豆腐?這又是何典故?”
四格格越發賣弄:“回慈聖話,陳麻婆乃成都北郊萬福橋邊陳姓店主之妻,因麵部微麻而得名。她創此菜在同治初年,被當地稱為豆腐狀元哩。”
同治初年,這勾起了慈禧的多少記憶。那時還是她的青春歲月,是她與恭王、文祥等中樞幹臣,曾、左、李等中興名臣一起,勵精圖治的日子。收起這段陳年往事,一股腦兒吃下半盤豆腐,慈禧愜意地歎一口氣。這也是一種放肆,按照宮中規矩,吃菜不許過三匙,包括每膳必上一百二十樣菜色,用意在於不能顯露飲食偏好,以保護禦體安全。在流亡途中,隻要有飯吃就是好的,哪還講究這些。在西安安頓下來後,慈禧仍然不願謹守規則。她的天性是不守本分,況且她相信下人,一路上同甘共苦,她不信有人會起投毒之心!
膳後閑話,說到宮中的各色麵點,像那麻醬燒餅、酥千層餅、白糖餅、清油餅、白馬蹄餅、玉蘭花餅、蘿卜絲餅、棗泥糕餅,顯得津津有味。起身移步時,慈禧意猶未盡,提起崇文門稅關進奉的石首魚,其肉鮮美無比。嗐,往事不回首啊!
為了辦好差事,巡撫在宮中安插了眼線。得到這條信息後,岑春煊馬上向下屬布置。底下人犯了難,陝西連蝦都很少見,石首魚為“海錯”之首,可到哪裏求取?岑春煊退而求其次,無有海錯總有河鮮,你們效忠的時候到了!功夫不負苦心人,候補道員唐承烈,覓得一批鮮鯉白魚,讓宮中的太後大快朵頤。
岑春煊竭誠當差,下麵卻不乏掣肘者,這些人都是州縣官。秋後八九月間,便有州縣報災情,近來更形成一窩蜂。各官眾口一詞:夏秋連旱,顆粒無收,餓殍遍野,盜賊蜂起,求賑,請恤,乞免錢糧。這都是嗆人肺管子的話,岑春煊直想破口大罵,把這種公文摜到地上。更讓他氣憤的是西安府屬各縣,竟然也來湊熱鬧,好像成心讓巡撫下不來台!
岑春煊把西安知府胡延找來,攤開幾份公文叫他看:“呶,長安縣的、臨潼縣的、興平縣的,還有藍田,藍田日暖玉生煙,香豔得很嘛。”胡延聽得頭皮發麻,賠著笑說:“老公祖,這些縣官沒眼色,卑職回去訓斥他們。”岑春煊眼一翻說:“你不卑,你是首府,別說我這巡撫,連兩宮都借居你這一畝三分地,要吃要喝要穿用,都得仰仗你的布施。這就有了州縣的跋扈、饑民的鼓噪,有了掀翻禦駕的喧囂。他們是不是看你的眼色?”
指控如此嚴重,胡延笑不出來了:“中丞誅心之論,胡延吃罪不起。請問大人,卑職是不是上奏自劾,請求嚴加懲處?”
不軟不硬地頂了一下,使岑春煊消了一些火氣。岑春煊歎一口氣說:“你別跟我賭氣,如果要自劾,第一個是我,接著才是你。你是支應局提調,支應局幹什麼的?支應皇差,伺候兩宮,你支應得不錯,且不說吃穿花用,連佳話都編造好了。你撰寫的《長安宮詞》,已是膾炙人口。比如,這首吟茶詩:石銚磚爐聽煮茶,行廚唯恐食單奢。鴛漿麟脯都無用,隻載城西水一車。”
凡是寫作宮詞,大都為了頌聖。頌聖是臣子本分,但若作為儒生,便於清名有礙了。胡延捉摸不透岑春煊的意思,隻好訕訕地聽他講:“這詩稱頌上頭體恤民艱,儉食節用,心清如水。西安井水南甜北鹹,城西南隅那口甕城水井,煮茶上佳,這便是城西水的來曆。這個典故用得好,可出了城圈兒就露餡。比如,你寫出巡途中,兵匪襲擾,皇太後為了保護皇上,親自坐在皇上輿車外麵。材官林泰清請太後入輿,太後泣曰:‘吾年已老,保皇上便是保天下。’唉,知府老兄啊,凡事不可逾常理,否則便是誣聖了。”
誣聖一詞刺痛了胡延:“上稟中丞,我聽林泰清親口說的。”
岑春煊朝地下一啐:“那是個末弁,問他何如問我?兩宮的保駕臣是哪個?你眼前的這一個!”
胡延胸中的那點硬氣,被一字一句挫下去了。岑春煊將話意扯了回來:“上頭體恤民艱,臣民也當感戴聖恩,就像你宮詞中講的那樣。兩宮來到西安,可以說驚魂未定,忽然聽到民間饑聲四起,這不是要趕他們倉皇起駕,再次逃亡嗎?”看出胡延急於辯白,岑春煊雙手往下按:“好了,別急,我不是叫下邊報假賬,隻想把這事涼一涼,讓上頭睡一個安穩覺。”
巡撫和知府的這番口舌,起因於軍機處的一番議論。那天岑春煊去軍機值房,發現三位大臣憂形於色,原來是接到山西的奏報,說是山西災情甚重,報災請賑。這在往年是常見的政事,放在今年卻不合時宜。庚子年驚雷頻傳:教案、民變、戕使、宣戰、破城、亡國,都是捂也捂不住的消息。山西遭災應當憐恤,可是朝廷當前的光景,能拿出什麼去賑濟?大臣們發了一陣愁,鹿傳霖撓撓頭說:“記得在路途中看到,山西的莊稼長勢尚可。倒是過了黃河,大塊田土旱成白地,連一棵草苗也看不到。怎麼沒聽陝西叫苦?”王文韶瞅瞅岑春煊問:“陝西收成還好吧?”岑春煊順口回答:“還過得去。”回頭便看見報災文書,叫他如何改口?
岑春煊由此想到吳永。吳永是直隸懷來縣令,是兩宮出京後第一個迎駕的地方官,贏得了太後的歡心,令其督辦前路糧台。吳永自知官職卑微,不便行文於各省藩司,奏請以岑春煊任督辦,吳永和俞啟元為會辦。這項要職是區區縣令轉讓的,使岑春煊感到別扭。加上吳永常為州縣說好話,為此沒少跟督辦大人拌嘴,更讓岑春煊窩火。岑春煊在甘肅藩司任上,對州縣官的伎倆多有領教:他們要麼誇張政績,要麼謊報災荒,不是涎著臉討賞,便是伸出手要錢。岑春煊鐵麵無私,拆穿了其中騙局,將一名知府、一名知州、三名知縣奏劾罷黜,因此獲得“官屠”的稱號。不過,這一回他沒有打算屠官,作為新任巡撫,既要立威,也需施恩,何時報災,要看時機。
這個時機,被吳永無意間搶走了。這一陣子,慈禧經常召見吳永,聽吳永講述州縣民情。她數十年間高踞九重,對於民間疾苦,可謂萬分隔膜。但她的父親曾做過地方官,她年幼時跟隨父母,在幾處州府遷轉。有時回想起來,那些鄉野光景,會令她惘然若失。吳永並非進士出身,算不上功名中人。而他在危難關頭挺身迎駕,顯示了血氣和擔當,比同輩官員強得多。慈禧對於吳永,有一種家人子弟般的感覺,使尊卑界限有所放鬆。況且在這裏,無法像宮中那樣看戲觀舞,聽一聽縣裏的民生戲,也可以打發落寞時光。
這天早朝後,吳永回罷糧台的差事,慈禧令他續說“僧人故事”。那是昨日提起的話頭,被軍機晉見打斷了。故事是這樣的:懷來城西有一古寺,是始建於唐朝的名刹,其住持僧人結交官府,橫行鄉裏,儼然成為一方豪強。吳永蒞任後,住持數次來拜,吳永以僧人無故不應謁官,拒不接待。鄉民聞知新官不庇僧寺,便有多人赴縣具呈,控告寺方強占田產。吳永派人勘查,案情屬實。吳永考慮,如果逐案審訊,僧人必定仗勢頑抗,所以準備變通辦理。這時縣裏要辦學校,吳永授意官紳赴縣呈告,浮屠寺曾占校產,應當加倍返還。吳永做出判決,僧人修行為本,何須厚植產業?令分出寺產一半,歸予學校管理,惠施地方,福報佛徒。據此上報府、省,並經批準定案。
寺僧並未束手就擒。這天忽有大起馬隊,簇擁著一輛高大的馬車,乘車的主子和跟班的仆從,正所謂鮮衣怒馬,氣宇軒昂。街市哄傳,北京王府派人來縣,專為清查某寺莊產。縣太爺和王爺杠上了,縣裏這回有好戲看了!次日那人果然來到衙門,投帖進去,具名為愚弟某某。吳永出見,那人身著三品冠服,昂然直入,一揖就座。吳永尚未詢問來意,那人使出問罪的口氣:“貴縣辦事,未免過於粗疏草率,怎麼將王府莊產任意改撥?王爺聞聽震怒,特命兄弟前來查辦。兄弟並不想與老兄為難,請問如何挽回才好?”吳永盯視那人:“王府莊產,糧稅雖不由本縣征收,然縣方皆另備檔冊,與民產截然分開。此次所撥寺產,簿冊契據逐一查明,絲毫無誤。且王府莊田從無托人代管之法,老兄此來恐有誤會,或聽和尚一麵之詞,受其請托。”那人變了臉色:“我受王爺之托,你給我聽明白了!”吳永道:“請問是哪位王爺?你有什麼證據?”那人暴跳起來:“我是禮王府的宗人,你竟敢如此藐視!”雙方沒有談攏。吳永揣測其人,確有相當身份,希望能夠就此罷手,彼此不傷和氣。
這班人馬離縣而去,不料過了幾日,竟然“班師還朝”。明知善者不來,吳永嚴陣以待。這天那人來衙求見,依然盛氣淩人:“我都查問明白,請老兄將田產歸還王府,此事一了百了。”吳永道:“省府縣三級核準,此事如何能改?”那人嘿然冷笑:“你隻認製台藩台,竟敢不認王爺?佛寺承受王命,現有和尚作證。”吳永問和尚何在,那人手指外麵。吳永立即下令鎖拿和尚,那人阻攔不住,一路怒罵而去。吳永發出朱票,令將該店所住人等,一起押傳來署。過不多久,二十餘人押到。吳永在大堂正中設萬歲牌,麵南設立公座,先傳為首之人問話。那人來到堂上,吳永喝令跪下。那人抗辯:“我乃太祖高皇帝子孫,豈能向你下跪?”吳永冷笑:“本縣不要你跪。你向上看,此係太祖高皇帝的法堂,你既自稱宗室,難道不向祖宗下跪?”那人躊躇一下,聲氣低了下來:“求縣台稍留世職麵子。”吳永嗬斥:“法堂之上講何麵子,跪下!”那人無奈,跪地俯首。吳永訓道:“你若真是宗室,可知宗室私自出京是何罪名?依法須交宗人府發落,至少亦須革職,永遠圈禁高牆。況你尚有包攬詞訟、勒索官府一段情節,罪狀尤為重大。如果不是宗室,則你假冒訛詐之罪更難饒恕。你兩罪必居其一,若不從實招來,將以大刑伺候!”那人隻得叩頭吐實,原來確係一黃帶子四品宗室,襲封輔國將軍。接受和尚利誘,試圖分占寺產。吳永將和尚判刑兩年,擇從人為首者予以杖責,對黃帶子當堂取保,驅逐出境,亦未將其真名存案申報。
這比戲台上的故事還要熱鬧。到了堂上那場戲,慈禧聽得屏住呼吸,直到案結,她才輕拍一下掌:“啊呀吳永,你是化身楊小樓了嗎?那個生角動作輕巧,嘴也輕巧,把事由演得嘎嘣脆。你敢說這是真事兒?”
“回老佛爺,小臣不敢生編。”吳永偷偷調換一下跪姿,心裏在後悔,不該扯出這麼長的一段,害自己的膝蓋受苦。
眼尖的慈禧瞧破了,禁不住一笑:“吳永的腿跪麻了?我是不是請皇上開恩,讓你以家人禮起來回話?”
在慈禧的右邊,光緒木然端坐,仿佛對那段戲碼充耳不聞。吳永慌忙叩頭:“小臣何敢在禦前失禮。”
“連個禮法都不敢變,何談變法,是不是啊皇帝?”這話叫光緒醒過了神,正要說話,慈禧卻已收起笑談,“怎麼,那小子是禮王府的?”
禮王雖在慈禧麵前失寵,但鐵帽子王的威勢豈容冒犯!吳永奏稱:“那人是遠支宗室,冒用禮邸名號。”
慈禧抿了抿嘴兒:“有名可冒,也靠祖上陰德啊。罷了,不扯這些。吳永你扮清官,又有什麼可靠?噢對了,你是從李鴻章幕府出來的。”
“臣不曾指望這些,何況李傅相,從來不以傲骨沽名釣譽。臣不過本分行事,過後捫心自問,未對僧寺徇私,隻因是非曲直乃縣民共見,縣官從眾而已。如果進一步誅心,放那宗室一馬,固然存了皇家體麵,何嘗不是小官自保之術。”
慈禧審視著吳永,好久好久,喟然歎息:“微末之員說出這般見識!王公大臣甚至更上邊的,終生在糊塗湯裏栽跟頭。”
在王公大臣“更上邊的”,唯有太後身旁的這一位。吳永替皇上難受,急急進言:“臣也當過糊塗官,上任伊始不明就裏,誤以為東鄉謊報實情,差一點激起當地民變。以後特別小心,因為牧民之官,鬧不好就會害民。”
慈禧沉吟著道:“牧民這個詞,我是跟著父親弄懂的。我無緣牧民,隻能牧官,希望你們不要虧待百姓。”
旁邊的悶葫蘆開了口:“額娘,幾天前山西報災的折子,軍機諸臣尚未議辦。”
慈禧想了一想:“昨兒下午我臨時出見,問過榮祿。榮祿說,議和、軍事是當前急務。他們的意思是,目前朝廷客寄於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怎麼說出客寄二字!”頓了一下,光緒放低聲,“兒子不是怪他們。”
慈禧略帶尖刻道:“你怪他們也怪不出法子。到處缺糧少米,咱們在京的日子,不也捉襟見肘嗎?好在陝西還沒叫苦,要不咱們往哪裏去?”稍停又道:“吳永,你還有什麼話講?”
吳永本想順勢退下,卻不知搭錯了哪根筋,叩個頭道:“其實陝災重於晉災。臣在西安知府胡延處,見到數縣報災的公文。胡延說,與其他州府比,西安還算輕的呢。”
兩宮都現出錯愕的表情。吳永正在後悔,聽見上頭說:“你下去吧。”吳永退出走到前院,聽見有人召喚。他走進軍機大臣議事房,看見三張陰沉的麵孔。王文韶開言責怪:“漁川,記得我以前警告過,不可在禦前輕言語。你有多少事情講,在裏邊耽延許多時,叫我等重臣瞎擔心?你掂得出輕重嗎?”
吳永幹張嘴無話回,卻聽內監出來傳喚,召見軍機。吳永癱坐在矮榻上,胸中仿佛爬滿了螞蟻,渾身上下刺撓無比。他知道這個婁子捅大了,卻不知哪裏對哪裏錯,如果追問良心,他覺得那話應該講。應該的變成不應該,實誠人落得討人嫌,在這個播遷的朝廷麵前,吳永找不到存身的位置。他想起在宣化時,恩旨賞吳永為候補知府。他是不是應當奏請回原省候補,離開這塊是非之地?
吳永正在盤算,三位軍機麵君回來了。他們沒再嗬責吳永,隻叫他順路通知岑春煊,來宮中議事。這是發作了,吳永心裏敲著小鼓,隻好去辦這不討好的差事。
聽吳永講罷原委,岑春煊倒沒有顯出慌亂。他是“強項令”,不僅對下,對上也敢強幾下子。他還跟吳永說了真話:“能在天宮待久的,都是千年老狐狸。像我這種牛犢子,不定哪步就會栽。你老兄的道行,別讓我說難聽話,好自為之吧您呢。”
岑春煊將那些公文,一股腦兒帶到軍機處。三大臣看了直咂嘴,抱怨岑春煊匿而不報,讓樞臣在麵對上頭垂詢時,像傻瓜一樣語無倫次。岑春煊嬉皮笑臉:“三位叔公不管怎麼罵,小子都不辯白,誰叫岑三苗性不改呢。”對這種沒正形的貨色,再大的官也拿他沒辦法。岑家號稱東漢名將岑彭之後,宋時隨狄青征西南,以後世居廣西為土司。貶岑者稱呼他是苗蠻子,他索性以蠻示人,卻也無往不利。
在行宮二堂正間,兩宮聽岑春煊奏報災荒。陝西夏秋連旱,有的地方從去年冬天就沒見雪花,以致十八縣絕收,三縣半收,九縣同時遭遇蝗災。西安百物騰貴,小麥由一石七八銅圓漲至二十七八銅圓,米一石二兩銀子。這叫有價無市,因為到處無糧,入倉存糧要作軍糧,不能用來救災。岑春煊的應急之策是,打算成立平糶局,分赴南方各省購米。難處在於錢無著落,正在緊張籌措中。
既有災情也有對策,兩宮感覺踏實了一些。慈禧詢問籌錢方法,岑春煊說得一套一套的,都在衙署和士紳圈子裏打轉,聽上去是老生常談。看看三位樞臣,一個個悶不作聲。慈禧厭煩起來,目光對著窗外出神。
這時光緒說話了:“籌錢購米,仍是遠水不解近渴。按照規程,每年寒冬都有設廠賙貧之法,陝西的條例是怎樣的?”
岑春煊回答:“臣問過戶房師爺,西安往例,十一月初一開設粥廠。今天是十月十三,尚不到施粥時日。”
光緒說道:“今年閏八月,按常年算今天是十一月中旬。你已欠貧民半個月的粥米。”
岑春煊叩下頭去:“啟奏皇上,欠了貧民的米,添了保駕的兵。西安增駐兵員三萬七千,而倉中存米少了三成,僅夠兩個月食用。”
光緒垂下眼簾,似在默默運算,接著吐出一口氣:“是啊,多少年來,我們都在掰著指頭數日月,從來沒有寬裕時,也未尋到富國術。現隻能拆東牆補西牆:你挖出一半存米設粥廠,再購進南米作補充。其實不光這一法,先前朝廷發旨催餉,各省運糧應在途中。”
慈禧從窗前掣回眼光,朝身旁睇視了一下。這一段君臣奏對,是她沒有聽聞過的。回想起來,自從再出垂簾二聖並坐,光緒便化身為一具木偶,讀書人所謂“屍居餘氣”了。原來,原來他還有這般英銳!說不出是悲還是愁,她向下邊問話:“皇上的意思,你們看怎的?”
這是很難回答的一問,無論站哪邊,都有懸崖等在身後。聽了一陣窗外樹鳥啁啾,王文韶發出蒼老的聲音:“臣以為應即開設粥廠,使行都民眾灌溉皇恩,亦為祈福宗社之舉。”
話不是不能講,要看如何講,這琉璃蛋修行到家了!榮祿暗暗佩服,與鹿傳霖相繼附和幾句,這便形成了朝廷大計。即日明發諭旨:陝省向例十一月初一開辦粥廠,本年遇閏,上限提前,改在城外多設分廠,動用倉糧。自十月十五起,即行開放。該撫務當遴派員紳,認真辦理,用副朝廷軫念災黎之意。
岑巡撫督率胡知府,風風火火地操辦這項皇差。在城關增設粥廠二十餘所,由於城外雁塔寺齋房多,便把這裏辦成最大的粥廠。除了粥廠還有暖廠,就是在廠棚中燃起炭火,讓無衣的災民得到些許暖意。開辦三日後,行在戶部撥銀十萬兩,將皇恩浩蕩落到實處。岑春煊上奏稱,每日有十數萬人赴廠就食。為感戴朝廷活命之恩,無數饑民磕頭告天,泣不成聲,此情此景令人淚下。
然而兩省巨災,不是眼淚便可洗刷幹淨的。上頭讓臣下拿出辦法,軍機處議了幾日,仍然歸結到“捐”字上。這是個討人嫌的字眼,但是除卻它,你給我鑽出個門路試試!這天上朝議事,榮祿把這個對策奏上去,等著上頭碰回來。慈禧聽罷很平靜:“遇到缺錢忙辦捐,知道你們就這點能耐。可這受到多少抨擊,就在前年,皇上還停過海防捐。”
那是戊戌變法正盛時,光緒力推裁官、停捐。這是禁忌話題,榮祿想要顯示骨鯁:“奴才當時主管北洋,便為海軍斷餉發愁。奴才聽說,戶部尚書王文韶,力諫不要停捐。”
被點了名的王文韶,正在挖空心思措辭,聽見光緒接話了:“海防捐最終沒有停。想法和幹法對不上,這並不是第一次。”
慈禧側了臉問:“皇帝的意思是?”
“回額娘話,兒認為可辦秦晉賑捐。百姓無飯吃,官吏有餘錢,得以移無用濟有用。”稍作停頓,他又放低聲音,下邊人幾乎聽不清,“當此非常時期,亦可借此覘民心向背、官意順逆。”
戶部尚書王文韶第一個磕頭,榮、鹿也都跟著磕。“廟算”就這樣定了,秦晉賑捐即日開辦。賣官鬻爵,明碼標價:報效銀六萬兩以上者,以盡先道員用;銀二萬五千兩以上者,試用道、府;一萬五千兩以上者,可予以同知、通判、州縣佐貳雜職。旨下數日間,從龍的四五品京堂便有多人報效,預示生意興隆。京堂是很光鮮的名目,又是頂沒味的差事,捐個道員盡先補用,無異於鯉魚跳龍門。無論何時,做官都是最好賺的買賣,此為萬世不移之理。
當然,任何話都可以反過來講,做官放在今天,並不能保證萬無一失。在京堂們的心目中,有一個難以企及的同類:太常寺少卿盛宣懷。他沒有當上極品高官,但他那一大把督辦,哪一個都是真金白銀。十月是太後壽期,盛宣懷進貢的除了金銀珠寶,還有鑾儀衛輦輅、麾蓋、儀仗全副,紵絲、江綢、名繡數車,另有蟒衣二百副,這是供太監換裝的。慈禧的五十歲和六十歲生日,先後被甲午戰爭和戊戌政變打破。沒想到臨幸西安,反倒過了一個賞心悅目的生日,使她得到極大慰藉。
各地貢物陸續到來。富庶的南方各省,進貢恐落人後,鄰近省份更要搶先。鄂督張之洞操持南方互保,生怕引起太後猜忌,所貢方物無所不包。川督奎俊貢秋梨、石榴等時鮮,在荒寒的陝西尤屬罕見,慈禧分賜榮祿曰:“此為爾叔貢物,我不忍獨享,爾其受之。”這是連皇上也得不到的恩典,令榮祿又是感動又是惶恐。原先行宮居室用紙裱糊,緊要邊沿飾以少量綾綢。貢物到後換用繡幕,朝堂仍用布帷裝飾,帝室以儉德示人,在當下尤其需要。
與貢物同來的還有援軍,其中川軍十營,人數為諸軍之冠。貴州提督夏毓秀在見駕時,慈禧見他麵部傷痕累累,便誇獎他的忠勇,卻不知這些疤痕,是少年鬥毆落下的印記。上諭擢升其為湖北提督,命率本部赴固關外駐紮,抵禦洋兵。夏毓秀聞令大駭,向榮祿求情。榮祿明知綠營兵力隻能充數,況且議和期間不宜誇張敵情。榮祿奏稱川軍畏寒,不必遠出關外,令其駐守韓侯嶺。川軍並未聞令即行,他們與滇軍、粵軍一起,在市井間觀光遊蕩,尤喜滋擾商鋪。甘軍餘部是地頭蛇,哪能叫南蠻子放肆,兩下起了衝突,鬧出多人死傷。如此內鬥內行,使樞臣大為惱火,喚來夏毓秀申斥一番。夏毓秀老實認罪,回去後並未率部開拔,續演陽奉陰違的戲碼。
所謂行在,其實就是走著說著,尊嚴和規矩都擺在口頭上。這是吳永悟出來的,他悟出的更深一層是,天家跟民家差不多,在無力回天的時候,他們也會認命。這使吳永生出一點悲憫,以小臣而憫天家,該有多麼滑稽!但他存有天良,豈能知而不言。他想起在宣化時,他曾上書言事,所提條陳大多落空。要不要再次提出?王文韶已告誡他兩次,他能屢教不改嗎?
吳永終於沒有忍住。他在十條中選擇三條,與當前急務連接:一是勤王各軍,請飭編補整肅,嚴定軍紀;二是請飭各省將應解京餉核定成數,分別解送行在戶部,以濟要需;三是受災嚴重地方,請豁免本年丁糧。因已被賜予專折具奏權,吳永將折子直遞奏事處。
第二天早朝議事,上頭發下吳永的折子,令軍機議奏。三大臣回到軍機房,相對苦笑。這個吳永,太多事了!不是說他奏事不對,而是在禦前失了分寸,打亂了尊卑上下的嚴格次序。中國從孔夫子開始,一應次序越擺布越清晰,失序就會大亂,就會輕起禍端。這不是危言聳聽,吳永恃寵生驕,是有可能從一個好人變成佞臣的。
幾個人正在議著,岑春煊走了進來。他撿起桌上的折子,從頭到尾看完,嘻嘻笑了起來。鹿傳霖問他笑什麼,岑春煊說:“這位懷來縣令,每到一地都跟縣令勾結。我這糧台發出的指令,他們總想打折。這是州縣慣技,不從皇糧公款中克扣,州縣拿什麼分肥?”鹿傳霖開玩笑說:“你怕他來跟軍機分肥?”岑春煊說:“他不分肥,他跟軍機鬥心機。”鹿傳霖笑不出來了,認真地問:“世兄有什麼辦法嗎?”
岑春煊故作高深,伸手指點折子上的字句。直到鹿傳霖不耐煩了,岑春煊說:“請飭各省將應解京餉核定成數一條,正合當前所需,倘若無人督促,誰願及時解餉?這可以請君入甕。”
鹿傳霖雙眼一亮:“好主意!你是糧台,吳是會辦,由你出奏正合適。”
岑春煊直任不辭。四人一起入宮,上奏議成辦法。岑春煊舉薦吳永、俞啟元,一路隨駕當差,熟悉艱難情形,定能仰體聖懷,使督撫們感恩出力。慈禧雖對這個建議有些疑問,但吳永終究是個小官,在此間可有可無,這便準其所奏。軍機隨即傳旨下去,令吳永赴兩湖,俞啟元赴江浙,催各省速發京餉,解行在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