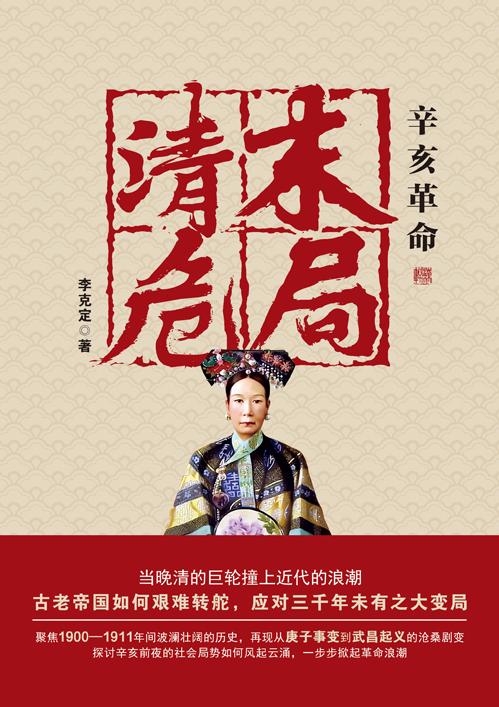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二、新政再起 老調重彈
行在的日子懶洋洋的,慈禧有時會產生錯覺,以為是在頤和園中,午睡醒來躺在榻上,漫不經心地默念戲詞。那一定是昨天聽過的演唱,聲腔韻味醒耳入心。隻是可惜,來西安後沒再聽戲,一是沒心情,二是不相宜。差一點亡了國的,你還要聽戲!
亡還是不亡,其實尚無定論。與和議同時進行的,是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暴行。他指揮聯軍南征北戰,蹂躪了整個直隸,兵鋒抵近山東,還要西窺秦晉,做出直搗行在之勢。這是對談判進程施壓,在往返折衝之中,談判已到最後關頭,慈禧看得很清楚。果然,她等到了李鴻章的電奏:
二十二日電旨敬悉。另旨催臣等克日開議,勿再遲延,曷勝惶悚。查各使責難肇禍諸臣,一律從嚴,並欲先行辦結後再開議。屢次辯論,俄、日、美尚可理諭,餘則驕橫。臣等僅憑筆舌相爭,應付本屬棘手。各使自行公商十餘次,又因請示外部,不無耽延。而於懲辦禍首未肯鬆口,現在洋兵在京,動輒生釁。倘欲自往辦理,必致枝節橫生,全局糜爛,臣等何能當此重咎,不敢不預為陳明。現唯催定開議日期,相機磋磨,力圖補救。如其始終堅執,臣等受國厚恩,但知以保衛宗廟社稷、皇太後、皇上為重,再行據實請旨辦理。
此奏強硬、堅實,每一字都硬邦邦的,容不得絲毫猶疑。慈禧也便下了決斷,將心中的定案和盤托出:莊王載勳賜自盡;載漪、載瀾監禁新疆,永不釋回;剛毅斬立決,以病死免議;毓賢正法;英年、趙舒翹令自盡;啟秀現被聯軍監禁,索回正法。
這是往事的結局,希望能成為將來的開篇,做出別樣的文字。慈禧識字無多,在這悲慘的時日,她後悔沒有分外努力,在成功的帝王術中學到本領,用來報仇雪恨。
罪臣一一行刑完畢,輪到端郡王載漪了。此為懿親,其子大阿哥還在宮中,怎受得生離死別之苦。發遣前夕,載漪向軍機處提出請求,希能跪辭慈聖。慈禧令傳回懿旨:見了傷心,不見了吧。載漪不是一個省事的,到了晚上八時,押送的武將匆匆跑到榮宅稟告:端郡王發瘋,要碰牆而死,哭喊必見慈聖!
榮祿無奈,去安撫這個不好惹的太歲。載漪把九天諸佛都罵到了,罵得最狠的是榮祿。他好端端地當著王爺,有人向慈聖獻計,讓他的兒子做大阿哥。現在可好,兒子是一隻囚鳥,老子當西域野鬼,你榮祿當朝宰相比泰山石還穩!榮祿好話說了一籮筐,看那人油鹽不進,榮祿變了臉說:“王爺你想怎的?慈聖說個不見,誰能拉她回頭?再說你見她作甚?不過是抱著僥幸,求她開恩放過你。趁早死心吧你!莊王載勳是被你害的,他的冤魂來抓你,我看你往哪兒躲!”
載漪被榮祿鎮住了。直到這時,榮祿才叫他見識自己的一片苦心:榮祿著人請大阿哥出宮,讓父子見上一麵。載漪淚如泉湧,大阿哥呆若木雞。載漪真正是“知子莫若父”,哭著說:“兒啊兒啊,別人都說你紈絝無知,為父曉得你是在韜光,因為在英主太後麵前,聰明的都坐不住。誰說你無才,叫他聽聽這首詩:‘入夜宮中燭乍傳,簷端山色轉蒼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訪柟台第五仙。’聽聽,聽聽,十五歲的大阿哥做出這種詩,別說去考狀元,考個皇上也能中啊!”
痛痛快快地發泄了一通,載漪還原為惶恐的父親。他找到避往別室的榮祿,撲通跪下。榮祿慌忙扶掖,哪裏扶得起?隻好爬跪在地,與載漪相對磕頭。載漪嗚咽著說:“載漪是渾球,粗柴話你別往心裏去,隻記住載漪求你:幫幫我兒,莫讓他成為宮廷棄兒!”
第二天,載漪、載瀾兄弟踏上漫漫長途,西征去也。榮祿進宮見慈禧,把這淒慘的場麵奏上去。之所以不隱瞞,是因為老人家參透人性,也因老佛爺洞察幾微,心腹之臣應該坦白。慈禧沉默很久,擺手讓他下去。慈禧兀坐很久,直到鐘敲午時。
談判進入談價,就是賠款數目。這是把中華國土放在砧板上,一塊一塊切下來,放上秤盤去稱。兩宮和朝臣能夠感受到,身體被人臠割的痛楚。所以在議事中,經常發生口角,太後和軍機,皇上和言官,有時候皇上和太後,竟也拌上幾句嘴,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在這朝綱紊亂的當口,太後竟然不以為忤,因為最大的危險在外麵。一個屋子裏的人,所爭的不過是掂棍或是掄刀,衝出大門去嚇狼。
爭論最激烈的,是節外生枝的俄約。所謂俄約,是俄國侵占了東三省,俄人企圖搶在公約談定之前,先與中國達成協議。他們以表麵上交還東三省為誘餌,實則通過種種條款,將東北權益吞進自己肚裏。李鴻章雖然識得透其中玄機,但卻希望借助俄國的蠻力,在公約談判中保住更多權益。他的主張招致一致反對,連在共事中唯他馬首是瞻的慶王奕劻,都在給榮祿的信中埋怨李鴻章:“中俄定約一事,不免過有成見。”山東巡撫袁世凱、安徽巡撫王之春,上書反對簽訂俄約。奉命會辦和談的劉坤一和張之洞,更是強烈抨擊,以至於雙方都大動肝火。李鴻章罵張之洞是書生,張之洞罵李鴻章是官僚,鬧得不可開交。
朝堂上也不消停。近因榮祿體弱多病,足疾更重,本已賜假休養,卻也連日扶杖入朝,參與辯爭。在榮祿看來,李鴻章不計毀譽,不避嫌怨,這才稱得起老成謀國。但他很少講話,反倒讓一個新人放言高論。這人是瞿鴻禨,起家翰林,任學政,擢侍郎。曾上書密言“和約可成,成法可變”,在慈禧心中留下了印記。榮祿病中念及中樞空虛,舉薦瞿鴻禨為學習軍機。瞿鴻禨力詆俄約,稱之為賣國條約,顯然有一種清流風采。
對於這件事,王文韶和鹿傳霖似無成見,有時附和瞿,有時讚成李,其實也屬老成一路。他們有命定的失敗感。無論如何敵已入都,最終談成的和約,一定賣國,逃得掉嗎?
俄國下了最後通牒:如不簽約,絕交動兵。李鴻章向朝廷也下通牒,要求拿出決定意見。這天從早朝議過了中午,決定仍然拿不出。慈禧一直靜聽臣下爭吵,這時要出來結束爭論:“李鴻章講得有道理:東北現在俄國手上,能夠交回,總是好的。”
光緒躊躇了一下,說話前俯下了首,做出知罪的姿勢:“皇額娘,俄國人以退為進,欲取故予。”
慈禧故作生氣,希望把他駭退:“不要文縐縐的,我聽不懂!”
光緒話不停頓:“從雍正六年的《恰克圖條約》開始,俄國奪走中國大片土地,俄國是傷我最重的強國!現又故技重施,虛聲恫嚇——”
“你為何認定是虛聲,他不會實做?”
“回額娘話,兒不認定,兒是揣測。誠如您言,東北如今在俄之手,他如果能夠自主,為何還要找我簽約?真是為我們好嗎?不!他需要得到認可,他是有求於我。因為他不是獨霸,日本和英國兩大勁敵緊盯著他,德、法、美也不消停,都要出手爭奪。他威逼中國簽約,是要拿到憑據。我們老實就範,那真是上他的當了!”
慈禧低頭不語。過了很久,倏然發問:“你們什麼意見?”
瞿鴻禨叩頭奏道:“臣拜服皇上聖明。”
讚成就行了,頌聖便過了。榮祿正在腹誹,聽到慈禧點名:“榮祿?”
榮祿哆嗦了一下。此時容不得多想,隻能憑感覺行事:“奴才認為皇上講得有道理。”
首相做出了樣子,王、鹿也便跟上來。慈禧歎息一聲:“我豈不知道皇上聖明?”看出光緒要辯解,慈禧把聲調放軟:“你不要趕著解釋,有些話,說得越多越不清楚。咱們是額娘兒子,也是太後皇帝。對是我們的,錯也是我們的,這筆賬打總來算,誰也推不過去。都說李鴻章親俄,也有人說我親俄,這話我都認了。皇帝,你知道為了什麼?”
光緒平實地說:“兒子不知為什麼,隻知皇額娘不親俄。”慈禧深深點頭:“你為什麼這樣認為?”
光緒答道:“俄國奪我滿洲,那是祖宗熱土,皇額娘哪能不恨俄國?您認可李鴻章,是支持他辦洋務,行新政,求自強,致中興。兒子以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
慈禧明知道,接下去他要說什麼。不知為何,她把那句話搶過來:“我們還得行新政?”
光緒精神一振:“您說的是,我們還得行新政!”
一下把話題引到這裏,人們始料不及。開弓沒有回頭箭,這話收不回去了。當天決定兩件事:拒絕俄約,加快與各國議和談判;籌議新政,逐步推行。從曾、左、李主導的洋務運動開始,中間經過康、梁籲請的維新,到今天要進行第三次變法。王朝命運多舛,卻也顯示出不屈的韌性。
軍機諸臣議定主旨,交由榮祿定奪。榮祿的文膽是樊增祥。樊增祥接到指令後,挑燈夜撰,三易其稿。榮祿帶著定稿,入宮恭請聖裁。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行在發布上諭:
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因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
湖北的亂事,並未因唐才常就義而結束。張之洞一麵在漢口緝捕會黨,一麵嚴防各地黨徒蜂起。唐才常的二弟唐才中,從武漢大網中脫隙而出,潛奔至沔陽縣新堤,向右軍統領沈藎告變。沈藎剛剛收到唐才常的來信,告以北京城破,自立軍要抓住這絕大題目,於二十三起兵。至此已經錯失良機,右軍倉促舉事,與前來兜剿的官軍打了一仗。因寡不敵眾,且戰且走,搶船渡江,轉戰湖南灘頭、源潭等地,攻破厘局,焚毀哨卡。湘軍信字旗、健字營,與追上來的鄂軍會合圍剿,自立右軍戰敗潰散。唐才中逃回瀏陽,被縣兵捕殺。沈藎潛回武昌,隱匿在友人陸潤祥家中,後來輾轉流亡到上海。
武裝暴動被鎮壓下去,亂源仍未消除淨盡,張之洞因之大開殺戒。特派護軍營二百人駐漢口鐵政局,形跡稍可疑者皆不免,兩日內殺百餘人。除武昌和漢陽外,尚有沔陽、蒲圻、應城、長樂、沙市、嘉魚等地,先後響應唐才常起事,至此都有多人被殺。加上湖南、安徽等省的黨獄,此役一共屠戮千人以上。
張之洞殺的另一要犯,是遠在江寧的辜人傑。從受審的犯人口中,供出辜某乃是自立黨魁,被會眾稱為“五省欽差大人”,可見其包藏禍心。張之洞正要向劉坤一通報,辜人傑的罪行已經敗露,不得不向江寧當局自首。原來,在大通戰役的尾聲中,辜人傑奉命率兵赴剿。他乘坐兵船逆流上行,駛至皖鄂交界時,忽見上遊駛來一隊兵船。兩隊相遇時才發現,這是徐寶山的緝私營。辜人傑像吃個蒼蠅一樣膩歪,本想避往艙中,忽然心裏一動,令武弁向對方喊話,問是何人帶兵?一艘大船從船隊中間開上前來,一個胖乎乎的家夥立在船頭,向副將大人施禮。聽他自報家門,是春寶山堂副龍頭,奉徐都司之命來到皖江,助剿亂黨。
辜人傑沉住氣問:“你助剿立功了嗎?”副龍頭咧嘴笑:“上稟大人,兄弟奪了首功!匪首郭老太,被我用鹽幫舊情釣上鉤,在酒醉中捆送水師,殺頭祭旗。要不是水師不頂打,大通何致於落入賊手?”辜人傑又問:“還有別的功嗎?”副龍頭忙不迭:“有有有,在洛家潭和竹木潭,我軍都舍命拚殺,大有斬獲。戰後論功,安徽大官請賞徐都司升遊擊,兄弟榮任七品守備,嗨,光宗耀祖啦!”
辜人傑突然翻臉:“你這緝私營,職在彈壓小偷小摸,膽敢擅自稱兵,亂我法紀!左右,開炮!”一聲令下,眾炮齊發,打得緝私營哭爹叫娘,人仰船翻。正打得高興,又一隊官軍從下遊駛來,這是水師總兵李祥椿的船隊。李祥椿在船頭與辜人傑互揖,問明原委,心懷疑慮,卻不說出。等辜人傑交差後回江寧,有關他袒護秦、吳,屠殺功狗的傳言,已在城中沸沸揚揚。辜人傑尋思逃無可逃,徑去投案。
張之洞聞訊致函劉坤一:“辜人傑係最大頭目,無論在押在保,均請解鄂審辦。尊意如欲貸其一死,俟解鄂後自當酌辦。”辜犯解到後,張之洞沒有細“酌”,批飭將其砍頭。張之洞給劉坤一的解釋:“現在康黨圖謀大舉報複,非多辦緊要匪首,即不足以保長江。故辜人傑一匪,更不能以自首而寬之也。”
在殺人的間隙,湖北官場大有變動。兩宮入秦,東路河南成為保障要衝,行在調於蔭霖任河南巡撫,而以河南巡撫裕長為湖北巡撫。這種安排,隱約包含上頭對張之洞的疑慮。東南互保這樁大事,可以做多種判斷:說好些是保衛疆土,說不好是守境自立。所以,張之洞身處危疑之中,需要有更多表現。張之洞有的是辦法,他親撰《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大旨為告誡士人和留日學生,勿信康黨邪說,毋任逆犯荼毒,當以忠君為念,並以保國為懷。
張之洞大文發布,正搔著康有為的癢處,他當即揮毫上陣,隔海與張公大打筆仗。他的文章體例是,引一段張著正文,然後以“駁曰”開篇,作針鋒相對之抨擊。總共十二段駁文,其中一段如下:
查唐才常之被逮也,大書曰:“湖南丁酉拔貢唐才常謀救皇上複辟,機事不密,請死。”張之洞曰:“爾文才甚優,何以作此?”唐才常斥曰:“爾讀書而不明理,乃忘君臣之義而背君附賊。”張之洞怒而殺之。唐才常一拔貢耳,乃能感激效死。而張之洞身為大臣,乃然坐視,媚事偽朝,大肆捕殺勤王之士,既無麵目見天下人,乃厚誣義士以作亂之名。夫安有千百文弱書生作亂哉!凡此皆為張之洞之誣罔,彼自命儒臣而不學如此,宜其妄抑民權草菅人命矣。
康有為的刀筆越鋒利,越能反證張之洞之忠貞,張之洞樂得跟他對罵。他還要挖康黨的牆腳。從審訊中得知,邱菽園是康有為的財東,也可說是窩主。如果斬斷這條財路,康黨血脈將會枯竭。張之洞以湖廣總督的名義,發布《通緝富有票著名匪徒單》,邱菽園赫然在列。通緝令谘送清朝駐英、日等國公使,以及沿海沿江各省督撫,要求廣為張貼散發。接著致電駐英公使羅豐祿,請派駐新加坡總領事,對邱菽園進行開導勸諭。
唐才常的這場慘禍,使邱菽園又是內疚,又是憤恨。疚的是自己寄贈三萬元,像是親送唐君歸陰。恨的是康有為坐擁集資,卻不能及時供應,致使前方陷入絕境。他心中已與康氏決裂,新加坡總領事羅忠堯登門勸說,等於順水推舟下行。邱菽園在《天南新報》上發出閉門著書的啟事,透露退意。張之洞趁熱打鐵,又給新任兩廣總督陶模發去一電。陶模是張之洞任浙江鄉試考官時取的舉人,張、陶有師生之誼。陶模心思細密,辦事周全。他向羅忠堯發去劄文,卻又將劄文發表在廣州、香港的報紙上。劄文大意:照得本部堂訪聞,去年有多人由上海、香港前往新埠,其人多湘楚籍,分寓邱菽園、林文慶處。邱由緬甸、暹羅籌資,遣人隱結粵省會匪。劄仰該領事縝密查明,詳細電複。湘楚前往該埠者,想皆求新之士,或以前與康、梁有交,或去年為唐才常所牽涉,所以畏罪遠引;抑或以中國未行新政,憤激出遊,求遂其誌。凡此不得已之苦衷,皆本部堂所深悉。況得罪朝廷,奉旨查拿者,隻康有為、梁啟超數人,其餘人士,蓋無幹涉。即當時偶有牽連,但使悔過自新,亦必在棄瑕錄用之列。
這篇劄文敲山震虎,卻又給虎開出生路,使邱菽園坐不住了。思來想去,自己摻和的這團亂麻,毫無生芽抽枝的希望,陪康殉葬,何苦來哉!他發電陶模陳述衷曲,並寫了一篇長達數千言的《上粵督陶方帥書》,以維新變法、尊光緒帝、反對立大阿哥、反對朝中守舊勢力為主旨,對自己的行為加以辯白。陶模據以致電張之洞:“邱與康詩酒應酬,偶助資財,似非同謀。我不變法,若輩日多,非殺戮所能止。請吾師勿再捉拿,湖北書院事亦勿深求,恐激成黨禍。”張之洞不為所動,繼續施加壓力。邱菽園故鄉福建官方,開始追究邱氏族人。而在另一方麵,張之洞授意新加坡領事,加緊威脅利誘。所謂利,就是取消通緝,免除罪名。到了這一步,邱菽園掙不脫鉤了。他先向福建捐銀二萬兩,又向湖北捐出一萬兩,作為“秦晉賑捐”的捐款,並且向張之洞出具稟文,做出不再資助康有為的保證。同時在上海諸多報紙刊出邱菽園的告白,宣布與康有為絕交。
這一仗打得漂亮,張之洞上奏行在,原原本本地描述策反康家死黨的故事。朝廷為之欣喜,由內閣明發上諭:“張之洞奏出洋華商表明心跡,請準銷案免究並予褒獎一折。既據該舉人輸誠悔悟,具見天良,殊堪嘉尚。邱菽園著加恩賞給主事,並加四品銜,準其銷案,以為去逆效順者勸。”
可謂一通百通,在廣東經手的另一件“好事”也在順利進行。張府大幕僚梁鼎芬是廣東人,他向張之洞報告:廣東舉人梁慶桂,號召廣東官紳捐獻錢財,奔赴行在,敬獻方物。當時新督陶模尚在赴任途中,廣州官場恰值交接的空當。張之洞主動與護理廣督德壽電商,由湖北方麵出奏。德壽暗罵張之洞掠美,但他處在尷尬位置,當即回電,欣然同意。梁慶桂一行來到武昌,張之洞對他們盛情款待,大加嘉勉,加派馬隊護送出境。預先致電河南、陝西,請飭地方官沿途照料。
這支官紳隊伍跋山涉水,一路風塵抵達西安。張之洞致電他的姐夫鹿傳霖,詳細剖白自己的心跡:
廣東人自兩宮西幸,係懷行在,鹹思盡臣子之心。梁中書慶桂,忠愛有才,集紳士四十餘人,敬備銀五萬數千元,分辦貢獻銀、物。黎郎中國廉,售所居屋,得銀二萬,即以為貢。此外二千、一千、數百、一百不等。富家固多,寒士亦不少,皆出於至誠,各省所未有。祈公提倡此舉,若得明旨優褒,先稱廣東百姓向來忠於國家,次獎備銀貢獻紳士,可否將四十餘人全列姓名,祈公明斷。旨發後,各省必聞風興起,粵省必踴躍繼來。海外粵商近年每為康逆所惑,今讀優旨,悔悟必多。此舉頗關大局,敬希垂顧。
鹿傳霖反複誦讀,對內弟的老辣很是佩服。這是忠藎,還是宦術?不管人們對他有多少指摘,你不能不承認,張之洞是老成謀國的。朝廷對此深有同感。廣東是什麼地方?那是康有為、孫中山的巢穴,多少次逆風惡浪,都是從那裏興起。如今風向變了,先有邱菽園的投誠,又有梁慶桂的獻忠,預示著多災多難的朝廷,必將否極泰來!
朝廷發出明旨,對粵紳予以優獎。在加官晉爵的喜慶中,行在又收到張之洞的電報:
據江漢關道稟,準日本領事函稱:漢口日商東肥洋行聞兩宮西幸,不勝酸楚。民雖異國,誼屬同文,立業在華,久沐天恩浩蕩,謹獻土產數品,以表悃誠。查所呈貢品,係魚翅二箱、海參二箱、魷魚一箱、鮑魚一箱,裝潢精潔。物品雖細,係出至誠,其恭順之情,出自洋商,尤屬難得,擬請旨賞收嘉獎。
比平亂和獻好更正經的政事,當屬新政重啟。張之洞收到新政上諭之初,有點不敢相信。在戊戌變法風潮中,他的《勸學篇》隆重問世,曾經引領風尚,比康、梁毫不遜色。政變使新政夭折,他的兩個弟子,楊銳和劉光第,在殉難六君子之列。也就是說,“張黨”在叛逆中三居其一,如欲誅心,張無所逃。所以對於維新,張之洞是驚弓之鳥。現在舊事重提,究竟所為何來?
張之洞要摸清動向,便有很多消息傳入耳中。引起他警惕的,是安徽巡撫王之春的電報,內稱有軍機章京密報:“奏複變法,勿偏重西。”意即在上奏意見中,不要偏重西方政法。此電令人驚疑,不重西法,那還變什麼?張之洞急電姐夫,打探內情。鹿傳霖的回電,對章京傳言表示不屑,明確告以此諭出自聖裁,並有全體軍機讚成。諭旨還是樊增祥起草的,這是你的門生,老弟又有何疑!
張之洞大為振奮,看來王朝重新上路,要尋回斷送的生機。不過,鹿傳霖回電還有這樣幾句:“似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此大舉動大轉關,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開痼癖而利施行,非公孰能為之?亟盼盡言。”這叫什麼?仍為瞻前顧後、憂讒畏譏,前麵數次變法,就是這樣斷送的!由於麵對的是姐夫,可以說幾句心裏話,張之洞便複電發牢騷:“人言內意不願多言西法,尊電亦言勿襲西法皮毛,免貽口實。不覺廢然長歎,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蓋變法二字,為環球各國所願助,天下誌士所願聞者,皆指變中國舊法從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頓之謂也。”
至於“大文字”,張之洞無比自負,環顧天下舍我其誰。但他牢記姐夫的警告,不會搶當先爛的出頭椽子。督撫們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各省之間函電交馳,互摸底細,生怕冒了頭,又怕落了單。這就有了聯銜上奏的設想,因為同執一詞便成為公論,比單銜奏議更具分量。那該由誰主稿呢?若按位分,劉坤一最高;若按文名,張之洞最大。劉坤一代表其他督撫推張執筆:“香帥博古通今,貫徹始終,經濟文章久為海內巨擘。非由香帥主持,斷難折中至當。” 張之洞連忙推辭:“湖北不敢率先作聲。鄙人主意多魯莽,思慮多疏漏,世人的詬病還少嗎?”
推讓多時,迄無定論。大家都不急,法非瞬間可變,事豈轉手即成?等等看,能夠觀察事態變化;慢慢來,可以共同承擔責任。沒想到朝廷等不及了,辛醜年三月初三,行在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辦理新政的最高機關。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昆岡、榮祿、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遙為參預。同時督促各省對於實施新政各抒己見,勿再猶豫觀望。這一下拖不成了,袁世凱致電劉、張稱:“二公現列參政,與他省份不同,不宜多省聯銜;山東打算單銜複奏。”
這就是事態變化,各省重新盤算,江、鄂聯銜會奏卻決定了。劉坤一堅持推張主稿,張之洞提議兩下各擬一稿,然後互相參照,再作修改。商定後各自選擇文士,劉坤一選的是張謇、沈曾植、湯壽潛;張之洞選的是鄭孝胥、梁鼎芬、黃紹箕。鄭孝胥等請示擬稿主旨,張之洞發了一段駭俗之論:此次應以仿效西法為主。原因在於各國厭惡中國,以為華人懶滑無用而又頑固自大,不以同類相待,必欲欺淩製服。所以不仿效西法,便不能消除各國歧視中國、仇視朝廷的惡意。看到三位幕僚匆忙記錄,張之洞又變了卦:“這是先前的偏激想法,作為談資可也。至於文字分寸,寫出來再作權衡。”
三名寫作裏手,開始咬文嚼字。張之洞眼觀六路,依然穿針引線。隻要有奏稿完篇,他都拿過來賞鑒。江寧的三位撰稿人,也被張之洞邀到武昌,作為座上嘉賓。張之洞是文章宗師,張謇是狀元才情,沈曾植與湯壽潛,各呈名士風采。酒瀾人未散,乘興話世情。張之洞問詢劉公的起居,聽張謇說劉公自感疲憊,精神大不如前,張之洞的心情跌落下來。他感歎說:“正值當緊時日,劉若撐不住,張又何所為!我不敢學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然劉、張已是同氣連枝。但願上蒼保佑江南,使巋然一劉巨木擎天。”
張之洞問起翁師傅的近況。張謇回稱:“讀書,寫字,尋食,發呆,這就是翁師日常。”之所以說“尋食”,是因家貧要靠侄兒、門生接濟。狀元帝師、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戶部尚書,而晚景如此,想得到嗎?張之洞嗟歎不已。張謇說起年前去探看,翻閱翁師案頭筆記,“伏案看《史記》,意致不佳,寫字亦倦”“讀《史記》一過畢。寫楹帖提不起,真弩末矣”“炯孫來見,話京師事,悲詫不已,真相對如夢寐矣”。神衰心未死,尚在言念京師,而京師對於我等臣子,真如刀劍劈開的巨創,欲求愈合,其可得乎!因此之故,新政重出不能虛應故事,張謇請二公撐起風骨,做中流砥柱!
一個多月後,劉坤一將張稿、沈稿、湯稿發至武昌。劉坤一主張不宜過激,所以屬意於穩健的沈稿。張之洞卻讚賞張謇擬稿,認為其全麵而且係統。其第一條就是“置議政院”,另有一條“設府縣議會”。這叫張之洞想起陶模的奏稿,陶奏也提設議院,上奏後卻被“留中不發”,與他省奏稿區別對待。以致陶模失望電張:“觀政府意,未必真欲變革。”那麼對於張謇的《變法平議》,隻好存下遺珠之憾了。張之洞將江南三稿,與鄂撰一稿糅為一體,取其精華,避其鋒芒,融冶成勁氣內斂的經世之作。
經過三個月的磋磨,《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采用西法十一條折》《請專籌巨款舉行要政片》,三折一片合稱“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終於發出,張之洞鬆了一口氣。這時,行在糧台會辦吳永,完成了湘鄂等地的催糧差事,前來謁見辭行。吳永是去年底到鄂的,對於這位天使,張之洞十分熱情,幾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酣暢談,聽吳永講述兩宮在漫漫征途中的苦況,張之洞揮淚不止。得知吳永中年喪偶,張之洞勸他續弦。吳永說顛沛流離之中,顧不上這些。張之洞撚髭笑說:“這事包給我了。”過不多日,武昌知府居中搭橋,吳永與大家許氏締姻。到了正月成婚,他得到一位如花美眷,樂不思蜀。
送別酒宴上,吳永對張公厚意千恩萬謝。張之洞笑言:“我籍貫是直隸南皮,你是我的父母官,我得巴結你呢。”笑談變成深談,張之洞鄭重地說:“我問一個隻有你才知道的事。路途相處之間,你對大阿哥可有了解?”吳永明知此問重大,稍作沉吟後,他講了一個小故事。那就是在河灘上午歇,大阿哥丟了一個手鼓,硬要吳永替他尋回來。吳永用半兩銀子向村民家淘買,才算順利完差。
張之洞思慮一陣道:“這事不該由我說。然而臣為國憂,不敢緘口。國家這樁滔天大禍,全為儲君入宮引起。今戰禍稍歇而禍根尚在,和議如何談得成?為兩宮安危計,理當及早請大阿哥出宮。你回去後可乘間進言,就說是張之洞所說,老兄有此膽量否?”
吳永深吸一口氣:“恩公既言關係重大,吳永誓必冒死上言。”
行在收到各省複奏,對江楚會奏尤為重視。慈禧太後發布懿旨:“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仿行西法各條,多可采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各省疆吏,亦應一律統籌,切實舉行。”
根據慣例,每幹成一件大事,疆吏都要請獎有功人員,同時舉薦人才。張之洞所舉人員中,有梁鼎芬和吳永,二人先後抵達西安。吳永屬宮廷親信,次日即蒙召見。麵奏各事畢,慈禧用開玩笑的口氣說:“我才知道,原來岑春煊跟你不對,你是被擠到外邊去的。”吳永忙叩頭:“臣也應該趕快催糧。”慈禧含笑說好。第二天便有恩旨,徐世昌、孫寶琦、吳永,奉旨以道員記名簡放。即日召見,皇上端坐在禦案後麵,太後設位於皇上後麵,那是高高的寶座,恰如戲台上之觀音王母像。禮畢慈禧笑謂內監,吳永今日也上了場,正式行起大禮來。
吳永牢記著張之洞的囑托,然茲事體大,哪敢冒昧。這天瞅個機會,吳永向榮祿請示行止。榮祿正在吸煙,一家丁立在旁邊點火裝煙。榮祿聽罷不吱一聲,隻是闔目吸煙。吸完一管,家丁填裝旱煙,榮祿執煙杆再吸,吐出的煙氣騰雲作霧,彌漫屋宇。直到換吸三次,榮祿才閃開眼縫,徐徐點頭道:“也可以說得。你的地位分際,倒是恰好,像我輩就不便啟口。但須慎重,切勿魯莽。”
不料這宗要事,被梁鼎芬占得先機。梁鼎芬曾作言官,以憨直敢言聞名。不得誌而為人作幕,仍然無所顧忌。此次兩宮召見,詢問兩湖政事,梁鼎芬是親力親為,講得有條有理。對於剿滅自立軍一役,更是繪聲繪色,使兩宮同感欣慰。奏對將要結束時,梁鼎芬趁機上言:“臣在武昌,後來在開封,都曾聽人傳告,外國人要待兩宮回鑾後,請廢大阿哥。臣思當前國勢極弱,外國人若有要求,恐怕無力拒絕。如果照辦,成何國體!以臣愚見,不如自己料理,以免外人開口。”
殿內無聲無息,靜寂如同古井。慈禧正視前方,側邊仿佛生出一雙眼,覷著身旁的動靜。光緒毫無反應。熬過好大時辰,慈禧方才動了動,示意梁鼎芬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