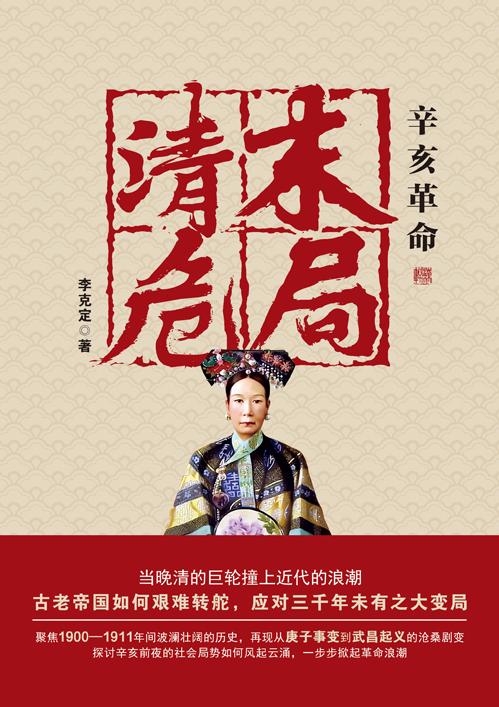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四、失先機軍功敗垂成
林圭籍隸湖南湘陰,時年二十六歲。除了開國會時回一趟上海,他已駐漢半年之久。在漢口設立自立機關,也是林圭的主張。林圭曾致函孫中山:“設此公所之意,因眾兄望事殷切,而逾期兩年,無甚著落,令人生疑。若無團聚議事之所,其勢渙散,何以自立?譬如,開設營壘,以示有人在此,不以滄海橫流移其心,然後知所歸附矣。”林圭豎起招兵旗,各路豪傑蜂擁而來,猶如磁石吸附鐵塊。令人驚訝的是,林大帥在軍營裏頗得人心。就在上個月,林圭召集軍中會友,在鸚鵡洲操演。幾天前,駐武昌的練軍營官來見林圭,報稱營中的炮口調轉方向,對準總督府,單等林兄一聲令下。這聽上去匪夷所思,然而事出有因:張之洞要改革軍製,大力培植護軍,練軍和綠營這些雜牌隊伍,均在裁汰之列。張之洞任用的護軍統製官,是目不識丁的張彪。此人年輕時是張之洞的貼身跟班,極受寵信,娶以愛婢,用為巡捕,保授總兵。如此任人唯親,你就得在戰亂中吃我一炮!
佳音不斷,戰鼓頻催。在翹首企盼中,狄葆賢從上海來到漢口。他帶來梁啟超的電函:“舉義之時,軍械足用否?若弟在外有接濟,當以何法收受?初起總以奪敵械為第一義,不能奪則毀之,不使資敵。若有敢死之士,能轟炸高昌廟之局否?西人銀行皆不肯放款於華人,借美款暫停止。檀香山計捐款十萬,現可得三四萬,尚未實收,先以一萬寄上。”
在十萬火急的軍情中,來電大談奪敵械,而他要炸的高昌廟,是遠在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實際寄款一萬元,這是打發叫花子嗎?唐才常兩眼冒火,瞪著電文說不出話。狄葆賢安撫地扶他坐下,講述國會近況。英文宣言發出後,英、美的反應比較謹慎,唯有日本給予肯定。這可以理解為,國會與自立會員,大多是留日歸國的,這也是英、美疑慮的原因。容閎和嚴複認為,各國都在觀望,我若起兵順利,他們都會承認國會。
現在的隱憂是,自立軍以會黨為骨幹,這些人敢打敢拚,坦蕩質樸,崇尚江湖義氣,具有血氣之勇。缺憾在於見識短淺,貪圖財貨,成則稱王稱霸,敗則一哄而散。我們在緊急關頭予以利用,無暇對其教育訓練,隻能如林圭所言“激之以義,動之以財,感之以信誠,餌之以爵位”。但這樣一點點餌,豈能使他們死心塌地、赴湯蹈火!李雲彪和辜人傑領回的港款,便先被其手下頭目冒領,住在上海花天酒地。畢永年將他們趕回湖南,這些頭目成事不足,剛在臨湘吃了敗仗,害得畢永年重新逃亡。
畢永年又失敗了?唐才常暗暗搖頭,送狄葆賢啟程返滬,回頭與林圭商議。一萬元杯水車薪,無法按時起事,隻好將日期改為七月二十。趕忙派人分頭通知,尚不知路途是否順暢。第二天上午,唐才常在居所閱讀常德來信,這是左軍統領陳猶龍所寫:“常德約計勁旅三千,人人義形於色,翹企舉事。唯各司事亟待關餉,因彙兌未至,弟在某洋行借得五百元,登時散盡,無以開銷。兄下撥款項確到日期,望預示知。”看到這裏,唐才常的左鬢隱隱作痛。他放下信箋剛要起身,聽見門外有人聲:“貧僧求見施主,下人安敢阻撓?”
唐才常走出門去,見仆人攔在一個人的前麵。那人身著道袍,頭戴僧帽,衣冠都不合身,顯得不倫不類。唐才常恍然認出那是誰的臉,失聲叫出:“鬆琥兄?”
畢永年咧嘴笑:“是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過相見之後,我將非我。”
唐才常將畢永年引進屋,讓座上茶,又張羅問他吃沒吃飯。畢永年撿起桌上的信,掃了一眼:“陳統領的?我原本與他鼓角相聞,隻是而今各奔西東。”他端起茶碗一飲而盡,順手抓起茶壺續水,再飲一大口道:“嗚呼痛哉,一水入喉,百脈皆活,唯我之心昨已碎了。你知道紅槍會嗎?這是哥老會的分支,在湘鄂交界分布甚廣。臨湘會首綽號‘黑虎星’,李、辜將其納入麾下,委任為富有山堂副龍頭。辜人傑親口告訴我,‘黑虎星’買通了官府和營弁,舉義時可使全縣易幟。”
大概有點燥熱,畢永年伸手拭額,似想掀掉僧帽,卻又止住:“我與李雲彪去臨湘,一入縣境便聽到風傳,陸溪有股匪冒充營兵,搶劫當鋪錢莊多家,並流竄於老龍口、寶塔洲一帶。這幾個地名令我生疑,因為那是‘黑虎星’的活動地界。我倆在陸溪口得到報告,‘黑虎星’在三坪街財神廟坐堂放飄。”
放飄就是放票,飄有隨風飄散,廣為流傳之意。畢永年接著講述:“財神廟在山腳下,廟前人來人往,不像幫會行事的樣子。我截住出廟的人,問他領到了什麼,那人笑而不答。這便進入廟門,但見迎麵設一神案,一尊黑大漢據案而坐,兩旁分列護衛,案上放著大堆票證。一名護衛向我們喝叫:‘前來入會,報上姓名!’沒等答言,黑大漢認出來人是誰,他起身參拜:‘龍頭老大李爺駕到,黑旋風失迎該打,萬望恕罪。’”
畢永年瞧瞧唐才常的臉色:“長話短說,以免絮煩。當場發現,此人放票既有富有票,也有貴為票,是他自己另立名號。這要繳錢買票,他給收買者許願,禍亂時可保身家,讓你非富即貴。如此坑蒙拐騙,使李雲彪也傻了眼,予以嚴厲斥責。那小子倒也聽話,乖乖地召集手下,對其重申紀律。接連數日,擇優汰劣,嚴格訓練,儼然成為可用之兵。我派人聯絡陳猶龍和沈藎,於十五日淩晨同時發難。誰知提前聽到民間風傳,雁峰山紅槍會首葉彪,大開山堂聚眾放飄,公開施放火槍土炮,揚言劫獄救出父兄,攻殺文武衙門眾官。原來葉彪是‘黑虎星’的同夥,先前的劫案就是他幹的。這一下風聲泄露,嶽州鎮總兵派兵三營,會同巴陵、新堤等縣營兵,前來圍剿。我軍在轉移時與敵遭遇,會眾不肯拚命,大多棄械逃散。‘黑虎星’被擒,李雲彪逃脫,畢永年潛奔至此,向自立軍總統報告我之大捷。”
這種自嘲刺痛了唐才常,畢永年仍不罷休:“我們經營多年,均以會黨為依托,原因是自己別無兵力,隻好吃現成飯。可這填得飽嗎?經此一役吾始大悟,若不痛改前非,必將一事無成。你看孫中山的廣州起義,雖然同樣失敗,但他的烈士乃是革命黨,可做再起之火種。康、梁給你的是什麼?最有力者不過是徐老虎之流,自鄶以下,土匪而已!”
唐才常找到發泄口:“徐老虎不是你說降的嗎?”
畢永年捶胸頓足:“是啊是啊,此乃我平生之大恥辱。連我都是會黨龍頭,吾欲贖罪,唯有自殺。今且現身說法,教你改弦更張,不要重蹈覆轍。”
唐才常牢騷滿腹:“怎麼改?馬上就要起事了!把我的部下全解散?”
畢永年瞅著他:“你不是連日期都改嗎?”
“這你也知道?噢,聽林圭說的。我不得已,我無兵餉。”
“你這總糧台變成無糧台,請問誰害的?天下笑話莫此為甚,還有改起兵日期的?聽我忠告,趕快易幟,丟掉康氏保皇旗。”
唐才常苦惱得抓腦殼:“我也想丟,拋不開呀。除去保皇會餉項供應,我指望誰?革命黨嗎?他們還在向四方乞討。”
畢永年急得敲桌子:“一個錢眼兒把你困了!我告訴你,欲求成事,全在‘名正言順’四字。保皇、革命把你撕為兩半,我看你如五馬分屍,血流滿地,把詩書和山河都染紅了!”
唐才常木然不語,兩顆淚珠沁出眼眶,倏然滾落。他聲音喑啞:“那是譚複生之血,中國億萬萬眾之血。畢鬆琥,你也逃不掉啊。”
畢永年悵然起立,緩緩舉手脫下僧帽,露出剃得光光的腦袋:“我已逃了,逃離塵世,逃出惡濁。我隻愧對譚、唐二君子,而可睥睨一世。”
唐才常睥睨著那個光頭:“好啊,章太炎剪了辮,畢鬆琥削了發。我唐才常,唯以一顆頭顱相酬,如是而已,豈有他哉!”
由於隔著省界和安慶省城,加之沿江戒嚴,大通前軍秦、吳兩統領,並未接到改期通知。自從開會歸來,秦力山就掰著指頭數日子,巴不得早到七月十五。吳祿貞勸他說,性急吃不得熱豆腐。秦力山說拉倒吧你,你是小李廣花榮,我是霹靂火秦明,哪耐煩這磨磨嘰嘰!前軍便是先鋒,咱若打不出樣子,會把全軍拖成瘸腿驢的。
大通雄踞江心,扼住長江咽喉,確為兵家必爭。二人周密策劃,以江北桐城為左翼,以南岸青陽為右臂,下遊銅陵當前鋒,上遊池州作殿後,照樣布置前後左右中五軍。鑒於官方注意江南,秦力山設重兵於桐城,欲收出其不意之效。十三至十四,會黨遊勇向各地集結,兵營中的弟兄也做好準備,待時而發。
桐城哥老會首領郭老太,早年曾加入鹽幫,後來開辟山堂自立門戶。幾年前發生蕪湖教案,郭老太打起滅洋旗號,在官方追捕下流亡他方。這回他召集會眾八百、鹽幫一百人,定於明日攻取縣城。郭老太的老營駐紮在湖畔漁村,他和一班親信宿在古廟中。十五日五鼓時分,龍頭副爺按照約定,來見老郭,準備與前來督戰的吳祿貞會合。進廟但聞鼾聲如雷,一股酒臭撲麵而來,醉漢們橫七豎八席地倒臥,連插足之地都找不到。在模糊的光線中,副爺趨到神像後麵,但見那張板床空空如也,令人摸不著頭腦。莫非老郭撒尿去了?副爺喚了兩聲,沒有得到回應,不由一陣心慌,踅過去踢打那些醉漢。
醉漢們陸續驚醒,一起大呼小叫,仍無郭老太的蹤影。有醉漢回答詢問,昨晚議論軍事,有鹽幫弟兄抬來幾壇白酒、大塊牛肉,說是從親戚運槍快船上弄來的。老郭與大夥飲啖盡興,分別醉臥,至於以後的事情,無人說得清了。副爺追問,鹽幫?是哪幾個?擾攘一陣,這才發現,幾十名鹽幫兄弟同時失蹤,留在宿營地的另一部分,對其中隱秘一無所知。
副爺明白遭了暗算,趕緊催促集合。尚未理出頭緒,忽然接到報告,有一支官軍殺到。這是桐城方麵過來的,會眾撤往村南,希望穩住陣腳再說。一杆人衝出村口,在晨光熹微中,望見村外出現兩股人馬,從斜刺裏殺奔前來。右麵那支打著水師旗幟,前鋒高聲鼓噪,軍陣中間推出一個人來,竟是被五花大綁的郭老太!他嘶聲朝這邊喊叫:“兄弟們救我!”
騎在馬上的水師參將張華照,用馬鞭指著郭老太嬉笑:“快快,救救這婊子養的,老子讓你們救。”副爺被激怒了,指揮大家奮勇向前,搶救龍頭。張華照冷笑揮手,但見刀光閃處,郭老太的腦袋迎刃滾落,血光迸射。會眾被這股凶焰驚呆,魂飛魄散中,官軍開槍射擊。副爺大聲叫罵,潰逃的會眾裹挾著他,向東南方向敗退。卻聽連聲炮響,這炮是向追兵打的!官軍發出嗥叫,張華照慌忙下馬,免得做了炮彈靶子。副爺看見,吳祿貞的精幹隊伍,用馬拉著幾門炮,排開陣勢轟擊。水師沒有帶炮,在陸戰中落了下風。
轉瞬間勝負易勢,吳祿貞揮隊衝殺,水師被打得七零八落。自立軍追至湖邊,但見湖上有水師船隊,乘風破浪而來。敗軍搶登泊岸的舢板,爬上水師船逃命。吳祿貞一麵指揮打炮,一麵召喚接應的船隻。原來他是乘船赴前線,登岸後將船埋伏在港汊中。其中有兩艘水師炮艇,炮艇管帶是孫道毅的換帖弟兄。艦炮和陸炮同時發火,打啞了水師船上的幾門炮,水師頓時陷入混亂。逃上舢板的張華照,正要攀上一艘大船,忽聽轟隆巨響,一顆炮彈擊中船舷,激起連聲驚呼,張華照失足落水。附近的起義軍趕來捕捉,水師官兵哪敢怠慢,搶先把參將救上船。
水師邊打邊撤,敗勢無可挽回,共有八艘兵船落入義軍之手。抵抗的官兵都被殺死,不願喪命的就在陣前倒戈。吳祿貞拉起自己的“水師船隊”,向南開進,在白蕩湖口駛入長江,順流而下,不久便望見大通的綠洲。船隊近岸,柳樹林裏擁出一彪人馬,打出的旗幟上,生翅的老虎張牙舞爪,這是秦力山設計的飛虎旗。兩軍會合,秦力山和吳祿貞計議,大通最先聞警,官兵登陴固守,急切間恐難攻克。不如放出風聲,合兵去打銅陵。那是府城所在,我若攻其必救,他會露出破綻。
當下整隊前行,進至大通南門,義軍開始打炮,做出攻城架勢。城上城下炮火連天,佯攻的義軍無法得手,這便拔隊而去。綠洲東南地勢高起,與南岸有淺灘連接,隊伍搶灘涉水,和岸上會眾互相呼應,造出更大聲勢。這不僅是大通的亂事了,寧池太廣道吳景祺、辦理皖岸督銷局道員錢鬆年、大通厘局知府許鼎霖、裕溪參將彭源洽,都向安徽巡撫和水師提督請發援兵。皖江兩岸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守土有責的大小各官,一個個如坐沸湯中。
大通鎮總兵去了江寧,主管厘局的知府許鼎霖,便是大通的最高官員。他為守城忙碌了半晌,太陽偏西時才回宅吃午飯。忽聽屬員來報,南門又發現敵情了。趕快推碗奔出,登上城頭觀看,但見城外塵頭起處,一隊官兵簇擁著一輛車,車上赫然裝著一口棺材。兵們喊叫城上開門,城上回問:“那是什麼?”那些兵火了:“什麼什麼?這是張參將,參將大人陣亡,快給老子開門!”
張華照陣亡了?許鼎霖又驚又疑,令人追問詳情。城下的敗兵哪能捺下性子,窮凶極惡地破口大罵,便要動手打門。認出是張華照的將旗,扶棺的幾名官弁的確是參將部下,許知府下令開門。棺車通過護城河橋,兵隊蜂擁入城,突然一齊發作,隱藏在棺車上的槍械,被抓起向城上開火。隨後跟進的炮車,也找到瞄準的目標。那是位於城牆根兒的火藥局。秦力山親自開火,他在日本學過炮兵,今天終於派上用場。這時候,城外的伏兵炮轟督銷局,擊沉該局的兩艘輪船,順勢奪取了炮船。知府會同大通縣令,在一團混戰中逃出城,將一座城池拱手讓出。
秦、吳舉義旗開得勝,前軍將士一片歡騰。當即盤查府庫,分發軍械,征集錢糧,並於縣衙前宰牲祭旗,張貼告示,向民眾宣布起事宗旨。布告文曰:
中國國會自立軍,為討賊勤王事:照得戊戌政變以來,權臣秉國,逆後當政,禍變之生,慘無天日。下立嗣之偽詔,覬今上之皇權,篡弑不得,則公然攻打使館,以外人為仇敵,以國家為孤注。勇敢廣集同誌,大會江淮,以清君側,而謝萬國。傳檄遠近,鹹使聞知。凡為義士,曷亟來歸!
一、保全人民,包括外人生命財產;
二、不準燒毀教堂,殺害教民;
三、不準擾害通商租界;
四、捉獲舊黨,應照文明辦法處理,不得妄加殺戮;
五、褒揚良善,革除苛政,共進文明,立新政府。
雖然近年亂事頻發,但是失陷一座縣城,卻是江南第一遭。安徽巡撫王之春,急派武衛楚軍統領李定明、營官傅永貴,會合先期抵達的營官李桂馨,分三路進剿。兩江總督劉坤一,飭派“龍驤”“虎威”“策電”三兵輪,駛往大通江麵堵截;並派衡軍統領王世雄率兵一營,乘“開濟”兵輪赴蕪湖駐防。水師提督黃少春,派長江提標三營舢板,星夜駛往大通;湖標舢板三十號上駛協剿,加派江勝左營步隊營官劉達義赴南陵會剿。
調兵遣將,大戰在即,已在大通吃了敗仗的李桂馨部,因軍心不穩,不得不向梅埂退卻。途中遇上武衛前營的傅永貴,兩下合兵再次進發。可他的怯戰傳給了傅營,官兵飲馬長江邊,被江洲上林立的旗幟嚇軟了腿,不敢渡江作戰。直到王之春添派的省城防營、蕪湖防營快速趕到,這才重整旗鼓。秦、吳衡量敵我形勢,沒有被一時得失蒙蔽雙目。義軍之勝在攻其不備。以我兵力之單、來源之雜、火力之弱,如果株守孤城,難免被一網打盡。我們的勝利希望,唯在四方並起,合鄂、湘、皖、蘇之焰為遍地烽火,使官方顧此失彼。大通惡鬥兩日,漢口的中軍如何?想來也已爆發,將以上遊勝勢,礪我前軍兵鋒。
十七日晨,李、傅與江防等營鼓勇渡江,進撲大通。官軍大炮大顯神通,將城上的旗幟打得稀巴爛。奇怪的是對手沒有還擊,等到炮彈放完,官軍呐喊著攻進城去,發現這是一座空城。但這仍是一場大捷,李、傅以收複縣城上報。在他們痛飲慶功酒時,靠近南岸的洛家潭發生戰事。本地團練發現一支船隊,浩蕩開進,抵近時才發覺事情不妙,趕忙施放抬槍。義軍先鋒許老大,率部八百突破岸防,趕鴨子一般痛擊團練。
不久遭遇敵方主力,統領李定明率軍防堵。官軍武器精良,占據有利地形,展開猛烈火力。許老大有“悍匪”之稱,他用不要命的衝鋒,兩次打開缺口,又被守軍封住。死拚傷亡極大,陣地上橫七豎八,布滿義軍屍體。許老大中槍後撤,吳祿貞火速頂上,將鋒頭推進至土壕前頭。他盯上幾棵大樹,李定明的統領旗幟豎在那裏。他派出一個小隊,在草木亂石間攀爬,同時打炮掩護。為了奪取生路,秦力山也攻上來了。在炮火連天中,小隊潛行至大樹周邊,向又高又胖的武將開槍。那人應聲而倒,引起一場混戰。盡管打倒的不是李定明,卻也讓義軍撕開一個口子,向西南方向的結嶺轉移。
轉戰五晝夜,義軍已成強弩之末。後來,又在木竹潭、戴家會打過遭遇戰,在南陵、銅陵等縣突襲哨卡,造成了恐慌。但在官方的報告中,自立軍已經淪為邀功的名頭了:李定明生擒首逆餘老五,奪取偽印、富有票、槍械、馬匹無數;李桂馨生擒朱炳榮等十人,奪回火藥、洋槍、元寶千件;傅永貴拿獲偽四王爺、偽七千歲、偽富有山主……
秦力山和吳祿貞躲過追擊,進入九華山,等待四路友軍蜂起,乘勝來援的好消息。幾天以後,從派往武衛軍的細作口中,得到中軍破滅的壞消息。至此真正絕望,二人遣散餘部,潛往江寧,密謀焚毀馬鞍山軍械局。事未達成,風聲泄露,江寧當局闔城大搜,秦、吳得到譚人傑的保護,做了漏網之魚。
遙遠的大通音信杳然,新堤、常德等地卻接連派人,討要兵餉,並且力促馬上舉事,不可久拖不決。唐才常催康、梁,沈藎來催他,唐才常被逼得焦頭爛額,還得安慰同樣焦躁的軍事顧問:箭在弦上,子彈上膛,我們馬上就向靶標射擊!甲斐靖這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行事風格表示不解。起兵哪有這麼幹的?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難道不是中國兵家的名言?老是這樣做處子,不怕被磨成老太婆嗎?
雖有萬般無奈,等米下鍋的困境無法打破,那七月二十的舉事,隻得再改為七月二十二。據此重新製訂計劃:二十二奪取漢陽兵工廠,率先獲得裝備軍需,一舉攻占漢陽、漢口;二十三渡江進攻武昌,拘禁護軍張彪以下將領,並將督撫納入掌握。當武漢三鎮行動之際,湘、鄂各州縣同時並舉,進而打通北上路線,做出營救皇上之勢。與甲斐靖對坐在鬥室中,反複磋磨用兵方略,唐才常有時陷入迷茫,有時感到別有興趣。那是針對地圖的。甲斐靖所持的武漢地圖,比上海印製的地圖詳盡清晰,而且更加準確。甲斐靖告訴他,甲午戰爭時期,日本間諜預先踏遍華北沿海地方,所畫地圖比北洋地圖精確多了。當時沒能染指長江,近來張之洞與日本加強合作,日本僑民的特長得到了發揮。當然,這要用之於友好,而非用之於戰爭。
唐才常心中駭然,竭力避開不愉快的聯想。不妙的事情還有很多,最切身的是裏巷流言,傳說省城將起反亂。不管行蹤如何隱秘,那麼多陌生人出入其間,啟人疑竇是免不了的。況且大勢敗壞,目中所見全是危險,人人都做好拔腿就跑的準備。擔任警衛的中軍管帶李生致,昨晚向總會報告,他去外麵巡邏時,看到附近有可疑的人員。李生致出身武秀才,跟李虎村是同鄉。唐才常沒有追問細節,他的心思不在這裏。說到根兒上,唐才常是讀書人,對於雞鳴狗盜之類勾當,他是鄙夷不屑的。
這天早上,唐才常從寶順裏前往李慎德堂,林圭昨夜住在那裏。走在街巷中,聽著周遭醒來的市聲,唐才常想著心事。身後響起急促的腳步聲,唐才常轉臉去看,瞄見個矮小的身影。唐才常回頭走路,那個小人兒超過了他,快步前行。就這樣走了一陣,那人突然轉身,跟他打個照麵。唐才常心中一驚,那張陌生的臉,帶出似曾相識的詞:小表弟!這是小表弟!
小表弟吃力地笑笑:“大表哥,我又見到你了。”
唐才常沉得住氣:“你怎麼來漢口了?是在跟蹤我嗎?”
小表弟低一下頭,好像誠心告罪:“先說上一回吧。我的確奉母命尋您投親,鄒秀才是我表親,順道送我到上海。他講了您好多不是,我也鬧不清真假。他教我探聽底細,說可以升官發財。你們趕我出來,倒讓我鬆一口氣。事後才知道,他要抓你向上海官府請功。”
說不清惱火還是憐憫,唐才常瞥著對方:“這一回怎麼說?”
小表弟打量四周,沒有發現人跡,急急訴說:“鄒秀才尋蹤來漢,已有三日。他說你今非昔比,要幹一票大的。我使了他的金錢,擺不脫這個人。大表哥,求您千萬小心。”
唐才常沉吟著道:“要幹大的?他說對了,大難臨頭,不管大人物還是小百姓,休想置身事外。唐才常光明正大,可以公之於眾,上至總督大人,我也照常來往,姓鄒的能奈我何!”
小表弟沒再多言,趴下磕了個頭,匆匆離去。唐才常睇視著他,忽一下心急火燎,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去跟林圭相見,果然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北京已破,聯軍入城,兩宮出京逃亡,相信將要臨幸西安!
張之洞也被此訊震驚了。如同罡風掃除迷霧,混沌的局勢至此廓清:京城陷落,剛毅等頑臣失去依恃,等待他們的唯有清算。兩宮出險,意味著社稷並未淪亡,李鴻章奉欽命與列強議和,代表的仍是慈禧太後。混戰多時,北方仍為正統所在,江南連偏安也做不到,所謂東南互保,注定做不到東南獨立。如此一來,唐才常那步活棋,已經成為一顆棄子,或者竟是一粒毒丸,處置不好,會連累老夫拉肚子的。
張之洞命令屬員,拜訪英國總領事館;並通過在上海的盛宣懷,探聽各國政府的意向。各方麵的反饋,印證了張之洞的判斷,而江寧方麵的急電,促使張之洞下定決心。大通失而複得,那是秦力山孤軍致敗;漢口腹心之患,豈容有所閃失!
張之洞親訪英國總領事傅磊斯,簡明扼要地說明來意,要求進英租界搜捕人犯。傅磊斯也很幹脆,當場簽發了搜捕證。他當然知道,上海租界的容記國會、漢口租界的唐記總會,都是在英方默許下開設的。唐才常籌辦自立會時,駐滬英國總領事,曾在一次酒會上信誓旦旦:“你可以在中國占一地方,作為根據地,如有需要,英國可派兵一萬予以支持。”這並非不講信用,而是如中國人所言“時移勢易”,不得不把可利用者棄之如敝屣。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東風便是明日到來,將在漢陽高舉義旗。在李慎德堂議事到天黑,唐才常和林圭、甲斐靖等人一起,回到寶順裏四號住宿。唐才常進院看到,傅慈祥和房東立在院中交談。房東名叫李大狗子,原在寶順洋行當小工,因勤快機靈,升工頭長再升買辦,集資甚富,置下此裏六棟洋房。傅慈祥告訴唐才常,因樓上西北屋頂失修,東家過來看看,準備補漏。補漏?唐才常對房東作揖,房東回揖後,抬頭瞅了唐才常一眼,便匆匆道別。
李大狗子走出樓院,回頭再看,四號樓聳立在夜色中,老翁一般孤獨。他歎了口氣,趕到另一街區的俄國洋行,找到容星橋。他把容星橋拉到隱蔽處,叫容星橋趕快化裝逃走。容星橋大驚失色,追問原因,李大狗子不露口風,隻催快走。容星橋要跟唐、林商量,李大狗子說,我把意思透過去了,走或不走,看天命吧。容星橋尋思無奈,跟著李大狗子來到李家,由李大狗子支派著,換上一身夥計衣服。李大狗子喚來幾名夥計,令他們跟容星橋結伴,押送貨物,星夜出發。
唐才常回屋便沉沉睡去,黑甜一夢,將到天明,霍然驚醒,發覺樓下有動靜,立起身看,但見下麵一片通明,大批官兵手持燈籠火把,將樓房圍得水泄不通。一名將領立在當院,指揮兵丁,即將登樓。房客全都驚醒,在樓道上麇集,看向唐才常。唐才常心中亂馬交槍,囂呼馳突,有一千個不甘心一萬個不服氣,唯餘一聲深長歎息:大事休矣!
突然響起爆喝:“殺下樓去呀!”
那是林圭,跟著吼叫的是武秀才李生致,還有甲裴靖。三人一起往下衝,跟上樓的官兵交上手。如同羊入狼群,林、甲相繼被擒。李生致身手了得,三拳兩腳打倒好幾個,飛奔上樓,叫道:“快走!”跑到樓道一端縱身一躍,跳到隔壁曬樓上,突圍而去。別人無此能耐,眼看那帶兵的率眾上樓,那人手持旗牌大令:“我乃巡防營都司陳士恒,奉兩湖總督部堂張鈞令,捉拿要犯!”
唐才常迎上前去:“事既泄露,不需捆綁,我跟你們前去。”
在寶順裏捕獲七八人,在李慎德堂捕獲十餘人,自立軍總部毀於一夜間。剩下的要事便是審案,首先在巡防營初審,證明身份、案由、是否認罪。因林圭和甲斐靖當場拒捕,在此用大刑伺候。唐才常聲明甲斐靖是日本人,問官不認這賬,什麼日本不日本,先打了這小子再說!在漢口走罷過場,於下午移送武昌臬司承審局。
武昌為總督駐地,湖北巡撫和布政使,也都駐在此地。唐才常是首犯,享受不綁之優待,提跪在承審局堂。他抬頭瞄了一眼,堂上坐著的那位,四十上下年紀,胖瘦適中的長弧臉膛,似乎在哪裏見過。堂上發聲詢問,唐才常報姓名籍貫後,接著發出一問:“我有一個請求,問堂上姓名身份。”庭丁齊聲喝叫,問官搖手止住,聲音顯得文靜:“我名鄭孝胥,祖籍福建,原在江蘇候補,現調湖北,是候補道。”
唐才常笑道:“失敬得很,你不是戊戌年皇上召見,特旨賞道員,派赴總理衙門行走嗎?”
鄭孝胥平靜點頭。唐才常立起身來:“既然如此,你是帝黨,與我同誌。我非造反,我要擁帝,保救皇上乃天下共識,你身受皇恩,將何以為報?”
鄭孝胥想了想,也站起身:“稱我帝黨,豈敢否認,現今仍是光緒年號嘛。我當避嫌,上報總督,換員審訊。”
換員尚未到位,梁啟超乘輪船到上海。他回國是來督戰的,武漢的敗報迎接他登陸,使他慌不擇路。他通過容閎、嚴複,請求英、美等國領事設法營救,並請井上雅二急電東京求救。日本政要犬養毅等七大老,緊急致電武昌,求為保全性命。張之洞置之不理,隻是默默打了一個回電腹稿:“公等蓋尚信其為憂國誌士,而不知其已自陷為叛國逆徒,律有明條,法難曲宥。”
終審大員蒞臨武昌,他是湖北巡撫於蔭霖。就在湖廣總督大堂上,提審重犯唐才常。唐才常移目觀望,但見堂宇宏敞,布設莊嚴,端坐的巡撫和肅立的將吏,形成一屋凝重的威壓,就像岩石一般觸手可及。在右排的將吏中間,唐才常認出一個知己,那是黃忠浩。那張鐵青的骨頭臉上,兩隻冷眼似有淚光,與唐才常的笑眼在空中相對,目光磕碰著,若有火花迸濺,化為流星散逝。
於蔭霖按律審問,唐才常依例作答,堂上未起波瀾。講述案由時,唐才常侃快說道:“事已大白,何須絮煩,請拿紙筆來,我寫給你看。”於蔭霖倒沒發怒,令人拿紙筆置於“案犯”前。唐才常奮筆疾書:“湖南丁酉拔貢唐才常,為救皇上複權,機事不密請死。”
供狀呈堂後,於蔭霖皺起眉問:“此為狡辯。皇上在位,何要你救?”
唐才常反口一擊:“皇上在位?戊戌年八月皇上失位,庚子年七月皇朝失都,北京而今淪敵國,兩宮終日在窮途。巡撫大人坐在堂上,看得見皇京城垣殘破、宮殿焚燒,可知道百姓妻離子散、屍骸滿地否?還有那張香濤製軍,他為何不來審我,他是愧對我嗎?他怕我這重犯審問他嗎?他是慈禧欽點的探花,一直是太後的寵臣,我不知他對皇上是否有忠心。當八國聯軍入侵時,他曾提兵勤王否?我是兩湖書院學生,由張香濤舉薦為拔貢,至死認他為恩師。可是他不認學生,不肯承認我以一匹夫,而有捐軀救國之誌、舍身拒敵之勇、濟世利民之術、革政變法之策。今天殺了我,明天他就能挽回國運嗎?”
審判至此有了結果。七月二十三淩晨,刑殺唐才常於武昌紫陽湖畔,同難者二十人。唐才常臨難詩雲:
七尺微軀酬故友,
淩雲浩氣頓荒丘。
楚師北定中原日,
炷藉天光祭此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