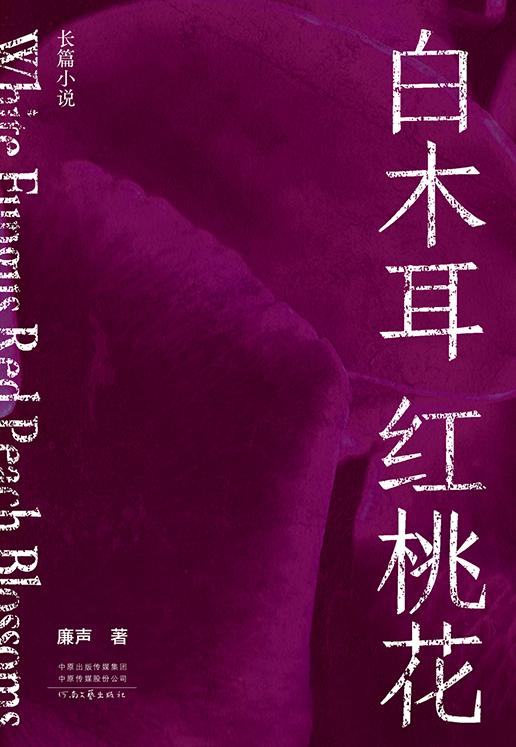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看到一個令人吃驚的場景
一下午,我腦子裏轉來轉去,總是紅記娘姨帶怨氣說的那句話。“這家夥”是姚隊長嗎?不是他,還會是誰?姚隊長真是勞改過的?莫非紅記娘姨對姚隊長有意見?為啥呢?要不,是對他老婆有怨氣……
下午拔秧時,誰都沒再提這個話頭,是姚隊長老婆在場的緣故?也可能是天氣太熱,太陽在頭頂上曬大半天了,秧田裏的水熱得燙腳,能硬撐著堅持拔秧就不錯了,誰還有閑心說別人家閑話?日頭偏西,陽光斜射在臉上,火辣辣的痛。隊長阿牛過來挑秧,招呼大家歇一會兒。眾人都十分勞累,拖一雙滯重的泥腳,費力走上土丘,一屁股坐在樹蔭下,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紅記娘姨也累壞了,像堆爛稻草一樣癱倒在地上,嘴裏哎喲哎喲地哼個不停。月娟媽還照原先那樣,靠坐在烏桕樹下,圓草帽拉下蓋著臉,一動不動,一聲不吭。
對拔秧早已很厭煩的大喜,悄悄對我說,哎,去不去那邊看看?那邊?什麼地方?我問。大喜用手指了指,那邊,就是副業隊種白木耳的地方呀,月娟和小琴她們在那幢土屋裏呢!
噢,原來就在離我們秧田很近的山坡下呢。我心癢起來,從地上爬起來,跟著大喜悄悄溜走了。
大喜熟門熟路,三繞兩繞,就到土屋前了。
門關著。裏麵一點聲響都沒有。
大喜臉上露出詭異的笑,低聲說,你猜,屋裏有沒有人?我說,不知道,一點聲音都沒有,恐怕沒有人。大喜又詭異地笑起來,說,他們肯定躲在裏麵,恐怕那個男人和她們兩個正在搞這種鬼名堂呢。大喜用兩隻手的手指頭做了一個很下流的手勢。我被嚇了一大跳,斥道,大喜你瞎講!我姐怎麼會……要麼是你阿姐!她們……怎麼會跟姚隊長那個……怎麼會?
大喜像他爸常貴那樣搖晃著長著卷毛的腦袋,一副不屑跟我爭的樣子,說,你不信拉倒。我爸講的,勞改過的會有好人?姓姚的家夥肯定沒安好心,把她們招進副業隊,就想把兩個姑娘搞上手,一個白木耳,一個黑木耳,好相貌,一個白一個黑,好味道。嘻嘻!我爸要我盯牢點,看到他們在搞鬼名堂,就趕去告訴他,把他們當場活捉。你敢不敢跟我去看,看他們搞沒搞鬼名堂?
我很反感大喜說這樣的話,大聲說,我不要聽,我不想看!心裏卻莫名地緊張起來,會不會真有那種事?萬一……
大喜不管我了,自顧自往一邊走去,繞過泥牆拐角,繞到後麵一側。我心裏很矛盾,走開幾步,又回過頭,還是跟過去了。
這才發覺,土屋後麵另有一幢低矮的土屋,僅半人多高,屋頂上蓋著稻草,那模樣有點怪,就像一幢屋子被土埋了半截。大喜像一隻壁虎,橫著身子,緊趴在泥牆上,兩隻手大大地張開,腦袋歪著,扒開屋頂的稻草往裏麵看著。我猶豫著走去,湊過去,像大喜那樣往裏看了看。
我突然一陣緊張,胸口怦怦亂跳!
土屋裏有人!有阿姐,還有月娟,再就是她們的姚隊長。三個人,兩個女的,一個男的,都站著,身子挨得很近,腦袋幾乎貼在一起,從上麵往下看,看清楚的是他們的後腦勺,看不清他們的麵孔。
三個人正在做一件奇怪的事。
一個形狀古怪的箱子,像商店的櫃台,上麵罩有玻璃麵板。隔著玻璃麵罩,我看見阿姐的兩隻手,還有月娟的手,伸進櫃箱裏,在擺弄著什麼。櫃裏還點著一盞燈,微暗的火,一閃一閃發光。她們兩人是坐著的,她們的一雙手,一雙白淨,一雙略黑,都在櫃箱裏。姚隊長站在她們身後,一邊跟她們說著話,一邊用手指點著,像是指揮她們,要這樣做,那樣做……雖然看不懂他們這是在做什麼,但絕不是大喜說的那種下流行為。我猜測,他們很可能是在做跟白木耳有關的事。這是正經在做生活呢!
我扭頭要駁斥大喜的胡說八道,發覺這家夥已經不見了。
晚上,我把下午隨大喜去那土屋偷看的事悄悄跟阿姐說了。她很生氣,罵了一句,狗日的大喜!狗眼看人低的小壞蛋!
我問,那個玻璃櫃箱,做什麼用的?阿姐說,那是接種箱,種白木耳最重要的一道步驟,就是接菌種,這是絕密技術,不能讓別人曉得的。所以,我們躲在那個半地下室接種。姚隊長隻相信我們兩個人,我和月娟。他講,種白木耳的絕密技術,殺頭都不能講出去的。我連連點頭,又問,我看到有盞燈,一亮一亮的,是什麼?阿姐說,那是酒精燈啊,消毒殺菌的,接種要在無菌狀態下進行。這個我在初中化學課學過。姚隊長對我講,你懂科學知識,很好,知識就是力量。月娟沒讀過中學,她不懂化學,不如我呢。
我肚裏憋不住,一串話脫口而出:他們那些人,為啥把你們兩個,你和月娟,叫作白木耳、黑木耳?大喜他爸常貴講,秧田裏也有人講,姚隊長喜歡你們,相貌好,味道好,還講勞改過的男人沒安好心,想對你們動壞腦筋……
阿姐懊惱了,麵孔漲得通紅,罵道:這些亂嚼舌頭的下作胚,講這種話要爛舌頭,爛嘴巴!姚隊長重用我和月娟,還不是為副業隊?種好白木耳,可以多賣鈔票,讓大家多分紅!你看到了,他做什麼壞事啦?沒有!他對我們沒有半點壞心思!我們都相信他,喜歡他!我們副業隊的姑娘,哪個不喜歡姚隊長?可我們心裏都清爽,嘴上不講的,隻有月娟,敢對我講,以後嫁人,就嫁姚隊長這樣有本事的男人。我很吃驚,啊?月娟介講,是想嫁給姚隊長?阿姐說,姑娘要是喜歡上一個男人,當然就想嫁給他啦。我們副業隊哪個姑娘沒介想過?不過,都曉得不可能。姚隊長他們是落難夫妻,蠻恩愛的。姚隊長最落魄的時候,他老婆一個人,獨守空門十年,吃多少苦?有男人想動壞腦筋,她就罵他們,用拳頭腳頭對付……哼,懶得跟你小鬼頭講,反正你也聽不懂。我不服氣,說你怎麼曉得我不懂?阿姐說,總歸你要記牢,那些人亂嚼舌頭的話,都不要相信!
天色暗下來時,忽然聽到門外有小孩子的哭叫聲。
我走出屋,看見門前兩個男孩,一個四五歲,另一個高出好多,在爭奪什麼東西,四隻手扯來扯去的。暮色暗淡,我認出大的那個是大喜,小的沒看清。大喜仗著身高力大,用力從小男孩手中奪過那東西。小男孩大哭起來,叫喊著,還給我,還給我。大喜得意地嬉笑著,一隻手高高舉著那東西,嘴裏說,我拿到手,就是我的了,嘻嘻,它歸我了。小男孩急了,撲上去抱著大喜的腿不放,還給我,是我的,是我家的,你不能拿走,還給我,快還給我……
我猶豫著,想不好要不要上前去阻止大喜欺負弱小的行為。大喜比我長得高,我怕打不過他。
大喜被小男孩抱著腿,想跑跑不動,用一隻手去掰那小孩的手,掰得太用力,把小孩的手弄痛了,哭得越發響越發凶,仍死抱著不肯放。忽然有人大步走來,一把奪過大喜手裏的東西。眼看被奪走戰利品,大喜憤怒地抬頭朝向那人,大聲叫喊,作啥搶我東西?還給我,東西是我的,還給我!
來人是紅記娘姨。她手上拿著東西,高高舉著,不給大喜,大聲問,到底是哪個的?小男孩帶著哭聲說,是我的,是我家的。給我,還給我吧。大喜嘴硬,還說是他的,偷偷用腳朝小男孩猛踢過去,差點把他踢倒。惹惱了紅記娘姨,把大喜用力推搡一把,讓他摔倒在地。大喜躺在地上耍賴,兩腳亂蹬,嘴裏罵罵咧咧,罵很難聽的話。紅記娘姨越發惱了,用腳頭重重踢他一下,恨聲說,你個小鬼頭,作啥像你爸常貴介一副死相?隻曉得欺負弱小,做壞事體!明明是搶人家東西,還有道理啦?再敢罵,信不信我把你踢到水溝裏喂烏龜王八!
大喜不敢再罵,一骨碌爬起來,跑掉了。
紅記娘姨朝那小男孩招招手,孝孝,來,這個還給你。
噢,我認出來了,小男孩是姚隊長的兒子。他站在那兒,怯怯地看著紅記娘姨,似乎對她還心存戒意,不敢伸手過來拿。紅記娘姨手中拿著的,是火柴盒子那麼大的東西,天色有點暗,看不清是個什麼。我把它拿過來,湊近看了看。東西有點沉,像是個鐵家夥,扁扁的,似黑非黑的外殼,認不出來是什麼。我發覺那東西外殼還刻著些外文字母,沒有中國字,我認不出。這是啥東西?我問紅記娘姨。紅記娘姨說,這是打火機,呃,是……外國打火機。
打火機?我頭一回聽說這個詞,也是頭一回見到這個東西,而且,還是外國……打火機?
紅記娘姨從我手裏拿過打火機,塞到孝孝手裏,說,你快回家去,把它藏好,以後再不要拿出來玩。聽到沒有?
孝孝手裏緊握著打火機,看一眼紅記娘姨,一扭頭,撒開腿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