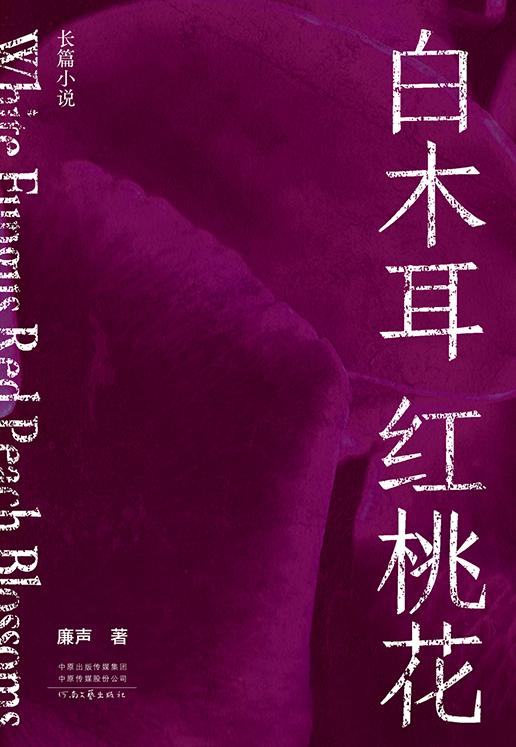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來了個黑黑的怪人叫老魯
過年前後,我們二隊有兩件大事。
年終分紅是大事。臘月廿三這天,預算方案出來了。勞動值比去年高很多,十個工分有六角六分。大隊副業隊賣白木耳賺了錢,所得利潤按人頭分給各小隊,我們二隊共二十三戶,八十一人,分得一千兩百多塊!我家掙工分最多的是阿姐。她在大隊副業隊,拿男人壯勞力一樣的工分,每月做滿三十天,總額超過爸了。分紅值高了,生產隊裏沒幾個倒掛戶,連月娟家都不欠債了。我家分到六十多塊錢,是現金!
分紅兌現這天,喝了酒的阿牛隊長滿臉紅光,把一筆筆現金送給各“找賬戶”,高聲說,大家把鈔票拿回去,買魚買肉買豆腐,做件新衣裳,開開心心過個年。有人說,阿牛,今年分紅高,大家開心,不曉得明年好不好,還能不能開心過年呢。阿牛說,放心,隻要老姚在大隊副業隊,就能用白木耳賺來鈔票,讓大家過好年。
那是我們家最開心最爽快的一次過年。養了大半年的豬,年前殺了,白肉賣掉,自家留一個豬頭,一個項圈,就是豬脖子,抹鹹鹽醃了,曬成臘肉慢慢吃,還有豬血豬肺豬大腸。這個年過得很豐盛!分紅得來的六十多塊錢,爸和阿姐商量後再做分配。三十塊給阿姐,買塊紅燈芯絨布,做件新罩衫。又買來半斤毛線,天藍色的,好看!阿姐說,要給自己打一件毛線背心。剩下的加上賣豬肉的錢,給家裏添置了一件重要的勞動工具:獨輪車。開年後頭一件農活,是把各家的豬欄糞起出來,送到大塢口生產隊的油菜麥田當追肥,我家的獨輪車初次上陣就大出風頭。隊裏人驚奇地發現,身單力薄的和順叔以往挑擔總是落人身後,如今推起幾百斤重的獨輪車噌噌往前。身強力壯的阿牛挑一擔一百七八十斤的畚箕擔,走在長長的黃胖嶺上,累得呼哧呼哧的,被和順叔獨輪車輕鬆超過!
隊裏另一件大事,起先我沒在意,後來想起來,這才是最要緊的事啊。
我們二隊多出兩個人。這兩個人都跟月娟家有關。
通往月娟家院子的水溝上那條長石板,忽然有個穿舊軍裝的陌生男人進進出出的。是誰呀?我想。這天他走進我家,麵帶笑容招呼我爸,和順叔,我來看你啦。他笑容親切,殷勤地遞給我爸一根香煙,然後,在板凳上坐落,和我爸聊了起來。
噢,他是常貴的弟弟,名叫常榮,前幾年出去當兵,剛從部隊退伍回來。看他相貌,哦,跟常貴有點像,個頭稍矮,頭發剪得很短,看不出是不是卷毛。常榮待人很有禮貌,麵帶微笑,連我這小孩子也笑嘻嘻打招呼,還送我一個子彈殼。呀,黃澄澄的子彈殼,太好啦!我對常榮頓時有了好感。
紅記娘姨在隔壁叫,阿聲,快過來幫我做事體。
我喜歡去紅記娘姨家玩,也樂意幫她做事。紅記娘姨老公在縣城上班,隻星期天回來住一天,大多時間就她一個人過日腳,一人進,一人出,有點冷清。紅記娘姨喜歡我,幾次開玩笑說,要我寄拜給她做幹兒子,讓我叫她媽,過年給壓歲錢。我叫不出口,她催我叫,害我麵孔漲得緋紅,她開心地大笑起來,拿東西給我吃。她家零食多,有麻餅、小桃酥、京棗這些糕點,夏季還有水果,杏子、梅子、李子、棗子,就是沒有桃子。
紅記娘姨家有棵桃樹,在屋子東側牆邊,春暖時開出滿樹桃花,有幾根枝丫爭相探出牆外,老遠就能看到一串串粉紅的花。桃花盛開時,紅記娘姨常站在樹下,仰起臉看桃花,麵帶微笑,一副癡呆呆的樣子。她還拿把剪刀,踮起腳,剪下幾枝含苞帶花的枝條,插在堂前一隻青花瓷瓶裏,在堂前做事,走過看一眼,再走過,又看一眼。
可我不喜歡她家桃樹,花雖開得好看,樹也長得好,高高大大的,結的桃子卻很小,核桃那麼點大,還不好吃,又硬又酸,沒人要吃。我對紅記娘姨說,能不能另外種棵桃樹,最好種水蜜桃樹,水蜜桃多甜,多好吃啊!好不好?她看我一眼說,我隻喜歡桃花,不吃桃子。
要過年了,幾戶人家湊了十幾斤黃豆,合夥做兩板豆腐。紅記娘姨家有做豆腐家生,又會這門手藝,就托她做豆腐。紅記娘姨叫我過去幫忙,拿小勺添豆子,她自己推磨,雙手緊握磨杆用力推,嘰咕一聲,石磨轉一圈,又嘰咕一聲,再轉一圈。石磨重,推起來有點吃力,紅記娘姨累得呼哧呼哧的。常榮走進門來,親熱地叫一聲,笑眯眯地搶過紅記娘姨手上的推手杠,用力地推起磨來。紅記娘姨蠻高興,端茶遞煙給常榮,她自己坦坦地坐在高凳上,用小勺添豆子。磨盤吱咯吱咯響,兩人高一聲低一聲地說話,紅記娘姨問個不歇,常榮耐心作答。
紅記娘姨問常榮,在部隊好不好。他說在部隊裏表現很好,評上“五好戰士”,入了黨,差點就提幹,穿上四個口袋的軍裝了,不知為啥沒提成,退伍回來,也不能安排工作,隻好回生產隊勞動。常榮情緒有些低落,說話時輕歎兩聲。紅記娘姨憤憤不平說,介優秀的青年人,沒留在部隊,回家背鋤頭挖田泥,不是浪費人才麼?又安慰常榮,別灰心,我幫你找比務農更好的行當。常榮感激不已,對紅記娘姨連說幾聲謝謝。
這天常榮哪裏都沒去,在紅記娘姨家幫著做豆腐。他幹活很起勁,嘴裏不停地哼著“日落西山紅霞飛”這支歌,時而又招呼我搭把手。做豆腐有好多道工序,豆子磨好,在紗布袋裏洗出漿水,濾過,下鍋燒開了,再舀起盛在桶裏,點鹵水,起花後撈起,裝進四方板匣內,收攏紗布,壓上硬木條,再壓石板,最後製成豆腐。夜深了,我犯困,回去睡了,常榮一直忙到半夜過,豆腐做好,搬起沉重的石板壓上才離開。紅記娘姨逢人就說,常榮是個好青年,好人才,浪費了太可惜。
沒多久,常榮在鎮裏有了一份工作,幫忙搞征兵,臨時性的,據說幹得好,有可能轉正。紅記娘姨去鎮政府,一屁股坐在鎮長黃和尚辦公室靠椅上,說,常榮在部隊表現好,是可用人才,人才不能埋沒。黃鎮長說,你講得對,人才要用起來。這樣,常榮就不用下田幹農活了。
我們二隊新來的另一個人,過了年後才知道。
正月裏,阿牛隊長和我爸出了趟遠門,去皖南,即我們習慣叫徽州的那邊,用分紅時預留的錢買回一頭騷牯牛。牛是農家寶,耕田少不了,二隊的社員們很關心,很好奇,都趕去牛棚看剛買來的牛。
真是一頭好牛,高大,健壯,雄赳赳,氣昂昂,哞聲洪亮,兩顆鵝蛋大的卵子緊貼後腚。有人說,花那麼多錢買來一頭好牛,可得好好照看,誰來管呢?阿牛說,有人,現成就有。問,哪個?阿牛說,老魯。讓老魯來管這隻騷牯牛。大家嘴裏噢噢幾聲,眼珠子轉轉,相互看看,表情怪異,都不說話。
我心想,老魯,哪個老魯?我們二隊有這個人嗎?
從阿牛身後一拐一拐走出一個男人,以前從沒見過,看不出多大年歲,個頭不高,相貌平平,短頭發,雜些白絲,一張皺皮疙瘩的麵孔,黑得有點嚇人,布滿橫七豎八的皺紋,像一隻漆黑的鐵鍋底下用菜刀胡亂劃過。他朝眾人一再地躬身致意,努力想弄出點笑容,漆黑的臉上那些皺紋古怪地扭動著。他的一雙手是直垂著的,兩隻腳努力靠攏,身子卻歪斜著,看上去有點滑稽。
紅記娘姨拉一下阿牛衣袖,低聲說,哎,你看他,這副歪七歪八的樣子,又是剛剛放回來,顧得牢這隻騷牯牛嗎?阿牛說,他自己講,這些年在那邊天天放牛放羊,內行得很。他一隻蹺腳,走路都不穩當,隊裏別樣活幹不了,不讓他看牛,還能作啥?紅記娘姨又問,他住哪裏?阿牛下巴努了一下,看到沒有?靠牛棚邊上搭個草披間,讓他先住著。
牛棚邊果然新搭起一間草披屋,僅半間屋大,看上去很簡陋,幾根毛竹撐起一副斜斜的屋架,上麵鋪些稻草,幾塊鬆木板釘合起來,當作房門。紅記娘姨嘖嘖兩聲,說,這種草披屋能住人嗎?阿牛說,先住下吧。我家裏拿來兩條長凳,幾塊木板,搭起一張床,還有一床舊棉被,老魯講,夠了夠了,能擋風擋雨就好,蠻好啦。紅記娘姨撇一撇嘴,好?好啥?像過去逃荒佬一樣。還有,吃呢?阿牛說,呃,我媽拿來幾個老南瓜。老魯講,有南瓜吃就夠了,蠻好。紅記娘姨譏笑著說,你那個媽,真當是個南瓜大媽,隻曉得吃南瓜!
紅記娘姨轉身要走,走兩步,呆了呆,又扭過頭來,對阿牛說,我有半袋米,拿來給他吧。光吃南瓜哪有力氣拉得動騷牯牛?噢,還有一條舊草席,反正不用,拿來給他墊床,再鋪點稻草。介冷的天,總不能讓他困在冰冷透風的木板上吧。她又招呼我,阿聲,幫我去拿東西。
我跟紅記娘姨到她家裏,等著她拎來一個米袋,找出一張舊草席,卷起讓我抱著。才要走,她又想起什麼,跟我說,你看到沒有?那個人作孽不?身上隻有一件脫殼破棉襖,裏麵是光背脊的。這幾天倒春寒,多少冷啊!我上樓把老徐一件舊夾襖尋出來,讓他穿在裏麵。她轉身要上樓,又說,阿聲你去屋外看看,那棵桃樹爆芽沒有?
我走到屋外,看一眼那棵桃樹,好像還是冬季裏那副死氣沉沉的樣子,走近了細看,發覺朝陽的那幾個枝條上,已綻出米粒大的花苞了呢。
我回屋跟紅記娘姨說,桃樹已經爆出花苞了。她點點頭說,我想也差不多了。已經過雨水節氣,天冷不了幾天,會慢慢暖和起來,等桃花開了,收了油菜麥,吃上麥餅,日腳就好過了。
那段時間,我經常往二隊牛棚那邊跑。
我對麵孔漆黑蹺一隻腳的老魯沒興趣,喜歡的是那頭威武雄壯的騷牯牛。來沒多久它就大大出名了。騷牯牛力大無比,犁田時走得飛快,四隻健壯的腳蹄把水踢得嘩嘩亂響,一天能犁好幾畝水田。還有它傲然超群的雄性氣勢,令周邊的大小母牛們豔羨不已,每每相遇,便朝它拋媚眼,哞叫兩聲。南門大隊其他小隊,三隊,五隊,六隊,還有北門大隊西門大隊,都有年輕母牛,隊長們看好我們二隊的騷牯牛,想借它下種生小牛,爭著把他們的母牛拉過來“相親”。那些日子裏,我們二隊的騷牯牛真是風光無限,風頭出盡。我們這些愛看熱鬧的男孩趕去看騷牯牛與母牛相會。騷牯牛雄心勃勃,來者不拒,一個衝鋒上前,昂頭挺胸,雙蹄高舉,陽具挺直,奮力跨上母牛後背,激情四射。我們為之激動不已,緊握拳頭,跳著雙腳,為騷牯牛的颯颯雄風大聲叫好。
隊長們拉母牛過來配種,按規矩要帶上雞蛋和老酒,是給騷牯牛的精力消耗作貼補的。雞蛋三五斤不等,老酒肯定有一壇,二隊當家人阿牛臉上笑眯眯,代騷牯牛收下禮品,讓老魯保管,囑他按時給騷牯牛喂補食,不能讓它虧了身子。我們喜歡看老魯給騷牯牛喂補食,灌雞蛋和黃酒。騷牯牛長得高大強壯,腦子卻笨,好東西不曉得自己吃,要靠人飼喂。老魯自製一件盛器,截了一節毛竹做筒子,有節的一頭鋸平,無節這頭削成斜角,磕幾個生雞蛋在竹筒裏,再倒進些老酒。他一手捏緊牛鼻上的繩頭,用力往上提,對牛喊叫,嘴巴張開,聽話,嘴巴張開!騷牯牛的嘴巴張開一點,他即將竹筒斜角一端插入它嘴角邊,用力一推送,竹筒裏的雞蛋與老酒便滑溜進牛嘴巴裏。如此幾次三番,騷牯牛吃進好多雞蛋和老酒,身體肯定更加強壯有力了。老魯幹這活熟手得很,蹺著一隻腳也能獨力完成。別人手法不對,兩三個壯勞力好幾雙手一起忙亂也不行,牛不喝水強按頭,有可能糟蹋雞蛋和老酒呢。
雞蛋和糯米釀的老酒,是很讓人嘴饞的好東西,給騷牯牛吃,會不會也誘使別的什麼人參與享受?那個人會是誰?懷疑目標似乎很明確,常跟騷牯牛在一起的,管著那兩樣好東西的,隻有一個人,老魯。據說有人自充密探,暗中查探獨住草披屋裏的老魯,觀其行蹤舉止,尤其夜深人靜四下無人時,提防著這個黑臉的看牛人,是否有與騷牯牛爭吃補品的舉動。
這是個敏感話題,我在家裏吃飯時偶爾提了一下,被爸一句話刹住了車:沒看到的事,別亂傳亂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