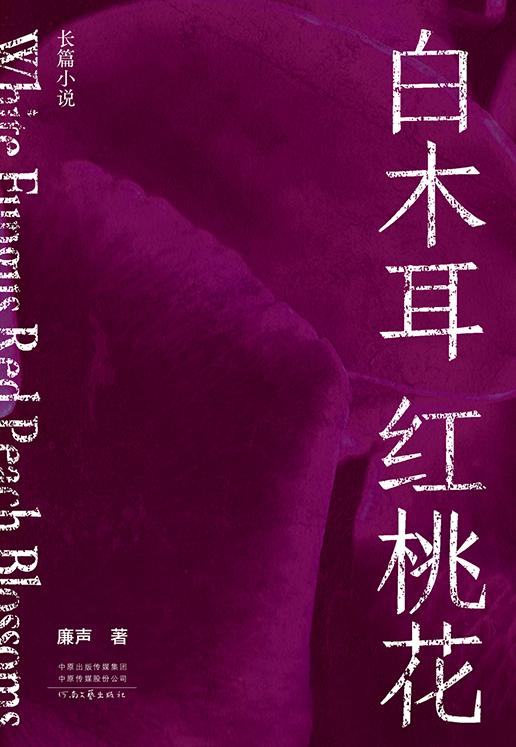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月娟被那男人打了一巴掌
那天姚隊長跟阿姐說一件要緊事,副業隊不光把白木耳賣給收購站,還要拿到街市上賣,擴大銷路。姚隊長決定派阿姐和月娟兩人上街賣白木耳。
出東山巷口,就是雨泉鎮唯一一條南北走向的大街,巷對麵是許步雲中醫診所,往北,挨著一爿豆腐店,再過去是三層樓的文化館,本鎮最高建築,跟它相對的是鎮上唯一的百貨商店。這裏是鎮中心位置,往南叫南門街,往北叫北門街。這裏也是約定俗成的菜市場,每天清早,街邊就擺起好些個菜攤,叫賣聲此起彼伏。拎著竹籃上街買菜的居民戶大媽大嫂,街邊擺攤賣菜的農業戶大叔大嬸,彼此熟識,為一把小青菜、一碗黴莧菜梗,他們討價還價,臉上帶笑,唾沫四濺;也有關係特別親密的,兩人四隻手,拿捏著一把菜,或兩條絲瓜,一個要送,一個不收,你推來我送去的,客氣得很。太陽升起兩三丈高,菜市場買菜的人少了,擺攤的人也挑了菜擔提了菜籃,漸漸散去。
這時候,阿姐和月娟來了,把賣白木耳的攤子擺了出來。
地上擺兩個搪瓷臉盆,盆裏盛滿清水,一朵朵白木耳,足有碗口那麼大,浸泡在清水裏,晶瑩如玉,看去像冰水裏堆著一捧捧白雪,頓感清涼爽快。副業隊兩個年輕姑娘守著臉盆,朝著大街吆喝。阿姐膽子大,直直地站在前麵,大聲喊叫:賣白木耳啦,大家看,多好的白木耳啊,營養豐富,價錢公道,大家快來買吧。月娟蹲在臉盆旁,臉不敢仰起,雖也跟著叫,聲音卻很輕,幾個字音在喉嚨口打轉,人家根本聽不清。
一些人聞聲圍攏來,很快圍成了一個圈。我擠在裏麵看熱鬧。
紅記娘姨也過來了,穿件印著粉紅桃花的短袖布衫,三隻手指頭捏著一小塊剛買來的豬肝。她笑嘻嘻對阿姐和月娟說,你們兩個怎麼把白木耳弄到街上賣啦?嘿嘿,這也是姚正山想出來的花樣吧?介貴的東西,哪個會買來吃?
也是,大家問問價錢,都說介貴,吃不起。說是這麼說,還是站著沒走。臉盆裏浸泡著大朵大朵的白木耳,的確漂亮,讓人覺得稀奇,站著看不夠,又蹲下細看,有人還用手去撈,被阿姐堅決阻止,說你不能撈它,弄破了,賣相不好。那人笑嘻嘻地說,弄破有啥關係,總歸要吃進肚裏的。
哎,你介講就不對了。開中醫診所的許步雲過來幫兩個姑娘的腔。他弓著老蝦般的腰背,眼珠子底下兩隻腫眼泡,趿著木拖鞋晃悠悠走來,說,賣相頂要緊了,把你麵孔抓破,相貌變難看,你也會懊惱,對不?嘿嘿,白木耳是難得的好東西,營養豐富,滋補身體,物有所值,女人吃了皮膚雪白粉嫩,老人吃了延年益壽。你們看月娟姑娘,皮膚又白又嫩,她在副業隊種白木耳,肯定吃過蠻多白木耳。對吧,月娟?
月娟皮膚確實白嫩,夾在一堆麵孔黝黑皮肉粗糙的人中間尤其顯眼。被人這麼說著,被許多隻眼珠子盯著,她羞怯起來,白淨的臉腮飛起紅暈,低下頭,沒說話,不說吃過白木耳,也不說沒吃過。
紅記娘姨一向喜歡跟許步雲抬杠,追問一句,許步雲,你講月娟皮膚白嫩,是吃了白木耳的緣故,那小琴呢?小琴也在副業隊種白木耳,她麵孔為啥黑不溜秋,一點都不白不嫩呢?
眾人看看阿姐,又看月娟,都笑了。有人說,真是呢,她們兩個賣白木耳的姑娘,一個白,一個黑,她們到底吃沒吃白木耳?為啥不一樣呢?還有人說,她們兩個,嘻嘻,一個是白木耳,一個是黑木耳。這麼一比一說,皮膚白嫩的月娟臉越發紅了,捂著臉轉過身去。阿姐卻惱了,瞪起眼睛說,哪個是黑木耳?我怎麼黑啦?我是健康色,勞動人民的本色!
眾人又笑起來了。紅記娘姨說,小琴,我講笑話的,你不要生氣。小琴你眼睛大,鼻梁挺,皮膚黑點啥要緊,這叫黑裏俏,蠻好看,鎮上沒幾個姑娘比得上你呢。這一說,阿姐才又露出笑臉。
紅記娘姨又問許步雲,哎,你講白木耳能延年益壽,你自己吃沒吃過?你許步雲吃了會長命百歲,會變成老不死嗎?哎,還有,我臉上這塊紅記,吃了白木耳,會不會褪掉?
許步雲嘿嘿笑起來,說你問我吃沒吃過?紅記我對你講,早先我白木耳不曉得吃過多少呢。白木耳真當對皮膚有好處,紅記你吃吃試試看,說不定臉上這塊紅記就褪掉了呢。紅記娘姨伸手摸一下左臉頰上那塊紅記,哼了一聲,許步雲你騙我吧,哪有介好的事體?
信不信由你。許步雲朝眾人說,你們曉得白木耳怎麼弄來吃的?請看。他變戲法一樣,一隻手忽然托起一隻小砂鍋,另一隻手揭開蓋子,呀,砂鍋裏是燉好的白木耳羹,稠稠黏黏的羹汁,冒著絲絲熱氣。他托著砂鍋朝眾人轉了一圈,大聲說,各位,看到沒有?這是我剛剛燉好的白木耳羹,賣相好吧?許步雲說著,大嘴巴還誇張地咂巴了幾下。有人看著眼饞,嘴裏說,弄點嘗嘗味道好不好?竟伸出兩個手指頭要往砂鍋裏戳。許步雲忙閃身,不肯讓人嘗他砂鍋裏的白木耳羹,叫著,哎呀呀,你作啥?你這兩隻手指頭邋遢不?
一個衣著鮮亮的婦女躥進來,快手快腳將徐步雲手上的砂鍋奪過去,嘻嘻笑道,老許,你講白木耳這樣好那樣好,能讓皮膚白嫩,我拿回去讓我家老黃吃吃看,看他那身皮肉會不會白起來。
這是鎮長黃和尚的老婆陶桂枝,衣裳花裏胡哨,燙一頭卷發,小鎮上算個時髦人物。許步雲沒留神被搶去手中砂鍋,有點懊惱,一看是陶桂枝,呃呃兩聲,說,好好,拿去給黃鎮長吃,蠻好。黃鎮長吃了,皮膚能白起來最好。
眾人一陣哄笑。紅記娘姨笑得最響,說,黃和尚那一身蠟黃蠟黃的皮肉要能白起來,豬八戒都會變天仙美女了!陶桂枝撇嘴說,我家老黃身上是黃是白,有你竺紅記啥事體?這一砂鍋好吃的,老黃肯定喜歡,他吃不完,我也會吃。白木耳是好東西,從前我外婆蠻會燉的,我小時候吃過,要不我皮膚也不會介白介嫩,嘻嘻。她從衣袋裏摸出個皮夾子,抽出一張大票,啪地拍在阿姐手上,小琴,這張十塊頭給你!給我稱白木耳,交給他。老許,聽到沒有?我不會白吃你的。你再好好燉上一鍋,自己留一半,剩一半給我!讓一下,我還有要緊事,哎,你讓一下……許步雲急叫起來:砂鍋,我燉白木耳要用砂鍋!
阿姐和月娟上街賣白木耳很順當,收回一堆鈔票硬幣,細數一下,有一百二十五塊三角二。阿姐一臉得意,說自己如何能說會道,會拉生意,還說連紅記娘姨都動心了,買了三塊錢白木耳,打算燉了吃,看看臉頰上那塊銅錢大的紅記能不能消褪一點。聽人家講,要是沒有那塊紅記,紅記娘姨年輕時要算雨泉鎮上最漂亮的姑娘呢。
阿姐對月娟略有不滿,說她膽小,縮在後麵,不敢大聲喊,不會招呼生意,意思是這個搭檔不太稱心。爸說,各人有各人長處,你們姚隊長用月娟也有道理。她心細,會算賬,是她收錢記數的吧?還有,月娟皮膚生得白,像她媽,賣白木耳,正好做招牌。阿姐不服氣,說我們副業隊的小芬,還有紅梅,皮膚也白,為啥不叫她們?爸想想,又說出個理由:小芬和紅梅沒有月娟好看。
爸說得有道理。月娟不光皮膚白淨,相貌也好,鼻子不高不低,嘴巴小小的,笑時嘴角兩側有小酒窩,眼睛不大,細長,單眼皮,俗稱丹鳳眼,眉毛細細彎彎,看去不笑也像笑。她家離我家很近,我早上去上學,有時會碰上月娟。她走路輕手輕腳的,沿著巷子一側牆邊低著頭走,卻能看見我,抬頭笑眯眯招呼我一下,阿聲讀書去啊?
東山巷有一百多米長,我家在巷頭,朝東走出巷尾,便是高高的東山。一條從東山灣淌出的小水溝,順東山巷而下,是各家淘米洗菜汰衣裳的水源。月娟家在水溝那側,從巷子的青石板路跨過水溝,有一條六尺長兩尺多寬的石板通道。不高的圍牆,圍起一個小院,進院有個半圓的拱門,兩扇對開的腰門。春夏季節,拱門和圍牆上爬滿濃綠的藤蔓,春夏時開滿了花,絲瓜花是金黃的,扁豆花是紫紅的,還有爬藤上牆的薔薇,五月初開出大片誘人的粉紅色小花。行人走東山巷路過那兒,望見月娟家院牆裏拱門和圍牆上盛開著紅的黃的鮮豔的花,還有那些飛舞的蝴蝶蜜蜂,心情都會好起來,臉上能溢出笑容。
小院裏一幢上好的磚瓦樓房,三間正屋,一側有披屋,前院有紅紅綠綠的花草,屋後還有小竹園,幾畦菜地,常年養一群雞,隔著牆院,看不見它們,但能聽到公雞的高亢啼唱,還有母雞生蛋後咯咯嗒咯咯嗒的歡叫聲,隔著圍牆和綠藤鮮花悠悠地飄蕩出來。這家女主人很少出門,總在家裏做各種家務,有時在門前水溝邊,低著頭蹲著洗衣裳,水聲嘩啦嘩啦,洗一大堆衣裳。
月娟家裏人多,她是阿姐,下麵好幾個弟弟,蘿卜頭一大串。很奇怪,弟弟們跟月娟一點不像,一個個黑不溜秋,細瘦個子,眼珠子大大的,一對招風耳,還有一頭亂蓬蓬打著卷的毛發,噢,對了,像他們的爸,劁豬佬常貴。
常貴是個古怪的男人,瘦高的個頭,長長的驢臉,一對往外突的大眼珠子,頭頂一撮稀疏的卷毛,整天騎一輛破自行車四處亂竄,車後架上帶個工具箱,裝劁豬閹雞的家什,還有網兜夾棍之類。破自行車咯吱咯吱響著,一雙小眼睛滴溜溜轉著,瞄著人家的豬圈或是雞窩。哪家母豬剛生下一窩小豬,常貴就像貓聞著腥味趕過去,手執小巧劁刀,三下五除二,利落地把幾隻小公豬屁股下的兩顆小肉蛋蛋給騸了。
我家母雞正月裏孵了一窩小雞,活下來七隻,近來四隻小公雞開始有雄性躁動的苗頭,爸說叫劁豬佬來把它們閹了,養線雞。常貴來了,架子擺得十足,先伸手要錢,閹一隻雞五分,兩角錢要到手,塞進口袋,又討茶水,又討煙抽。他在堂前一隻長板矮凳上坐著,嘴上叼著煙,一側凳上擺著茶水,一側擺放工具,右腳旁,四隻小公雞被套在網兜裏,已知難逃厄運,可憐兮兮地叫著。常貴歪著腦袋,看也不看,伸手抓出一隻小公雞,用兩根指頭寬的竹片夾棍、一截細繩把雞的兩隻腳綁住,擱在腳膝頭上。
我在一旁蹲著,看劁豬佬怎麼閹小公雞。
常貴手勢熟練,把小公雞一對翅膀交叉挾起,雞身直挺挺橫在膝上,露出肋處的嫩皮肉。他用短小的劁刀輕輕一劃,頓顯一道半寸長的創口,又用兩隻黃銅片扁鉗左右一拉,用竹弓彈緊,露出一個彈球大的孔洞。常貴用兩根被煙熏得蠟黃的手指拿捏著一個筷子般長的細柄小匙,用它探進孔洞撥拉幾下,又拿出一根細棍,上麵係一條細線圈,是馬尾,再探進孔洞裏,亂搗幾下,竟讓他弄出一顆如赤豆大的東西,一會兒,又弄出一個。我問,這是什麼呀?常貴笑道,小公雞卵子。你摸摸自己襠裏,是不是也有兩個,嘻嘻,要我把它閹掉嗎?
常貴利索地把四隻小公雞閹完,架著二郎腿,悠閑地點起一支煙,拿起小碗,把碗裏的六月霜茶一口一口慢慢喝完,起身拍拍屁股要走。我忽然看到,剛閹過的一隻黃毛雞不對勁,痛苦地倒在地上,翅膀撲騰撲騰扇動,兩隻腳亂蹬,身子也抽搐起來。我著急地叫起來,小黃毛要死啦,它要死啦!果然,它很快就不動彈,僵著了。小黃毛是這群小雞中我最喜歡的,我心疼得哭了。
花兩角錢閹四隻小公雞,死了一隻,怎麼辦?是退錢,還是賠償?爸皺著眉頭跟常貴商量,問怎麼辦。常貴搖晃著細脖子上長卷毛的腦袋,振振有詞地說,醫院給病人做手術也保不定要死,還講存活率呢,我給你家閹四隻小公雞,死一隻,百分之七十五存活率,蠻好啦。爸說,常貴,我們共小隊的,又住介近,算隔壁鄰居吧?小公雞讓你閹死了,一點不賠說不過去吧?好啦,雞不要你賠,最起碼死掉那隻雞的五分鈔票總要退給我吧?常貴拉長一張驢臉,兩顆眼珠突出,活像死羊眼,很委屈似的說,和順你曉不曉得?我做這個手藝,在外麵風風雨雨,多少辛苦,多少吃力,掙點小錢不容易,還要交小隊裏每天一塊鈔票,才記十個工分,值不了幾角,虧多少啊!我要吃飯,要養家小,對不對?
說來說去,爸還是說不過常貴那張嘴,隻好不響,拉倒了。
過兩天,紅記娘姨也把常貴叫來閹雞。
這回更慘,閹三隻小公雞,死了兩隻。紅記娘姨氣得大罵:你個死常貴,算啥狗屁劁豬佬?要不是看梅珍的麵子,才不會叫你來呢!你那把劁刀作啥弄的,小公雞都讓你閹死了,你賠我!敢不賠,我告到鎮長黃和尚那裏,把你這套騙人的家什都收去!常貴的長脖子一下縮攏。他答應賠,對紅記娘姨說,以後給你家劁豬閹雞都不收鈔票,好不好?這樣你最合算吧?
紅記娘姨要把兩隻閹死的小公雞扔掉,常貴說浪費可惜,求她把小公雞褪毛剖肚,剁小塊,弄點辣椒大蒜,炒了一碗給他做下酒菜。他坐在紅記娘姨家堂前八仙桌邊,拎出一個漆色斑駁的軍用水壺,壺裏裝著酒。他一邊喝酒,吃小雞肉,一邊跟紅記娘姨聊天。喝了酒,常貴麵孔漲紅起來,一張大嘴巴叭叭地說個不停,當中夾好多騷話。紅記娘姨罵常貴,你這隻騷狗,隻曉得喝貓尿,放騷屁。常貴誇張地長歎一聲,說,我這隻騷狗現在騷不成了,隻能在你紅記這裏放放騷屁過過嘴癮。紅記娘姨說,介想發騷,家裏現成有個天仙美女,隻管回去騷。常貴搖起頭來,唉唉,家裏那個天仙美女,不讓我碰她,想煞也發不了騷啦!紅記娘姨說,咦,作啥,你又欺負梅珍啦?常貴說,哎呀,我哪裏欺負她啦?怪我褲襠裏的東西,一弄就把她肚子弄大,生出介多兒子,吃口太重,養不起,嚇煞啦!
常貴歪著頭盯著紅記娘姨看,發出古怪的笑聲。紅記娘姨說,你盯我看作啥?男人的臉被酒燒得通紅,連脖子都紅了,說話有點大舌頭,紅記,你真是可惜,相貌介好,皮膚白嫩,要不是臉上有塊紅記,也算蠻漂亮的。你發發善心,讓我劁豬佬發一回騷吧。嘿嘿,反正你老公在縣城上班,星期天才回家,你底下那裏,嘿嘿,空著也是空著,說不定我能幫你留個種呢……說著話,忽然就伸出一隻手去拉紅記娘姨。
被滿嘴騷話的劁豬佬冷不防拉過去摟在懷裏,一隻手生硬地按在鼓鼓的胸乳上,紅記娘姨滿臉臊紅,一下惱了,急了,伸手啪地打常貴一巴掌,狠罵一句,你這隻騷狗,想發騷,尋隻老母豬發騷去!滾滾,你給我滾出去,再不要來我家!
紅記娘姨這一巴掌打得又脆又響,像一道閃電穿過薄薄的板壁,傳到我家這邊,清清楚楚的。之前兩人說的那些話,幾乎也一字不差地漏過了隔板。
爸在灶前燒菜做晚飯。我先是站在紅記娘姨家門口看閹雞,看常貴喝酒說騷話,又被叫回家,在灶下燒火。阿姐和月娟在桌前數錢算賬。這天她們賣白木耳又很順利,收回好些整錢毛票,還有一大堆硬幣。月娟在一個小本子上記著當天的流水賬,阿姐一塊兩塊一角五分數著錢。隔壁常貴對紅記娘姨說那些騷話,聲音那麼響,我們都聽得清清爽爽,月娟像是沒聽到似的,一直低著頭不作聲,可臉是繃著的,眉頭緊皺,而且一再地把錢賬弄錯。阿姐吃驚地叫起來,月娟你今天作啥,怎麼又算錯啦?
紅記娘姨那一記響聲脆亮的耳光,讓月娟再也忍不住了,眼淚一下湧出眼眶。我在灶下瞄去一眼,正好看到月娟那張淚水直流的麵孔。
忽然門外有人喊,小琴,小琴,接著又喊,月娟,月娟。聽聲音是副業隊的姚隊長。阿姐和月娟快步走出屋子。爸手上拿著鍋鏟,也走到門口,臉上帶著笑,朝門前站著的那人打招呼:姚隊長,到家裏坐坐,喝口水。姚隊長客氣地謝絕,說不坐了,跟她們講兩句話就走。
我也跟出去,想聽聽姚隊長跟阿姐她們說什麼,被爸拍了一下頭頸,說你出來作啥?管牢灶下的火,別把飯燒焦了。我隻好回轉,過一會兒忍不住又從灶下走出來,看到阿姐一臉怒氣回屋來,嘴裏大聲說,哼,沒見過這種人,真不講道理!可惡,太可惡了!
我肚裏嘀咕,她說的“這種人”是誰,總不會是她們的姚隊長吧?
當然不是。阿姐說的是常貴,月娟她爸,那個在隔壁紅記娘姨家喝酒說很多騷話頭頂上一撮卷毛的劁豬佬。
姚隊長站在我家門前,招呼阿姐、月娟出來,問她們當天賣白木耳的行情。偏偏這時被紅記娘姨摑了一耳光的常貴軟塌塌走出來,扭頭看到月娟,就搖搖晃晃走過來。不曉得觸到哪根神經,他晃悠著長卷毛的腦袋,滿臉通紅,蠻橫地打斷副業隊姚隊長和兩個女隊員的交談,衝月娟大聲斥罵:介夜了還不回家,在外麵跟男人搭七搭八,想作啥,發騷啦?
無端被斥罵,月娟委屈地哭了,嗚嗚哭出聲。常貴掄起一隻手朝月娟臉上打去,啪!重重地打在她臉上。冷不防挨了一巴掌,月娟被打蒙了,捂著臉問常貴,你……你作啥打我?常貴越發地憤怒了,一對死羊眼脹得血紅,罵道,你在外麵丟人麵孔,老子還管你不得啦?又把手高高掄起,要朝月娟臉上摑去,卻被人一把擋住,緊緊捏著,任他再怎麼掙紮,也不能掙脫掉。
緊緊捏牢常貴那隻手的,是姚隊長的手。
常貴兩腳亂跳,嘴裏咿咿呀呀,掙了好幾下,還是沒能掙掉,急得叫起來,姚正山,你放手!我打月娟,礙你啥事體?她在副業隊聽你的,在家她是我的囡,跟我吳常貴姓吳……你姓姚的管不著,你……你放開手……哎喲喲痛煞啦!
姚隊長看也不看常貴一眼,對月娟說,賬目的事我問小琴,你先回家去吧。月娟聽姚隊長的話,點點頭,抹一下眼,朝自家方向走去。
後來呢,後來怎麼樣?我急切地問阿姐。後來?後來人都走了。我不相信,說,可是那個人,沒跟你們姚隊長打起來嗎?阿姐輕蔑地笑笑,哼,那個劁豬佬,他敢跟姚隊長打架?他打得過人家嗎?我問,他沒罵你們姚隊長?阿姐說,他敢罵嗎?他像癩皮狗一樣向姚隊長討饒,哎喲喲姚正山算你力氣大、本事大,我弄不過你,服帖你,好不好?你放手,求你放手,這總好了吧?姚隊長這才把那隻打人的手放開,常貴,你酒喝多了,回家睡覺去吧。那個癩皮狗一句話沒有,搖搖晃晃,跌跌絆絆,回家去了。嘻嘻。
哎呀,真可惜,沒看到這精彩的場景!我心有不甘,對阿姐說,姚隊長那麼厲害,為啥不讓那個喝醉酒亂打人的家夥多吃點苦頭?想到最喜歡的那隻被常貴閹死的黃毛雞,還有那人死不肯退還五分錢的賴皮相,我越發憤憤然,頭腦中閃現出極暢快的畫麵:姚隊長像魯智深怒打鎮關西那樣,用力揮動拳頭把常貴那顆長卷毛的腦袋打成個爛西瓜,叫他趴在地上乞求饒命……
阿姐說,姚隊長不像常貴那種男人,不會亂動拳頭打人的。
我們姐弟倆說這件事時,爸一直沒出聲,這時說一句,好啦,人家的閑事少管,都過來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