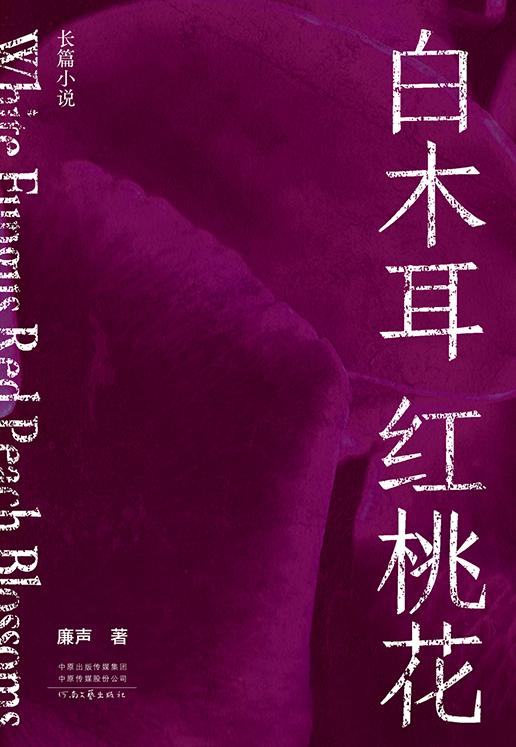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上闋
我跟著紅記娘姨
手拎著竹籃
在田塍上慢走
弓著身
尋找雜草叢裏隱藏著的鮮嫩綿青
阿姐和她們的隊長
許多年前,我還是小小少年,九歲,讀小學三年級。
一天,我家菜刀不見了。爸在生產隊勞動,中午趕回家做飯,找不到切菜的刀,隻好到隔壁紅記娘姨家借菜刀用。紅記娘姨輕笑兩聲,說玩菜刀這種事,你隻管問阿聲好啦。我放學一回家,就被爸埋怨一通,認定是我幹的好事,問我到底把菜刀放哪兒啦?我一下漲紅了臉。我是用菜刀幹過一些出格事,用它削木陀螺,將柴條截短做蛤蟆棍,把竹竿削細了紮風箏,還用菜刀削過鉛筆,斫鐵絲做彈弓,等等,但今天我碰都沒碰它!我很委屈,大聲而堅決地否認:不是我拿的,不是我!我沒拿菜刀!
阿姐連蹦帶跳地衝進門來,嘴裏還哼著歌,是誰幫咱們翻了身哎,是誰幫咱們得解放哎,臉紅撲撲的,很興奮的樣子。問起菜刀,她大聲說,菜刀是我拿的。作啥要拿菜刀?爸瞪起眼珠問。阿姐仰起頭,很大聲很驕傲地說,我考進大隊副業隊了!我們副業隊種白木耳要用菜刀!
十七歲的阿姐一心想進大隊副業隊,做夢都想這好事。她說,別人家女兒進副業隊,種白木耳,做一天生活,跟男人一樣拿十個工分,還有補貼費,說話時臉上滿是羨慕。哎呀,阿姐今天也進副業隊了,而且完全憑自己的本事考進去的!難怪這麼得意,一張微黑的圓臉泛出紅光,洋溢著得勝還朝的喜氣。
我問阿姐,你怎麼考進的?阿姐說,當然是考題目啦!有道很簡單的題目:水變成蒸汽,是化學變化還是物理變化,你知道嗎?我搖搖頭,說不曉得。當然是物理變化啦!阿姐得意地笑著,說,水的存在有三種形態:固態、液態、氣態。水變成蒸汽,水的化學成分不變,隻是物理形態變了。懂了嗎?我們三個人考副業隊,十二道題目,隻有我全部答對,滿分!其他兩個人錯很多,淘汰了!
接著,阿姐大聲宣布:我肚子餓了!
阿姐真是餓了,吃了滿滿兩大碗飯。爸幾次給她夾菜,臉上笑眯眯的,一點沒責備她的意思,再沒提菜刀的事。阿姐說,進大隊副業隊種白木耳要帶自家菜刀,這是規矩。他們要用磨得很鋒利的菜刀切木楔。我好奇地問,切什麼樣的木楔,做什麼用,白木耳怎麼種啊?阿姐輕蔑地說,你小鬼頭不懂的!我們副業隊種出來的白木耳,你知道有多白嗎?比新棉花還白!有多大朵嗎?碗那麼大!嘻嘻,沒見過吧?我懇求阿姐,你帶我去看看,看你們怎麼種的,好嗎?阿姐警覺地看我一眼,說,不行!我們姚隊長講,種白木耳的技術要保密,不能讓外人曉得,看看也不行!姚隊長講,誰泄密就開除誰!
以後阿姐每天一大早出門幹活,天擦黑了才回來,到家就嘩啦一聲躺倒在竹靠椅上,大聲喊,餓煞啦餓煞啦!又喊,吃力煞啦吃力煞啦!嘴上這麼說,臉上帶著笑意,眼裏放著光。爸巴結地盛了一碗飯,大聲喊我,阿聲,快端去給阿姐吃。家裏那隻蘆花母雞生下一個蛋,蒸一碗蛋羮,也端過去給阿姐吃。哼,明顯是哄她高興麼!
哄阿姐高興,因她肚裏有股憋了很久的怨氣。讀完初中,阿姐沒能接著上高中。她考了,沒錄取,不是成績不好,是爸那個曆史汙點,阻攔了阿姐繼續求學上進的腳步。阿姐痛苦不已,哭了好幾回。哭也沒用,還是沒能上高中。沒書可讀,隻能到生產隊勞動。阿姐細胳膊細腿,腰肢柔軟,是舞蹈隊隊長,在台上領頭跳藏族“洗衣舞”,這副細溜溜的腰身幹農活不行,挑擔,叫肩膀痛;拉豬糞,嫌豬屎臭;割稻,又喊腰酸背疼;下田拔秧,更怕螞蟥叮腳。二小隊那些男人婦女說阿姐是嬌小姐,拿她當笑話講,評工分,男人全勞力一天十分,婦女是半勞力,六分,阿姐才評三分!
阿姐讓我列一道算術題,四十的百分之三十,是多少?我想了想,列出一道算式,寫出答案:十二。阿姐歎口氣說,你曉得不,居民戶用糧票在糧店買最便宜的四等秈米,一角三分七一斤。我們二隊年終分紅隻有四角,我吃吃力力從早幹到晚,才掙一角二分,一斤四等秈米都買不到!你想想,當農民可憐不?幹活累得要死,還養不活自己,太寒心啦!
現在好啦,阿姐考進大隊副業隊,專種白木耳,幹的是技術活,輕鬆幹活,心情愉快,還拿得多,工分加補貼,比爸在生產隊勞動掙十個工分還多。阿姐在家裏的地位顯著提升,一下子揚眉吐氣,翻身農奴把歌唱了!
我好奇心重,想知道阿姐她們副業隊的事,想看她們拿自家的菜刀在副業隊切什麼樣的木楔,做什麼用呢?求了幾回,阿姐還是不答應,還說要保密。我很沮喪,仍心有不甘。人就是怪,沒見過的,很想知道,越不讓去不讓看,就越想去越想看。這天放學回家,隔壁紅記娘姨坐在門前剝毛豆。她朝我眨眨眼,招招手讓我過去,問我,想去副業隊看阿姐?我點點頭。紅記娘姨說,她們一幫姑娘在一起幹活,也沒啥好看的,真想去的話,我告訴你在哪裏。
東山巷尾端,一麵坡上有幾間不起眼的泥牆舊屋。還沒走近,就聽到有哢嚓哢嚓嘰嘰喳喳的聲響。我湊近那屋,看到裏麵有十好幾個人,都是年輕姑娘,穿藍花布衫的、紅格子罩衫的,紮辮子的、剪短發的,手上都紮著袖套,腰間係著圍裙,屁股穩坐在長條凳上。菜刀前端鑽個小洞,固定在凳前鐵架上,像把小鍘刀。姑娘們一手緊握菜刀柄,一手拿根細長的桑枝條,哢嚓哢嚓地鍘著,鍘下一小段一小段的顆粒,拉羊屎似的落在腳前一個筐裏。我猜這小顆粒就是阿姐說的木楔。姑娘們幹得很帶勁,哢嚓聲不斷,土屋裏像淌著一條清流湲湲的小溪。姑娘們一邊幹活,一邊還有說有笑的,看上去挺開心。
我沒敢進屋,從屋外一個窗口朝裏麵偷眼張望。哈,看到阿姐了!她在一個角落裏,抿著嘴巴不說話,很努力地在幹活,兩隻手臂起起伏伏,兩條紮著紅玻璃絲的辮子,不停地甩來甩去,看上去有點滑稽。她的額頭、臉頰,還有鼻尖上,綻出一顆顆細小清亮的汗珠,都來不及用手背或袖管擦一下。我分明看出,阿姐麵前那個筐裏的木楔比別人多一些呢!
忽然,說笑聲沒了,屋裏一下安靜下來,除了哢嚓哢嚓的鍘刀聲,再沒人嘰嘰喳喳說話,姑娘們收起臉上的笑顏,垂下眼眉,有點膽怯的樣子。不知什麼時候,有人走進屋裏。是個高個子男人,直直地站在屋子當中。我在窗外,隻能看到他的側身和半邊麵孔,短發,黑黑的臉,鼻梁挺直,眼睛不大,眉毛很濃,漆黑。咦,這人好像有點眼熟,從我家門前走過?
他起先沒說話,用目光掃了一圈,在跟前一個紅格子罩衫姑娘的筐裏抓一把,展開看了看,一下惱了,喉嚨很響地說,看看,你們看看,幹的什麼活兒?我講過要鍘多長?一厘米!一厘米多長,都讀過書,學過數學,一厘米,一米的百分之一,三分之一寸,多長?不會不知道吧?看你們鍘的,長長短短的,能用嗎?好多是廢料,浪費掉了!紅格子罩衫姑娘低聲嘟噥兩句,惹他更生氣了,把手中的東西重重地摔在地上,厲聲說,做生活三心二意,嘰嘰喳喳講啥,還有理了?不好好做就不要做了!走,馬上走!紅格子罩衫姑娘被罵哭了,淚珠子一顆顆滾落在臉頰上。我怕被那人看見,也要挨罵,趕緊溜走。
吃晚飯時,我得意地對阿姐說,去過你們做生活那裏,東山巷走出頭,山坡上有間土屋,是吧?阿姐很驚訝,咦,你去啦?你怎麼找到的?是紅記娘姨告訴你的吧?我反問,你怎麼知道是她告訴我的?阿姐說,旁邊有紅記娘姨的自留地,她過來摘菜,有時會過來看我們一眼。哎,你看到我啦?我說,對啊,看到了。你們那裏有十多個人。我還看見有個男人很凶地罵你們,穿紅格子罩衫那個被罵哭了。阿姐說,你聽到我們姚隊長罵小芬啦?哎,有沒有聽到姚隊長表揚我和月娟?姚隊長表揚我們兩個鍘得又多又好,你沒聽到嗎?我說,沒聽到。我有點害怕,趕緊跑開了。阿姐說我是膽小鬼,又得意地說,曉得不,姚隊長還讓我進耳房了呢!
耳房?我不明白,問阿姐,耳房是什麼地方?
阿姐說,就是種白木耳的房子啊。我也是頭一回進耳房。哎呀,你是沒看到,那些長在樹幹上的白木耳,一大朵一大朵的,就像盛開的潔白的雪蓮花,太漂亮,太美啦!我太喜歡它們啦!我說,姚隊長讓你進耳房做什麼呢?當然是采白木耳啦。阿姐說,采白木耳蠻有講究的,不能亂來,要用小竹刀,貼著根部慢慢地刮,要很小心,大朵白木耳不能弄破了。姚隊長讓月娟教我怎麼用竹刀,怎麼擺放白木耳,不能粗心大意。
我想,能把她們這些人鎮住的姚隊長,一定很厲害。
過兩天,我遇上他了。我是說,遇上姚隊長了。
上午第四節課的下課鐘聲一敲響,饑腸轆轆的我就急不可待地衝出教室,一路快跑,要趕回家去吃午飯。我家離學校最近,出校門,往左拐個彎,幾十步就到了,運氣好的話,我是說,碰巧家裏中飯已經做好,那我就是全校第一個吃上中飯的小學生。不管怎麼也算第一名啊!
癟塌塌的肚子催促我快跑,出校門,拐個彎,朝家門口飛奔,忽然看到我家門前有個高個子男人,直挺挺地站著,對麵是我阿姐。他們倆在說話,好像已經說完,或者,他們僅僅打了個招呼,我跑去時,阿姐已轉身進屋門,而那個男人,我認出是姚隊長,也扭身大步朝這邊走來。因為跑得急,我根本收不住腳,而姚隊長邁開大步走來也沒看到我。他個頭高出我一大截,目光掠過我亂蓬蓬的頭發,瞄向前方,而我像一隻受驚的野兔,猝然竄過來,差點撞上他胸口。他吃驚地看我一眼,看到一臉驚恐的我,一雙張皇不安的眼睛。
我以為肯定要紮紮實實地撞到姚隊長身上了,不料他一個側身,很靈巧地閃過我,幾乎沒停一下,甚至沒再看我一眼,當我是一塊討厭的攔路石頭,直挺挺地走過去了。
我愣在那兒,呆呆地看著姚隊長走過去。他一身與眾不同的衣著,淨白的襯衫,藏青色長褲,襯衫下擺係進褲腰裏,皮帶收得很緊,雙手勻稱地擺動,以標準的軍人行進姿勢,穩穩地大步往前走去。
一直記著那次跟姚隊長的對眼,記著他那雙熠熠發光的眼睛,他的白襯衫藍長褲,還有後背挺直的身影,直至他死後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