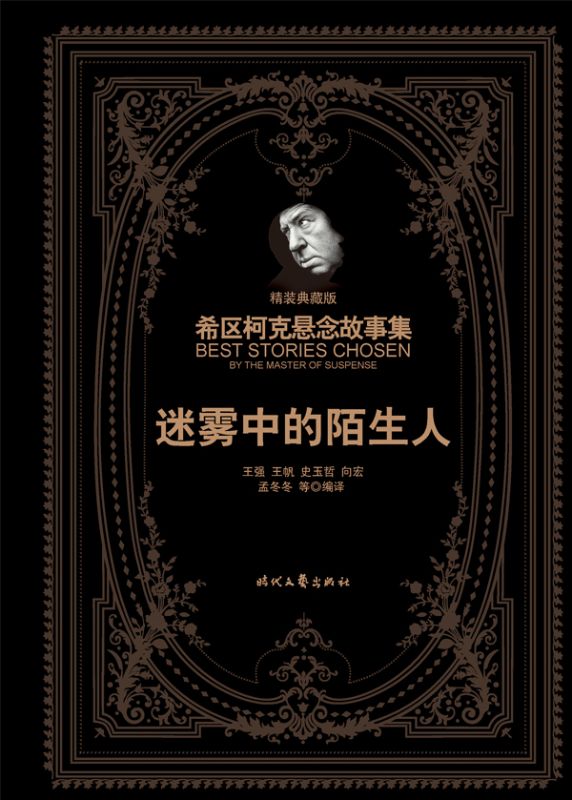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生日殺手
信寫得很簡潔,字體很大,寫在普通的白紙上,那種紙到處都能買到。信封上貼著一角三分的郵票,平信,哪裏都可以寄的。信封上寫著“紐約市,傑弗遜大廈十六號,詹姆士收”。信紙上沒有稱呼,隻有一行字:
“你活不過你的生日,3月10日。”
詹姆士身材高大,膀大腰圓,一頭濃密的紅發,連胡子也都是紅的,看起來像一個北歐海盜。他獨自一人坐在傑弗遜大廈的住所,正在吃早飯。那封信放在所有信件和當天報紙的最上麵。他的四周全是五顏六色的畫,那些畫使他名利雙收,有些畫已經完成,有些還沒有完工。他身邊的咖啡已經變冷了,讀信前點著的煙鬥擱在咖啡杯旁,也已經熄滅了。
他先拆開這封信,因為它沒有寄信人的地址,其他信件,他都知道是誰寄來的,如果在別的時候,他會認為這是一個惡作劇,但是,當他從信箱取出早報時,上麵的頭條新聞引起了他的注意:
“案,仍無進展。”
一年前,城裏出現了一位綽號“山姆之子”的凶手,專門殺害談情說愛的男女,搞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現在,又出現了這個“生日殺手”。
起初,“生日殺手”的受害人之間,似乎有些聯係。一位受害人是女法官,名叫金斯基;然後是一位助理檢察官,名叫路易;然後是安格爾,《新聞觀察》雜誌社跑社會新聞的記者;他們每個人都接到過和詹姆士一樣的信件,隻是生日不同而已。
每封信幾乎都是在生日前三天寄到的。金斯基法官沒有理睬那封信,在她漫長的法官生涯中,接到過許多恐嚇信,所以沒把那封信當真。她生日後幾小時,被槍殺在公寓大廈的電梯裏。沒有破案線索,沒有目擊者。
兩個月後,助理檢察官路易在生日前兩天,也接到恐嚇信,內容除了生日不同之外,和金斯基法官接到的完全一樣,經專家鑒定,筆跡出自同一個人之手。刑偵處的理查德警官,從這兩樁暗殺案中看出了一點可能的聯係:有人向法官和檢察官報複,報複他們的起訴和判刑。可是,是報複哪一件案子呢?路易檢察官在金斯基法官的法庭上,起訴了二十多件案子。
路易助理檢察官沒有等待刑偵處查出結果,便決定去國外度假。但是,在飛機起飛前二十分鐘,他被子彈射死在肯尼迪機場的洗手間裏。沒有線索,沒有目擊者。
三個月過去了,理查德警官沒有查出任何線索。接著,跑社會新聞的記者安格爾,在他生日前三天也接到恐嚇信。他立刻將信送到理查德警官那裏,同樣的筆跡,同樣的句子,隻有生日不同。這之間有什麼聯係嗎?安格爾采訪了路易起訴到金斯基法官那裏的十三個案子,這已經把案子的數目從二十減少到十三。
警方決定向安格爾提供保護,他同意了——但是,他已經約好了要去采訪一位證人。他和理查德警官的手下約好,一個小時以後,到“耶魯俱樂部”接他,但是,他們沒有接到他,他被槍殺在停車場的汽車裏。沒有線索,沒有目擊者。
理查德警官努力追查和金斯基法官、路易助理檢察官和記者安格爾有關的十三個案子,沒有發現任何線索。接著,又有第四個人遇害,這一下,理查德的整個假設都成問題了。
吳富是唐人街一家餐廳的老板,他被人殺死在餐廳和停車場之間的空地上,口袋裏有一封“生日殺手”的信。理查德絞盡腦汁,也無法把這位餐廳老板和另外三個人連在一起。吳富的親友確信,金斯基法官、路易助理檢察官和安格爾三人中,沒有一個人曾經去過吳富開的餐廳。吳富本人從沒任何犯罪行為。他也沒有批評過“生日殺手”,也從沒向別人提過凶手寄了恐嚇信給他。吳富死的那一天,剛好是他生日。
理查德不是一位普通的警察,他獲得過法學學位,學識淵博,致力於維護法律和秩序。他認為應該阻止犯罪,讓人民過上安寧的生活。詹姆士呢?他是一位藝術家,一生疾惡如仇,反對暴力。他繪畫的主題一直是反抗邪惡的暴力。他同情窮人和弱者。因為他們兩人的目的相似,所以理查德和詹姆士成了好朋友,經常在一起。
詹姆士打電話給理查德警官說:“今天早晨我接到了一封信,你也許會感興趣。”
“有人威脅你,讓你不要買警察球賽的門票?”
“是你的那種信。”詹姆士說。
“我的哪種信?”
“生日殺手。”
沉默了幾秒鐘後,理查德說:“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如果報紙上登的沒錯的話,信的內容和其他人接到的一樣。”詹姆士說,“當然,你必須親眼看看,才能確定字跡是否完全是一樣的。”
理查德的聲音變得冷冰冰的,與平常判若兩人。“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明天?後天?”
“這一點很有趣,”詹姆士說,“這封信上說:‘你活不過你的生日,3月10日。’那是明天,可是3月10日不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8月10日,離現在還有5個月呢。”
“你現在在哪兒?”
“在我的畫室,但我過一會兒就要出去,我正在克林畫廊舉辦個人畫展,如果你接到請帖的話,你就知道了。正式開幕的時間是今天上午11點,我必須早一點兒趕到那裏。克林畫廊在57街,第5大道的東邊。”
“我到那兒和你見麵,”理查德說,“把信帶來。”他又關心地叮囑說,“當心點兒,詹姆士,他大概是在名人錄上查到你的生日的,那上麵把你的生日印錯了。”
那是一個寒冷的3月天。
詹姆士告訴自己,人應該勇敢,但不能魯莽。有個心理不正常的人把他列入死亡名單,那個心理不正常的人已經下手殺害過四個人,而且沒有留下一點點蛛絲馬跡。
當他穿上褐色西服,準備去主持個人畫展的開幕典禮時,在心中把四個謀殺案思考了一遍。凶手總是在近距離下手,而且沒有證人:金斯基法官在電梯裏遇害,路易檢察官在機場的洗手間,安格爾在停車場的汽車裏,吳富在房屋後麵的黑暗裏。這位凶手在最後一分鐘時,是不是麵對受害人,讓他們知道為什麼他們要死?
凶手作案的過程中,沒有留下從屋頂襲擊的跡象,空曠的地方顯然是最安全的地方。這使詹姆士感到,他最大的危險可能是在公寓外麵的狹窄的走廊裏,很顯然,“生日殺手”不在人多的地方下手……四個案子中,沒有一個目擊證人。以前那個叫“山姆之子”的凶手,有不少人看見他逃離現場,還能描述凶手逃跑使用的汽車,但是這位“生日殺手”,沒有人見過,他選擇的時機很恰當,那個時刻,隻有他和被害人在現場。
詹姆士從五鬥櫃上麵的抽屜取出一把手槍,塞進他的大衣口袋,這把槍是有執照的。
該出發了。當他打開公寓門,走到走廊時,他全身緊張。他手裏拿著手槍,隨時準備射擊。陽光從走廊的盡頭照射進來,白天的這個時間,沒有陰暗的地方可以躲藏。
他走到走廊的盡頭,右拐有一道樓梯直通街麵。他拐過去,朝四周觀察,沒有人影。樓梯角有一個狹窄的通道,通往地下室的門。假如他直接走下樓的話,地下室可能會有人突然出來。他下了一半樓梯,然後轉身,向後退著走,麵朝地下室的入口處。
沒有人,什麼也沒有。
走到街頭,就好像從黑暗的地下隧道走進溫暖的陽光中。在大廈門口,進進出出的人們微笑著向他打招呼,他在這一帶很有名,大家都認識他。“生日殺手”顯然不會在這裏下手,因為這不符合他的作案方式。
大廈門口停著一輛出租車,但他沒有上。單獨和一位司機在汽車裏,誰知道那個司機是不是殺手呢?他覺得自己有點太神經質了,但是,殺手不留痕跡地殺了四個人,不能對此掉以輕心。混在人群中比較安全,詹姆士決定步行去克林畫廊。
理查德比他早到會場,他身材細長,溫文爾雅,不像一個警察。畫廊中早已擠滿了愛好繪畫的人,當高大的紅胡子畫家走進來時,人群中一陣騷動。這兒有一百位目擊者。
理查德的表情很嚴肅,他把一份畫廊準備的小冊子遞給詹姆士,裏麵有畫的編號,以及詹姆士的小傳。
“你的生日印錯了。”警官說。
小傳上這麼寫道:詹姆士,1948年3月10日生,康涅狄格州,湖景城。
詹姆士找到畫廊的老板。“克林,怎麼會出這樣的錯呢?”他問。
克林皺著眉頭瞧瞧那份小冊子,說:“詹姆士,這是從你自己寫的自傳上複印下來的。”
“我當然知道哪天是自己的生日。”
“原稿在我辦公室,我這就去取。”克林說完,走進裏麵的辦公室。
“你怎麼這麼晚才到,”理查德說,“我正為你擔心呢!”
“我步行來的,這樣好像安全些。”詹姆士說,從口袋裏掏出恐嚇信,遞給理查德。
理查德皺皺眉頭說:“他媽的,同樣的筆跡!看來真是同一個人。”
克林從辦公室回來,手裏拿著一張紙。“詹姆士,你就是這麼寫的。”他說。
詹姆士一看,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兒了。他是用圓珠筆匆匆忙忙寫下這日期的,結果剛下筆時,筆尖幹燥,把8月的“8”寫得像是“3”。
“問題不是很嚴重吧?”克林問。他是個天性開朗的人,長著一張滿月般的臉。詹姆士的個人畫展非常成功。“我們開幕才半小時,已經賣掉三幅畫了。有兩幅是在華盛頓畫的,畫的是那幾個叫‘馬沙林’的,把幾位人質押在三棟大樓的事;還有一幅在海濱走鋼絲的畫。今天早晨你起床後,你的財產又增加了一萬五千五百美元。”
“你是今天早晨把小冊子發出去的?”理查德問。
“對,我親手發的,”克林說,“不過,兩星期前,已經向有潛力的顧客寄出了好幾百份。”
他們在展廳中漫步,來到一幅題為“海濱賣藝者”的畫前,畫框上貼有“已售出”的紅條,突然,理查德的手猛地抓住詹姆士的手腕。
“天哪!”理查德叫道。
“怎麼了?”詹姆士問。
理查德用另一隻手指著畫。畫的背景是海濱,有許多彩色的遮陽傘,遊泳者在遠處衝浪,日光浴者戴著太陽鏡。前景有兩個男人在做雜技表演:一個人正在做倒立,雙臂張開,站在倒立者兩腳上的是第二個人,那人正咧著大嘴在笑。
“不可能!”理查德說。
“難度很大,不過,他們做到了。”詹姆士說。
“我不是說雜技,”理查德說,“我是指站在上麵的那個人——那個咧嘴笑的——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我是畫畫那天才見到他的。”
理查德放開詹姆士的手腕,臉上的肌肉在痙攣。
“他的名字叫米倫,”理查德冷冷地說,“他在時代廣場殺死了一位女警察,後來在獄中懸梁自盡。你不知道你畫的是誰?”
“不知道。他當時正好在海濱上。”
“你畫得非常像。”
“我有照相機一樣的眼睛。”詹姆士說。
理查德盯著他的朋友,“他被路易檢察官起訴,指控他犯有一級謀殺罪,陪審團判他有罪,金斯基法官判他終身監禁。他是個吸毒者,他向時代廣場的一位女士購買毒品,那位女士剛好是便衣警察,他開槍射死了她。審理那件案子時,輿論界大肆抨擊警察的辦案方法,安格爾寫了一篇文章,為警察辯護。”
“這麼說,他們三位都與這位米倫有關。”詹姆士說。
“而你又畫了他。”理查德說,“倒立的那個人是誰?”
詹姆士回憶了一下。“很難記住一張倒立的臉。”
“可是他並不是整天倒立著的啊,他站起來時是什麼樣的呢?”
“我不記得了。”詹姆士皺著眉頭說。
理查德找到克林,問他誰買了那幅畫。畫廊主人聳聳肩。“一位老人,他有點怪,因為他付了現金,並且要立刻帶走。我告訴他,畫必須留在這兒,一直到兩星期後畫展結束。他開始很不高興,但最後不得不同意了。”
“他沒有留下姓名?”
“沒有。不過我開了收據給他,讓他畫展結束後,拿著收據來取畫。”
“描繪一下他的長相。”
“年齡很大,看上去身體很不好,一頭厚厚的白發,不像是拿得出兩千五百美元買畫的人,不過,他是用現金買的。”
理查德轉向詹姆士。“這個生日殺手案子,總算找到了一點頭緒。”
“你知道什麼了?”
“米倫在監獄裏自殺——那天剛好是他的生日!”理查德說,“報紙刊登了此事。現在,有某個心理不正常的報複者,在別人生日時報複。我們散步去吧。”
半小時後,詹姆士來到一位叫斯通的年輕律師的辦公室。在乘出租車去那裏的路上,理查德向他解釋說,這位斯通曾經當過米倫的辯護律師,雖然最後官司輸了,他卻出了名。
斯通長得又黑又小,但顯得精力充沛,他不停地在椅子裏扭來扭去,同時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理查德以前和他談過,因為米倫和“生日殺手”的三位受害人有關聯。現在,他把詹姆士剛剛接到的恐嚇信交給斯通,還有一份畫廊的小冊子,裏麵有那幅《海濱賣藝者》畫的黑白照片。
“把你告訴過我的,再告訴詹姆士一遍。”理查德說。
斯通吐出一口煙,說:“許多人認為,我為米倫辯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其實,是有人付錢聘請我為他辯護的。”
“米倫請的?”理查德問,顯然,他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誰付的錢,”斯通說,“反正在訴訟的那幾個月裏,我每兩個星期送一次賬單給米倫。每次送出賬單後兩天,我就會收到寄來的錢,而且是現金,一千美元,或多一點,每次付的都是全新的鈔票。信封裏沒有信,沒有任何東西。錢是用平信寄來的,比普通信多貼一點郵票。”
“那些信封你還留著嗎?”理查德問。
斯通咧嘴一笑。“因為你打電話說要來,所以我留著。”說著,打開抽屜,拿出一個信封。理查德把信封放到詹姆士收到的信旁。
“一樣的筆跡,”詹姆士說,眼睛眯了起來,“‘生日殺手’為米倫付律師費?”
“看來是這樣。”理查德說。
“總共大約付了三萬美元。”斯通說。
“斯通先生,你怕不怕收到恐嚇信?”詹姆士問。
律師聳聳肩。“我為什麼要怕呢?我試圖救米倫,他被判刑,應該由路易檢察官負責。詹姆士先生,你怎麼得罪他了?”
“好像是因為我畫了他的像。”詹姆士說。
“我認為不是這樣的,”理查德說,“你也畫了另一個人——倒立的那個人。”
“但我沒有畫他的臉。”詹姆士說。
“不過你可以憑記憶回想起那個人的臉,我希望你最好想起來。”理查德說,“越快越好,他認為你的生日是明天。”
詹姆士本來準備留在畫廊,吸引那些來參觀的人,但是現在他改變了主意,回到傑弗遜大廈的畫室。那天在海濱,他曾畫了好幾十張素描,這些素描也許可以使他想起一些當時的情景。
理查德堅持要派警察保護他,但是詹姆士不願意。他很久以前就認定,一旦麵對死亡,他願意一個人來對付,他並不怕死。他鎖上畫室的門,扣上防盜鏈,檢查了臥室和壁櫥,一切都很正常。
他在資料櫃裏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在海濱那天他用的素描本,那差不多是兩年前的事了。他在畫架前的椅子上坐下來,掏出口袋裏的手槍,放在旁邊的桌子上,以備萬一。
那些素描沒有給他提供什麼線索。那天陽光燦爛,許多人在做日光浴,少女差不多全裸,男人的皮膚曬成古銅色,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什麼了。
這一天真是夠緊張的,詹姆士發覺自己筋疲力盡,他坐在搖椅上睡著了。
這一覺一定睡得很長,因為當他醒來時,房間裏漆黑一片,隻有街燈照在窗戶上。詹姆士看了一眼手表,差不多是半夜11點了,他睡了將近7個小時。
一個古怪的想法出現在他的腦海裏,如果明天是他的生日,那麼還有一小時災難就要來臨了。
他打開電燈,到屋角的一個櫃子前,倒了一杯加冰塊的酒。他想整理一下思路,他覺得自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那個開中國餐館的吳富和這個謀殺案仍然沒有關係。
突然,他的大腦裏就像電光閃了一下,看到了海濱上的雜技表演,他看見米倫終於跳下來,落到沙灘上,放聲大笑。接著,那個倒立的人翻了個跟頭站了起來,那人也在微笑。那是個東方人!
詹姆士從桌子上拿起手槍,放進外套口袋。現在,他是獵人,不是獵物。他走到大廈外麵,看到有一輛出租車停在那裏。
“去唐人街的‘中國宮殿’。”詹姆士對司機說。
“那一帶現在都關門了。”司機說。
“你就照我說的開吧。”
出租車把他帶到城中心,停在“中國宮殿”的外麵。詹姆士付了車費向門口走去。有些顧客正從店裏走出來,詹姆士走到門口,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攔住了他的路。
詹姆士覺得心怦怦亂跳。現在,他記起了那張臉,記得很清楚,那張臉正是倒立者。
“對不起,先生,我們已經關門了。”那個中國人說。
“我不是來吃飯的,我想和你談談。”詹姆士說。
“我們正在關門,先生。”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吳烈,是這個店的老板。”
“我想你應該認識我,我叫詹姆士。”
吳烈的頭上冒了汗。
“如果你不介意服務員打掃衛生的話,請裏麵坐。”吳烈說。
店裏隻剩下一張桌子上還有四個客人,他們正結賬要離開。吳烈領詹姆士來到角落處的一張桌子。“對不起,我得派個人站在門邊送客。”他走過去,和一個服務員談了一會兒,彬彬有禮地向正要離開的客人鞠躬,然後走回詹姆士那邊,在他的對麵坐下來,“詹姆士先生,有什麼事嗎?”
“我等你都等煩了。”詹姆士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你心裏清楚得很,”詹姆士說,“我告訴你,吳先生,在我的外套口袋裏有一支手槍,它正對著你的肚子,如果你敢輕舉妄動的話,就叫你肚皮開花。我收到你的信了,我知道你就是‘生日殺手’。”
吳烈舐舐他薄薄的嘴唇。“詹姆士先生,看看你的周圍,你可以看出,你沒有機會離開這裏了。”
那些中國服務員已經停止了清掃工作,堵住了每一個出口。
“這麼說我們兩個人都要死了。”詹姆士平靜地說,“有個笑話得告訴你,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那也沒有關係,”吳烈說,“我可不能再等了,你在克林畫廊開畫展,是不是有人告訴你,你畫的那個人是米倫?”
“理查德警官告訴我的。”
“一個聰明人,可惜還不夠聰明。”
“是你買下了那張畫?”
“我派人去買的,希望在你回憶起來之前,把它從畫廊弄走。”
詹姆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在你我死前,我想知道原因。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為什麼連你父親也要殺?吳富是你父親,對嗎?”
吳烈斜靠在椅背上,兩眼看著頭上的吊燈。“米倫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說。
“所以,你就著手實施這個喪失理智的報仇計劃。你殺害檢察官、法官和那位記者的動機我可以理解,可是為什麼連你父親也下手?他和這個案子沒有關聯。”
吳烈開始輕輕地在椅上來回搖動。“讓我告訴你,”他說,“隻說這一次,因為沒有人知道詳情。”
詹姆士點點頭,他的手指扣住手槍的扳機。一個輕舉妄動,吳烈的故事就永遠無法講下去。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他有所舉動的話,他也永遠無法聽故事了。那些中國服務員似乎遠遠地把桌子圍成一圈,不過他們沒有掩飾一件事實,那就是說,他們兩個人落在陷阱中間。
“越南——那是政治家的戰爭,也是當權派的戰爭。”吳烈說,“米倫和我在越南認識。你或許會問,一個中國人加入美軍,在越南做什麼?”他苦笑著說,“告訴你,我是美國人,出生在摩托街這兒,在這個城市讀書,從哥倫比亞大學機械係畢業。你知道,這是一個隻講機會的國度,一位中國機械師唯一的工作,隻能在他父親的餐廳賣雜碎給愛吃中國菜的美國人!但是,軍方接納了我,他們不是因為我是機械師才接納我,而是我講的語言,在越南可以派上用場。”
吳烈的痛苦敘述,讓詹姆士動了一點同情心。他繼續說:“我在西貢遇見米倫,那時我們兩人都在度假。當兵的在休假期間,不是酒就是女人,還有好多大兵吸毒。米倫是個敏感而熱情的人。他看見許多老年人、婦女和孩子被瘋狂地殺死,他看見農作物和森林被摧毀,他看見沒有軍事價值的偏遠村莊被夷為平地;於是用吸毒來忘卻他所親眼目睹的一切。他很想戒,但上了癮,戒不掉。我試著幫助他。我憎恨毒品對人類的毒害,尤其是對米倫。當他毒癮發作,經受痛苦煎熬時,我陪伴著他,有時候我以為他戰勝了毒品。”
“大兵們在哪兒弄到毒品的?”詹姆士問。
“黑市買賣,經營這種生意的還是肩膀上有金色杠杠的,他們因此發大財。世界到處都一樣,弱肉強食。嗯,在一次空襲中,米倫和我救了一些高級軍官。我們兩人一起受傷,一起就醫,然後一起光榮退伍。
“回到家,我有工作——在這兒賣雜碎。米倫則找不到工作,他仍然在和毒癮苦戰。我把空閑時間都花在幫助他上。一般人認為,一個男人愛另一個男人是邪惡,或者是病態,但是我愛他。我願意付出一切來幫助他解除痛苦——毒癮的痛苦。我們在空閑時間盡量遠離毒品,就像那天你看見的那樣,我們到海濱消磨時間。有一天,我父親派我到舊金山做生意,我拒絕了,因為我知道,米倫會毒癮發作。
“可是,我父親一定要我去,如果我丟了這份工作,就無法幫助米倫了,所以我不得不聽父親的話,到舊金山去。我們約好,每天通一次電話。但是,第二天,他沒有接電話,我知道他出事了!”
吳烈一拳砸在桌子上。“我不得不在舊金山多待了幾天,米倫一直沒有再接電話。等我回來時,一切都完了。他殺死了一位偽裝販毒的女警察。”吳烈痛苦地扭動著身體,“詹姆士先生,在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就是這麼辦事的。警察一發現他們吸毒,就把他們投入監獄。”
“吳烈,他不僅販毒,他還殺死了一位女警察。”詹姆士說。
“那是他被發現後才殺了她!我聽說有一位叫斯通的律師很有才華,所以鼓勵米倫聘請他,斯通律師認為有機會救米倫。”
“你就是付律師費的人?”
“是的,斯通律師在法庭的滔滔雄辯很有力。米倫是個病人,警方利用他的病,驅使他殺人,那種事,他從沒有做過。斯通律師指出,米倫是個需要救助的人,不是應該懲罰的凶手。檢察官不以為然,法官也判他有罪——而米倫,可憐的米倫,撕床單做成繩子,在他生日的那天自盡了!這些沒有理解之心,沒有同情心的人殺死了他。”
“所以,你就一個接一個地殺掉他們?”
“是的,一個接一個。”
“可是你父親呢?”
吳烈舐舐嘴唇。“他逼迫我到舊金山去,假如我沒有離開紐約的話,我可以阻止發生在米倫身上的事,我會陪伴著他,幫助他熬過毒癮發作的痛苦。”
詹姆士沒有說話。
吳烈冷笑道:“事情就是這樣。現在,詹姆士先生,假如你殺了我,你永遠無法活著離開這裏;假如你沒有殺死我——你也無法活著離開這裏。”
房間裏靜悄悄的,靜得詹姆士覺得都可以聽到廚房水龍頭的滴水聲。接著是一陣叫聲,很多人從一扇門外衝進來。圍成一圈的服務員被衝散,而且有一聲槍響。
詹姆士對麵的吳烈突然站起來,像變魔術一樣,從袖口拿出一把刀。他向詹姆士撲過去。畫家躲閃了一下,同時開了槍,他是對著吳烈的膝蓋開的,而不是胃部。吳烈尖叫一聲,倒在桌子上。
“你這該死的傻瓜!”理查德說。他站在詹姆士的身邊,詹姆士躺倒在地板上。“你為什麼不讓我們來處理?”
詹姆士想放聲大笑,但忍住了,同時站了起來,問理查德說:“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我接到一份米倫服役的報告,他和吳烈一起受勳,是這點把事情湊到一塊了。我花了幾個小時才使法官簽了一份搜查證,警察辦事得依照法律條文。我一直想找到你,找不到,我就明白,你可能記起那個倒蜻蜓者的麵孔,自己去扮演擒賊的角色了。”
詹姆士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他問:“你想,一個男人會在這個餐廳喝杯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