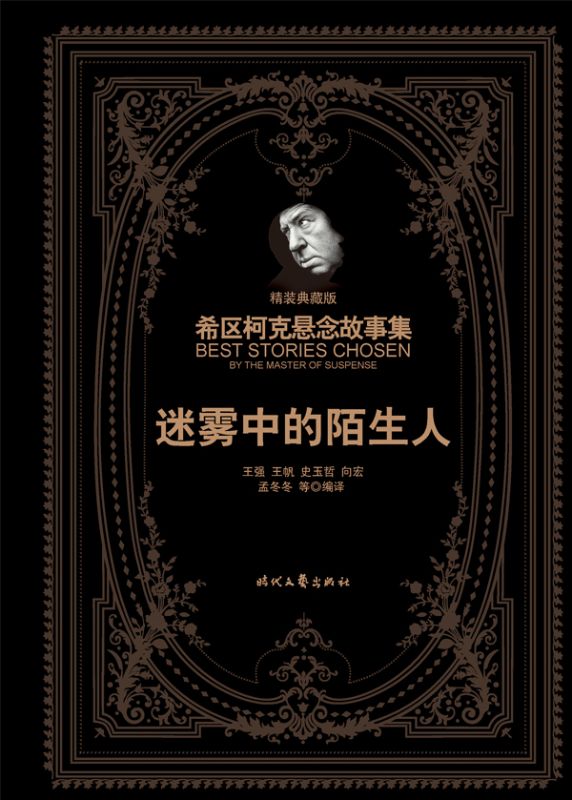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死亡花朵
開學那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珍妮第一次告訴我夢見花的事。珍妮是我的堂妹。那天我們經過藥房隔壁的花店時,她陰沉沉地說:“我們又要接到親戚死亡的消息了。”
“你為什麼這麼說呢?”
“昨晚我又夢見花了,我每次夢見花,我們就會有親戚去世。”
“這可能是巧合吧。”我說。
“過去幾年來一直這樣,非常靈驗。”
第二天,舊金山來電報,說祖母去世。
六個月後,我父親心臟病去世,珍妮告訴我,前一天晚上,她又夢見了花。
父親過早地去世,使得我隻好去輪船上工作。我母親身體一直不好,我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接管父親的油漆批發生意。我喜歡的是收音機,如果父親還活著,我會上大學,學習機電專業。我把父親的生意全部賣掉,憑著對無線電的一些知識,獲得了一張報務員的執照,到輪船上當報務員。薪水一半留給母親,一半留著自己用,並且積蓄了一些,準備做大學的學費。
在家休息的時候,我時常和珍妮見麵,因為她家離我家隻隔著幾條街。工作後的一段時間,查理叔叔、萊利姑媽和朱利堂嫂相繼去世,我恰巧都在家休息。每次有親人去世,珍妮都告訴我她夢見了花。祖父和堂弟去世時,我在海上,但是珍妮在信中告訴我,每次接到噩耗前,她都夢見了花。
這件事,她隻悄悄告訴了我一個人,因為我們像親兄妹一樣,並且我們都是家裏唯一的孩子。她不願把夢見花這事告訴別人或其他親戚,生怕一旦她做了夢,就會引起親戚們的焦慮,尤其是碰巧有人生病的時候。這件事我隻向一位牧師提起過。他搭我們的船去巴拿馬,在一次聊天中,我問他:“你認為我堂妹的夢有什麼意義嗎?”
他年事已高,身材魁偉,留著一把褐色的胡子。他懷疑地搖搖頭。
“我看不出你堂妹的夢有什麼意義,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那些夢的起源也許很邪惡。魔鬼是無處不在的,隻要我們不讓夢來影響我們,不迷信它們,它們就不會傷害我們。”
我把牧師的話告訴了珍妮,她說:“每次做了那種夢,我心裏就很煩,並且會等著看這回是誰。我不由自主地會受到影響。”
“你相信夢,時間長了,就成了迷信了。”
“可是,那種夢很靈驗,我忍不住會相信它。我覺得這對我並沒有什麼害處。”
“我也覺得沒什麼害處。”我說。雖然如此,她的夢還是讓我覺得很不安,我希望她以後別再做那種夢了。
大約一年後,珍妮和鮑比結了婚,他們乘船去度蜜月。他們是在公司查賬時認識的,珍妮當天就邀請鮑比一起去吃晚飯,兩人交往了一年後就結婚了。他們決定乘船度蜜月,這是因為珍妮想和我在一起,那時我已經是船上的報務主任了,專門跑百慕大等航線。
起航時,我們船上客滿,共有旅客一百五十名左右。珍妮和鮑比不像別的新婚夫妻那樣形影不離,他們喜歡和船上的旅客一起玩。鮑比會玩雜技,很喜歡露一手,在第一天晚上的業餘人員表演中就得了頭等獎;珍妮則在橋牌比賽中得了第二名。
他們在船上玩得很開心,全船的旅客都很喜歡他們倆。航程過半時,上來了一群從委內瑞拉油田回紐約的石油工人。他們很有錢,每天晚上都打撲克玩。他們和鮑比一拍即合,因為鮑比是個狂熱的撲克牌迷。
珍妮通常在雞尾酒廳玩橋牌,午夜前結束。但是在吸煙室玩的撲克牌則不然,有時候玩到淩晨。有一次,鮑比淩晨2點才回到船艙,他說他手氣極好,大贏特贏,舍不得離開,珍妮笑著對他說,下次他再這麼晚回來,她就把他鎖在房外,不許進來。
第二天晚上,淩晨2點30分時,鮑比還沒有回來,珍妮下了床,鎖上房門,然後躺下看小說,心中想著鮑比被鎖在房外的狼狽相。
然而,鮑比久久不歸,珍妮抱著小說,竟然睡著了,連床頭燈也沒關。早晨7點時,她醒了過來。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鮑比,她奇怪他怎麼沒有叫醒她,雖然她睡得很沉,但在門上敲一兩下,總會吵醒她的。她斷定,鮑比發現門鎖著,猜測她可能睡下了,就決定不打擾她,然後到某個油田工人那裏睡沙發去了。
突然,她驚慌起來。夜裏,她曾夢見花,她夢見花在窗戶的花瓶邊。她立即起床,穿上衣服,盼望著鮑比隨時會進來,然後梳洗,刮胡子,準備吃早飯。可是吃飯的鐘聲敲過後,仍不見他的人影。珍妮衝上甲板,希望他會睡在某個石油工人的房間裏。她看見那群石油工人站在甲板的欄杆邊閑聊,便急忙走過去,向他們打聽是否見過鮑比。然而他們都不知道,鮑比也沒有在他們的房裏過夜。
珍妮又問其他旅客,但是那天上午誰也沒有見過他。她慌慌張張地到報務室找我。
“鮑比一定出事了。”她呻吟道。
我勸她鎮靜時,她告訴我,她昨夜夢見了花,鮑比又失蹤了。
“他可能躲在什麼地方,以報複你把他鎖在門外。”我說。
這想法有點一廂情願,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船上這段時間,他們兩人喜歡互相捉弄對方。有一次,鮑比往珍妮的床上撒沙子,她則趁他全身抹上肥皂時,請服務員關掉水龍頭,他們兩人是針尖對麥芒,誰也不肯吃虧。
“今天下午他就會露麵了,”我說,“10點鐘船上要演習如何使用救生艇,以及發生火災時如何逃生。”
然而,演習時仍然不見鮑比的人影。珍妮又跑進報務室,差不多要歇斯底裏了。
“他一定是失足掉到海裏了。”她哭著說。
“這麼晴朗的天氣,那是不可能的,”我對她說,“他一定是在哪兒躲起來了。你在這兒等著,我去去就回。”
我讓她留在報務室,自己徑直來到船長的辦公室,心中希望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船長認為,如果鮑比是開玩笑的話,可能一時還不會結束這場鬧劇。船長通過喇叭呼喚鮑比,但沒有反應。船長命令大副搜索全船,同時把一位石油工人叫進辦公室,那位工人告訴我們,撲克牌玩到淩晨4點,但是鮑比3點半就回船艙了。
“他沒有回房休息,”船長說,“他失蹤了。”
那位石油工人很瘦削,皮膚黑黑的,他仔細考慮了一會兒後,問:“昨晚他太太是不是把他鎖在外麵了?”
我回答說:“是的,她開玩笑鎖上了門。”
“那麼,事情可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們,他太太曾威脅說,如果他再那麼晚回去的話,就把他鎖在門外。但是,他說他知道一個對付她的辦法。他打算從船欄杆翻下去,一腳先滑進浴室的窗孔,他說他曾經試過,發現那麼做很容易。他是想從浴室走進去,讓她大吃一驚。我們認為那太危險了,但他不聽,我想他一定是沒站穩,掉到海裏去了。”
假如石油工人的猜測是正確的話,鮑比失足落水的時間已經在八個小時之前。不過,他是個遊泳高手,如果他能保存體力的話,在溫暖、平靜的海上可以漂浮幾個小時。就怕他滑落時撞到船身,或被攪到推進器裏,或遇到鯊魚。
船長決定掉頭回去尋找。船長在處理事情上有時很固執,我想他這麼做是出於對珍妮的同情,即使明知找到鮑比的機會是很渺茫的。
我急忙趕回報務室,珍妮穿著輕便的上衣和粉紅色的休閑褲,黑色的大眼睛充滿了痛苦。我告訴了她石油工人的話,她輕輕地說了聲“我的夢!”就昏倒在地。
我派人找來船上的醫生和一位女報務員,珍妮醒來後,我陪她回到船艙,醫生在離開她的船艙時,給了她一些鎮靜劑。醫生走後,珍妮哭著對我說:“這全是我的錯,我再也見不到鮑比了。”
我則認為這是鮑比的錯。C區船艙的窗孔在左舷欄杆的下麵,想從窗孔鑽進去的話,必須先翻越欄杆,抓住欄杆最下部,再把腳降低到窗孔,插進去,兩腳先滑進去,再把手從欄杆處下移到魚尾板邊,當雙肩安全進入窗孔後,再放手。這艘船沒有空調,窗孔敞開,以便讓海風吹進。
我知道,船上有好幾個服務員曾用這種方式為沒有帶鑰匙的旅客開過門。可是,這種冒險的事,通常都是船停靠在港口時才敢做。在海上,尤其是在夜晚,在船正航行的時候,沒有人這麼做過。鮑比一定是瘋了。
當船回到鮑比可能落水的地點時,天還很亮,海麵平靜如鏡,對尋人很有利。
以鮑比可能落水的地點為中心,船長命令繞一大圈,一直忙到天色暗了下來,結果什麼也沒有。整條船籠罩在一種陰鬱的氣氛之中。當船長下令放棄搜索,照原航線行駛時,大家都承認,船長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船長並沒有放棄希望。他陪我到下麵船艙看望珍妮,想安慰她。珍妮仍然躺在床上沒有動,她相信她的夢是由於鮑比之死而來的。她還換了一身黑色衣服。
“你不能這樣就放棄希望,還早呢。”船長說,“鮑比很可能被附近的船隻所救。假如拯救他的船是沒有無線電的小船隻的話,你就不可能這麼快得到鮑比的消息。隻有等小船到了下一個港口,才會有消息。可那個港口也許在地球的另一邊。”
可是珍妮隻是哭泣。當船長離開之後,她哭著對我說:“我本來可以把夢見花的事告訴他的,但是他不會像你一樣明白事情的嚴重性。”
“我也不可能像你那樣清楚,珍妮,那個夢可能意味著家族中的其他人,而不會是鮑比。那個夢也可能是個錯誤,它並不意味著死亡。”
“菲爾,這不是你的真實想法,你隻是和每個人一樣,想用假希望來安慰我。”
“我是真心這麼想,不是在騙你。你自己看不出來,因為你迷信你的夢,迷信正傷害你,使你執迷不悟。”
“我不能承受更大的打擊了。”
我無法勸解珍妮,她為鮑比而傷心,認為他已經死了。第二天,她整天都留在船艙裏,茶不思,飯不想,拒絕接受同船旅客的同情和安慰。我把時間全都花來陪伴她,在令人心碎的哭泣間歇,她總是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裏,眼睛死死盯著門上的門閂。偶爾,她會呻吟說:“為什麼要那樣做?為什麼事先沒有料到會出事?”
那天晚上,我回房休息之前,又去船艙中看了看她,隻見梳妝台上有一份沒有動過的食品,咖啡也冷了。我連門都還沒有關上,珍妮就哭叫道:“沒有鮑比,我活不下去。”
我並不擔心珍妮會自殺,因為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珍妮,”我勸告她說,“別太難過了,這樣你身體會垮的。如果鮑比見到你這副樣子,會很難過的。”
“你別再折磨我了,我再也見不到鮑比了,我要發瘋了。”
珍妮的眼睛裏布滿了血絲,流露出一種異樣的神情,這神情讓我感到害怕。也許她真瘋了,我感到很難過。現在唯一能使她保持心靈健康的,就是希望鮑比還活著這一信念了。在我看來,唯一能使她免於崩潰的,就是鮑比獲救的消息。
我在離開前對她說:“珍妮,好好睡一覺,你需要休息,明天也許就會有好消息傳來。”
她躺在床上,凝視著頭頂的甲板,似乎沒有聽到,但在我關上房門說“再見”時,她作了回答。
第二天早上大約7點鐘,我收到一封令我欣喜若狂的電報,那是鮑比打來的,他被一艘沒有無線電設備的帆船救起,他一直沒法和我們聯絡,一直到帆船把他送到阿根廷的聖胡安市。我沒有搖電話找服務員,而是親自衝到艙房去找珍妮。我敲敲她的門,但裏麵沒有反應。我想珍妮也許終於睡著了,就推開門,向裏麵張望。
沒有珍妮的影子,浴室門開著,我大聲喊她,也沒有回答。我想她也許上甲板了。我正準備離開時,發現了一個信封,它夾在梳妝台的玻璃上。一看見它,我的心涼了半截——珍妮失蹤了,留下一封信。我再次進入房間,看了看信上的名字。那是留給我的,信的內容把我嚇壞了。
“再見,親愛的菲爾,我到陰間去見鮑比了。珍妮。”
珍妮在窗孔前放了一把椅子,她不但要去陰間與鮑比相會,而且還選擇了同一個地點離開人間。我知道船第二次掉頭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珍妮不會遊泳。
當珍妮開始人生的最後旅程時,魔鬼的笑聲也許緊隨其後。這回她的夢,不是預示鮑比的死亡,而是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