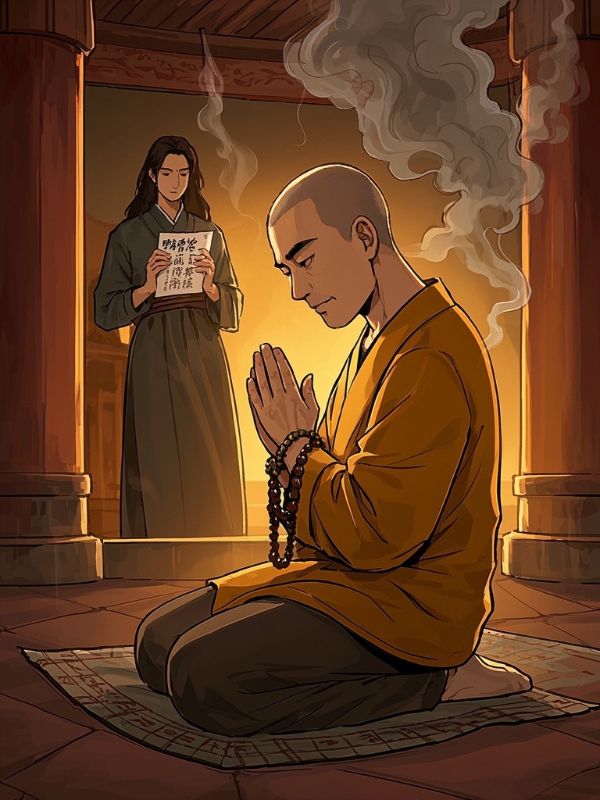打開小說閱讀吧APP
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2
奶奶被推進了搶救室,門頂上“手術中”的紅燈亮起。
醫生說,是突發性大麵積腦梗,情況很危險,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
我爸一瞬間老了十歲,蹲在牆角,雙手插進頭發裏。
我媽靠著牆,無聲地流淚。
我拿出手機,一遍又一遍地撥打裴聲的電話。
第一個,無人接聽。
第二個,無人接聽。
......
第十七個,他終於接了。
背景音很嘈雜,像是在KTV。
“喂?岑鳶,什麼事?”他的語氣很不耐煩。
我喉嚨發緊,聲音沙啞:“裴聲,你在哪?奶奶......奶奶在搶救,醫生說情況很不好。”
“我知道了。”
他的聲音聽不出任何情緒,“我這邊走不開,幾個重要的學界前輩都在,我得陪著。”
“可是奶奶......”
“岑鳶。”他打斷我,“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你要學會理性接受。醫生在裏麵,你在外麵著急有什麼用?別搞得天塌下來一樣。”
“這是你的親人!”我幾乎是吼出來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傳來他更冷的聲音。
“她是你的奶奶,不是我的。當初結婚時就說清楚了,我們是獨立的個體,不要搞親情捆綁。行了,我掛了,你冷靜一下。”
電話被無情地掛斷。
這時搶救室的門突然開了。
醫生摘下口罩,疲憊地對我們搖了搖頭。
“我們盡力了。老人家年紀大了,送來得又有點晚......準備後事吧。”
我握著手機,渾身發抖。
奶奶是被裴聲氣成這樣的,至少得讓他給奶奶道歉。
於是我不死心地繼續打。
第二十通,第三十通......
直到第三十七通,他發來一條短信。
【我在給舒瑤的畢業畫展寫序言,別再打了,會打擾我的思路。】
舒瑤。
那個他一直“資助”的藝術係女大學生。
他說她才華橫溢,是藝術界的未來之星,他有責任為這樣的天才保駕護航。
原來,為天才的畫展寫序言,比親人的生死更重要。
我無力地垂下手,手機滑落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