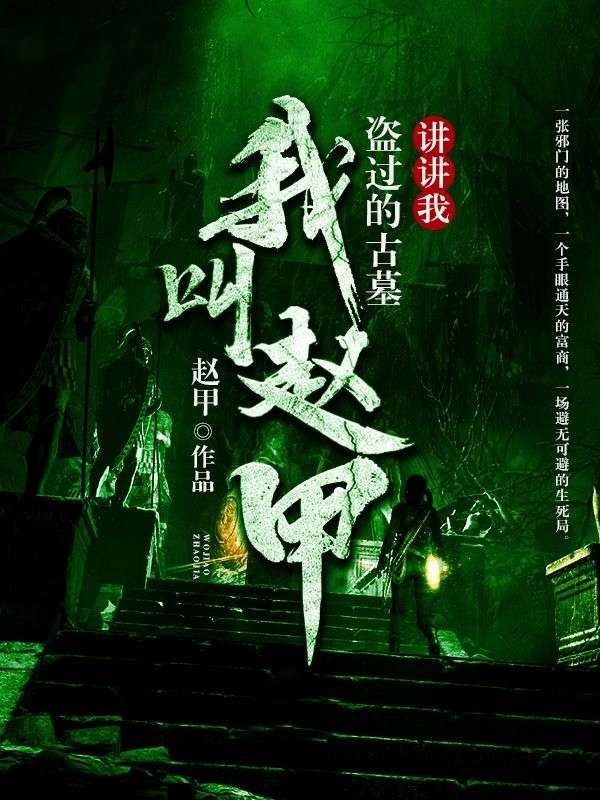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9章
阿虎死狀極慘,那股混雜著血腥和酸臭的味道,順著裂穀下的陰風飄了上來,熏得人直犯惡心。
錢宏業和奎狼兩個人,臉色慘白如紙,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他們帶來的,是現代化的武器和身經百戰的士兵,但在這種完全超出認知範圍的機關麵前,連一張廢紙都不如。
恐懼,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
它能讓一個身經百戰的兵王,手腳冰涼。
也能讓一個翻雲覆雨的富商,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我連眼角的餘光都懶得再瞥一眼那具屍體。
幹我們這行,最忌諱的就是手賤和自作聰明。
你不敬畏這地底下的規矩,那地底下的規矩,就會教你做人。
“胖子,幹活。”我拍了拍還在發愣的胖子,語氣平淡得像是在說咱們吃飯一樣。
胖子回過神來,看了一眼半空中那具慘不忍睹的屍體,狠狠地打了個哆嗦。
他沒說什麼,隻是默默地從背包裏拿出安全繩和下降器,開始往自己身上套。
我把我們這邊所有的過山鯽,一共十五根,都拿了出來。
將第一根鋼釘的環狀那頭扣在安全繩上,然後身體後仰,整個人順著崖壁,緩緩地降了下去。
找到第一個樁孔的位置後,我用手裏的工兵鏟,將裏麵殘留的腐朽木渣和碎石清理幹淨,然後將那根過山鯽的尖端,對準樁孔,用盡全力,狠狠地插了進去!
嗡——
鋼釘入石,發出了一聲沉悶的嗡鳴。
我拽了拽,確認紋絲不動後,才將自己的身體重量,慢慢地轉移到了這根鋼釘上。
這是一個極其耗費體力和精力的過程。
我整個人,就靠著一根安全繩和一根鋼釘,懸吊在這深不見底的裂穀之上,腳下是呼嘯的陰風
清理樁孔,插入鋼釘,固定身體,然後再去夠下一個樁孔......
我就像一隻壁虎,一寸一寸地,在這垂直的崖壁上,架設著一條通往對岸的生命線。
胖子在上麵負責給我遞送鋼釘和工具,我們倆配合得天衣無縫,沒有一句多餘的廢話,全靠手勢和眼神交流。
這是我們多年來,在無數生死關頭,磨練出來的默契。
大概花了半個多鐘頭,一條由十五根過山鯽首尾相連組成的、簡易的龍骨梯,終於橫跨了這十幾米寬的裂穀。
它看起來很脆弱,但這東西,比那座喂屍索橋,要可靠一百倍。
我第一個踩著龍骨梯,走到了對岸。
胖子緊隨其後。
他體型雖胖,但動作卻很靈活,每一步都踩得很穩。
等我們兩個人都安全抵達對岸後,我頭也不回地就開始收拾東西,仿佛對岸那兩個人,根本不存在一樣。
“趙老板!”奎狼的聲音,從對岸傳了過來,帶著一絲他自己都沒察覺到的顫抖,“這東西......該怎麼弄?”
他手裏拿著一根我們“賣”給他的過山鯽,卻像拿著一塊燙手的山芋,完全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他可以毫不猶豫地跳上那座死亡之橋,卻不敢像我一樣,把自己吊在這萬丈深淵之上。
我停下手裏的動作,回過頭,隔著裂穀,靜靜地看著他。
“那是你們的事。”我淡淡地說道,“錢,我已經收了。貨,也給你們了。至於你們會不會用,敢不敢用,與我無關。”
錢宏業的臉色陰沉得能擰出水來。
他死死地盯著我,眼神裏的殺意,幾乎凝成了實質。
但他終究沒有發作。
他知道,在這裏,他引以為傲的金錢、地位、武力,全都失去了意義。
在這裏,隻有我,和我所知道的那些規矩,才是唯一的通行證。
“奎狼,”他從牙縫裏擠出幾個字,“我們自己來。”
接下來的場麵,就有些滑稽了。
奎狼,這個曾經的兵王,哆哆嗦嗦地學著我的樣子,把安全繩綁在身上。
但光是把自己降下去那一步,他就嘗試了七八次才成功。
他打第一根鋼釘的時候,因為角度不對,差點把自己給甩出去。
錢宏業則蹲在崖邊,臉色鐵青地看著,一言不發。
我和胖子,則像是看戲一樣,坐在對岸的一塊大石頭上,抽著煙,吃著壓縮餅幹,補充著體力。
“甲哥,咱們真不管他們?”胖子湊過來,小聲問,“萬一他們掉下去了,咱們出去也不好交代啊。”
“交代?”我吐了個煙圈,“是他自己的人,急著去送死。也是他自己的人,笨得跟豬一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胖子,這趟活兒,從頭到尾,能信的,就咱們仨。”
“現在九川留在了後麵,就隻剩你和我。我們隻要保證自己能活著走出去,就夠了。”
胖子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不再說話。
最終,在天黑之前,錢宏業和奎狼,一身狼狽,筋疲力盡地,總算是爬了過來。
奎狼的一條胳膊,還在剛才打樁的時候,被岩石劃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鮮血直流。
他們過來之後,一句話沒說,隻是癱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
那種從死亡邊緣爬回來的虛脫感,讓他們的眼神都有些渙散。
我沒去理會他們,而是舉起手電,開始觀察這邊的環境。
裂穀的對岸,不再是溶洞,而是一條向上延伸的人工隧道。
隧道的牆壁上,開始出現一些精美的浮雕,內容大多是祭祀、戰爭和狩獵的場麵。
而在隧道的最深處,隱隱約約, 有兩盞青色,像是鬼火一樣的光芒,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地閃爍著。
“長明燈......”我喃喃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