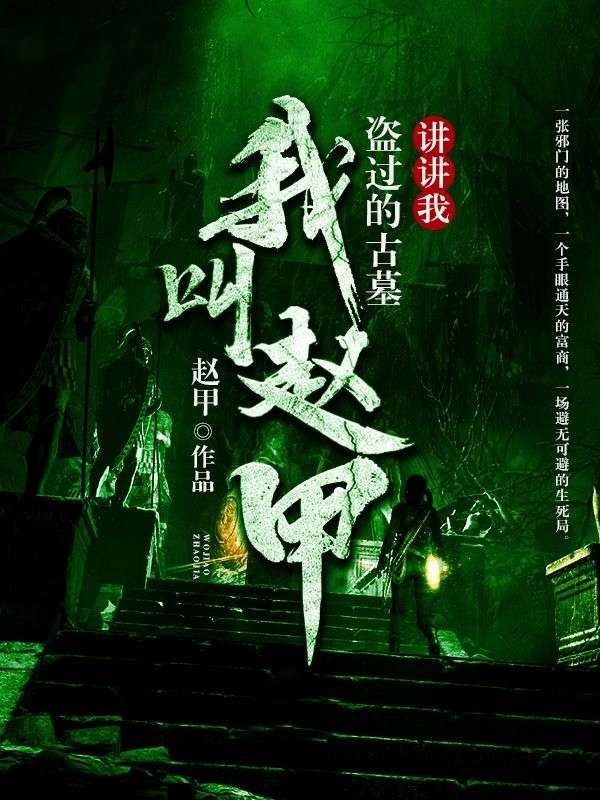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8章
告別了九川他們,我們剩下的五個人,氣氛變得更加詭異。
隊伍的構成很奇怪,我和胖子走在最前麵,錢宏業走在中間。
奎狼和那個叫阿虎的壯漢則斷後。
我們兩撥人,就像兩塊互相排斥的磁鐵,被硬生生地綁在了一起。
中間隔著一個心思深沉的錢宏業。
沒有了九川的地質勘探,我隻能更多地依賴自己的經驗。
我讓胖子從背包裏拿出一捆麻繩,一頭係在他腰上,一頭係在我腰上,中間留出五米左右的距離。
這是老土夫子走生穴的法子,萬一前麵的人一腳踩空,掉進什麼裂縫裏,後麵的人能有個反應的時間,把人救下。
奎狼看到我們的舉動,嘴角撇了撇,似乎想說什麼,但終究還是沒開口。
他和他的人,也學著我們的樣子,用軍用繩索連接了起來。
溶洞越往裏走,道路越是崎嶇。
腳下的暗河時隱時現,有時候在我們左邊,有時候又鑽到岩層下麵。洞壁上開始出現一些人工開鑿的痕跡,是一些簡陋的壁畫,上麵畫著一些頭戴羽冠的小人,跪拜著某種看不清麵目的神祇。
“甲哥,你看這畫兒。”胖子用手電筒照著一幅壁畫,小聲說道,“這些小人,怎麼都沒有臉?”
我湊過去一看,果然,壁畫上所有的人形,臉上都是一片空白,看著讓人心裏發毛。
“有兩種可能。”我沉吟道,“一種是,畫這畫的人認為,神靈的樣子,凡人是沒資格看的。”
“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祭拜的神,根本就沒有臉。”
我的話讓胖子打了個哆嗦。
我們又往前走了大概半個多鐘頭,前麵的路,被一條深不見底的裂穀攔住了。
這裂穀大概有十多米寬,黑漆漆的,手電筒的光照下去,就像是被黑暗吞噬了一樣,根本看不到底。
一股股陰冷的風,夾雜著嗚嗚的怪嘯,從裂穀下麵吹上來,讓人汗毛倒豎。
在裂穀的上方,架著一座用三根粗大鐵索組成的懸橋。
鐵索上鋪著已經腐朽得差不多的木板,很多地方都露著空洞,看著就讓人兩腿發軟。
“看來,這是唯一的路了。”錢宏業走到裂穀邊,看著對岸的黑暗,說道。
“這橋......還能走人嗎?”胖子咽了口唾沫,“我這體重,上去不得直接把它踩塌了?”
“阿虎,你先過去試試。”奎狼回頭,對他手下那個叫阿虎的壯漢命令道。
阿虎點了點頭,沒有絲毫猶豫。
他解開身上的繩索,從背包裏拿出一個抓鉤,用力一甩,抓鉤帶著繩子,哐啷一聲,牢牢地鉤住了一塊岩石。
他拽了拽,確認穩固後,就準備上橋。
“等一下。”我突然開口。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指了指那些鐵索:“你們不覺得,這鐵索的顏色有點不對勁嗎?”
經我提醒,他們才注意到,那三根碗口粗的鐵索,在手電筒的照射下,並不是生鏽的暗紅色。
而是一種泛著油光的烏黑色,像是被人盤了上千年一樣。
“這叫喂屍索。”我聲音有些發幹,“是古時候一種極其歹毒的機關。”
“工匠會用上百種毒蟲毒草,混著人油,常年累月地塗抹在鐵索上。”
“這東西,看著結實,其實毒性早就侵入到了鐵索的內芯。”
“人走在上麵,身體的溫度和重量,都會激發裏麵的毒性。用不了幾步,人就會渾身麻痹,手腳不聽使喚,活生生地掉下去,摔成肉泥。”
聽我這麼一說,阿虎那張黝黑的臉,瞬間就白了。
“那......那怎麼辦?”奎狼也有些慌了。
“趙老板,你既然認得,一定有辦法破解,對嗎?”錢宏業看著我,眼神裏帶著一絲期待。
我搖了搖頭。
“沒辦法。”我回答得斬釘截鐵,“這種機關,無解。唯一的辦法,就是不碰它。”
“不碰它?那我們怎麼過去?”奎狼急道。
我沒有理他,而是走到裂穀的邊緣,將手電筒往下照去。
我沒有看深不見底的穀底,而是仔細地觀察著我們腳下這邊的崖壁。
很快,我在離我們大概五米深的崖壁上,發現了一排非常不起眼的小孔。那些孔洞隻有拳頭大小,呈一條直線,向著裂穀的對岸延伸過去,消失在黑暗中。
“路,在那裏。”我指著那些孔洞。
“那是路?那他媽是給猴子走的吧!”胖子探頭看了一眼,嚇得差點沒坐地上。
“這是古時候的棧道。”我說道,“隻不過,木頭的部分早就爛光了,隻剩下了當年打進去的樁孔。隻要我們有工具,重新架設一條路,就能過去。”
“我這裏有軍用膨脹岩釘和攀岩繩!”奎狼立刻說道。
“不行。”我再次搖頭,“你那種岩釘,打進去動靜太大。誰也不知道這一下去,會驚動什麼東西。”
“而且,這裂穀下麵,風向很亂,繩子蕩來蕩去,太危險。”
我一邊說,一邊從自己的背包裏,拿出幾根特製的、一米多長的精鋼長釘。
這種釘子是中空的,一頭尖銳,一頭是環狀,重量很輕,但硬度極高。
“用這個。”我把鋼釘遞給胖子,“這是過山鯽,打進樁孔裏,首尾相連,就能搭成一條最簡易的龍骨梯。雖然不好走,但絕對穩當。”
“好辦法!”錢宏業眼睛一亮。
“但是......”我話鋒一轉,看著他們,“我這過山鯽,數量有限,剛好夠我們過去。”
“而且打樁、鋪設,都需要極大的體力和技巧。我的人,隻負責我們自己。”
我的意思很明確。
我可以帶胖子過去,但錢宏業他們,得自己想辦法。
“趙老板,你這是什麼意思?”錢宏業的臉色沉了下來,“我們是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也得明算賬。”我毫不退讓地看著他,“這趟活兒,從頭到尾,都是你們的人在出問題。我救了你們的人一次,仁至義盡。”
“現在,我不可能再拿我和我兄弟的命,去為你們的無能買單。想過去,可以,你們自己想辦法。或者......”
我頓了頓,伸出兩根手指:“一根過山鯽,二十萬。我賣給你們。”
“你!”奎狼氣得渾身發抖,伸手就要拔槍。
但這一次,錢宏業攔住了他。
錢宏業死死地盯著我,足足看了有半分鐘。
那眼神,像是一條毒蛇,想把我整個人都吞下去。
最終,他笑了。
“好,好一個趙老板。”他點了點頭,鐵青著臉道:“等回去我就安排人轉賬。我買十根。”
我沒說話,也懶得去糾結他說的真假,隻是單純想惡心他們一下而已。
胖子把十根過山鯽數出來,放在地上。
就在這當口,那個叫阿虎的壯漢,大概是急於表現,也可能是被我剛才的態度刺激到了。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鋼釘,又看了一眼那座喂屍索橋,一咬牙,對奎狼說道:“隊長,老板,我覺得沒那麼邪乎,我過去試試,我速度快,屏住呼吸,一口氣衝過去!”
不等奎狼和錢宏業反應,他猛地一個助跑,縱身一躍,就跳上了那座懸橋!
他動作確實很快,腳尖在腐朽的木板上連點,像一隻猿猴,朝著對岸衝了過去!
眼看他就要衝到一半了!
突然,他的身體在半空中猛地一僵,整個人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樣,直挺挺地停在了橋中央。
然後,在我們所有人的注視下,他的皮膚,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黑。
他的嘴巴大大地張開,似乎想要求救,但喉嚨裏隻能發出嗬......嗬......的聲音。
前後不過三秒鐘,他就直挺挺地向後倒了下去。
但他沒有掉進深淵。
就在他倒下的瞬間,橋下的黑暗中,猛地射出了無數條像是頭發絲一樣的東西。
噗噗噗地刺穿了他的身體,將他整個人,像個破布娃娃一樣,吊在了半空中。
那些頭發絲,竟然是活的!
它們蠕動著,鑽進阿虎的七竅,他的身體開始劇烈地抽搐、融化......
一股濃烈的、夾雜著血腥和酸臭的味道,飄了過來。
錢宏業和奎狼,臉色慘白,呆呆地看著這恐怖的一幕,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則連看都懶得再看一眼。
我轉過身,淡淡地說了句:
“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