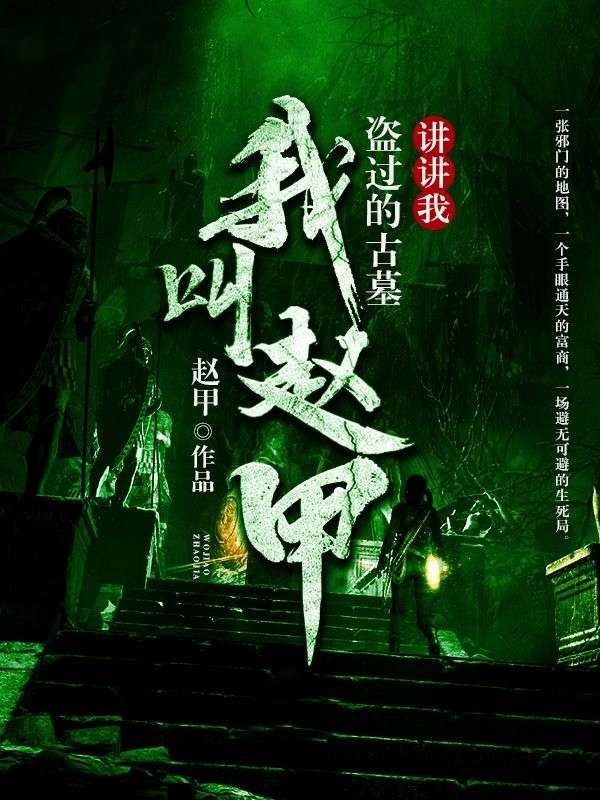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7章
一個小時的休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在這段時間裏,沒人敢真的睡著。
溶洞裏雖然暫時恢複了平靜,但誰都知道,黑暗中,不知道還有多少雙眼睛在盯著我們。
那個斷臂的隊員,在我的藥丸作用下,悠悠地醒了過來。
他很年輕,估計也就二十出頭的年紀,醒來後發現自己斷了一條胳膊,隻是睜著眼睛,默默地看著溶洞的頂,眼淚順著眼角往下流。
戰爭年代,斷手斷腳是家常便飯。
但在和平年代,這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我走過去,遞給他一根煙。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複雜,有後悔,也有茫然。
他用僅剩的那隻手接過煙,顫抖著,半天都點不著。
我拿過打火機,幫他點上。
“謝謝。”他吸了一口,聲音沙啞。
“叫什麼。”我說道。
“......周平。”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沒再多說。
有時候,男人之間的安慰,不需要太多言語。
胖子湊到我身邊,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壓低了聲音:“甲哥,你說這巴國的老祖宗,是不是有點心理變態啊?”
“修個墳,又是血蘭,又是人麵蚰的,這他媽是怕死人太寂寞,給他找點寵物養著玩?”
“這不是寵物。”我看著遠處那道漸漸熄滅的火牆,搖了搖頭。
“這是鎮墓獸。我師父以前說過一個故事,是關於咱們一個前輩的。”
“那前輩當年在內蒙掏了一個元代大官的墓,那墓裏什麼都沒有,就一口石棺。”
“他們撬開石棺,裏麵也沒屍體,就一窩密密麻麻的紅毛蠍子。”
“那前輩命大,跑了出來,同行的七八個人,全折在了裏麵。”
“後來才知道,那墓主人生前信奉薩滿教,他認為人死後,靈魂會被地下的惡靈吞噬。”
“所以他死後,用自己的血肉和秘術,養了那一窩毒蠍,用來保護自己的靈魂安寧。”
胖子聽得頭皮發麻,問我:“你的意思是,這些人麵蚰,是這墓主人專門養在這兒的?”
“很有可能。”我點了點頭,“巴人巫術盛行,神秘莫測。”
“這溶洞四季如春,又有暗河,是養這些陰邪東西的絕佳場所。”
“剛才那上百隻,恐怕還隻是先鋒軍,真正的大家夥,還在後麵。”
我和胖子正聊著,錢宏業和奎狼走了過來。
奎狼的臉色很難看,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兵,然後對錢宏業說道:“老板,周平這個情況,不能再跟我們繼續前進了。”
錢宏業點了點頭,然後看向我,問道:“趙老板,你的意思呢?”
這個問題,很棘手。
按理說,帶著一個重傷員,在這種環境下,確實是累贅。
但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裏,跟讓他等死沒區別。那些人麵蚰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但也不能把他丟下。”我沒怎麼猶豫,直接說道。
奎狼忍不住開口,語氣生硬,“帶著他,會拖慢我們所有人的速度,增加所有人的風險。”
“那也是你的人。”我冷冷地看著他。
“你!”奎狼被我一句話噎得滿臉通紅。
“好了,都少說兩句。”錢宏業出來打了圓場。
他沉吟了片刻,說道:“趙老板說的有道理,我們不能放棄同伴。”
“這樣吧,奎狼,你留下來,再帶一個人,照顧周平。”
“你們在這裏建立一個臨時營地,等我們出來。剩下的,跟我跟趙老板繼續前進。”
這是一個看似兩全其美的辦法,但我心裏卻是一沉。
錢宏業這是在分化我們的力量。
奎狼和他的人,雖然剛才表現不佳,但畢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戰鬥人員,是隊伍裏最強的火力。
現在,他要把這股最強的力量,留在後方。
是真的顧及同伴,還是想保存他身邊的武裝力量,方便他在找到東西後,對我下手?
我看著錢宏業那張看不出任何情緒的臉,心裏冷笑。
“不行。”我搖了搖頭。
“為什麼?”錢宏業的眼睛眯了起來。
“你的人,我不放心。”我直言不諱,“他們不懂這裏的規矩,把他們留在這裏,跟讓他們送死沒區別。”
“萬一他們再搞出點什麼動靜,把那些蟲子或者別的東西引過來,誰也活不了。”
我頓了頓,指了指九川:“讓九川留下來。”
“他懂地質,也懂機關,知道怎麼找一個最安全的地方藏身。”
“再讓奎狼留下兩個人,負責保護和照顧傷員。”
“剩下的人,包括你和奎狼,跟我們繼續走。”
我的這個提議,讓所有人都愣住了。
胖子急了:“甲哥,讓九川留下?那咱們......”
我擺了擺手,打斷了他。
我知道,這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九川雖然是我們的重要戰力,但他心思縝密,性格沉穩,是留守的最佳人選。
而且,把他留下來,也等於是在錢宏業身邊安插了一個我自己的人,可以互相牽製。
這是一種平衡。
錢宏業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權衡其中的利弊。
幾秒鐘後,他點了點頭:“好,就按趙老板說的辦。”
“奎狼,你讓一個人,跟九川一起,留守。”
奎狼雖然不情願,但也隻能服從命令。
就這樣,我們這支臨時拚湊起來的隊伍,在剛剛經曆了第一場血戰之後,就麵臨了第一次減員。
我們把大部分的食物、水和一些必要的藥品留給了九川他們。
臨走前,我把九川拉到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用油布包著的小羅盤,塞給了他。
“這是分金盤,我師父留下的。”我壓低了聲音,“如果十二個小時後我們還沒回來,或者你聽到裏麵有什麼不對勁的動靜,不要等,也別想著來救我們。用它,找到這個溶洞的生門,自己想辦法出去。記住,活下去最重要。”
九川看著我,重重地點了點頭,隻說了一個字:“懂。”
告別了留守的三人,我們剩下的五個人。
我、胖子、錢宏業、奎狼,還有另外一個叫阿虎的壯漢,重新整理了裝備。
火牆已經徹底熄滅,隻剩下一地焦黑的灰燼。
我站在隊伍的最前麵,舉起手電,照向了那條被黑暗籠罩,通往溶洞更深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