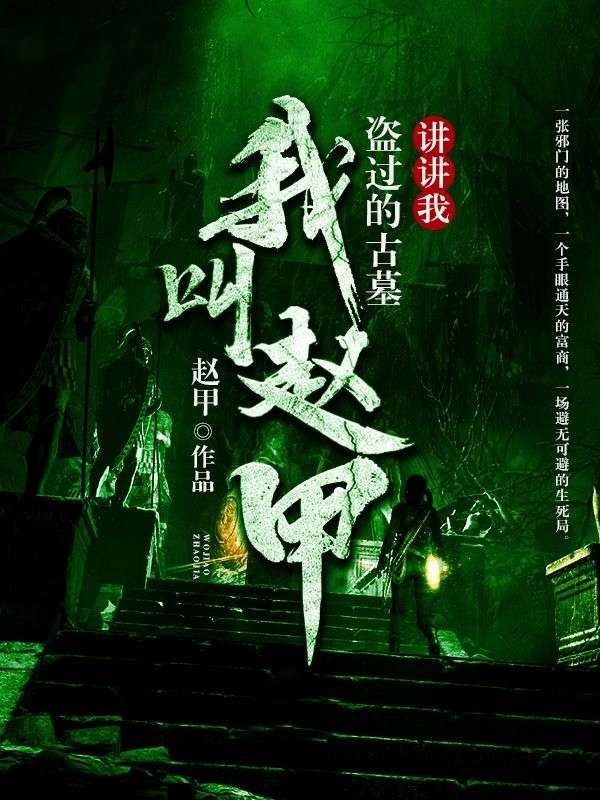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6章
整個溶洞裏,死一般地寂靜。
隻有火牆燃燒時發出的劈啪聲,和我們幾個人沉重的喘息聲。
奎狼的嘴唇動了動,似乎想說什麼,但最終一個字也沒說出來。
錢宏業是第一個從震驚中恢複過來的。
他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物,臉上很快就恢複了那副波瀾不驚的表情。
他走到我麵前,很自然地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遞給我。
“趙老板,擦擦吧。”他看了一眼我臉上濺到的墨綠色毒液,語氣平靜地說道,“看來,這次我請對人了。”
我沒有接他的手帕,隻是用手背隨意地抹了一把臉。
我盯著他,一字一句地說道:“錢老板,剛才那種情況,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我這話,是說給錢宏業聽的,更是說給奎狼聽的。
奎狼的身體明顯僵了一下,握著槍的手,青筋暴起。
錢宏業的眼神閃爍了一下,隨即笑著點了點頭:“當然。趙老板的規矩,就是我們的規矩。奎狼!”
他回頭,語氣陡然變冷。
“向趙老板道歉。”
奎狼猛地抬起頭,滿臉的難以置信。
讓他這個曾經的特種兵王,向一個土夫子道歉,這比殺了他還難受。
“老板......”
“道歉!”錢宏業的聲音不大,但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嚴。
奎狼的臉漲成了豬肝色,他死死地瞪著我,牙齒咬得咯咯作響。
最終,他像是泄了氣的皮球,從牙縫裏擠出幾個字:“對不起,趙老板,是我魯莽了。”
我沒說話,隻是收回了工兵鏟,轉身走到那個斷臂的隊員身邊,檢查他的傷口。
我知道,這一關,算是過去了。
但我也很清楚,梁子,算是結下了。
奎狼這種人,絕不會真的服我。
“胖子,九川,警戒。”我頭也不回地吩咐,“把咱們帶來的雄黃和石灰粉,混在一起,在火牆後麵再撒一道防線。那些東西怕火,但更怕這玩意兒。”
“好嘞,甲哥。”
胖子和九川立刻行動起來。
他們做事,從來不多問為什麼。
我則專心處理那個傷員。
他的命雖然保住了,但失血過多,臉色慘白得像一張紙。
我從我的百寶囊裏,又掏出一個小瓷瓶,倒出幾粒紅色的藥丸,給他喂了下去。
“這是什麼?”錢宏業在我身邊蹲了下來,好奇地問道。
“補氣的。人參、鹿茸、血竭......碾碎了拿蜂蜜和的丸子。”
我一邊說,一邊重新給他包紮傷口。
“他這條命是撿回來了,但能不能撐到出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錢宏業看著我熟練的動作,沉默了片刻,突然問道:“趙老板,你師父劉半尺,當年在道上,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我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
“我師父?”我抬起頭,看著遠處跳動的火光,眼神有些悠遠,“我師父常說,我們這行,是向死而生。敬鬼神,敬天地,但最該敬的,是人命。”
“他說,一個土夫子,要是對人命沒了敬畏,那他就離死不遠了。”
錢宏業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沒再說話。
火牆的火勢,慢慢地開始變小。
那些人麵蚰,似乎也知道占不到便宜,在火牆外徘徊了一陣後,就如潮水般地退回了黑暗的通道裏。
危機暫時解除了。
但所有人都笑不出來。
溶洞裏彌漫著一股燒焦的蛋白質和毒液混合的惡臭。
地上到處都是蟲子的殘肢斷骸,一片狼藉。
那個斷臂的隊員,更是像一口警鐘,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這裏到底有多凶險。
“原地休整一個小時。”我站起身,下達了命令,“檢查裝備,補充體力。一個小時後,我們繼續出發。”
這一次,再也沒有人提出任何異議。
奎狼默默地安排他的人,將受傷的隊員固定在擔架上,輪流看護。
其他人則靠著岩壁,沉默地啃著壓縮餅幹。
我走到暗河邊,用清水洗了洗工兵鏟上的汙跡。
冰冷的河水,讓我因為剛才的搏殺而有些發熱的頭腦,冷靜了下來。
我看著水麵倒映出的那張,因為疲憊和緊張而顯得有些陌生的臉,心裏忽然感到一陣茫然。
我本想金盆洗手,安安穩穩地開個小鋪子,了此殘生。
可江湖,就像一張網。
你以為你跳出去了,其實,隻是換了個地方,繼續被它牢牢地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