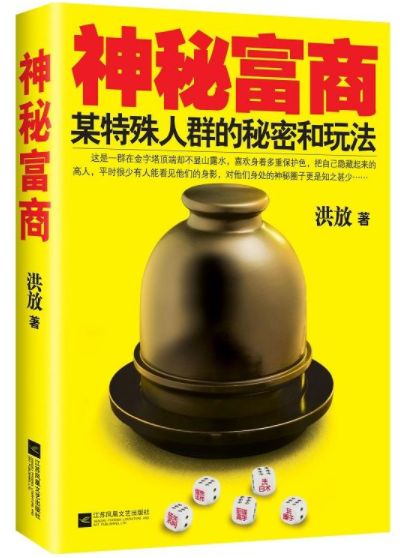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4:每個富豪都有秘密
晚飯後,賈晴晴請大家移步,到就設在綠洲裏的太極養生中心,說吳總還有事,恐怕暫時不能回來。我先請大家稍稍休閑一下。
太極養生中心,其實就與玻璃房子隔一小段路。那路上,雖然是夜間,但聞得到一陣陣的花香。賈晴晴介紹說,“你們別小看了這條路,叫花徑。”
殷夢說:“好名字,古人有詩:花徑不曾緣客掃。”
“就是出自這典故。”賈晴晴說:“這名字是吳總自己起的。包括那海,其實也有個名字,叫愛琴海。後麵還有一座小湖,叫如仙湖。”
嶽超聽著這些名字,恍惚間有種如入仙境的感覺,而同時他又覺得現如今的富豪,特別是像吳元照這樣的富豪,真的不是那些從前的草包了。都有學問,都有思想,都是能上得了大台麵見識過大場麵的。這麼想著,他覺得自己越發的小了。富而無知,也是很可怕的啊!就是剛才賈晴晴講的那詩,還有那典故,他都不曾知道。他隻好跟在後麵聽著,這方麵看來是得向殷夢好好地學學了。
一座古舊的竹編小門,乍一看就是一座簡單的四合院子。門邊卻掛著一隻小燈籠,上書“太極養生”四個字,進門院內幾無人聲,也沒人迎接。賈晴晴帶著大家往裏走。鄒燕要上前,卻被製止了。賈晴晴說:“你走不通的。這院子裏有講究。”
鄒燕停下來,問:“什麼講究?看著不就是一院子?跟北京的四合院一樣。還有講究?”
“是有講究的。”賈晴晴朝左首屋子那邊喊了聲,“小秦,來人了。”
很快就從那竹屋裏挑簾子出來一個女孩,穿玄色衣服,似乎是影子般地飄到大家麵前。賈晴晴說:“帶著客人們,走走這八卦。”
啊,原來是八卦,難怪這叫太極養生。嶽超望望腳底下,一個大的黑白八卦圖呈現著。小秦說:“大家跟著我。閉上眼,心在走即可。”
都閉了眼。很多時候,人是喜歡對一些虛幻的事物產生依存的。比如這就是。也許毫無益處,隻是依存。但就在這茫然的依存中,心思卻一下子靜了。這大概就是這八卦的魅力。大家走完了,便到了另一座竹門前。進去後有一過道,分左右兩邊。小秦說:“男賓左,女賓右。”
男左女右,果真都是一套古法的。嶽超和張董往左,隨著服務生進了個小套間。裏麵除了兩張沙發和茶幾外,幾乎沒有其他陳設。沙發前是一塊兩丈見方的竹簟。服務生說:“請更衣。”並且介紹說更衣後就躺在這竹簟上,全套的保養都是電腦控製。如果有什麼需要就隨按室內的那個紅色按鈕。
服務生走後,張董說:“想不到老吳這裏還有這些玩意兒,真是個富豪玩主。”
嶽超說:“看不出來。深著呢!”
兩個人更了衣,按照竹簟上的標示躺下,很快,就有聲音提示:“太極氣養生開始。”接著,竹簟子上忽然就冒出暖暖的熱氣,整個人就被熱氣包裹了。這熱氣說來也怪,不是軟綿綿的,而似乎是有形狀和力量的。它們往身體的關鍵部位跑去,就如同一隻手在按摩、在揉搓、在打擊、在輕撫。這氣時熱時冷,有時又灼燙,有時又寒涼。無論是熱還是冷,都往身體裏麵去,讓人感到它在尋找你身體內的疲憊之處、鬆軟之處和病疼之處,其遊走無形,宛如八卦之飄逸;其招招著實,又似八卦之剛健。人的身體這時候就如同一枚芥子,被這氣團團地裹挾著、飄蕩著、升沉著,體內的穢濁之氣也漸漸地清空了,世界變得清明起來……
都不說話。
隻有氣體在流動,在身體上、在竹簟上發出美妙的變幻之聲,這聲音,如同遠古之天籟,清淨、脫俗、空靈;又像是浩浩平野之大風,剛柔相濟、虛實相生。
等到醒過來,已經是一個時辰以後了。嶽超邊穿衣邊問張董:“感覺如何?”
“好!就得時常這樣。”張董說,“這設計真的精妙。我就說吳元照這家夥,有個性!了不得!”
室內又恢複了清淨,服務生過來上茶,是上好的綠茶。服務生說:“太極養生後飲綠茶,可清心潤體,請慢用。這茶水是天然的山泉水,有蘭花香。”
聞聞,果真就有。
喝了茶,賈晴晴讓人過來,說吳總回來了。但天太晚了,大家就在綠洲休息,明天再談事。休息的地方就在前麵主樓,每人一個套間。房間的陳設也是豪華之至,嶽超看了下,大部分家具都是進口的,衛生間裏的洗漱用品和化妝品上都是外文。再看窗外燈光,並不多。可見這綠洲基本上是不對外的。那麼下午來時所見的那些在大堂裏談話的人,可能就是江南集團的客戶或者吳總他們的熟人。江南集團做到這麼大,來來往往的人物很多。綠洲確實是個好去處,安靜,私密,甚至溫暖。
殷夢打電話來,問衝澡了嗎?
答說:“剛衝了。”
殷夢說:“我想過去。”
答說:“夜不早了。那……好吧!”
嶽超突然就有些急躁了。他在室內來回踱步,他的急躁倒不是因為殷夢馬上要過來,而是突然感覺到在這綠洲國際在吳元照這樣的大富豪的光環下,自己這三十年來的拚搏一下子變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他更加感到急躁的是:吳元照他們過著的富豪生活,許多都是他從前沒有想到過的。富不在錢多錢少,當然,錢是基礎。但更重要的還是富後的生活狀態、生存策略和品味。這海水、這太極養生,完全就是極致的做派。他想:要是自己再奮鬥幾年,或許也能過上這樣的日子。到那時,他最想做的事不是這海水,也不是這太極養生,而是建一座博物館,把他那收藏在地下室的寶貝,還有許多散落在民間的寶貝都拿出來,讓他們重見天日。
門鈴響了。他開門。殷夢如同一尾魚般滑了進來……
嶽超是被一陣鳥鳴叫醒的。難得的鳥鳴,雖然南州別墅裏也有許多樹木,但是鳥兒少,即使有,叫聲也那麼稀薄,談不上好聽。而這裏鳥兒的叫聲,清脆,新鮮,就像兒時在鄉下聽到的鳥鳴。他醒了,卻沒睜眼,隻是聽著。他聽出黃鶯的叫聲,婉轉明亮,又聽出了灰喜鵲的叫聲,稍微有些靦腆,還有那些正疾飛的雀子的叫聲,透著機靈;他聽了會,心靜著。疲勞也隨之解除,他看了看身邊正熟睡的殷夢,恬靜而溫和,像個孩子般。這條昨晚纏繞著他的魚,此刻放鬆著。他輕輕吻了下她的臉,下床,站到窗前,外麵院子裏的樹葉經過露水的濕潤,越發的清明可愛。再遠處,是那座湖,叫如仙湖吧,此刻湖上正有薄薄的嵐霧。世界蘇醒了,世界正迎來又一個愛恨交織的白天。
早飯後,吳元照特地安排嶽超到他的江南集團參觀。跑了數百公裏,看了集團下麵的十幾家企業,嶽超愈發地有些糊塗了。這些都統一署名為江南集團某某公司的企業,經營的種類五花八門,給人的感覺就是拚湊。他對殷夢說了印象,殷夢說這就是集團,鬆散化的集團是現代企業發展的一個看好的方向。那麼……他想探討一下這些集團的運營和管理,但他知道這為時太早,而且也不合適。回到江南集團的總部,吳元照問嶽超:“是不是覺得就像一盤散沙?”
“如果吳總讓我說真話,就是。”嶽超沒隱諱。
吳元照說:“我就是要你說真話。我要的就是散沙的效果。沙子的先天成分就注定了它永遠都是獨立的個體,你隻能通過適應它的方式聚攏它、管理它,但不能消滅它的個性與獨立。我的這些企業,算起來有三四十家,都是一粒粒在市場裏經過磨打的沙子,我收購它們,投入資金、管理與新技術,保留它們的自身特色與市場。如此一來,這些沙子都既獨立又獲得了團結的力量,因為有我作後盾了,它們不怕,有了底氣。而我的所有想法所有規劃,都隻有通過這些一粒粒的沙子的運作來實現。從這個角度上講,江南集團是最大的,但也是最小的。”
張董道:“最大與最小的集合。”
“對了。集合。”吳元照哈哈笑著,說,“嶽總哪,我聽晴晴說你們也要到江南來發展,好!現在一是政策好,空間越來越大;二是市場經過這麼多的風雨洗禮,該淘汰的淘汰了,留下的往往都是金子;三是我覺得嶽總你這個人能行。做大做強企業不必要事必躬親,不必要隻看眼前,要長遠,要舍得。這是一種酒的名字吧?我沒喝過那酒,但我覺得這名字好。舍得,有舍才有得。”
“吳總說得對。我在南州也做了三十年了,到了出來發展的關節上。這方麵還請吳總關照,指點。”嶽超說,“我已經將礦山租給別人了,現在還有房產公司和一家重型機械公司。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哈,嶽總哪,我不是說你,既然要出來,那就得先有方向。我相信嶽總在南州也是個風雲人物,能失了方向感?”吳元照話說得直接,看得出他不太滿意嶽超的虛掩。
嶽超幹脆就直說了:“我想發展精密機械這一塊,市場我熟悉,而且符合現在的高科技和創新需求。”
“這個……”吳元照停了下,既像對嶽超說,又像對張董說一樣:“這個……目前市場我不太清楚。不過我的一個朋友在南方倒是主營這個。但是似乎也在轉行。還是個技術儲備的問題。嶽總這點不知考沒考慮?江南市這一塊高校多,有技術優勢,但就我所知在精密機械這方麵專家不是太多。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方向,但先還是以投資為主,尋求合作,逐步地開拓市場。”
“我同意吳總的意見。”張董分析說,“製造業現在普遍在向高科技方向發展,而且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沒有相當長時間的基礎積累,貿然進入風險很大。與其冒著風險,不如先行從投資方麵入手。嶽總在南州有礦業,那就是大筆的資本,可以融資。這方麵你可以跟吳總合作,吳總是不怕沒有錢,就怕不用錢。”
“我也不是那樣的吧?哈哈。”吳元照問。
“一切市場的實質都是資本的再分配。我隻是說了實話。而吳總你,是真正把握了市場。”張董道。
嶽超聽著,先是有點糊塗,漸漸的,就明白了。吳元照還真的是說了實在話,建議提得中肯。而且,就他自己的心裏,對搞精密機械這一塊,也有些不著底子。他想到的是自己畢竟有些熟悉,另外現在國家對製造業這一塊扶持力度也相當大。然而經吳元照和張董這麼一說,他有些動搖了。他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地理一理了。
下午,鄒燕提出來要到南州走走,說南州有江,她要去看長江。殷夢說這倒是好,幹脆大家一道到南州。吳元照和張董說下午要趕到北京,賈晴晴說集團這邊還有一些事要處理,就隻有鄒燕跟了嶽超、殷夢回到了南州。一路上,鄒燕說到現在企業家特別是那些大富豪們,有了錢就到了北京。為什麼到北京?北京機會多啊!第一個機會是國家政策機會,率先一口吃到國家扶持政策的紅利,這個你別看,還真是了不得的。就那個吳總,我聽張猛說,每年從國家部委那裏拿到的扶持資金,都有好幾千萬。第二個機會是人才。北京是高地,人才都集中在那兒,你一去發展,人才就來了。第三個,鄒燕說那些富豪為什麼喜歡呆在北京?就是吳總,一年有一半時間都呆在那兒。為什麼?
殷夢說:“為生意唄!”
鄒燕用標準的美聲笑道:“生意?生意也不需要天天做啊。真到了他們這樣,隻管資本流了。隻管方向。具體的事都是其他人在做。他們是會朋友、喝茶、給名人捧場。當然……”
嶽超朝鄒燕望了眼。
鄒燕繼續道:“北京那些院團的角兒,三分之二都是他們捧的。還有那些剛出道的影視演員,一砸都是幾百萬。我聽說吳總也捧了一個,就是前不久那台熱播劇的主角。江南集團讚助了五千萬。”
“五千萬?大手筆啊!”殷夢歎道。
“不算大。我聽說還有上億的。有個山西煤老板,這些年經他手捧紅的有十來位了。光投資就有好幾個億。還有其他開支。到北京,找不著人來捧,在演藝圈就很難有出頭之日啊!”鄒燕感歎著。嶽超聽不出她是在替自己感歎,還是在替那些被捧紅的演員們感歎,甚或是在替那些甩出大把的票子的大佬們感歎。
殷夢悄悄問了句:“鄒小姐現在在?”
“單幹。”鄒燕倒是答得痛快,“我現在很少出來唱了,平時在家畫畫。現在圈子裏的那些人,我看不慣。有時陪陪張猛出去旅遊。他忙,反正我隨意。”
嶽超想這鄒燕與張董也就是張猛,到底是?不像是夫妻,那麼就是……且不問了。正好手機響了。
是葉書文。
嶽超說:“我剛從省城回南州,準備晚上過來。”
“不必過來了。我另外有事。再聯係。”葉書文說。
“那好。”嶽超也沒問什麼事,他知道有些事是該問的,有些是絕對不能問的。對於葉老板,他清楚得很,既然說了有事,就是有事。他想起包裏用綢子包著的玉扳指,心裏一瞬間顫了下。把這玉扳指從他的密室裏拿出來,真的比割肉還讓他心疼。但是,沒辦法。他必須如此。就像一個女人不得不獻出自己的貞操一樣,她也是不得不如此。對於寶貝,要獻出,隻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基於情到深處的愛,一種是基於迫不得已的壓。現在玉扳指至少暫時還可以放在他的身邊。他一恍惚,仿佛就覺得又看見三十年前的那個夜晚了。黑漆的墓道,那兩個再也沒有出來的男人,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姓甚名誰。他們當時也是一個圈子,圈子裏隻稱呼綽號。他記得那兩個人一個叫小頭一個叫長發。別的,什麼都不知道了。當然,他還知道他們永遠留在了那大墓裏。三十年了,他們的靈魂還是不是在墓室中飛翔、尋找……
活在光明的人,在尋找更大的光明。
而他們,卻在黑暗中尋找更深的黑暗。
到了南州後,殷夢陪著鄒燕出去逛逛,臨走時嶽超叮囑說:帶張卡,如果鄒小姐有什麼需要的,就消費。殷夢說南州這小地方,人家北京來的大藝術家能有什麼消費?嶽超笑笑,說帶著總比不帶好,以防萬一嘛!
嶽超自己則回到別墅,以最快的速度將玉扳指送回了地下室。出來時,他又看了一遍那些寶貝,幽綠的光芒中,他慢慢地關上了地下室的鐵門。
妻子占小榮告訴嶽超,兒子嶽非又打電話來了,要錢。嶽超說不是剛剛打了五萬過去嗎?占小榮說他出去旅遊了趟,都花了。嶽超想罵一句這狗日的,隻知道花錢。但看占小榮慈眉善目地站著,也便沒說了,隻歎道:“這孩子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懂得心疼錢?我再給他打十萬吧,反正過兩個月他就要回來了。你沒問他考研的事?”
“沒問。”
“唉!那就算了吧。我累了,先休息下。”嶽超回到書房。自從殷夢進入他的生活後,他與占小榮的關係,僅僅維持著一個夫妻名分。占小榮住在前麵的主樓裏,而他則要麼住在耕雲山莊,要麼住在後麵的小樓裏。殷夢是從來不在別墅裏和他一起過夜的。這是個原則,他不會放棄。這會兒,占小榮也沒說什麼,隻是說:“錢重要,身體更重要。好好休息吧!”便自顧去念經了。
書房的隔壁是個小臥室,平時嶽超就睡在這兒。他喜歡一個人睡,少年時是,就是後來混跡江湖,他也不喜歡擠在別的人身邊睡覺。再後來結婚,雲雨之後,他就會翻到一邊,占小榮曾嗔怪他不懂得人間風情。他隻是回以鼾聲。跟殷夢,一開始他倒是喜歡抱著她睡,現在也不行了。他感覺如果那樣,自己的空間就總是被侵犯了似的。他需要秘密,他也是個有秘密的人。這一點,上午在和吳元照說話時,他就曾閃過一個念頭:資本最初的源頭到底在哪裏?是不是正如民間所言:第一桶金幾乎都是黑金?那麼,吳元照當年到底幹了什麼得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或許這都是秘密。蓋茨也應該是有秘密的,隻是他沒有說;李嘉誠也是,說出來的都已經不是秘密。就比如他嶽超,這些年南州還有其他地方也有過不少宣傳,但他何曾說到過三十年前的那段經曆?成功者,是可以略去人生中某一段不光彩或者不成功的經曆的。人們要的,是你成功的放大效應,而對於走麥城,勇於袒露傷口,或許恰恰給了對手最大的機會。
躺在床上,頭腦卻一下子清醒了。
他閉著眼睛算了算,南山礦現在的市值少說也得十來個億吧。雖然這幾年沒請人評估過,但他有概念。如果將這十來個億以及房地產上的十來個億都倒騰出來,像張董和吳元照說的那樣,去投資,那麼他就會真正地走入了資本運作的時代。可是,二十多個億,怎麼投?往哪裏投?風險呢?
理不清。他覺得還得向葉老板報告,同時還得再向吳元照,甚至竇天寶去請教。富豪是學習來的,學習也從來沒有好意思與不好意思之分。他梳理了一下,竇天寶的恒泰實業這些年來與自己的江科還真的沒有直接的業務往來,而且一時也難以想起來誰能夠做這個中間人。好在不急,三十年的時光不僅僅練就了他和江科,也練就了他的好性子,不急,不急,不急才能穩妥,穩妥才能有所成。
晚上,在大富豪888,嶽超請了政協主席王念和文化局局長黃有成來陪鄒燕。在南州這塊地盤上,如果說要請人來陪客,嶽超隻要一個電話,就能讓他想請的人放下手中的活計前來。這麼多年的關係了,有多少人跟江科跟嶽超的關係,早已超越了一般的與企業家的關係。何況用開拓的話說,支持企業家就是支持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即使是領導幹部支持企業家也是領導幹部的職責所在。
鄒燕一見王念,就說主席好帥,是標準的美男子。王念長得確實不錯,身材保持得好,五十多歲了,居然沒有將軍肚。聽鄒燕一誇,這個久經考驗的政協主席竟然臉紅了,他望著鄒燕說:“鄒小姐是貌若天仙哪,正應了那句唱詞:天上掉下個鄒妹妹……哈哈!”
黃有成在邊上隻是笑,他近來心思重重,那個南州戲劇團裏的年輕女一號不知怎麼的懷上了。那女孩子平時看起來文靜得像一潭水似的,這會兒捂著肚子給他下了最後通牒——要麼娶她,要麼給她二十萬。這兩者對於他都難辦。娶她,不可能。妻子不會同意離婚,組織上也不會同意。二十萬,他是沒有的。這些年來他的所得都交給妻子了,前幾年才開始覺悟起來弄點私房錢,也早花在這女演員身上了。這兩天,他正在發愁錢從哪兒來。這事拖不得,夜長夢多,夜長事也多。要是在這事上被捅了出去,那是很沒意思也沒必要的。所以下午接到嶽超的電話時,他先是遲疑了下,接著就答應了。他看到了曙光。他得抓住。但是,或許正是因為吃了年輕女一號的虧,這會兒,他對鄒燕也沒什麼好感覺。古人說世上最難養的是女人,而女人當中最難養的是娼優。當然現在說這話不對了,可是,就他當下的遭遇,又確確實實地認可這句話。他看鄒燕,覺得那笑聲裏都是陷阱,都是溫柔的致命危險……
王念卻不管這些,與鄒燕一來一往地唱和著。趁這空檔,黃有成請嶽超單獨到小房間裏,皺著眉道:“嶽總,有個事得請您幫忙!”
“好說。”
“是這樣的……”
黃有成剛剛提到南州戲劇團的女一號,就被嶽超給岔開了。嶽超說:“這事就請黃局別說了。”
“怎麼?”
“我不清楚,也不問了。不過我們是朋友,這事得處理。要多少?還是我讓人去處理?”
“這……二十萬。我先借吧。”
“不用了。明天我讓人送過去。”嶽超轉了話題,問,“聽說博物館那邊新近得了件寶貝,是元官窯的青花。下次請黃局說說,我去欣賞下。”
“這個沒事。我來安排。”黃有成因為問題解決了,說話聲音也高了,也爽了。他拍拍嶽超的肩膀,說:“我聽說市裏提出要在南州建幾個特大型企業集團,江科應該在吧?”
“這事不太清楚。”嶽超關鍵是沒了興趣,南州對於他來說,已是狹小的天地了。不過馬成功到南州來後,他們才見過兩次麵。一次是馬成功到任的第二天,由秘書陪著來江科調研,另外一次是前幾天在北京由文化研究會招待,恰好他們都在京,因此又碰了一回。馬成功這人看起來比較含蓄,話不多,對江科對南州首富嶽超,也看不出有太多的熱情。這讓嶽超多少有些不快……他記得馬成功說了句話:是企業的還給企業,是政府的還給政府。這就像殷夢曾給他說過的那個什麼聖經上的話差不多,有些玄,有些讓人吃不透。
出來時,殷夢正讓服務生準備取菜。蔣三給嶽超打電話了,說有事要商量。是關於南州礦的事,還說嶽總你這是給了我一個餅子,套在我的脖子上。我難受啊,得合計合計。嶽超不好推辭,他知道蔣三這人的流氓脾氣,你不同他見麵,他就是找遍南州也會攆過來的。嶽超說:“那就過來吧,3個8。”
王念問:“誰啊?”
“蔣三。”
“他……”王念顯出不悅的樣子。
嶽超說:“有事要商量。”
蔣三很快到了,這回後麵沒跟人,隻一個人在服務生引導下進了包廂,見著王念,趕緊喊了聲:“主席好!”又喊了“嶽總!”再睃了下全場,沒喊黃有成,隻對其他人點了點頭,然後坐在嶽超的邊上。嶽超說:“既然都來了,就開始吧,請王主席主持,歡迎歌唱家鄒燕小姐來南州。”
王念坐在主陪席上,他側臉看著鄒燕,臉上竟漾著紅光,說:“鄒小姐是著名的歌唱家,能來南州,是南州的盛事。首先我提議大家共同敬鄒小姐一杯!”
酒幹了。
王念又道:“鄒小姐的很多歌大家都熟悉,我就不說了。到了南州,得為南州唱一曲啊!”
“這個當然。”鄒燕道,“隻要有好詞好曲,我一定唱。”
“那就說定了,將來南州市歌就請鄒小姐來演唱。”王念說,“嶽總到時再請一下鄒小姐,我們服務好,她把市歌唱好。這是功德無量的事啊!我提議,我們再共同敬歌唱家一杯。”
又幹了。
嶽超說:“市歌演唱,非鄒小姐莫屬。至於我們出點力,是應當的。”他又望了望蔣三,蔣三馬上道,“我們也得出力,宣傳南州嘛!好事,大好事!”
鄒燕笑著站起來,說:“我真得謝謝主席了,還有各位老總。我敬大家一杯。到南州來,就是南州人了,我一定唱好。我下午路上看了下南州,真漂亮,清潔,安靜,真是個宜居城市。我以後老了,嶽總哪,能不能在這邊也給我一套房子,我就來這兒了。殷總,沒意見吧?”
殷夢說:“哪有意見呢,歡迎哪!”
鄒燕將酒喝了,大家也都幹了。接著就是來來回回地敬酒。這中間,鄒燕說到動情處,真是風情萬種,連殷夢也都有些眼熱。嶽超卻很超脫,一是因為殷夢在,二是他骨子裏對演員都沒什麼好印象。蔣三的熱情就像打了雞血一般,不斷地敬鄒燕酒。而且還一次次地起身站到鄒燕邊上,惹得王念對他幹瞪眼。有兩次,王念甚至直接打斷了蔣三與鄒燕的對話,橫空與鄒燕喝酒。但嶽超看得明白,什麼樣的鑰匙能開什麼樣的鎖,都是天定的。這蔣三明顯就能看出,就是開鄒燕的鑰匙。
果然,酒席臨近尾聲。蔣三邀請鄒燕到他的俱樂部去為南州市民獻歌,鄒燕沒有任何含糊地答應了。蔣三說:“我不會虧待鄒小姐的。十萬。”
鄒燕唱了句:“真的好想你,感謝你的盛情美意……”
一室大笑。
九點不到,蔣三拉著鄒燕走了。殷夢有些不放心,嶽超說:“沒事。她們都是經過大世麵的人。”
王念看著正上蔣三車的鄒燕,吐了口唾沫,說:“世道,什麼世道?這歌唱家的素質也這麼低下了?”
“歌唱家也是人嘛!”嶽超笑著想起蔣三今天晚上來本是要找他說事的。結果一遇上鄒燕,什麼事也沒說,隻顧著調情了。他想蔣三也還是有些魄力的,他直接開口給十萬,這就比某些人隱隱藏藏地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