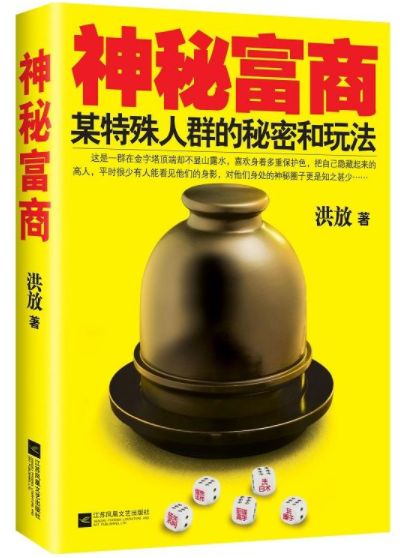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5:極品會所
燈光打在瓷器上,發出幽暗的柔和的光芒,神秘而充滿想像。嶽超慢慢地端詳著,跟在他後麵的是博物館的年輕的研究員小高。小高向他介紹說這件東西是從南州山南縣的一件古墓裏發掘出來的,僅有一件,很奇怪。經過專家鑒定是元青花,而且是官窯造。
嶽超並不關心這些,他隻關心這瓷器在他麵前所閃出的那迷人的光澤。
這光澤直達他的心裏,與他那些寶貝們的光澤交合在一起,迷幻、古遠、幽深且無比的內斂。
他足足看了半個小時。
小高問:“嶽總對瓷器有研究吧?”
“隻是看看。”
“我覺得嶽總是懂得瓷器的。其實這些物件在地下埋了那麼多年,今天出來就是希望能被有識之士讀懂的。”小高開始浪漫了,“每一件瓷器都有精神,都附著著它曾經的美麗夢想。”
“應該是的。”嶽超說,“不過那隻是曾經的夢想,永遠不會有人懂的。無論是在地下,還是在這燈光之下。”
“元青花曾是中國瓷器的高峰。精美絕倫,又賦予創造之美。我看每一件青瓷,都覺得如對美人。”小高指著瓷器,說,“比如這件,我會想像誰曾是它的主人,一位長者?一位少年?或者一位少女?也許隻是一位普通的窯工,甚至是從窯裏出來就被帶到了這墓裏。它一定是有故事的,隻不過是我們後來都無從知曉。”
“它拒絕知曉,也不需要知曉。”嶽超打斷了小高的話,說,“我想再靜靜地看幾分鐘。”
“好吧。”小高退到門邊,隔著幾米地看著嶽超。這個南州第一的企業家大富豪,此刻正靜心於一件才出土不久的青花瓷,誰能想到一個叱吒風雲的企業家,內心也會有這麼一片難以讓人捉摸的世界呢?
又過了十分鐘,嶽超才回頭身來,又回頭看了眼那件放在櫥中的青花瓷,歎了口氣,一言不發地離開了收藏室。就在他剛走到外麵的陽光下時,黃有成打電話來了,問看得如何?是不是一件好東西?嶽超說我不清楚,我隻是想看看,我喜歡看瓷器,但我不懂。黃有成說那就怪了,不過喜歡看就行。下次再有什麼我記著,入館之前就請你看。有喜歡的,就可以變通一下。嶽超懂得這話的意思。現在市麵上的許多文物,一半就是由各級的考古相關人員弄出來的。古墓打開了,卻不見得就有文物。即使有了,也不見得就能被收藏進博物館。環節太多,就容易生出亂子。三十年前他在外地就曾認識一個道上的文物販子,他的貨都是從內行官道上來的,有的甚至還貼著某某博物館、某某文物所的標簽。當然,黃有成講的事,他是沒有興趣的。他隻對他那地下室的寶貝們感興趣。在此之外,他是不會再染指或者收購的。他謝了黃有成。至於上次讓人送過去的那二十萬,黃有成曾說要打個借條,他說也好。黃有成就到江科的辦公室,當場打了借條。他也看了,然後當著黃有成的麵就撕了。黃有成說這……這哪成?他一笑,說這是我的事,黃局長你放心。
嶽超記著黃有成當年對他的一段恩情。這黃有成自然也知道,不然,他不會向嶽超開口的。那是二十多年前,嶽超的重型機械行業剛剛開始運作,資金少,人才少,十分艱難。有一次因為一百萬的貸款,銀行老是批不下來,讓他一籌莫展。就在這時,他認識了時任南州經貿委科長的黃有成。黃有成說我看你嶽超是個能成大事的人,我來替你想辦法,結果就真的將貸款批下來了。這筆貸款挽救了嶽超的江科重型機械廠。一個人一生會遇到許多恩人、貴人和敵人,而在最艱難的時候遇上的,就更加值得一輩子記著。現如今,黃有成雖然是文化局長了,但與江科已無多少交集。何況現在江科要辦的事,黃有成也使不上力了。但是那恩得記著,這當著麵將借條一撕,也是將嶽超內心裏那一份記著和感恩撕沒了。一個成功者,要懂得用人借力,但人生路漫漫,更要懂得舍棄一些人、放下一些事。否則,背著包袱前行,充其量也隻能是隻勤勉的蝸牛,而不會是奔馳的駿馬。
葉書文到中央黨校學習去了。嶽超剛聽到這消息時有些吃驚,怎麼才到省裏就被派去學習了呢?不會有什麼事吧?他打電話給葉老板。葉老板說都有這麼個過程。他因此就放心了,說既然這樣,我下次到北京專程去看望葉老板。葉書文說那倒好,到時聯係我。不過這邊學習搞得認真,得提前聯係,不然到時不好請假。嶽超說那是,放心。心裏卻想大有大的難處,他又想這跟商場上也沒什麼區別,小富豪在當地,像螃蟹一樣的橫行,可是見了大富豪,立馬就變成了小蟲子。特別是富豪們之間,那就是財富和名聲讓你不得不低下頭。都一樣,都一樣囉!
不過北京是真的得去,上次跟吳元照談了,要請張猛張董來給江科操作,看能不能在資本運作上做些文章。這事因為張董隻在江南呆了一天而沒細談,得到北京當麵拜訪。那個鄒燕鄒歌唱家,倒是又來了南州一次,要在南州拉些讚助,出一張《南州好》的MTV。歌唱和曲子都由她來請人,到時拍攝在南州來拍。一應費用由南州這邊承擔,南州市掛一個出品單位的名頭,嶽超做總策劃。這事給王念彙報了。王念說宣傳南州,可以,建議找蔣三,他是念念不忘蔣三那天晚上給他的難堪的。鄒燕湊近王念,身上的香水味直往王念的頭腦裏深入,然後嗲著聲音說:“他哪能跟您相比?不是一個層次的人。他隻不過是個暴發戶,這樣的人我見到了,應付而已。而您,我是認真的。回北京後我就想著再見見您,好好說說話,聽聽您教導。這不,專門來拍《南州好》,我不就是想多當麵向您討教嗎?您不會看著我從遙遠的北京飛過來不理睬吧?”
王念眯著眼,說:“好,好!這事我讓有關部門策劃一下。明天開個會,你說說想法。至於投入這一塊,我來請政府支持,當然也可以請些需要宣傳的企業來支持。”
鄒燕當晚就在大富豪888宴請王念,當然錢是嶽超出的。嶽超沒參加,隻讓殷夢去陪了下。殷夢回來說,沒想到現在的歌手們還真的開放,還有那個王……,平時看著挺嚴謹的,怎麼也……嶽超說各懷企圖,各有所思啊!
嶽超不想得罪鄒燕,也沒必要,因此鄒燕在南州,他囑咐殷夢安排好食宿,至於拍片子的事,全部由政協那邊負責,江科不參與。他隻是有一點不太明白,上次就聽賈晴晴說鄒燕和張董一直在一塊兒,既然在一塊兒了,怎麼還會為了幾個錢如此招搖,如此低俗呢?或許張董也隻是作戲罷了,都是戲,那就都放開了。唉!
就在嶽超準備第二天進京的時候,蔣三來了。
蔣三一進門就顯得消極,粗雪茄隻冒煙不見亮,臉色也不太好看。嶽超讓人上了茶,蔣三說:“嶽總哪,你可是把兄弟我給坑了!”
“坑了?這怎麼說呢?”嶽超嘴上問著,心裏卻有底。自從兩個月前他讓蔣三正式管理南山礦後,當地的村民一直不斷上訪、堵門,環保部門也經常去催促整治。礦上的正常生產秩序受到了很大影響,日產量下降了一半。蔣三一開始上了些兄弟,結果村民來得更多。那陣勢,連蔣三也覺得不能再擴大了,隻好收兵。他又讓人暗中去瓦解那些村民中的首要分子,結果也無效。村民們達到了協議:誰要是接受了礦上的好處、幫礦上說話,他們一家就是全村的敵人。誰願意當全村的敵人?他讓人準備送出去的幾十萬塊錢,都原封不動地拿了回來。這下,他真的沒轍了。他隻好來找嶽超。其實上次鄒燕第一次來時,他就準備和嶽超商量下怎麼對付那些堵門的村民和環保部門。後來因為與鄒燕有那麼一曲,才耽誤了正事。不過,想到鄒燕,他倒覺得那小娘兒們不僅嗓子好,身子倒真的嫩。如今,居然跟王念那老頭兒摻和到了一塊兒,真的是簡直叫人不敢相信。也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不過現在蔣三可沒心思去憐香惜玉,他要讓礦上正常生產,要嶽超出麵來給他方子。他喝了口茶,嶽超皺著眉,說:“你沒動家夥吧?”
“沒動。他們人多。”
“那就好,千萬不要搞僵了。我們要分析一下他們為什麼鬧?為什麼堵門?”
“不想讓礦搞下去了嘛!”
“不對,不是要讓礦倒了,而是要得到利益。我以前搞那麼多年,他們也一直在鬧,我就一直跟他們糾纏著。鬧得厲害了,給村裏一些利益,讓所有村民都得到。得了利,他們就會安靜一段時間。”
“嶽總哪,現在可不一樣了。你知道他們提出什麼要求了嗎?老李沒說吧?”
“什麼要求?”
“收回南山礦。說南山礦坐落在他們村,就是他們村的資產。要麼收回,要麼給他們采礦租金。”
“租金?”嶽超還真的沒料到這一著,他覺得這背後也許有高人指點了。
“一年兩千萬。”
“這……”嶽超說,“不可能。礦山是國家的資產,我們是正式取得礦山開采權的。這個不能答應!”
“可是不答應,門天天堵著,連小火車都被堵著不能到碼頭。你說怎麼辦?依老子當年的脾氣,索性做了那幾個帶頭的,我看他們能怎樣?”
“這可萬萬不能。事情沒到那一步,就是即使到了,用黑道上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人命,千萬別去碰這個釘子。全國都在打黑,何必硬往上撞呢!”嶽超勸著蔣三,其實也真的怕蔣三去硬碰硬地亂來,畢竟礦還是他嶽超的,蔣三隻是負責開采。要是真出了事,嶽超是脫不了幹係的。
“那這事……就這麼停了?”蔣三臉氣得黑紅黑紅的。
嶽超給他續了水,說:“別急。現在南山礦麵臨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環保,一個是村裏。環保好對付,大不了就是罰。對於村民呢,我一直在考慮,真不行,就按照他們的方案,讓他們入股。把他們套進來,他們總沒話說了吧?”
“兩千萬?那我還開什麼礦,賠得褲子都沒得穿了。”
“當然不是兩千萬。這個我再考慮考慮。等我從北京回來我們再定。”
“那得快點。這兩個月我可是賠了好幾百萬了。”蔣三接著問起鄒燕。嶽超說正在跟市裏談拍片子的事。蔣三說這些娘兒們都是隻認錢不認人的。那天晚上到我的俱樂部唱了兩支歌,我給了十萬。這次來之前讓我給她打二十萬過去,說急用。我沒打。這不,來南州連招呼都不跟我打了。絕情哪!嶽超笑著勸他:“她是她,你是你。管她絕情還是怎樣,隻要你蔣總不多情就行了。跟她,也就逢場作戲罷了,戲唱完了,就別再想了。”
蔣三說:“還是嶽總高明,難怪殷總那麼死心踏地地跟著你呢!”
嶽超沒回答,蔣三便告辭,說快點從北京回來,礦上的事我真的頭都大了。
嶽超相信蔣三說的是實話,像蔣三這樣流氓型的人物,是有些霸道有些蠻橫,但是講話卻往往是不太繞彎子的。何況嶽超自己心裏也急,好不容易把南山礦這個燙手的山芋給送到了蔣三手裏,不至於讓他又送回來吧?
他記著張董給他說的話,可以把南山礦當作固定資產抵押,獲得一大筆流動資金的。這點很重要,所以他得守著南山礦,他要讓南山礦成為他資本運作的第一筆賭注。
第二天下午,嶽超到了北京。殷夢沒來,她得陪著鄒燕。臨走時,嶽超讓她告訴鄒燕他要去北京,鄒燕說那不好意思,我得在南州再呆幾天,下次嶽總到北京我再請嶽總喝茶。
到北京後,嶽超先住了下來。這回他沒麻煩南州文化研究會,而是直接入住了。稍稍梳洗,他就打電話給葉書文,說他到了,晚上請葉老板出來坐坐。葉書文說那好,我晚上正好沒課。他說那這樣,我馬上帶車過去接您。
賓館是有租車服務的,嶽超租了輛奧迪A8,其他的車到黨校那兒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那是什麼地方?要注意影響,尤其要注意不要給葉老板帶來麻煩。一個小時後,車子到了黨校大門口,門衛不讓進,他隻好請葉老板出來。葉書文磨蹭了半個鐘頭才出來,嶽超在車內看著平時頗有官威的葉老板此刻正在匆匆地往門口走,那姿勢那身形,竟看不出一點官威了。可見到了這大官聚集的地方,官威是擺不得的。就像在吳元照麵前,他在南州偶爾還擺擺的富豪的架勢,也隻好老老實實地收斂了。
上了車,葉老板說就去上次我們去的那地。
那地在市郊,門頭溝。
一座掩映在綠蔭叢中的會所,從外麵乍一看,幾乎同周邊的鄉村人家沒有什麼兩樣。但是進了大門,穿過綠化區,裏麵便是幾排並不高的四合院建築。這是這會所的特色,全部是四合院,大的有三四十間接待室,小的僅三四間。大部分客人來了,都是直接訂一座四合院。然後關上門。裏麵的服務也是有特色的,有中式服務、有日式服務、有泰式服務、還有非洲式服務,服務生和服務小姐也是各國盡有。但是,一般情況下你是很少看得見他們的。隻有你點了服務,他們才如同蝴蝶般悄然而至。嶽超第一次來這裏,是和南州文化研究會的魯天主任一道。魯主任說讓你開開洋葷,結果點了非洲式服務。服務小姐黑得比電視上還純粹,不過說真話,細看下來,還真美得瓷實。但是嶽超到底有些不太適合,最後換了日式服務才作罷。那次他就注意了下,這些服務小姐沒有從正門進來,那從哪兒悄然而至的呢?難不成真是飛了進來?他觀察後才發現:四合院大門關上後,與外麵的聯係全部是地下暗道。她們就是從地下暗道上來的。這看起來平常的會所,卻真是機關重重、山重水複呢!
嶽超點了座最小的四合院,三麵牆,一麵房子,四間。中間是茶室,兩邊各一間休息室,還有一間棋牌室。坐定,他問葉書文:“來點日式點心?還是……”
“就中餐吧。我們兩個人,就不搞那形式主義了。”葉書文說:“學習也有好處,可以少喝酒少應酬。輕鬆!”
“那是啊!葉老板難得如此輕鬆,權當休息吧。”嶽超邊說邊讓站在邊上的服務生上兩套中式餐點過來。同時來一瓶高檔紅酒。服務生說紅酒有三百英鎊到一千英鎊不同的檔次,請問客人需要點哪一種?嶽超望望葉書文,然後說就六百英鎊的吧!六百英鎊按時下的彙率也該是六七千元,這個檔次也夠了。葉書文沒說話,隻是看著窗外的樹。那些樹在夜晚的燈光下顯得更加迷離、曖昧和不動聲色了。
菜不多,精致,可口,兩個人邊啜飲紅酒,邊談話。嶽超就將他打算進軍省城商務圈的想法說了,又提到與吳元照及張董的見麵,當然還重點提到了南山礦的問題,說打算將南山礦搞資產抵押,從銀行融出一部分資金來,進入資本市場。葉書文聽了,先沒做聲。等酒喝完了,飯也吃過了,才說:“嶽超啊,想法很好。不滿足於南州,是對的。何況現在南州的情況有變化,走出來是必須的也是合適的選擇。不過我倒是有些建議,一個是南山礦這一塊,那必須操作好,否則會成為你將來發展的最大的製約;另一個是進入省城商務圈和資本市場,你暫時還沒有什麼經驗,這得有人引領。當然,你同吳元照見了麵,很好,也可以再拓展一些,包括北京的商務圈。明天我給你介紹一個北京的大商人。你們好好談談,看能不能合作。至於資本運作這一塊,我不是很懂,要請行家來把關。我對江科是很重視的,你得一步步地都走好。現在的市場,機會多,風險也多。許多大企業、許多大富豪,就是因為投資不慎,一夜間可能破產了。還得穩,穩中求進。”
“葉老板教導得對,所以說我得來聽葉老板的意見,這意見給了我信心,也給了我提醒。我會好好謀劃的。”嶽超說著,就從包裏拿出他一直從南州就帶在身上的玉扳指,打開綢子包裹,遞到葉書文手上。葉書文手有些輕輕顫抖,在燈光下慢慢地看著,又反複地對著光源,眯起眼認真地審視著。良久,他將玉扳指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到綢子包裹裏,說:“好東西,真東西。我估計是元以前的。”
“葉老板果真慧眼。道上人也說最晚宋朝的,還有說是唐朝的。這個東西小,適於把玩。葉老板就留著慢慢欣賞吧,反正好東西也得懂它的人來收藏才合適。放在我這兒就沒意思了。”嶽超雖然如此說著,心裏卻一陣陣地疼。他得親手將自己的寶貝送出去,卻還得裝出無所謂的樣子。這種疼,除了往骨子裏爬外,誰能知曉?
葉書文也沒推辭,但是將東西又遞給了嶽超,說:“還放你那兒吧,等回江南再說。我在黨校這邊,不方便。”
“也好。”
十一點,車子回到了黨校大門口,葉書文臨下車時,嶽超又遞了張卡過去,也沒解釋,就告別了。
初夏的北京之夜,人聲嘈雜,嶽超回到賓館,就看到殷夢打了好幾個電話,又發了信息。他趕緊回過去,卻沒人接。隻好回了條短信:已安全到。晚與葉老板聚。
其實,剛才從會所回來後,嶽超就有種被掏空的感覺。倒不是說累,更不是說身體上的疲勞,而是心理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空洞與無聊感。早些年,在江湖上跟著那些混混們一塊時,有時得了幾個錢,總要找路邊那些透著粉紅色光亮的小洗頭屋,在裏麵將幾個錢填了窟窿才滿足。後來,自己辦廠,真的有了一大筆錢時,他也曾在南州之外的地方,特別是那些賓館,晚上經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電話,著實放蕩過幾回。有時是河南姑娘,有時是雲南姑娘,有時是四川的,有時是江南的,各種各樣,風姿萬種,隻要你出錢,什麼事都幹,什麼名堂都能想像得出來。十幾年前,有一次不知怎麼的他惹上了麻煩,下身得病了。這下可結結實實地讓他戒了那愛好,不管到哪兒,都不再好那一口了。就是現在,哪怕在剛才那會所裏,他也是隻接受按摩,其他的一概不要。如果小姐不願意,他照樣會付錢。有時,他甚至連按摩都不要,隻在裏麵偷閑睡上一覺。但他不能對葉老板說自己沒有享受服務,那是忌諱。他也裝出十分享受的樣子,兩個人都不說,卻有同一條繩子上的螞蚱之感慨。特別是那些涉及企業經營的業務部門的領導,有時還非得他親自陪同。他往往是裝模作樣,或者中途脫逃。他漸漸接受不了那些女人的冰冷的手指,還有滿身的脂粉氣息。他喜歡殷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殷夢天然,殷夢靜下來時,就像他那些地下室裏的寶貝一樣,沉靜如水,如幾千年悠悠時光。
衝了澡,上床看了會兒電視,嶽超便漸漸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