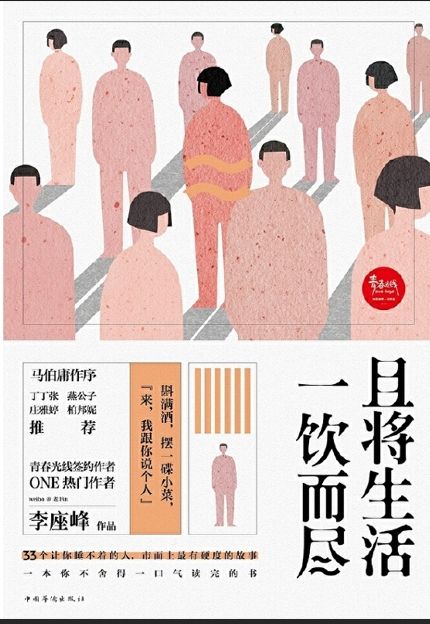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01 神探
一九九三年春天,張本望做刑警的父親破獲了一起特大刑事案件,獲全國嘉獎,其事跡還被拍成了連續劇。十七歲的張本望坐在小板凳上看著電視裏一個陌生人扮演著自己的父親,暗暗立誌長大後也要當一名刑警。
但文化課奇差的他連警校都考不上。
張本望在二十五歲的時候連著鬧了好幾天絕食,終於促使父親動用關係讓他成為一名戶籍警察,雖然沒有刑警威風,可好歹也算有套警服。戶籍警察工作相對輕閑,張本望一有時間就坐在辦公室裏看那些從圖書館借來的心理學書籍。
那會兒好多科班兒出身的警察辦案都還處在跟鄰居親友打聽死者生前跟誰有過節和誰吵過架,然後把那人逮回來揍的階段,哪有人研究什麼犯罪心理。經過幾年研讀,張本望空有一肚子理論知識卻無用武之地,隻能在他負責的這一片兒居民區裏找點兒樂子。
“家裏就您一個人?”張本望敲開一戶人家的門,捏著筆問開門的大姐。
“哦,我還有個兒子,上初二。”
張本望朝灶台上掃了一眼:“孩子中午回來吃飯嗎?”
“不,他帶飯。”
“您中午一個人吃的飯?”
“嗯。”
“一個人吃飯怎麼收拾出兩副碗筷?”張本望又看了一眼灶台上那堆還沒來得及刷的碗碟,“三個菜,兩葷一素,大姐您可夠能吃的。”
大姐有些慌張,但看到張本望那套不合身的製服時馬上又鎮定下來,撩了撩頭發倚到門框上。
“孩子他爸常年在外麵出差,家裏家外都我一人操持,幹得多就吃得多。怎麼了?吃得多犯法嗎?”
張本望倒有些不好意思,扶了下眼鏡兒:“沒沒沒,您怎麼吃都不犯法。”
張本望說著轉身準備離開,想了想又回頭:“跟裏屋那位說一聲,下次來別把摩托車停胡同兒裏邊兒,鄰居們來回走路不方便。擱胡同口兒就成。”
大姐臉色一沉,“砰”的一聲關上門。
張本望扯了扯歪到一邊的領子,朝下一戶人家走去。
大姐直奔裏屋,跟從裏麵疾走出來的男人撞了個滿懷。
男人捏著腰帶試了好幾次才給穿進腰帶扣兒裏:“走了嗎?”
“你慌什麼?!走了。”
男人把門推開一條縫兒往外瞧,見外麵人影兒也沒一個,關上門回身抱住大姐。
“走,再回去躺一會兒。”
“哎呀,不是剛躺完嘛,你先讓我把碗洗了,再陪我說會兒話兒。”大姐推開男人開始洗碗。
男人又去把門推開一條縫兒朝外麵看了看。
“那算了,我走了。”看外麵真沒人,男人從裏屋拿出外套邊穿邊說。
“哎,這就走了啊?下回哪天過來啊?”
“不來了,以後都不來了,再來就讓人逮著了,你們這兒的小警察挺厲害。”
“哎呀,警察不管這事兒!”
“那我也害怕!”
男人撂下這麼句話推開門一溜煙兒走了。
年至而立,張本望的父親在一次抓捕行動中被逃犯開槍打中脖子,由於地處偏僻,送到醫院時已無力回天。
張本望給父親送完終,隨即要求加入刑警隊。幾個領導起初不同意,後來看在他烈士父親的麵兒上,答應說以後有任務的話會找他配合行動。
張本望穿鞋一米七出頭兒,體重不到六十公斤,看著刑警隊的同事們個個高大健碩,也覺得自己這樣兒進刑警隊實在給人民警察抹黑,於是每天下班後就跑到刑警隊的訓練館打沙袋。兩禮拜之後,張本望體重上升了一斤。他興致勃勃地找了一個刑警同事跟他對練,被對方一腳踢折了左小臂。
所有人都埋怨那個同事,說他對菜鳥兒下重手。
“我真沒使勁兒!”
一個月後,那同事落下個跟祥林嫂一樣的毛病。
張本望的胳膊剛好利索沒幾天,局裏接到舉報說郊區某處民居裏有個人很可疑,有可能是在逃的通緝犯。
上頭經過研究,準備派看起來最不像警察的張本望扮成個收廢品的先去踩點兒,確認之後再實行抓捕。
蹬著個破三輪兒的張本望敲著掛在車把下麵的破臉盆,每隔十來秒吆喝一聲“破爛換錢”,慢慢地騎進由幾排小平房組成的居民區。
正值晚飯點兒,上班的也都回家了,時不時地有人出來拎著破銅爛鐵叫住張本望,張本望就停下來稱重算錢。
“喲,大媽,您這搪瓷臉盆都鏽成篩子了,這我沒法兒收,收上去沒人要啊。”
“哦,是嗎?那麻煩你幫我撇了吧,擱家裏也礙事兒。”
張本望把臉盆接過來隨手扔進三輪車裏,又把大媽拖出來的一堆紙箱拆開疊在一起捆好,用秤杆子另一頭兒的鉤子勾起來稱。
“一塊九,給您算兩塊!”
“這麼一大堆紙殼兒才兩塊啊?”大媽不太高興。
“紙箱不值錢啊大媽,您這小區普遍沒啥油水兒啊,我來這兒轉悠快一個鐘頭了,就收了幾個瓶子外加您這一堆紙殼兒。”
大媽“哼”了一聲,接過錢往兜兒裏一揣,“你那是來晚了,上個禮拜一個收破爛兒的在隔壁單元東邊兒把頭兒那家花三百塊錢收了個八成新的電冰箱呢!”大媽邊說邊往回走,“那家估計是不想過了。”
張本望心裏咯噔一下,收拾好東西爬上車子,朝隔壁單元東邊兒把頭兒那家蹬去。
“哎,收破爛的!”
張本望慢悠悠地從那家門前經過,騎出去二十來米時,被身後一個低沉的聲音喊住。他捏住車閘回頭看去,見一個蓬頭垢麵的男人從那戶人家的門裏探出頭來。
“哎,你過來啊,快過來!”
“哦,來啦來啦。”張本望費勁巴拉地來了個U-turn,把三輪車蹬到那男人跟前。
男人從身後拽出一個滿是啤酒瓶子和空易拉罐的蛇皮袋丟到張本望麵前,自己抻著脖子朝西邊兒看了看。
張本望蹲下來一邊分揀一邊數著,同時用餘光打量那男人。這人的褲子膝蓋處折痕十分嚴重,腳上穿的不是拖鞋而是膠鞋,極有可能就是和衣而睡從不脫鞋隨時準備跑路的通緝犯。
“九塊五。”
張本望直起身子準備掏錢。
“不用給我錢,你幫我去附近超市買包白塔,剩的錢你留著。”
張本望一愣,馬上高興地點點頭轉身就走。
“好好好。”
“回來直接扔院裏就行。”男人說完關上門。
等在居民區外麵的同事們聽張本望一說,立刻分頭從幾個方向朝門口停了輛三輪車的那戶人家包抄過去。
張本望帶著大夥兒跑在最前麵,因為興奮,臉上一陣陣發緊。
“爸,您要是泉下有知的話就保佑保佑我,兒子今兒要給您老露臉了!”
想到這兒的時候,張本望人已經來到了那戶人家門外。
“大哥,煙我給你買回來啦!大哥?”
張本望在外麵喊了兩聲,門裏一點兒動靜都沒有。
“踹門!”帶隊的在身後低聲說道。
聽到這句話,張本望右腿頓時似有神力注入,兩步助跑後一腳踹在門上。那門沒鎖,毫無阻力地應聲彈開,把他晃得右腳往前狠邁一步差點兒閃了大胯。張本望剛收回腳站穩,那門從牆上又彈了回來,直接把他拍了個滿臉花。與此同時,院裏一直舉槍對著門口的男人開槍了,子彈打在了包著鐵皮的門上。
張本望捂著鼻子蹲在地上,幾個刑警把他拽到一邊後趴下來,推開門一起開槍把那男人打傷擒住送往醫院。
到了醫院把那人的臉擦幹淨一認,果然是在逃的殺人犯。
鼻梁上貼著紗布的張本望在公安局內部會議上領了個獎狀。
當晚,媳婦兒給他做了一桌子好菜,可張本望卻一直悶悶不樂,他覺得作為一個警察,踹門時讓門把自己鼻梁拍斷實在丟臉,不光自己,連帶著死去的老爹也跟著丟臉。
二〇〇五年開春,張本望一家住進了樓房。
半年後,他所在的小區出了樁離奇的失蹤案。
收清潔費的阿姨向物業反映,說2號樓1單元602的住戶一連幾天家裏都沒人。物業去問601的住戶,也說大概有一個來月沒見著這家人了。回去一查,這戶住著一個離異帶孩子的女人。
接到物業報案後,警察先查到這女人的工作單位,打電話過去一問,得知她已經兩個月零七天沒上班,並且沒有任何形式的請假。警察隨後又去那孩子上學的學校了解情況,老師說這孩子兩個多月沒來上學,打發同學去家裏找總沒人。
警察來小區調查的時候,剛巧張本望下班回家。
張本望問明了情況後要求跟著一起上去看看,對方同意了。
撬開房門後,張本望和幾個警察走進602。
張本望吸了幾下鼻子,除了長時間不開門窗所帶來的黴味兒之外沒有一絲屍臭。冰箱裏的食物已經全部腐敗。地麵很幹淨,有明顯的清洗痕跡。木質菜板上有常年用菜刀切菜剁菜所形成的凹陷,卻看不到菜刀。爐灶上還放著一口被鋼絲球蹭得發亮的煎鍋。張本望在垃圾桶裏翻了翻,沒找到鋼絲球。
“回去先報個失蹤慢慢查吧。”
“等一下。”還在廚房轉悠的張本望說著把頭伸到抽油煙機底下,扭頭瞅著上麵的集油罩,“老王,給我把鑷子。”
張本望用鑷子在集油罩上刮下來一些油垢,放到塑料袋裏封好遞給老王,“麻煩幫我送去化驗一下,辛苦哈!”
老王接過塑料袋,又看看張本望,點點頭沒說話轉身收隊。
化驗結果,那油垢裏有人油的成分。
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但現場被清理得過於幹淨,除了人油之外找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警方召集人手密集調查了一個多月,毫無進展。
這天,在警局連續加班了好幾天的張本望也開始泄勁,決定回家好好睡一覺。騎著自行車經過2號樓時,他心有不甘地朝1單元602的窗戶望了一眼。
這一眼,讓張本望渾身一激靈。
他跑回家裏拿了些吃的和日用品,跟媳婦兒說了句要去執行任務就下了樓,直奔2號樓1單元602。
門沒鎖,張本望走進去來到窗戶前,看看下麵沒人注意,就伸手拉上窗簾,然後在窗邊坐下,邊吃邊透過窗簾縫兒看著下麵來來往往的人。
張本望跟局裏報了病假,每天就坐在602的窗戶邊往下看,直到半夜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又跑回去繼續看。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上午,一個中等個子的人出現在小區裏,這人雙手插在褲兜兒裏匆匆地走到2號樓底下,突然抬起頭朝1單元602的窗戶望過來。
張本望躲在窗簾後渾身雞皮疙瘩暴起。
那人朝這邊看了幾秒鐘後轉身快步走出小區,張本望起身瘋一樣地追了下去。
那人正走著聽到身後有腳步聲,回頭看見朝他狂奔的張本望,拔腿就跑。
對方一開跑,張本望就發現自己的速度不如人家,他大喊一聲:“再跑我開槍啦!”
那人馬上開始跑S形路線,張本望漸漸地追近了。
“站住!”
張本望再次喊道。
前麵那人聽見張本望越追越近,一把拽過路邊攤煎餅的大嬸,勒住她的脖子回身惡狠狠地看著張本望。
“過來我就弄死她!”
張本望往前衝了好幾步才刹住,雙手支著膝蓋呼哧呼哧地喘。
“把槍扔給我!”
那人又喊。
張本望心說,媽的,要是有槍我早就用了,還能留著扔給你?
“快點兒!不然我掐死她!”
這句“掐死她”給張本望提了個醒,“掐死”?對啊,這小子手裏沒武器,掐死個人得好一會兒呢!
張本望想到這裏猛地撲過去,和那人扭打在一起。
大概兩個回合不到吧,張本望就被對方反擰住胳膊摁在地上,對方一邊搜他的身一邊問他槍在哪兒。
“你別摸了我沒槍!”
聽到張本望說沒槍,剛才被挾持的大嬸放心地從煎餅攤子上抄起舀麵糊的大湯勺,照著那人後腦勺掄圓了就是一下。
那人慘叫一聲鬆開張本望的胳膊,捂著腦袋在地上打滾,大嬸上前一腳踩住那人的肚子,手裏的大湯勺上下左右翻飛,專挑那人雙手沒護到的地方敲,一會兒工夫那人就不動彈了。
“你是警察嗎?”大嬸從煎餅攤上扯過一塊抹布邊擦勺子邊問。
張本望點點頭,揉著胳膊吃力地站起來。
“唉,這身板兒的也能當警察了現在,哪兒還有個好。”
張本望從地上撿起眼鏡兒戴上,看了看比他粗好幾圈兒的大嬸。
“謝謝。”
原來,一個多月前張本望在1號樓樓下向上看的那一眼讓他想起之前讀過的一本關於犯罪心理的書,說有很多罪犯會忍不住再次回到作案現場看一看。
抱著這點希望,張本望在602埋伏了一個多月,居然真的被他等來了凶手。
那人被帶到局裏後,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並帶著警察去小區附近的河邊撈出了那把用來分屍的菜刀。這人是在夜裏尾隨女被害人回家,將其強奸後連同孩子一起殺害。接著剔骨碎屍,並花了好幾天的時間用煎鍋把肉塊煎成焦炭,用煤氣灶的火把骨頭燒酥,然後通通搗成粉末用馬桶衝走。
鑒於張本望在這個案子上的傑出表現,局裏決定送他去刑警學校學習,畢業後回來當刑警。
誰知張本望不但一口回絕了局裏的安排,連片兒警也給辭了。
張本望拎了瓶白酒跑到父親墳前,喝一口倒一口,絮絮叨叨地說了一個來小時,中心思想就是自己實在不是幹警察的料,再在公安局待下去,自己保不住命不說,恐怕還要連累別人。希望父親理解自己的決定。
往回走時,晴天響了聲霹雷。
張本望停住腳仰頭兒看著天,笑了。
“爸,你嗓門兒還是那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