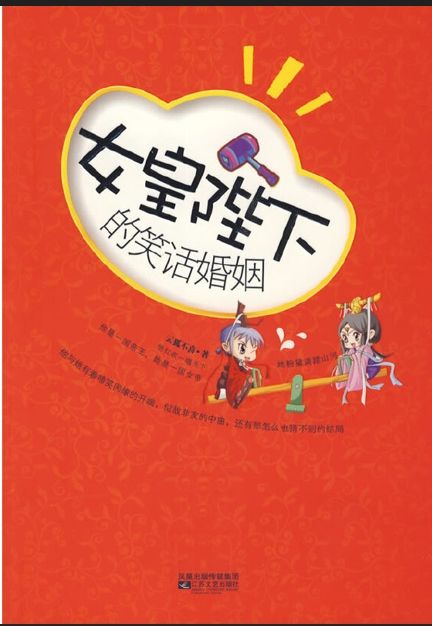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四章 是男人就不打賭!
葉蘭心這人不正經歸不正經,說過的話倒總歸是算數的,她說不打算近期回國了,結果,就果真不能近期回國了,注意,是“不能”。
抽掉牙事件的第三天,葉蘭心由新後和德熙帝共同主持的賠罪宴上一回來,掀開車簾的一瞬間,所有的侍從女官都傻掉了。
且說早上出去的時候,她好歹還隻腦袋上纏了個布條,臉頰青腫,現在回來了,好嘛,一身全是白布條,從脖子往下包得跟白粽子仿佛。
……這是怎麼了啊?被門擠了還是被馬踢了?
一群人盯了一會兒葉蘭心,立刻轉頭,眼光齊刷刷地看向馬車旁邊護送她回來的大越平王。
看著麵前一群拿眼刀剜他的,並且有架勢立刻圍過來的女人們,蕭逐歎氣,止住了生平第一次想拔腿就逃的衝動,三言兩語,把事情分說明白。
原來這次賠罪宴上,蕭逐的生母楊太妃也在場。
宮裏是消息傳得多快的地方?葉蘭心的求親能瞞得了誰去?於是乎宴席上太妃就不由得多看了葉蘭心幾眼。
所謂擒賊先擒王,想要泡到一極品美男,攻克極品美男他媽那是理所當然的任務,於是在太妃麵前,葉蘭心表現得那叫一個端莊,配上本就清秀的容貌,玄色宮衣,瓔珞嚴妝,十足十一副未來國君的矜貴之態。
蕭逐十五歲上曾迎娶過元妃柳氏,可惜柳氏紅顏命薄,婚後未到三年就香消玉殞,結果一晃眼看快十年,他就沒提過再娶的話頭,現在難得聽到他和哪個姑娘家傳出了點兒“親密接觸”,太妃就不由得不把心思朝兒子的老婆孩子熱炕頭方向聯想。
一頓飯吃下來,蕭羌半路有緊急公務處理,告辭離開,新後也不方便多待,席麵上立刻就隻剩下太妃蕭逐他們三人。葉蘭心倒一貫坦然大方,蕭逐看到她就不期然想起昨天的事情,言談之間就有些心不在焉,太妃曆經三朝,後宮風浪裏打滾過來的,何等乖覺?察言觀色之間,就隱隱看出兩人之間波濤暗湧,心下立刻起了推波助瀾的念頭,說了沒幾句話就借口退下,順手把宮女帶走,刹那間,小廳裏就隻剩下蕭逐和葉蘭心兩兩相對。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從蕭逐的語焉不詳裏,大致可以推測為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發生了“儲君色令智昏”這個基本性事件,然後在基本性事件上延伸,大概是葉蘭心因為什麼,整個人橫過桌麵,結果一不小心,沒什麼力氣的爪子沒撐住,人整個撲在菜上了。
幸虧今天沒吃火鍋啊~蕭逐描述完畢,塑月儲君很感慨地加了一句自己的總結。
然後眾女官語:殿下,我們覺得照您這和平王殿下見一次麵殘一次的狀況看來,您還是放棄這個美人的好……
葉蘭心豪情萬丈,說沒事,就算殘了咱也心殘誌堅!
女官們就隻好一邊對天仰淚,一邊給真都帝打小報告,說恐怕儲君暫時回不來了陛下……
十幾天後,真都帝萬般無奈的回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她去吧……
於是,塑月儲君葉蘭心因受傷故,羈留大越。
而幾乎就在同時,東陸列強之一,榮陽帝國太子娶妃,塑月派出的慶賀正使,正是剛剛病愈的成王葉晏初,隨行武官是當色名門第一,赤色之陽家的現任族長,時任殿前左都指揮使的陽泉。
外人眼裏道,榮陽帝國不愧是東陸昔日第一霸主,如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個太子娶妃,塑月便派出了這樣陣容。明眼人卻都心裏一陣揣測,這位陽家年輕族長的隨侍,是不是代表了某種政治上的動向,而這種動向又能不能代表整個年名會的意思?
於是,這一次出行,萬眾矚目,萬眾猜疑。
唯獨葉蘭心,悠閑度日,詩書晚唱,不亦樂乎。
平心說,葉蘭心這次傷得不輕也不重,怎麼說也需要靜養一段時間,驛館畢竟人多事雜,不方便她修養,德熙帝想了想,就撥了京郊瑞原上一座行館給她靜養。
葉蘭心這幾次受傷雖然主因都是她咎由自取,但是誘因卻不折不扣都是蕭逐引起的,這位年輕的大越親王對此頗有些內疚,反正他在京城也是閑著,在葉蘭心入住行館後,就經常去探望她。
他是武將,雖然精通音律,雅擅丹青,倜儻瀟灑,但與風流二字無緣,每次去看葉蘭心,全然不知道帶些討好女孩子喜歡的東西,隻知道變著法子給她搜找京城裏的良藥,希望她早些痊愈。
對蕭逐這點,葉蘭心搖頭咂嘴,說真是難為了他那麼一張風情萬種的臉啊,你說這大越皇族要把這麼漂亮的孩子保護得多好,才能養出這麼個性格的人?
眾女官心說,隻要遠離你這種人就好了……
這天天氣晴好,外麵的梨樹已開始長了綠葉,一片雪白裏點點嫩綠,偏生最頂上的部分映著陽光又透出點粉白味道,嬌媚可人,又兼有好風送爽,葉蘭心興致來了,喚來琴師在舟上演奏,自己則在水榭裏張了帷幕,靜臥聽琴。
琴師奏的,是一曲雍容華麗《思帝鄉》,葉蘭心靠在榻上,看著手裏書信,旁邊司墨女官伺候著筆墨,根據她的指示處理文件。
拈起一張信箋,葉蘭心看了幾眼,忽然笑出聲來,朝女官晃了兩晃:“阿初和陽泉已經離開塑月國境了。”
女官隻看了她一眼,就決定不去理這個閑荒了的儲君,繼續該幹啥幹啥,葉蘭心兀自托著下巴看手裏的信箋,“阿初這倒黴娃,病才剛好,就要跟著陽泉跋山涉水,希望別半路上出了事才好。”說到這裏,她又長長的歎了一口氣:“不過幸好,陽泉辦事妥貼,應該沒什麼漏子好出。”
聽她說了這句,女官放下筆,正色看向葉蘭心。
葉蘭心手裏攀著柄泥金折扇,似笑非笑的看回去,女官輕聲問了一句,“殿下果真不擔心嗎?”“呀,我擔心什麼?”
“如殿下之前所說,年名會的動作隻是一個警告,但是,殿下,這可是陽家的族長親自出馬和成王一起上路的啊。”
葉蘭心沒有立即回答,她聽了一會兒琴聲,拿扇子柄撓了撓頭,忽然展顏一笑:“我說過的啊,不用擔心。”她對自己的女官搖了搖指頭,“第一,阿初絕對不會背叛我,第二……”她微微彎身,修長纖細的指頭攏著自己膝蓋,一雙眼睛深覺有趣一般的看著自己所器重信任的女官,然後微笑:“陽家不會效忠阿初的。你要記得,陽家從前朝開始,到本朝,近千年時間屹立不倒,始終是名門,在本朝更是名門第一,就一定有他的道理。陽家的立身之道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陽家隻效忠於帝國。你仔細想想,他始終是堅定的站在帝國最高統治者這一邊,對不對?他從不卷入立儲等等事情,這反而確保了這個家族超然中立的地位,才能近千年而不墮啊。”
聽到她這麼一說,女官楞了一下,仔細思量而去,發現麵前笑眯眯的儲君說的,居然分毫不差。
“隻要陽泉不是笨蛋,他就不會放棄自己家族的超然地位,來插手管這檔子閑事。”
“……那……假如陽泉是個笨蛋呢?”女官沉吟著問了一句,卻讓葉蘭心噗哧一聲笑出來。
她晃晃手裏扇子,帶起一線涼風,“陽泉要是個笨蛋,那他和阿初聯手又有什麼關係呢?嗯?”
說完,她直起身子,隨意遠眺,一片平靜煙綠湖麵映入眼中,葉蘭心愜意的一展扇子,輕輕搖了兩下,然後忽然想起來什麼似的轉頭,看著思考她的話的女官,輕輕扯出一抹笑意,扇子在掌心唰的一合,“明白了?”
女官聽到這句,猛的抬頭,似乎若有所悟,對上葉蘭心笑眯眯的眼睛,她慢慢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後再度俯首叩拜,用的卻已是正式稱呼,“臣妾明白了。”
說完,看了眼麵前玄衣青凰,臉帶笑容的女子,女官無聲輕輕一個行禮,退回案前繼續處理文書。
葉蘭心也坐回去繼續幹活,她處理文件極快,過沒片刻就全部處理完畢,一股腦兒丟給女官們複核,便悠閑靠在水榭麵湖的扶欄上,聽著遠處小舟上琴聲嫋嫋,一邊欣賞,一邊按著拍子輕輕的哼著,無限愜意。就在這時,有侍女通報,說平王來訪,葉蘭心想想,扇子一展,說了一個請字,又向四周掃了一眼,女官侍從立刻識趣起身離開,隻留下一葉小舟上載著琴師,遠遠地飄著。
片刻之後,水榭邊綠柳小徑上有沙沙響聲,透過煙綠一層水軟輕紗看去,隻看到朗朗日光下,一名紅衣青年分花拂柳,向這邊而來。
楊柳依依,那人抬頭看向她的方向,看到了簾後的她,一雙明若秋水的眼眸便輕輕斂了一下,頷首示意,葉蘭心眨眨眼,居然難得的沒有不正經,反而按照禮數微微欠身,還了一禮。
看她還禮,蕭逐楞了一愣,第一反應是她是不是吃錯藥了?趕緊搶上幾步,上了水榭,將將要碰到簾子,才想起來兩人身份,便硬生生頓住腳步,向簾後的女子一絲不苟的行禮。
看他那麼生硬刹住腳步,葉蘭心就差不多知道蕭逐剛才想到了什麼,不禁抱著肚子悶笑起來,蕭逐也知道她在笑什麼,也隻能隨她笑夠,自己端端正正在紗簾這端坐定,眼觀鼻鼻觀心,心靜自然涼狀態中。
等她笑得差不多了,蕭逐從懷裏掏出一隻扁玉盒,輕輕從紗簾下麵放了過去,“殿下,這是給您帶的傷藥。”
果然,我說你這男人就一點兒情趣都沒有啊都沒有,這時候不送花不送小鳥不送什麼小玩意,直接點,來包合歡散也成啊,結果是傷藥……
誒……葉蘭心吧嗒吧嗒走過去,認命地接過來,就聽到簾子對麵,那紅衣俊美的男人聲音柔和清澈,對她說了一句話。
他說:“殿下,這藥逐試過了,應該不會再出意外了。”
葉蘭心身上既有瘀青又有摔傷還有燙傷,嚴重的一個部位要塗個三四種不同的藥物,結果大概是多種藥物綜合作用,她身上有些傷口附近起了疹子,有些幹脆就潰爛了。
其實地方都不大,問題也不嚴重,葉蘭心自己都沒放在心上,但是對麵這男人卻知道了,這次再來的時候,就告訴她,為她找到了不會潰爛的藥物。
啊啊,這個男人啊……
想到這裏,葉蘭心泥金扇子忽然就掩住了麵頰,整個人埋在袖子裏吃吃笑了起來,蕭逐坐在她對麵,這會完全不知道她在笑什麼,隻能端正坐著,很正直地看她。
過了片刻,葉蘭心笑夠了,也不回榻上去,隨手抓下來一個軟墊就坐在了離蕭逐不遠的地方,一雙深灰色的眼睛筆直凝視過去,然後微笑,“殿下是在自己身上試的嗎?”
“……是。”輕聲答道。
葉蘭心點點頭,接過藥膏,手腕一動,扁玉盒子在手裏輕輕一個拋高,她看著對麵的男人,忽然說了一句跟之前的對話全然沒有關係的話,“阿逐,要不要打賭?”
打賭?坐在她對麵的青年眉尖微皺,卻沒有立刻回答,隻一雙眼掃了過去,安靜等她說話。
一方玉盒在葉蘭心手裏上上下下,一點日光射過帷幕,帶些薄綠湮染過來,一瞬之間,她手裏竟仿佛拋著一塊溫潤綠冰,襯得她笑容也柔和了起來。
“嗯,贏的人可以要求輸的人一個要求,不過分吧?”
放在你身上的話,就很難說過分不過分了……蕭逐想了想,問道:“賭什麼?”
葉蘭心斜斜靠在榻腳,上下打量了他幾眼,用“我就吃虧些好了”的語氣道:“賭劍術如何?”
劍術?蕭逐上下打量了對麵女子幾眼,隻看到一雙深灰色的眼睛笑得如一隻小小的狐。
並沒有任何傳聞說塑月儲君擅長劍術,而就這些日子接觸下來看,她應該不諳武功。
想到這裏,蕭逐卻慢慢的搖了搖頭,葉蘭心有些驚訝,問他為什麼不賭,蕭逐慢慢說道:“以己之短應彼之長,必然有詐。”
被這句話噎了一小口,葉蘭心有那麼片刻說不出話來,她訕訕地摸摸鼻子,又想了想,忽然一擊掌,說道:“那賭琴藝怎麼樣?”
琴藝?塑月儲君雅擅琴藝他倒是知道的。蕭逐又想了想,依舊慢慢地說道:“以己之長應彼之短,彼必敗之.”繼續搖頭。
喂喂,做人不帶這樣的啊!葉蘭心被這句話又鬱悶了一會兒,忽然明白什麼地一抬頭,果不其然,在對麵那絕代美貌的男人眼底,看到了一絲隱隱約約的笑意。
“……你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跟我打賭對吧?”塑月儲君說話的聲音裏隱約帶了點兒咬金切玉的顫音,蕭逐依然是端正無比的正座姿態,甚至還頗為有禮地微一傾身,恭敬答道,“誠如殿下所言。”
葉蘭心被噎的完全說不出話來了……
此輪交鋒,蕭逐勝。
葉蘭心不甘心地在地上滾來滾去,蕭逐依然一幅穩如泰山的架勢,眼底卻已柔和出一片瀲灩神色。
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這樣輕鬆過了。
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真正笑過了,哪怕隻有一瞬間,哪怕隻是一個最微弱的弧度。
看著葉蘭心撒潑打滾的在地上滾了好幾轉,最後停在他麵前,蕭逐低頭,正對上她那雙深灰色的眼睛。
片刻之前,有白雲皚皚的彌漫開來,光線柔和曖昧下來,攤平在他麵前的女子,眨眨眼,長長睫毛微微閉上,然後再睜開。
葉蘭心平心而論,並不是如何美麗的女子,容貌僅僅清秀而已,但是她卻有一雙非常美麗的眼睛。
長而密的睫毛張開的一瞬間,透出其下拱護的一雙深灰色眸子,然後,蕭逐在那雙眸子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光線遊移迷離,折過菲薄煙綠帷幕,遠處有琴音一線拋高,時斷時續,麵前映出他全部影子的眼睛,是非常微妙的深灰色,如同雨前天空一般,透出一種說不出的安靜柔和。
她沒說話,他也沒說話,就這樣隔著一層煙綠帷幕,彼此安靜相對。
過了片刻,蕭逐忽然輕輕笑了起來。
非常柔軟的笑容。
這是葉蘭心第一次看到這個絕代美貌的青年發自內心的微笑。
蕭逐的笑容很輕,他真心笑的樣子和應酬微笑大不相同,先是微微地眨眨眼,唇角彎起,一點點笑意慢慢堆積,直到眼角,然後很孩子氣很柔軟很滿足地微微眯起眼睛。
那是純真溫柔,甚至還有一點小心翼翼的笑容。
葉蘭心當真是為這個笑容楞了一楞,過了片刻,才回過神來,眨眨眼,剛要說話,卻發現舌頭有點打結,不太說得出來,蕭逐看著她一臉鬱悶,笑容不由得加深了一點。
她長發未束,到處亂滾,停下的時候,頭向著他的方向,一把柔亮漆黑的長發如一匹散開的絲帛,越過簾子,蔓延到了他的身邊,看得時間久了,襯著水榭裏一色煙綠,忽然就有了一種正慢慢浸入湖水中的奇妙感覺,那黑發就如同水底蔓生的淒淒水草,透出一點微妙的味道。
蕭逐看了他片刻,慢慢開口:“殿下,如果有什麼事情需要逐幫忙,就請直說,逐說過的,隻要是逐力所能及之事,都願意補償殿下,直到殿下滿意為止。”
誒,真的是,打賭不是那增加趣味乜,這男人真沒情趣……葉蘭心嘟囔著,又姿態不雅的翻了個身,側躺在地板上,斜著一隻眼睛看他,然後很清晰的一字一句地說:“陪我去榮陽。”
……這真是出乎意料的答案啊……
蕭逐苦笑起來。
大越製度,親王不得擅離封地,如果他答應陪她去榮陽,就要先過自己侄子那關,德熙帝肯不肯答應先放一邊……這個時候,她提出要求,要去榮陽,毫無疑問,就是衝著成王晏初去的。那天德熙帝提醒過他之後,他就調來了與塑月相關的所有資料研讀,得出的結論就是,塑月現在一派平和,但在儲君問題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大禍臨頭。
那麼,她拖他一起去榮陽,自己無論怎麼想,都勢必要被拽進那一灘爭儲的禍水裏,而且自己身份比不得旁人,是一國親王重臣,私入他國一旦被發現,後果可輕可重,一旦對方認真計較,就不堪設想了。
但是,不答應?
低頭,看著那雙一眨不眨緊緊盯著自己的深灰色眼睛,蕭逐發現,立刻拒絕的話,自己也說不出口。
畢竟,他做出過承諾的。
他承諾她,補償她,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償到她滿意為止。
想到這裏,蕭逐覺得自己越發想苦笑出來。
看著他,葉蘭心翻轉過來,坐起身,隨手把簾子扯到一邊,直接和他麵對麵,手腕一舉,廣袖軟軟滑下,露出下麵一段纏著繃帶的肌膚,用很嚴肅的語氣說:“阿逐,我受傷了。”
他無言點頭,嗯,他知道啊。
“都是因為你才會受的傷。”
“……”勉強點頭,雖然他很想說至少一多半責任在你自己吧姑娘……
“我這個狀況,自己溜去榮陽的話,非常危險,半路一定會很悲慘的死在山裏,死掉就算了還一定沒人埋,會被野獸咬成一塊一塊的,連骷髏都會被鬆鼠築巢——這簡直是一定的。”
鬆鼠一定不會在骷髏裏築巢的……蕭逐很想糾正葉蘭心這個常識性錯誤,但是看到那雙很認真的灰色眼睛,他又莫名其妙的有點兒心虛,隻好虛與委蛇地點點頭。
“那麼,即便這樣,你也不肯陪我去榮陽嗎?”塑月儲君以無比氣勢欺了過去,那雙筆直看他的深灰色眼睛讓蕭逐心虛越發嚴重,蕭逐想了想,禮貌的向後膝行一步,低頭認真思量了片刻,才低聲道:“請殿下容逐回去想想,此事關係重大,即便可行,也需陛下首肯才行。”
話說到這裏,對於蕭逐而言,其實已經等同於承諾了。葉蘭心敏銳的察覺到了這一點,也沒有再繼續逼他。
任他拉開兩人之間的距離,葉蘭心忽然輕輕歎息出聲,她說:“我說啊,人的一輩子長得很,我們都才二字頭的年紀,不要把自己弄得跟戲文裏頭的主角一樣隨波逐流的,很多事情該爭就爭,該抽就抽,對不對?”
如果說前麵那些話還讓他心裏起了漣漪,但是當聽到該抽就抽這四個字的時候,蕭逐的視線就不可控製地落到了她那還微微帶了點兒青腫的臉上,察覺到他的看點,兩個人都默了一下。
看她難得訕訕的樣子,蕭逐心情忽然又稍微好了點兒,他笑道:“那殿下是在鼓勵我拒絕您的要求嗎?”
似曾相識的對話,葉蘭心卻不像上次那樣立刻就說,她抱著胳膊想了一會兒,然後惡狠狠地說道:“不行,我的要求你不能拒絕,別人的麼……你放心……”齜牙,微笑,“有我在,他們沒機會的!”
蕭逐終於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笑完之後,他臉色一肅,隻問了一個問題,“殿下為什麼要去榮陽?”
她早就料到蕭逐會問這個問題,輕輕頷首,“我有我必須要在榮陽做的事情。”
蕭逐也不是不清楚塑月的現況,他略思忖了一下,點點頭,就不再問了。
不外乎,成王晏初。
笑歸笑,即便心裏已答應了,但是德熙帝那關卻還是要過的。
從瑞原行宮回來,蕭逐立刻進了宮,把事情跟蕭羌說了。
按照他對自己侄子的了解,德熙帝答應這件事的幾率不會很高,說的時候,他其實已做好了說服蕭羌或去向葉蘭心告罪的雙重準備。
結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聽了他的話,蕭羌沉吟了片刻,吩咐身旁侍奉筆墨的花竹意去取了文書來,他翻到自己要找的那份,看了看,一雙本就桃花春風的眼睛微微眯細,似乎想到了什麼,然後菲薄唇角一彎,襯著窗邊斜射夕陽一縷慘淡,居然有了一分驚心清麗。
統治著偌大帝國的男人站在書案後,輕輕笑道:“這件小事,我自然是答應阿逐的。”說完,他把榮陽太子娶妃送來的國書向前一推,“你做出使正使,也算給足榮陽麵子,如何?”
這句話一出,聰穎如蕭逐,立刻明白蕭羌的意思。
如果他是以使者身份前去榮陽,即便被人揭了身份,也不過微服先行,正大光明。
蕭羌這個處理,幹淨利落。
看蕭逐神色裏略有一點兒欣喜,蕭羌也不禁輕笑了起來,又溫言軟語的和自家王叔說了幾句話,送走蕭逐,坐回案前,挽起袖子繼續批閱奏章,然後,就在花竹意抱著一疊做好節略的文件過來的時候,他並未抬頭,隻是手裏的筆忽然輕輕劃出一個弧度,指向了花竹意的方向,“副使的話,你去吧,愛卿。”
花竹意楞了楞,眨眨眼,忽然笑開,“呀呀,陛下能離得了我?我這般稱職的文官可是很少喲~”
聽了這句,德熙帝慢慢抬頭,一張本就清雅的麵容在淡薄燭光下,更多添了幾分清淺風流。他定定看了笑眯眯回看他的中書令片刻,忽然展顏一笑,聲音恁是多情:“自然是要,試試看才知道到底能不能離得開,對不對,愛卿?”
花竹意唇邊笑意不減,看了片刻蕭羌,確定他無意更改旨意之後,瀟灑一躬到地,“那臣,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