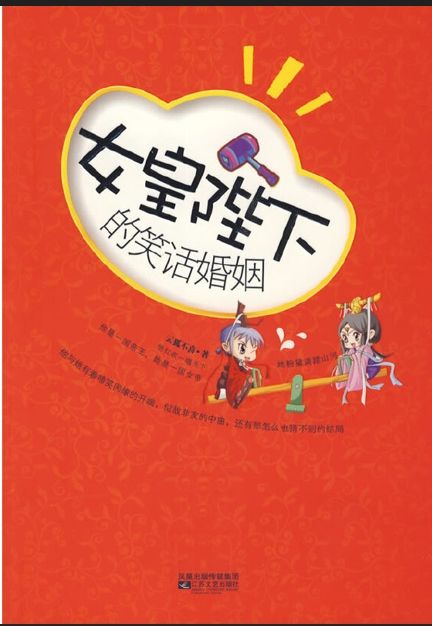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三章 你答應?我拒絕
如果說蕭逐是被生平第一次求親震驚得魂不附體的飄出了驛館,花竹意就是興奮並八卦的一路小跑直殺皇宮,向皇帝陛下報告這個好消息。
其實就現在的情況而言,大越和塑月結親,確實是很好的解決途徑。
當年兩國之間就是因為結親而鬧得不愉快,現在以結親來化解,確實也不錯。
當世東陸列強諸國之中,長昭荒蠻,榮陽自顧不暇,龍樓閉關鎖國,沉國又是大越死敵,剩下塑月,卻已是近百年未遭遇戰火,養精蓄銳多年,避免與之為敵是中策,和它結為同盟才是上策。
而且,如果大越和塑月結親的話,那麼在大越對麵,塑月旁邊的沉國,一半以上的國境將會被徹底封鎖,大越若要出兵,占盡地利。
此外,蕭逐為人正直重義,真去了塑月,日後一旦兩國有什麼嫌隙,他絕不會坐視不理。
——這確實是很劃算的交易。
聽完花竹意一頓嘮叨,蕭羌一張清雅麵容含笑,就問了一句,那王叔不答應要怎麼辦呢?
沒關係!對於這個問題,花竹意表現出了異乎尋常,在蕭羌看來怎麼都和幸災樂禍四個字脫不了關係的熱情。
從利誘開始,以情動之,以理服之,以德從之,一直到了“實在不行,咱先在食物裏下一堆化功散,然後從禁軍裏挑一堆身強力壯的,拿個用九天寒蠶絲織成的麻袋兜頭一罩,送上轎子陛下你覺得這主意怎麼樣?為臣覺得挺好的,真的。”
……你會被平王撕碎的,真的。嚴肅思考了這個方法片刻,蕭羌正色回答。
中書令大人一拍桌子,特大無畏的說了一句,臣不怕!
那是,有熱鬧看你怕過啥……
德熙帝默默的扶牆無語片刻之後,看著一臉燃燒態的花竹意,忽然唇角慢慢彎起了一個笑容,他輕飄飄說了一句,“愛卿,你似乎還忘了一件事。”
“啊?”還有啥?花竹意抓頭。
德熙帝唇角弧度彎高幾分,立刻眉角春風,多情風流,他勾勾手指,花竹意傻兮兮的靠了過去,就看到這個生就一雙桃花眼的男人俯身在自己耳邊輕輕說了一句,“朕還沒同意呢,愛卿。”
然後笑眯眯的皇帝陛下飛起一腳,直接把他踢了出去。
去,給我擺平!
把花竹意踢出去之後,德熙帝望著遠方宮闕萬間,臉上笑容慢慢收斂,他沉吟片刻,吩咐了一句,“備車。”
頓了頓,追加一句,“去平王府。”
被一腳踹出皇宮,中書令大人二天之內第三度拜訪驛館塑月儲君,奉上了德熙帝親筆所寫,滿紙都是客套言辭,實際上裏裏外外隻有“要追我叔叔憑自己本事上,老子不拉皮條!”這一句話的一封文書。
接到文書,葉蘭心三兩眼就挑出重點,腦袋上還繃著白布帶子的塑月儲君長笑一聲,答了一個“好”字,關門送客!
坐了大概不到一注香就又被請出去的花竹意多少有點無語問蒼天:他這個月是不是驛馬星動啊,怎麼老跑來跑去的?
花竹意被恭送出門,剛準備閃人,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在寬大的袖子裏摸摸摸,摸了半天,拽出來中午蕭逐給他,他忘記拿出來的那瓶傷藥,折了回去,慎重的雙手奉上,麵呈給了葉蘭心。
“……這是?”葉蘭心接過女官遞上的玉瓶,看了看,一雙深灰色的眼睛波光流轉,看向了花竹意。
花竹意笑得一貫見牙不見眼,撓撓頭,“平王殿下托我轉交的傷藥,專治跌打,外敷一日三次,散血化瘀最好不過,還希望您收好。”
“……啊,平王嗎?”葉蘭心看著掌心那個精致瓶子,又看了看麵前笑得陽光燦爛的青年,定定看了半晌,慢慢的鄭重點頭,緩緩道:“這定情信物我就收下了。”
這一句話立刻又炸裂了一票,連花竹意都不禁晃了一晃,心裏話說,拿個玉瓶當定情信物,儲君殿下您還真不挑……
看葉蘭心把玉瓶仔細收好,花竹意慢慢笑起來,彎腰一躬,笑道:“還請殿下好好養傷,才是塑月之福。”
聽了這句話,本來還拿著瓶子上下看的葉蘭心頓了頓,斜斜向下一掃,也慢慢的笑起來,“啊,那是自然,多謝花令關心。”
花竹意客套了幾句便退了下去,葉蘭心把玩了一會兒玉瓶,讓侍女收了,托著下巴出神的想了一會兒什麼,淡淡吩咐了身旁女官一句,“備轎,我要出門。”
“您要去哪裏?”
葉蘭心站起來,無所謂的拍拍玄色宮裝上的皺褶,“去平王府。”
這時候去?去幹什麼?女官不解看她,葉蘭心也沒解釋,隻是露出了一個懶洋洋的笑容,走過去,清澈的深灰色眼睛凝視著自己的女官和侍女,“讓你們去就去嘛,嗯?乖孩子。”
雖然完全不知道她葫蘆裏在賣什麼藥,但是既然下令,當下人的就隻能遵從,於是,片刻之後,一乘小轎就悄然出了驛館,向平王府而去——
蕭羌微服從後門進入平王府的時候,已經是下午時分了。
屏退一切隨人,白衣帝王輕袍緩帶,無聲地走進內院,蕭逐就站在一株梨樹下,仰頭望著頭頂上方一片雪白,鮮烈紅衣上點點梨白,拂了一身還滿。
呃,看起來似乎還處於恍惚狀態,沒回過神來。
那是,是他也得傻哪兒……被女人求親確實是大越男人,尤其是皇族男人一輩子想都想不到的待遇……
蕭羌心有戚戚焉地走過去,也不說話,陪著自己小叔叔往梨樹下一站,學他一樣仰頭看去,之間頭頂上滿目雪白,看久了居然有一種燃燒一般的放肆感。
蕭逐又看了片刻,才安靜低頭,看向身旁的蕭羌,蕭羌任他看了片刻,轉頭,一雙春風多情的眼睛慢慢彎起,然後微笑,“阿逐,放心,我不會讓你嫁出去的喲~”
“……”對“嫁”這個字抽了一下,蕭逐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侄兒,沒說話。
他以為,蕭羌會很開心這樁婚事。
而且,他已經做好了答應的準備。
蕭逐從來就沒對自己的人生抱有過什麼浪漫的期待。
生在皇室,錦衣玉食,那麼相對的,他就要承擔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中就包括了婚姻。
皇族婚姻,情愛與否全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能不能為皇族為國家帶來利益。
更何況,他了解自己的侄子。
麵前這個清雅多情,笑得眉眼春風的男人,擊沉國,約長昭,罷黜母族,賜死繼承人生母,鐵血手腕,毫不容情。
那是一個以利益為上,隱忍冷酷的君主。
但是,他對他說,沒事,什麼也不必擔心。
蕭羌笑著為他拂去一肩落花,伸手,輕輕抱住他,蕭逐也沒拒絕,反而撒嬌一樣把下頜蹭在蕭羌頸窩,埋下了臉。
一時靜謐,然後,他聽到蕭羌慢慢地說,沒事,現在國泰民安,大越還不用犧牲親王去換取利益。
蕭逐忽然就笑了起來,他又眷戀一般蹭了蹭蕭羌帶著木葉香氣的發絲,然後把麵前的帝王推開,“阿羌,我很感動,但是,我願意,這件婚事。”
蕭羌一震,再看向他的眼神裏帶了一絲奇妙的波動,然後那個紅衣青年笑了起來,安慰性地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阿羌,已經無所謂了。”
從那一天開始,已經什麼都,無所謂了。
如果他的婚姻可以為這個偌大帝國帶來利益的話,那麼,就這樣吧。
凝視著蕭羌慢慢皺起的眉毛,蕭逐臉上笑意越發深了起來,聲音柔緩,如同拂在梨花花瓣上的輕風:“何況,那裏是塑月不是嗎?”
在他說這句話的一瞬間,蕭羌忽然渾身一震,月白長袖下的手微微一顫,臉上現出了微妙神色,幾分淒苦惆悵,從帝王眼角眉梢浮動而出。
“所以,塑月這樁婚事,我答應。”蕭逐退開,單膝點地,以鄭重大禮,向麵前的帝王恭敬屈膝,不過,眼神卻越過了蕭羌,看向了他身後的院門。
蕭羌陡然察覺不對,立刻回頭,卻看到院門口一名總管模樣的人誠惶誠恐地垂手侍立,而站在他身旁的女子,玄衣青凰,正是葉蘭心。
蕭逐早看到葉蘭心進來,這句話就是說給葉蘭心聽的。
葉蘭心站在當場,卻沒有立刻過去,她歪側著頭,仔細想了片刻前因後果,又看看氣氛詭異的蕭羌和蕭逐兩人,再聯係蕭羌的態度,腦子裏稍一推演,就差不多明白在她來之前這兩個男人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對話。
斜起一邊眉毛看了看院子裏並列一處,一紅一白兩道修長身影,葉蘭心想了想,施施然走過去,來到依然維持跪拜姿勢的蕭逐身邊,笑眯眯地問了一句,“如果我沒聽錯,平王殿下是答應這樁婚事了?”
蕭逐禮貌向她略一頷首之後,輕輕點頭。
“……”蕭羌想要說話,但看了一眼兩人,眉心漸起一道褶皺,卻一言不發。
葉蘭心繞著蕭逐走了兩圈,然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地——蹲了下來。
蕭逐隻聽到有衣衫摩擦聲音,覺得眼前一動,他反射般一抬頭,就看到葉蘭心蹲在他麵前,一張臉從下麵湊了過來,從上往下筆直地看他。
——好大一張臉。
蕭逐基本上除了過世的元妃沒這麼近看過女人的臉,他楞了一楞,略略退後,卻還是沒有起身,葉蘭心也毫不在意一身華貴宮裝全掃了地,也吧啦吧啦朝前湊了湊,側著腦袋看他。
蕭逐這輩子就沒碰到過這樣無賴又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又退了退,葉蘭心死皮賴臉地跟著繼續在地上挪。
蕭羌看著這兩個基本無視他存在的人,其實就想說一句:王叔,你後麵有條溝……
直到他退無可退,卻還是維持的姿態時,葉蘭心長長長長地吐出一口氣,說道:“你答應了是吧?”
他知道她在問婚事,看著麵前那張臉頰微腫,眼角眉梢皆是無賴的臉,蕭逐略閉了下眼睛,低低答了聲:“這個問題您剛才已經問過了。”
“確認一下嘛~”葉蘭心笑眯眯的,“我說,既然不願意,那就不要答應嘛。”何必把自己搞得跟被強搶的良家民男似的?呃,好吧,自己到目前為止的言行,跟惡霸確實沒什麼兩樣就是了。
“……那若逐拒絕了,殿下會就此罷休嗎?”
“當然不會。”答得斬釘截鐵,猶豫都不帶猶豫一下的。
“……”蕭逐默了一下,輕歎一聲,“那這樣的話,逐拒絕有什麼意義嗎?”
“我說,那是兩回事吧?”葉蘭心奇怪地看他,“我向你求親是我的事,你要拒絕是你的事,這兩者不相幹吧?莫非過去你和別人相處的時候,一直都是看看覺得對方會堅持到底就什麼都答應下來?”
聽了這句話,蕭逐剛要反駁,但是心裏一動,卻發現反駁的話居然說不出來。
看他兩眼茫然,葉蘭心又歎了口氣,努力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算啦算啦,那些過去的事情就隨便它吧,從今往後,不要這樣就好了。”
拍了拍裙角的土,葉蘭心忽然伸出手去,把那張始終低垂的臉硬生生扳了起來。蕭逐猝不及防,一個抬眼,塑月儲君那張笑得大大方方的臉就映在了那雙始終明澈如秋水的眼中。
她頭頂梨花如雪,有陽光金色瀑布一般傾瀉而下,然後他的視線就被金色、雪白並一張女子的笑臉填得滿滿。
然後,葉蘭心對他說:“所以呢,平王殿下,這件婚事,你同意了我很高興,但是抱歉,現在,我拒絕。”
“——”誰能告訴他現在這是什麼狀況?不,誰能告訴她這女人腦袋裏到底轉的都是什麼東西?蕭逐不可思議地看著麵前笑得大大咧咧的女子,卻被對方一指點在了唇上。
她的體溫略低,觸感落在他唇上,仿佛一片花瓣落下。
蕭逐聽到那個注定要成為一國之主的女子一字一句地對他說:“如果說殿下是為了什麼負疚啊這些浮雲一般的理由才答應這件婚事的,那麼,殿下不覺得對我太失禮了麼?”
蕭逐渾身一震,凝神一看,麵前那深灰色的眼睛裏,滲出的,是一線認真。
……似乎……確實是這樣。
在一開始就把自己定義在了被害者的角度——呃,雖然實際上他確實是被害者沒錯,但是現在……
蕭逐定定看了片刻葉蘭心,忽然唇角一彎,非常慎重地向她低頭行禮,“是逐錯了。請殿下恕罪。”
“恕什麼罪啊,反正以後都是一家人啊對不對?”葉蘭心很大力地伸出手拍拍他,拍得蕭逐一臉黑線。
等等,什麼叫反正以後都是一家人啊?!你不是拒絕婚事了嗎!
接受到蕭逐的疑惑視線,葉蘭心笑得越發燦爛光輝,嘴巴一咧,一排白牙栩栩生輝:“啊,我的意思是,我會追求平王殿下到殿下答應婚事為止,阿逐,就不要大意的被我追求吧~”
喂!我什麼時候和你親近到你可以叫我阿逐了?!
不對,我現在想這個做什麼?
蕭逐在發現自己的思維方式似乎被麵前這女子詭異的邏輯帶離到了非常微妙的地方,他努力把思維拉回正常地方,卻發現對方已經若無其事地拍拍裙子站了起來,而就在葉蘭心站起來的一瞬間,在場兩個都很無言的男人忽然聽到了卡巴一聲脆響——
狐疑的視線齊齊看向聲音的來源:葉蘭心。
臉上的笑容和動作忽然一下子都被這卡巴一聲脆響凝結住了,葉蘭心眨眨眼,看了看蕭逐,又看了看蕭羌,可憐兮兮小心翼翼地說了一句話:“……我好像……把腰閃了……看樣子,要麻煩一下平王殿下了……”
“……”
“……”
蕭家的兩個男人無語問蒼天了……
蕭逐本想招來侍女把她丟出去拉倒,但是葉蘭心就仿佛一隻八爪魚巴住他死不放手,總不能跟她在光天化日之下撕巴吧?沒辦法,就在全體王府下人的注視下,大越平王殿下把昨天剛被他抽飛的塑月儲君抱出王府,恭送上外麵驛館的轎子。
蕭逐出府的時候,懷裏八爪魚儲君一隻,身邊玉樹臨風白衣玉冠皇帝一隻,這等陣仗,就不得不觸動了京城百姓的八卦指數。
於是,在廣大順京人民群眾之間流傳的謠言迅速從“昨天儲君調戲美人未遂”變成了原來昨天那一拳是“打是親罵是愛,愛得不夠用腳踹的範疇啊……”,其中還有升級版,把新婚的皇帝陛下也掃了進去,變成“不倫之戀!叔侄情變,儲君小三慘遭毆打……”
先把閃了腰的葉蘭心送上轎子,按照禮儀,再把蕭羌先送走,上車的時候,白衣帝王扯了他的袖子一下,輕輕對他說了一句,多留意一下塑月的情況,就登車而去。
聽了這句話,蕭逐心裏一動,再送葉蘭心的時候,看著那個車裏的女子大大的笑臉,心裏不知怎的,就忽然有一絲奇異的憐憫。
葉蘭心卻心情甚好地跟他揮揮爪子,說美人你放心,別說閃了腰,就算閃了脖子,明天你的賠罪宴我也會去的~
蕭逐非常幹脆地一把拉下了轎簾。
轎子裏的葉蘭心捂著腰笑得象隻偷到了腥的貓,一路轎子晃晃蕩蕩,她就沒笑停過。
直到半路上從驛館有一騎飛奔而來,送上一張密封的信箋。
看了一會兒特殊的蠟封圖案,葉蘭心臉上笑容稍斂,輕輕拆開。
裏麵是密碼文字,通篇下來,譯出來隻有四個字:成王病愈。
她知道那是誰。
比她晚了一會兒到這個世界上,她的雙胞胎弟弟,成王晏初。
也是,自小就以賢明著稱,遠比她的呼聲要高,塑月的第二順位王位繼承人。
取出隨身攜帶的火折,點了小火,看著手裏信箋燒成灰燼,落在了轎子裏鋪的軟毯上,葉蘭心唇角驀地一勾,弧度增大。
啊啊,弟弟的病好了啊~~
真好呢。
這個增大的笑容一直維持到回了驛館,見到了自家明顯也得到消息,正轉來轉去的女官們,葉蘭心越發笑得開懷。
進了內室,她笑眯眯地朝榻上一坐,看向了專門負責自己文件往來,也是自己心腹的司墨女官,問道:“國內是不是讓我早點回去?”
“是。”司墨女官親手掩上了門扉窗戶,確定再三,才答道:“成王殿下預定下個月月初回京,據我所知,已經有幾個當色名門的子弟,去和成王接觸了。”
“阿初回來本來就是要襄助朝政的嘛,當色子弟前去接觸也是正常,你們反應太大了。”葉蘭心仍是不甚在意的安撫自己的女官。
塑月製度自與他國不同,擁有權力廢黜皇帝的,並不是先皇配偶,而是由被稱為當色名門的七家大貴族所組成的年名會。
這七家大貴族都淵遠流長,其中皇族葉家也算在內,卻隻位列第四,曆史甚至沒有前三個家族悠久。
而當這七個家族的族長共同提出廢黜令的時候,即可廢黜皇帝。
塑月是一夫一妻無妾製的國家,又男女皆可繼承,便不存在立嫡之爭,隻要立長就好,而在立儲問題上唯一擁有發言權的,就是年名會。
在嫡長子過分不堪的情況下,由皇帝提出,五名以上年名會族長同意,就可以另立儲君,這本是為了不讓庸才繼承皇位而想的法子,曆代幾乎就沒有用過,但是到了葉蘭心這一輩,卻出了個小小的問題,就是,因為生的是雙胞胎的緣故,誰也不敢萬分確定,她就一定是長女。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晏初出生不久,因為身體多病的緣故,就被葉蘭心的舅舅,也就是真都帝的兄長,同時也是葉氏族長,年名會年官,精擅醫術的安王葉詢收為了養子,帶在身邊悉心照顧。
這下情況就變得分外詭異莫測起來。
因為,葉詢才是上一代本來的繼承者——
葉詢文武全才,是上代先帝元後所出的長子,真都帝的兄長,本是毫無爭議的儲君,卻因為在戰場上身負重傷落下殘疾,甚至於連娶妻生子都做不到,而自願讓出儲君的位置,讓自己的妹妹登了基。
按照塑月的繼承法則,被葉詢收為養子的晏初,就等於同時和葉蘭心具備了第一順位的繼承權——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狀況,即,到底誰能成為下一任皇帝的決定權,有一半落在了年名會的手中。
在兩名第一順位繼承人同時存在的時候,年名會和皇帝一樣,也具備了對繼承人的發言權。年名會本身就是由大貴族組成,都不需要七大貴族聯手施壓,隻要其中幾家聯手,幾家中立,對塑月而言,就已是絕大的壓力,需用皇帝仔細掂對掂對的了。
而現在,晏初病愈,立刻就有年名會的人搭了上去,雖然都是年輕的,不重要的子弟,但是卻也模模糊糊代表了一定當色名門的某種意向,確實是個問題。
葉蘭心優哉遊哉的靠在榻上,輕輕一敲桌麵,似笑非笑:“是不是現在所有人都認為,我該立刻回國,然後展現一把自己的英明神武,好讓我弟弟和年名會的人都老實下來?”
“是!”雖然覺得她的措辭有些奇怪,但是女官還是答得斬釘截鐵。
“哎呀,你說,我在儲君這個位子上是不是表現得特別不稱職?”她笑吟吟的問,女官楞了一下,卻堅決的搖了搖頭。
雖然葉蘭心表現得時常不怎麼靠譜,但是她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內,還真沒有捅出過簍子來,就算不靠譜一把,你說是運氣也好,怎樣也好,也通常會讓事情朝好的方向發展。
“好,那麼,既然我不算不稱職,地位也沒有危如累卵,那麼,年名會真的那麼傻,要把賭注投到一個目前階段看起來幾乎沒有勝算的阿初身上麼?”
“啊……那殿下的意思……”
“年名會無非是借此警告我,我和他們還走得不夠近,嗯?明白了?他們通過這個動作告訴我,我如果和他們走得太遠,那麼他們就會考慮其他的和他們走得近的人,比如阿初。”
女官遲疑起來,“殿下要怎麼處理這件事呢……”
“耶,這件事很燙手哦,所以……”葉蘭心微笑微笑再微笑,“等它涼下來再說吧,既然誰都想我要回去,那我幹嘛要順他們的意呢?嗯?”看到女官眼裏一線驚詫,葉蘭心笑了起來,衣袂鋪展,玄色長袖上青凰翩飛,仿若夜裏的一道驚夢。
她笑眯眯把自己鋪在榻前的幾案上,隨手抓了顆果子丟在嘴裏,一雙眼睛眯成月牙態,“我葉蘭心就是讓人猜不到不是麼?什麼都讓別人猜到了,好無聊啊~”
眨眨眼,“你說是不是呢,嗯?”
“殿下既然不擔心年名會,那成王那邊……”女官欲言又止,小心看了她一眼,葉蘭心輕輕咋舌。
“嘖嘖,阿初那邊你完全不用擔心,我的弟弟,不會背叛姐姐。因為……我是他……最喜歡的姐姐啊。”以一種微妙的表情說完了這句話,不再多說,葉蘭心笑眯眯又抓了一把果子,悠閑的一顆一顆丟到嘴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