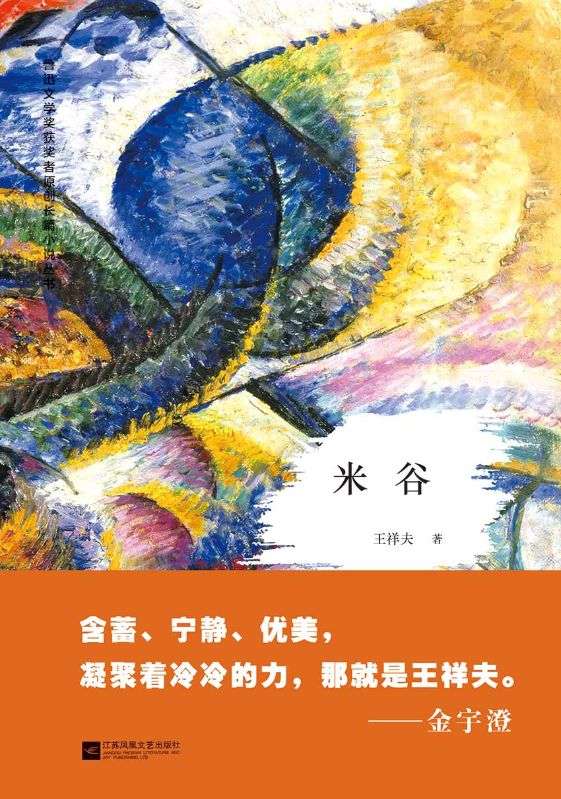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6
米穀的肚子一天一天大了起來。人們看著米穀的肚子大沒感到吃驚,感到吃驚的是米穀自己。米穀擔心怎麼回去和家裏人交代。天氣一天比一天熱了起來,長途站一帶更加熱鬧了,那天中午,米穀聽到了螞蚱叫,“蟈蟈蟈蟈、蟈蟈蟈蟈”叫得很歡。米穀跑到街口去看,是個鄉下人,挑了一挑碧綠的蟈蟈在那裏賣。
米穀買了一隻蟈蟈拿在手裏看。
“米穀!”
有人喊她了。
長途汽車站一帶太亂,米穀沒看見喊她的人,隻聽見這個人還在喊。
“米穀!米穀!”
米穀還是沒看見人,米穀急了。那個人還在喊:
“米穀!米穀!米穀!”
米穀這下子看見了,是村裏的鮮頭,天這麼熱了,鮮頭還圍著塊紅頭巾。
“米穀!米穀!米穀!米穀!”
鮮頭從人縫裏喊著擠過來,激動得一下子哭了起來。
“你哭什麼?”
米穀對鮮頭說。
“我看見你就想哭。”
鮮頭說。
“你咋看著我了?”
米穀說。
“我一下就看著你了。”
鮮頭說村裏的人都以為米穀你讓人販子給賣到西安去了。
“我又找不著你們,你吃了沒?”
米穀問鮮頭吃了飯沒。
“米穀,你遲了。”
鮮頭看著米穀,用頭巾擦著嘴角說。
米穀不知道鮮頭這話是什麼意思,她忙問鮮頭什麼事。
“我不能說,你回家就知道了。”
鮮頭搖搖頭說。
米穀急了,搖搖鮮頭,要鮮頭告訴她家裏到底出了什麼事。
“你爸和你弟弟來城裏找你,找不到你。”
鮮頭說。
“他們什麼時候進城了?”
米穀問鮮頭。
“進了一次又一次,進了一次又一次。”
鮮頭說。
“我一直就在汽車站。”
米穀說我們家出什麼事了?
“他們以為你在火車站,他們找了你一次又一次就是想讓你回一趟家。”
鮮頭說。
“什麼事你說。”
米穀的心跳亂了。
“米穀,你晚了。”
鮮頭又說。
“你快說什麼事!”
米穀的心提到嗓子眼了。
“你再也看不見了。”
鮮頭說。
“是不是我奶奶?”
米穀要哭出來了,兩眼發直了。
“不是你奶奶,是你娘。”
鮮頭說。
“我娘!”
米穀又哭不出來了,她一下子攥緊了鮮頭,鮮頭叫了起來。
“我娘怎麼了?”
米穀說,攥得更緊了。
“米穀你放開你放開,你再攥我你娘也不在了。”
鮮頭“哎喲,哎喲”地叫了起來。
“我娘不在了?”
米穀說。
“你娘不在了,已經給埋到玉米地裏去了。”
鮮頭說。
“我娘不在家裏了?”
米穀的話有些亂了,腦子也亂了。
“你娘死了,給埋在玉米地裏了。”
鮮頭說已經有兩個月了。
米穀的眼裏掉出了眼淚,眼淚很快就把衣服濕了一片,接著又把衣服濕了一大片,接著把褲子也濕了一大片。米穀坐在那裏哭了又哭,她和鮮頭坐在街頭,米穀哭,鮮頭也跟上哭,周圍的人不知道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鮮頭是個要飯的,當然,跟要飯的坐在一起哭泣的人也應該是要飯的,這時候有人走過來了,把五毛錢的票子放在了鮮頭的手邊。這時有人說話了,說這兩個要飯的為了什麼事哭成個這樣?
“你們出什麼事了?”
這是一個老頭,臉紅紅的老頭,像是剛剛從澡堂裏出來。
米穀哭得是昏天昏地,她還在哭,但她聽見鮮頭在一旁說話了。
“她的孩子死了,餓死了。”
鮮頭靈機一動說。
“她的孩子?”
那老頭指指米穀。
“可憐可憐給點兒吧。”
鮮頭把手伸了伸,說。
那老頭把一張五元錢的票子放在了米穀的手邊。
“可憐可憐再給點兒吧。”
鮮頭又說。
又有人過來,把一張一塊錢的票子放在了米穀的手邊。
“可憐可憐多給點兒吧。”
鮮頭哭得比米穀都厲害了。
又有人過來了,彎下腰問:
“你們倆,是誰的孩子死了?”
“她的孩子。”
鮮頭指指米穀說。
“她的孩子?”
那個人也指指米穀。
“可憐可憐都給點兒吧。”
鮮頭對周圍越來越多的人說。
這時有人認出米穀了,說這不是小飯店前賣羊肉串的嗎?
這時又有人在那裏大聲說話了,是在說米穀:
“你們看她的肚子,她的孩子還在她的肚子裏呢,怎麼就說她的孩子死了呢?”
這時圍上來的人更多了,他們都想要看看米穀的肚子。
鮮頭不哭了,她站起來,吃驚地看著米穀。
“米穀,你有啦?”
鮮頭拉著米穀站起來,米穀又捂著肚子坐下去。
“米穀,你咋就有啦?”
鮮頭又大聲說。
“米穀,你和誰有的?”
米穀坐在那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把身子努力彎下去,彎下去。
這時候小年輕出現了,他看見這邊圍了好多的人,他不知道這裏出了什麼事,他過來了,看到了人群裏的米穀,也看到了米穀旁邊的鮮頭,他聽到了鮮頭在那裏盤問米穀。他擠進人群,把擋在他前麵的人推開,小年輕站在了米穀的麵前,對米穀說:
“米穀,咱們回家。”
“我娘死了。”
米穀說。
“你娘死了還有我。”
小年輕說。
“我娘給埋在玉米地裏了。”
米穀站了起來。
“咱們回家,米穀。”
小年輕拉了一下米穀。
“我娘沒花過我一分錢就給埋在玉米地裏了。”
米穀傷心地說。
“看啥?看啥?都回家看你媽生孩子去!”
小年輕對圍上來的人大喊一聲,揮了一下手,手裏是一把穿肉串的鐵扡子。小年輕拉著米穀回家去了,鮮頭在後邊緊跟著。她想去米穀家裏看看。
鮮頭跟在後邊小聲問米穀:
“這就是你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