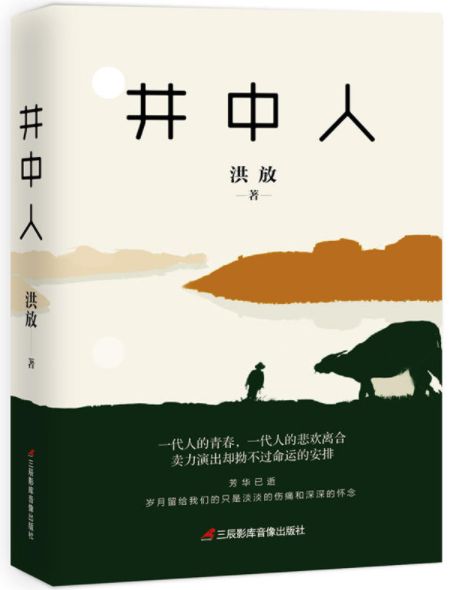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四章 初聞桂香
倘若死者能說話,那麼,胡滿香應該是個最想說話且最應該說話的人。
新世紀來臨前的那一年中秋,胡滿香摔倒在百花井邊。等到大院子裏的人發現她時,她已昏迷。送往醫院後,雖然多方搶救,還是沒有產生奇跡。她去世時,才63歲。她沒有來得及給丁成龍和孩子們留下任何一句話。當然,她或許留下了話,隻是丁成龍和孩子們都沒聽見,而百花井聽見了。百花井看見和聽見了一個東北女子在異鄉的井台邊,走過了人生的最後一程。
桂花正開,滿院清香。
喪事結束後,丁成龍和三個孩子坐在百花井邊。誰都不說話,一切安靜,靜得能聽見井下青苔往水麵俯身的聲音,能聽見幽暗的水滴落向井底的聲音。
終於,大兒子葉抗美開口了。
葉抗美個子高,在三個孩子中,他長得最像丁成龍。他喊丁成龍“老頭子”,而不是喊“爸”。他說:“老頭子,我得將媽帶回去。”
“回新疆?”丁石子問。
“當然。媽生前就有這願望。那裏有很多她的老熟人,而這邊,幾乎沒有。”葉抗美用手劃了一下,對著丁成龍又問了句:“老頭子,你沒意見吧?”
“你們說呢?”丁成龍望著二兒子和女兒。
丁昌吉歎了口氣,說:“要是媽真的有那想法,就回去吧!”
“可是,那怎不是……一輩子了,死了,還得葬在異鄉。”丁石子心事重重,又重複了一遍:“將來要是上個墳什麼的,還得跑到新疆去?”
“那倒不必。有我在就行了。”葉抗美態度堅決。
丁成龍站起來,他瘦高的個子,使他看著就像一塊尖石,樹在桂花樹下。他繞著井台走了三圈,然後道:“就讓你媽跟抗美回新疆去吧!”說罷,他頭也不回地回到了書房。
頭七剛過,葉抗美就帶著媽媽胡滿香的骨灰,回新疆去了。別墅裏更加空蕩,以往,胡滿香在屋裏頭走來走去,或者嘮叨不停。但現在,胡滿香跟著大兒子,再一次踏上了去往邊關的道路。丁成龍心裏頭的滋味,他自己也無法描述。在胡滿香的骨灰啟程的那天早上,他捧著胡滿香的骨灰,老淚縱橫。他覺得這一生,他真正愧對的人,如果要能數第一的話,那一定就是這個裝在骨灰盒中的女人人。他對大兒子葉抗美說:“一定得找個向陽背風的坡上,給你媽媽好好地安個家。”
丁成龍這話發自肺腑。一九五四年冬天,當時他從宣傳辦正式調到文教局已經兩年了。他主要負責群眾文化宣傳,包括秧歌隊、文工團、夜校等。胡滿香的父親胡仁義就在這年國慶後,由東北調來廬州,直接到文教局任副局長。在部隊裏,胡仁義是正團。一個原來手裏頭有好幾百號戰士的團長,現在成了十來人的文教局的副局長,胡仁義覺得自己一下子懸空了,不踏實。他也不願意坐在自己的單獨的辦公室裏,而是整天跟丁成龍這班下屬一道,到處跑,到處轉。胡仁義典型的東北漢子,嗓門大,性格直。喜歡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不高興了,就罵人。高興了,就請大家去下館子。兩個月後,年關將近。胡仁義副局長一時興起,又請丁成龍他們幾個人去城隍廟吃貢鵝。那天,他們放開來吃了三隻貢鵝,喝了三瓶老白幹。結果,胡仁義對已醉態十足的丁成龍說:“這娃我喜歡!我要你做我女婿!”
丁成龍迷蒙著眼,他沒把胡局長這話當真。
然而,胡仁義卻又跟著問了句:“成吧?”
“成!”丁成龍想都沒想,就答道。
“好!”胡仁義一拍大腿,夾了塊鵝腿,直接遞進丁成龍的嘴裏,然後對著其它人道:“從今天起,老子就是你的老丈人了。哈,哈!好!”
丁成龍這一下子酒卻醒了,忙想解釋。但他又不知道到底要解釋什麼。按理說,他也二十六了,該成家了。副局長願意把自己女兒嫁給他,那也是他的福分。何況胡局長的女兒,他其實也是看到過的。他們一家剛到廬州,局子裏同事在一塊吃過餐飯。那個女孩眉眼不小,倒也大方,樸素。不過,他壓根兒也沒想到會胡仁義局長成為翁婿。婚姻是一生的大事,本來是得同家裏人商量商量的。可是他十幾年前就已經是孤身一人了。他隻好同自己商量。而自己正在酒醉之中。他望著胡仁義,搖搖頭,又點點頭。胡仁義一下子急了,猛拍了下桌子,吼道:“你個丁成龍,看不上俺閨女是吧?看不上也得看上,就這麼定了。下周結婚。”
撂下這句話,胡仁義副局長“咚咚咚”地跑下樓去了。
一周後,丁成龍和胡滿香光榮地結為革命夫妻。他們為此在百花井分到了三間住房。新婚之夜,胡滿香倒也幹脆,對別別扭扭地丁成龍說:“磨蹭個啥?不就是夫妻嘛!趕緊做事,還得生孩子呢!”
胡滿香這話,一直在丁成龍的腦子裏裝了五十多年。他沒想到這個東北女子,直爽得像火柴,一點就著,沒有一絲一毫地膩歪。而且,在後來的人生歲月中,胡滿香的這種個性,幾乎成了丁成龍孤寂心靈的一道籬笆,保護著他,看守著他,溫暖和成全了他。而他,給予胡滿香的,卻是太少太少。
丁成龍記得在百花井旁,胡滿香聽他講完父親、母親和兩個哥哥的事情後,她說:“真可憐。不過,往後有我了。將來還有娃!”
春天,百花井大院子的牆角,開出了許多小花。胡滿香會將那些花摘來,插在玻璃瓶裏。小屋裏立馬就有了生氣。丁成龍下班回家,胡滿香正撫著肚子,問他:“要當爸了,興奮不?”
丁成龍有些羞澀地笑了。
不過,這時光也僅僅維持了不到一年。而讓這時光終結的,到底是哪個時代?還是丁成龍個人?或者正是那個讓丁成龍一輩子難以原諒的馮誌國?
當新婚的丁成龍和胡滿香抱著被子住到百花井時,孟浩長住在公主府第裏麵已經十二年了。
十二年,天翻地覆。
十二年,人去樓空。
孟浩長依舊住在最靠裏麵的那間小房間裏。原來一溜五間的房子,現在有兩間劃給了其它住戶。剩下三間,一間是廚房和餐廳,一間是孟浩長的房間,另外一間,住著高巧雲。高巧雲已經二十多歲,她就在出了百花巷不遠處的廟前街物資供應站上班。最近一段時間,她時常感到孟浩長心思重重。她問他,他也不說。她隻好處處留意著。
孟浩長的父親孟雲生當年離開廬州去法音寺時,專門對高巧雲吩咐說:“我這一去,從此與俗世不通。浩長這孩子,天性懦弱,還得請你多照顧。”
高巧雲流淚點頭。她無法拒絕。從十歲那年隨著母親來到孟家,她一直將孟家當作自己的家看待。孟浩長的父親孟雲生,更是拿她當女兒一樣。孟浩長的母親李晴兒解放前夕跟隨孟雲生的副官跑到香港去了,孟雲生為此差點撥槍自殺。如果不是孟浩長抱著孟雲生的大腿,如果不是高巧雲在邊上哭著說:“如果跑的跑了,死的死了,將來少爺還怎麼活?”,也許孟雲生就真的開了槍。但孟雲生到底是個懂得憐惜的人。他摸著兒子的頭,又看著高巧雲,將上了膛的槍放到了桌子上。然後,他讓他們都出去。
孟浩長問:“爸,你真的不會再……”
“不會了。不會的!”孟雲生說。
高巧雲牽著孟浩長的手出了房門,他們剛到屋外,就聽見孟雲生撕心裂肺地“哇”地哭了起來。
那天晚上,孟雲生一直哭到天亮。
第二天,孟雲生加入了起義隊伍。三天後廬州解放。孟雲生成為了第一批被安置的起義人員。組織上安排他到廬州中學當副校長。但他隻當了三個月的副校長,一九五0年的端午,他獨自去了紫蓬山上的法音寺,從此再沒回過廬州城。
丁成龍和胡滿香每天黃昏的時候,喜歡出了百花巷,到淝河邊上散步。淝河兩岸,芳草萋萋。落日渾圓,波光瀲灩。有一天,胡滿香就問道:“成龍,那住在裏麵那是姐弟倆?”
“姐弟?”丁成龍伸手將麵前的樹枝移開,說:“你是說那在府裏的那一男一女?”
“就是。我看他們不像姐弟,但,也不像是夫妻。那男的,太小了。”胡滿香雙手護在肚子上,半個月前,醫生已正式告知她:她將要做媽媽了。
“那就不是姐弟。那是……”丁成龍這幾年在廬州,自然也聽到過孟雲生的一些事跡。而且也知道孟雲生有個兒子,還正在上學。他剛到百花井時,就曾聽也住在百花井的一個老鄉說:“那府裏麵住著從前的孟公子,就是起義了的後來又上山做了和尚的孟雲生的兒子。”但是,他並不曾知道那個跟孟浩長住在一起的年輕女子的來路。
胡滿香說:“看那女的,長得也端莊,人也溫和。挺好的!”
過了兩日,一向喜歡熱絡人的胡滿香便搞清楚了住在府裏的這一男一女的基本情況。男的叫孟浩長,讀高二。女的叫高巧雲,是從前孟家下人的女兒。現在就一直住在孟家。他們家原來有五間房子,如今住著三間。高巧雲在物資站上班,據高巧雲說:他們倆個人現在其實都是孤兒。孟浩長的母親跟人跑到香港去了,父親上了紫蓬山法音寺,當了和尚,不問世事。而高巧雲的父親早年就因為肺癆死了,母親也在剛解放那年因病離她而去。高巧雲說她跟孟浩長就是姐弟,在一塊十來年了,比一般的姐弟還親。
胡滿香一下子喜歡上了高巧雲。按年齡,她比高巧雲還小。她叫高巧雲“姐”。有時候,她就坐在高巧雲的房間裏,兩個人聊廬州城解放前的那些事兒。當然,聊得最多的還是孟家的事,包括孟浩長的母親,毫無征兆地跟著孟雲生的副官私奔。“那事徹底擊垮了孟先生!”高巧雲稱呼孟雲生為“孟先生”。解放前,她稱呼孟雲生“老爺”。解放了,不興這稱呼了,便改了先生。這也隻是私下裏的稱呼,平時,她很少提及孟雲生。孟雲生獨自在法音寺,暮鼓晨鐘,參禪學佛。胡滿香罵孟雲生寡情,怎麼就舍得丟下兒子一個人上山當和尚了呢?高巧雲好看的眉毛蹙成了兩支糾結的小花,她歎道:“孟先生心裏苦呢!”
“心裏苦?”胡滿香自然不放過。
高巧雲說:“孟先生當年打死也不會想到孟太太會出那樣的事。平時,你再怎樣,也看不出來呢。孟太太人長得漂亮,耐看。穿衣打扮也很得體。以前,廬州那些軍官太太們在一起聚會,孟太太總是最顯眼。孟先生對孟太太那個好,哎呀,簡直是少見的。孟太太要什麼,孟先生就給什麼。每天晚間,孟先生跟孟太太還常常在一塊兒唱戲,拉著我們來聽。兩個人唱得眉飛色舞,就像水一般。平時,我們從來沒見他們吵嘴,外出聽戲,吃飯,串門,都是兩個人一道。可誰承想:就是這樣的孟太太,竟然跟了副官……”
“那副官難道比孟先生對她還要好?”胡滿香問。
高巧雲說:“說不準。反正我是沒看見。孟先生自然也不會看見。孟先生是個讀書人,除了陪著孟太太外,其餘在家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房裏看書,寫字。孟先生對那個副官太信任了,讓副官陪著太太出去騎馬、逛商店。有時候,還讓副官陪太太外出吃飯。結果……孟先生哪曾想到,就會出那攤子事呢?”
“他們是怎麼走的?孟先生一點也不知道?”
“一點也不知道。也或許,孟先生是知道的,隻是不說。反正,就是四月初六那天,早晨太太說要出去一趟,我們也都沒在意。結果到了晚上,太太也沒回來。派人到處找,後來發現副官也不見了。有人報告說看見副官和太太一起坐火車走了。孟先生當時就想自殺,子彈都上了膛。孟先生雖然是個軍人,可他重感情,哪能受得了這麼大的刺激?後來雖然沒自殺,還是出家了。”
“那現在有孟太太的消息嗎?”
“據從那邊過來的人說,孟太太跟副官到香港後,就住在了一塊。後來又到了台灣。前兩年,還有人問到了百花井這邊,說孟太太托人給她兒子捎了封信。這信我沒看見,是浩長直接收了的。他讀完信,便點火燒了,從此也沒再提起。”
“我怎麼一直沒見那孩子出來?”
“他現在很少出來。除了每天去上學外,都窩在家裏。從孟先生上山出家後,他就這樣了。我勸了多少次也無用。唉!都怪孟太太,好端端的一個家,就這麼……”
“那將來?你要是嫁人了,咋辦?”
“我不嫁人。我得守著當年給孟先生的承諾,照顧好浩長。除非他……”
胡滿香回家將她與高巧雲的對話,原原本本地複述給丁成龍。丁成龍也歎氣,說他以前知道孟雲生,但不知道孟家還出了這麼件大事。不過,孟雲生解放後,政府可是對他不薄,讓他當了副校長。他怎麼還去紫蓬山出家呢?可憐了那孩子。不過,想了想,也無所謂。當年,丁成龍看著大哥丁成江被殺、接著又聽見二哥遇害,那年,他才十七歲,比孟浩長還小。十七歲的丁成龍進了桐柏山區,成了遊擊隊一員。一直到解放,那六七年的時光,可是槍林彈雨中度過。有好幾次,他與死神擦肩而過。當年在淮河大壩上找到他並且帶他進入根據地的三個人,其中兩個是在丁成龍眼睜睜看著的情況下,中彈犧牲的。還有一位,是解放前夕與丁成龍一道化妝進城偵察,結果被人當街認出。這人為了保護丁成龍,撥槍戰鬥,被敵人的機槍打成了篩子,全身鮮血噴湧而出,陽光下如同彩虹。
丁成龍心裏潛藏著這些疼。但他從來不說。他就是這個性。即使對胡滿香,他也從來不說這些。他隻把這些充滿血與火的往事,烙在記憶深處。
隻有一次,胡滿香再次說到孟浩長時,丁成龍冒了句:“有個姐姐挺好!我也曾經有個姐姐的。”
“你也有?”胡滿香對丁成龍那失蹤了的父親、死了的母親和兩個哥哥,都清楚。但她可從沒聽說丁成龍也還有過姐姐。
丁成龍說:“是有過。是在豫南軍分區時。她在醫療隊,比我大三歲。也是魯北人。她長得挺拔。四八年,在一次反掃蕩中被敵人包圍。她用最後一顆子彈……”
胡滿香看著丁成龍,她看見丁成龍的眼睛發紅,便道:“戰爭哪有不死人的?我父親的很多戰友兄弟都犧牲了。好在現在新社會了,再也沒有戰爭了。再也沒有了!”
丁成龍心想:經曆過戰爭的人,是不會忘記戰爭的。包括他,也包括嶽父胡仁義。聽胡滿香說:有時,在夢裏,胡仁義還會喊著戰友的名字。當年跟著胡仁義一道從東北參軍的九個小夥伴,現在也就隻剩下他一個人。胡仁義有時喝著酒,就大哭。哭聲中,數著一個一個名字。他記得那些犧牲的戰友的姓名、年齡、老家。他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對照著想想是不是有從前的戰友,特別是那些犧牲的戰友的親屬。如果有,他一定會找過去。他說:沒他們死,就沒我們活著。我們現在活著,也得替他們活著。
也正因此,丁成龍對當下的日子心滿意足。每天,他到文教局上班,忙東忙西。下班回家,胡滿香已將飯菜燒好,熱菜熱飯,讓他時時想到當年母親在時的情景。胡滿香從小就一個人跟著娘在東北四處流浪,解放過後,胡仁義回老家才找著他們娘倆。胡仁義名字叫仁義,心底裏也確是一個講仁義的男人。在部隊裏那麼些年,他沒再成家。雖然他也不敢期望著等革命勝利了,能回家見到妻子和女兒。命運總是厚待仁義者。當他在十五年後再回東北老家時,迎接他的不僅僅是當年的那個小媳婦,還有長得活脫脫像他的十幾歲的女兒。他硬是用胡茬將胡滿香的小臉,親了個遍。然後,他帶著這母女倆,從東北到關中,又到了廬州。他沒再生養。文教局年齡稍大些的男人在胡仁義酒後也壯著膽子問過他:咋不再生一個呢?現在天天跟嫂子貓在一塊,能生則生啦!胡仁義也不生氣,倒是痛痛快快地說了大實話:不行了。家夥不行了。四五年跟日本人打戰時,一塊彈片打中了下身,現在還卡在裏麵。
大家立馬肅敬。從此不再提起。
丁成龍當然也知道這些。他甚至連跟胡滿香也沒提起過。經曆過戰爭的人,哪個不受過傷?有的在身上,有的在心裏。有的是身心俱傷。隻是都不願意露出來而已。露了,那是對戰爭的褻瀆,是對那些在戰爭中死去了的戰友們的褻瀆。
但因了胡滿香與高巧雲的頻繁走動,丁成龍終於踏進了孟家的屋子。
孟浩長掩著門,窗子上貼著白紙。高巧雲輕輕地推開門,孟浩長年輕而蒼白的麵孔,顯得波瀾不驚。高巧雲將丁成龍讓進屋,說:“浩長,這是丁科長,咱們鄰居。你們聊聊!”說著,她就退出門外。
孟浩長示意丁成龍坐下。丁成龍想這也不是個結凍的孩子,知道讓他坐下,就說明了這點。他坐下,問道:“在家看書呢?快高考了吧?”
“嗯!”
“聽說,你父親去……”
“嗯!”
“這是你畫的?”丁成龍指著牆上掛的畫。
“嗯!”
連續三個“嗯”,讓丁成龍幾乎無話可說了。好在孟浩長突然來了興致,問:“你也懂畫?”
“懂一點。以前在部隊時,搞宣傳,接觸過一點。我們那宣傳隊當時還有個著名的畫家,叫劉子村的。他給我畫過幅畫,可惜後來弄丟了。”
“劉子村?我知道。海上畫派。他曾經長期在上海居住。後來去部隊了?”
“一九四七年時,他來到我們宣傳隊。四八年底,在徐州會戰中,犧牲了。”
“可惜!太可惜了!他可是大畫家。他的山水,講究人文意境,在海上畫派中,獨樹一幟。可惜,可惜了”孟浩長竟站起來,來回踱步。這種感歎和踱步的方式,顯然與他十九歲的年齡不相稱。這甚至有一種秋意般的老成與孤獨。
“看來你對繪畫很有研究。”
“談不上研究。畫了十幾年了。我從八歲就開始畫畫。”
“找了先生?”
“沒有。我一直自個兒看畫譜。我不喜歡讓人教。那樣畫出來的,就永遠都是別人的。”
“這想法倒是新鮮。”丁成龍又看了看牆上的畫,以他這不是太懂畫的人的眼光來看,確實不錯。他拍拍孟浩長的肩膀,說:“真的不錯!將來會成為一個好畫家的。”
“那有什麼意思?都沒意思呢。”孟浩長又低了頭。
丁成龍趕緊道:“有意思的。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從一個山坡走向另一個山坡。山坡與山坡之間肯定有深穀,你走過去了,就能看到對麵山上的鮮花;你走不過去,就會老死在這邊的山坡上。”這話其實是姐姐說的,丁成龍一直記著。
孟浩長大概是被丁成龍這麼文縐縐的話給蒙倒了,他望著丁成龍,眸子清亮,即使有些許的憂鬱,但內在裏還是藏著一縷靈光。他又站起來,說:“我早就看見你和那個大姐姐一道搬到百花井來了。今天晚上,我們喝酒。我知道我父親有一壇好酒埋在井台旁的桂花樹下。我們喝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