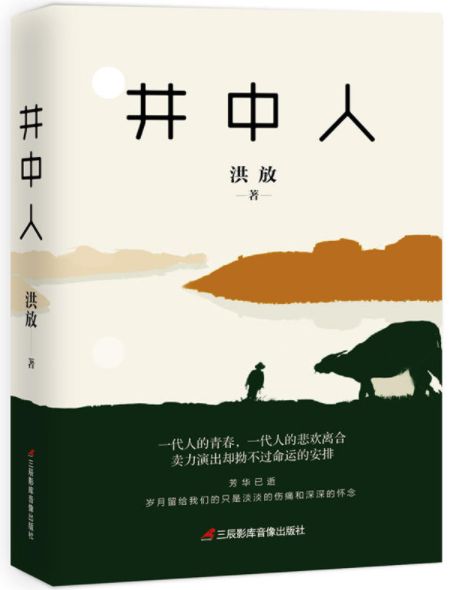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五章 白雪光升
李光升從東大圩坐車到廬州城,然後坐公交到百花井,等到他叩響孟浩長房門的時候,已經是上午九點了。
孟浩長不在家,門上貼著個紙條:有事外出,敬請諒解。
這紙條李光升看著親切。1982年春天,他第一次一路問人,轉了七八個彎,走進了百花巷。然後,沿著巷子,看著高牆上密密的爬山虎,心情五味雜陳。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誰?那將是一個怎樣的男人?個子是高是矮?身材是胖是瘦?更重要的,他無法揣度這個男人會怎樣對待他?會怎樣對待他所要述說的故事和將要提出的那些他們在“山窮水盡”之後所想出來的沒有辦法的最後辦法?
李光升那年25歲,在東大圩,這個年齡絕對是個應該成家立業的年齡,可是,他仍是光棍一條。父親長年癱瘓,母親孟小書多病體弱,妹妹才十五歲,正在讀初中。這幾年年成不好,建成於宋的東大圩本來是廬州的糧倉,可現在,三年兩頭災,不是旱就是澇。李光升三年前曾由媒婆介紹,定了一門親。本來議定去年臘月成親。可是,臨到過門,女方提出了八千塊錢的彩禮錢。母親咬咬牙,要賣家中的僅剩的那件皮襖子,被躺在床上的李天大給製止了。李天大說:那是你最後的念頭了,再不能賣了。母親含著淚,說:天大,我這一生拖累你了。李天大也抹著淚,說:不是你拖累我,是我拖累了你。我要是早死了,也不會把這家拖成這樣……
李天大說的也有理。他長年癱瘓在床,藥物不斷。家裏稍有點積餘,便花在給他看病上。一家人總是希望李天大有一天能站起來,雖然無力回天,但也勉為其力。眼見著東大圩實行了農業責任製,田分到了戶,家家都在田裏下功夫,李天大這個從前的農活老把式更是難耐。兒子李光升勸他:也別急,分田到戶了,日子會出頭的。你躺在床上,不要管別的事情,隻要將做農活的那些老把式教給我,我保證能將咱們家的那些田種得比誰家都好。李天大流著濁淚,開始教李光升如何在田裏精耕細作。果然,到了秋天,李家的收成遠遠高出了其它人家。賣了糧,家裏一下子有了積餘。母親便張羅著再給李光升娶親。可就在這當口,母親病了。
母親不僅病了,而且是重病。
醫生對李光升說:“拖得太久了。回家去吧,有好吃的,就吃一點。別的,也沒辦法了。”
李光升拉著醫生的手,哭著哀求:“真的沒辦法了?哪怕有一點辦法,都求求你救救我娘。”
醫生搖搖頭。
李光升又拉著母親,到了省立醫院。同樣的結論,同樣的腔調;他還是不甘心,又去醫學院附院,托關係找到一位老專家。老專家反反複複地問了半個多小時,然後請李光升到了裏麵的小辦公室,搖著頭說:“要是早來三個月,估計還能想想辦法。現在,真的是太晚了。我看你這孩子人也誠實,就別再折騰了,好好地讓你母親走舒坦些吧!”
回東大圩的路上,母親一直沉默。臨到家門口時,母親對李光升道:“記著,從現在起,一是不能告訴你爸爸,二是不要告訴小雪。我知道自己的病情,你也不必太操心了。”
李光升喉嚨發緊,卻哭不出來。母親掏出手帕,說:“都這麼大人了,還哭?別沒出息了。回到家,不要慌張,就說我這是老毛病,吃點藥,調理調理就好了。記住沒?”
“記住了。”李光升哽咽道。
回到家,李光雪纏著哥哥,問媽媽到底是啥病,怎麼人突然就一下子瘦了。從前媽媽可是那麼好看的,現在瘦得突了形,隻剩了骨頭。李光升看著妹妹,想說,卻又不敢說。他隻好轉過臉,裝作若無其事,說:“老毛病。調理調理就會好的。”
光雪說:“我看不太像。哥,你沒騙我吧?”
“我咋要騙你?”李光升嘴裏這樣說著,聲音卻變了。
光雪雖然才十五歲,可她伶俐精明。哥哥突然變了聲音,她一下子猜出了幾分。她先是呆著,望著哥哥;然後又問了句:“哥,媽媽是不是不能治了?”
“這……”李光升顫抖道:“這事別跟爸說。”
李光雪又呆了下,李光升怕妹妹承受不了,想過來拉她。她卻跑著出了門。她一口氣跑到莊子外麵的南坡上,西邊夕陽正漸漸沉進山裏,一大片火紅燃燒著,慢慢地變成暮靄中的蒼青色的灰燼。李光雪痛苦地望著夕陽,和更加蒼黑的暮靄。她一直覺得母親是個有故事的人,母親的大度、優雅,以及她對父親的那種小心翼翼,都讓她想更深一點地走進母親的心裏。可是……
病來如山倒。何況孟小書的病,並非突然到來,而是積勞成疾。即使兒子李光升也幫她瞞著丈夫李天大,女兒李光雪也一如既往,笑著跳著。可是,孟小書心裏早已在做著告別這人世的準備。她趁著能動,將簡樸的家好好地收拾了一遍。那些衣物,都被她歸置得井井有條。一些衣服上的破洞,她也細心地給補綴上。她又請人在老屋後麵蓋了兩間瓦房,好給兒子李光升娶親。這一切辦妥當了,她歇下來,捋了捋,她在這個人世上還要辦的隻有兩件事了。一件是為李天大的將來做個安排;第二是見見孟浩長。
孟浩長這個名字,近二十年來,從來沒人在口頭上提起過。當然,在心裏的默念,也許超過了千次萬次。孟小書終於撿了個晴好的日子,對李光升說:“我要進城去!”
“進城?”兒子有些吃驚。最近母親的狀況越來越不好,走路都有些艱難。如此身體,怎能進城呢?
“是的。我得進城。我隻到城隍廟和百花井去看看就回來。”孟小書態度堅定。
李光升不再言語了。他帶著母親,坐車進城。然後再坐公交,到了城隍廟。孟小書硬撐著上了城隍廟的二樓,她站在樓台上,朝四周一望。廬州城跟十幾年前的廬州城大不一樣了。但再怎麼變,在她的心裏,她依然記著城隍廟,記著城隍廟前的那家貢鵝店。記得孟雲生老爺和李晴兒太太帶著少爺,還有她,坐在店裏吃貢鵝;她似乎還能聞見貢鵝的香氣,還能看得見少爺孟浩長吃著貢鵝那種甜潤的模樣。廟前街依舊繁華,隻是不見了當年的影子。她趕緊收回了目光,對兒子說:“不看了。回去吧!”
兒子問:“咋又不看了?不去百花井了?”
“不去了。”孟小書複又站在樓台前,望向東邊。她一眼就看出了那條藏身在諸多房屋之間的百花巷。巷子就是指引,緣著巷子,她看見了那片空闊的大院,連片的公主府第,她甚至覺得自己看到了那棵桂花樹,和桂花樹下那井台。
她長噓了口氣。這一口氣,使盡了她平生的氣力,她慢慢地癱了下去。
半個月後,孟小書彌留之際給了兒子李光升一張字條,上麵寫著“百花井,孟浩長。”兒子問“這是……”她說出了這一生最後一句話:“他是你親爸!”
孟浩長正提著毛筆,眼看著李光升。這個年輕人長相樸實,目光沉著。他問:“你是來找我的嗎?”
“是的。我找……”李光升將攥在手上的字條打開,又看了一次,說:“我就是找你!我九點就到了,您不在。門上貼著條子,知道您沒走遠。這不,就又轉過來了。”
“找我?為什麼找我?”孟浩長慢慢地往畫案前移。他的眼睛還在盯著那畫到一半的山石。
“是我媽讓我來找你的。”李光升努力著將這句話說了出來。
“你媽?”孟浩長眼光還是盯著山石沒動,嘴裏不經意問道。
“是我媽。我媽她……認識您!她叫孟……”沒等李光升說完,孟浩長卻猛地轉過頭來,眼睛炯炯有光。他幾乎是搶過了李光升手裏的小字條。他掃了一眼,便頹然地坐到了椅子上。李光升忙上前扶住,問道:“沒事吧?您沒事吧?”
孟浩長擺擺手。他又看了眼小字條,這是孟小書的筆跡。這筆跡他太熟悉了。這筆跡最初就是從孟浩長的手把手中流淌出來的。這筆跡中浸潤著孟浩長和孟小書兩個人的綿綿不斷的氣息。
孟浩長拿著紙條湊到鼻子邊,聞著,聞著,又聞著。
李光升顯然是被孟浩長這舉動給鎮住了,他攥著手,不知如何是好,嘴裏隻是說:“沒事吧,這……”
“你媽媽她……”孟浩長問,聲音有些顫抖。
“她已經走了。”
“走了?去哪了?”孟浩長剛問完,就覺出了這“走了”的弦外之音。他手開始微微發抖,他重複了句:“走了?真走了!”
“難怪我十幾天前做夢,還夢到她。夢到她來跟我辭行,說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現在,她可真的去了!”孟浩長望著李光升,問:“她是哪天走的?”
“十一月初七。”
“初七?應該是這個日子。那天,我同丁老師去城隍廟吃貢鵝,晚上回來就做了那夢。”孟浩長喃喃自語。
李光升看著孟浩長一頭銀發,這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白臉,清瘦,而顯得不同於一般的鄉下老人。他悄悄地拿孟浩長跟自己的長相比了比,根本就沒有任何可比性。自己生得壯實,而孟浩長去清秀;但是,母親孟小書臨走之時,可是一字一頓地告訴他:眼前這個人就是他的親生父親。
難道?其實李光升一直在心裏難以釋懷。當母親告訴他這一切後,他隻覺得大腦裏立時被徹底地被震裂了。他看著癱在床上的李天大,這個苦命的男人難道不是自己的父親?這個男人自己知道這一切嗎?母親又為什麼要在臨走之前將真相告訴他?還有,既然他是這個姓孟的男人的兒子,那麼,妹妹小雪跟這個男人有沒有關聯?
百思不得其解。李光升在忙完母親的喪事後,一直沉浸在這種不解的苦惱與憤懣之中。
終於,他決定要來廬州城,要親自見一見孟浩長。
在來廬州城的路上,他一路默念著孟浩長的名字,反複在手心裏比劃著“百花井”三個字。他有些明白母親非要堅持抱著病體再走一次廬州城,再登一次城隍廟的心意了。母親是想最後看看這些。母親這一生,在李光升的眼裏,似乎都一直與東大圩聯係在一起。隻是這幾天,因為動了要見孟浩長的心思,李光升會在夜晚靜靜地對往昔作些回憶。這樣,在他記憶的最深處,仿佛曾經有過廬州城的影子,也仿佛有過一條小巷,一片院子,一大片房子,還有高高的山牆,母親抱著他站在桂花樹下的身影……當然,一切都已模糊,有的,甚至僅僅隻是李光升的想像與揣度。然而,它卻形成了一種潛在的指向,那就是在他最深的記憶之初,也正是與母親臨終前給他的紙條上麵所寫的“百花井,孟浩長”有關。
一個人如果永遠活在一間秘不透風的黑屋子裏,也是一種幸福。在黑屋子裏,他能看天,聽風,識雨,能自由思想,心生滿足:然而,當有一天,外來行腳的人給他打開了一扇窗子,他便萌生了知曉外麵世界的好奇與勇氣。而且,這種好奇與勇氣也便成了一種動力,推著他走出黑屋,撲向無限的未知。
李光升現在就是這樣。他想知道的太多了。可是,他卻一句也不能開口。
他怕!他怕他這一開口,會將二十多年的歲月徹底砸碎;會將這百花井裏的曾經有過的一切徹底砸碎。
然而,孟浩長卻開口了。
孟浩長端詳著李光升,問:“你是她兒子?她幾個孩子?”
“兩個。我,和我妹妹。”
“就兩個?”
“就兩個!”
“你多大了?”
“25.”
“25?”
“是的。過年就26了。”
孟浩長剛才還在顫抖的身子,此刻竟然好了。他站了起來,拉過李光升。李光升比他高一個頭,身材壯碩。他伸出手,半仰著頭,摸著李光升的額頭,說:“你媽媽讓你來的?”
“媽媽她隻給了我這字條,是我自己決定要來的。我想弄明白。”李光升感到孟浩長撫摸他額頭的手,太過於細膩了。不像李天大那粗糙的大手。那大手雖然粗糙,卻比這細膩的手更有力,更溫暖。
孟浩長停下手,讓李光升坐下,然後開始泡茶。他將茶杯端到李光升手裏時,又問了句:“她還告訴了你什麼?”
“她說您是我的親生父親!”李光升舒了口氣。
孟浩長身子一震,聲音又顫抖了。他道:“你媽媽說的是真的,你是我的兒子。是我和你媽媽的兒子!”
李光升突然覺得心裏空蕩蕩的。他喝了口茶,便起身要走。孟浩長有些驚訝,說:“怎麼就走了呢?既然來了,怎麼著也得吃餐飯。”
李光升說:“我還有些事。家裏還有人要照顧呢!”
“還有?是……”
“我爸!他癱了好多年了。”
“啊!我記得他叫李天大,是吧?”
“是的。”
“他是個好人!”孟浩長停了停,說:“我得去看看他!”
丁成龍直到老了,還時常跟孟浩長提起當年到東大圩的事情。在此之前,丁成龍也曾經到過東大圩。
東大圩,出廬州城四十裏,相傳為北宋大科學家沈括所設計修建。圩廣萬畝,處巢湖下遊,得地利與水利之便,向來為廬州糧倉。自大圩圈建之日,這裏就一直是廬州城裏富商巨賈們的覬覦之地。大批的銀錢開始投向東大圩,東大圩也由此成了廬州外圍最大的租田。上萬畝良田,被近百個大戶人家壟斷。這些大戶人家又將田地出租給周邊農戶,靠收租盈利。部分長年耕種在東大圩的農戶,就成了一些大戶在東大圩的老佃戶。一應耕種事務,悉數交給這些老佃戶處理。大戶們隻是到了秋天,收取租錢。當然,每年春天,大戶們也例行到東大圩走一圈。有些大戶與老佃戶建立了數代的關係,親近猶如親戚。在這樣的關係之下,他們之間走動得更加頻繁。逢上閑暇,城裏的大戶們也會帶著家眷,到東大圩來體驗一把鄉村生活。
東大圩的規製與體製,到了一九四九年,土崩瓦解。東大圩成了集體所有的大糧倉。廬州農業的亮點和重點,也就集中在東大圩。像丁成龍這樣的在文教局工作的國家幹部,自然少不了也要經常下鄉到東大圩。
在丁成龍的眼裏,東大圩就是一處普通的圩口。一九五四年,巢湖大洪水。丁成龍和文教局的其它人被組織成抗洪小分隊,赴東大圩堵口。洪水肆意,張牙舞爪,漫天鋪地,隨時要撕碎東大圩堤。丁成龍和部隊的戰士,還有周邊的老百姓,排成人字長隊,站在齊腰深的洪水中,堵口築壩。但最後,圩還是破了。不僅僅圩破了,還有九個參與搶險堵口的人被衝走了。洪水之後,丁成龍再到東大圩,一片濁黃色的東大圩,跟他當年在戰場上所見十分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戰場那是人禍,而這是天災。他看見一些農民正在圩埂上徘徊,神情淒苦。他想起了古人那句著名的唱詞: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從那年大水後,丁成龍再沒去過東大圩。當孟浩長跑到文化館來,說要請他一道去東大圩時,他還真的愣了下。接著,他問:“怎麼突然要去東大圩呢?去寫生?”
“不是。是去看一個故人。”孟浩長道。
“故人?”丁成龍有些驚詫。
“是的。好多年前的故人。其實你也認識。”孟浩長說:“你曾在百花井見過。”
“哪是?”丁成龍立即在腦子裏搜索了一遍,沒有答案。他問:“到底是誰呢?”
“等到了就知道了。”孟浩長拉著他,出了文化館大門。
一年多前,丁成龍正式回到了廬州。他的帽子問題得到了平反。在重新安排工作時,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要麼回到文教局機關,要麼到下屬館站。他選擇了文化館。他對機關已經沒有任何興趣了。機關如同一隻對開的門,曾狠狠地夾疼了他。他不想再踏進去。而文化館,正切合了他這些年在新疆所從事的工作。在新疆二十多年,除去那些逃亡與奔波之外,他幹的工作,大多與文化宣傳有關。
丁成龍隨著孟浩長到了城隍廟。孟浩長切了一隻貢鵝,又賣了些點心,然後兩個人到車站乘車。
東大圩之冬,多少有些蕭瑟。圩埂上的柳樹,全禿著光杆子,黑漆漆的;草已發黃,有些已開始零落進泥土。圩埂上,不時有低矮的房子。圩區房子,因為地勢問題,基本上都是沿著圩堤興建。因處在迎風口,所以房子一般較低矮。路不太平坦,架子車的車轍,壓出了兩道深溝。溝裏積水,渾黃。
孟浩長手裏捏著孟小書寫的字條,從進入東大圩開始,他就不斷地感歎著。他一會兒指南,一會兒指北,告訴丁成龍:那南邊原來有個大莊子的,現在沒了;但那棵大樹似乎還在。那北邊曾經是東大圩的村部,再早些的時候,他的父親孟雲生曾帶著他在那本是保長辦公室的小房子裏住過一晚。母親李晴兒早晨會蹲在水邊,照水梳頭。父親指著母親,對孟浩長說:“那就叫臨水照花!”在父親眼裏,母親就是一朵花。父親不曾想到:就在他說出這句話的第三年,母親這朵花就插到了別人的袖口上了。
父親到紫蓬山後,孟浩長再也沒到過東大圩。解放了,東大圩已經屬於了人民。父親當年購買的租田,也全部交給了集體。東大圩與孟家的聯係,變成了單純的佃戶李老實與孟浩長的聯係。那時,孟浩長與高巧雲住在百花井,李老實每次進城,都拐到百花井來。他背著個大袋子,袋子裏是新鮮的蔬菜瓜果。他放下袋子,接了高巧雲遞過的茶水,擦著汗,感歎一聲孟先生怎麼就舍得出家了呢,再無話。這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有時,他會帶著他的兒子李天大一道。李天大同他的父親一樣,甚至更加沉默寡言。孟浩長很少跟他們父子說話,隻有高巧雲,張羅著給他們一點點心。換季的時候,也會送他們一點布料。逢上年節,李老實會偶爾送來雞、魚和豬肉。孟浩長便讓高巧雲去城隍廟切一隻貢鵝送給他們。這一來一往,直到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才戛然而止。
孟浩長走得很慢,丁成龍幾次催促。可孟浩長就是耐著性子,他似乎是要數清楚路上的螞蟻。
日將中天,終於到了中廟。
李光升的家正對著圩埂。屋基坐落在圩埂下麵的一處平台上。門前是一大塊場子,四圍栽著些樹木。樹木大都光著頭,伶伶而立。孟浩長隻是隨便看了看,他的目光被南角的一處井台拉了過去。那井台圓形的台麵,青石的井圈,同百花井的那井台井圈如此相像。而井台旁邊,也有一棵桂花樹。
丁成龍當然也看出來了,他對著孟浩長道:“這……簡直就是搬了個百花井來了呢!”
孟浩長正要回答,屋裏傳出咳嗽聲。接著就聽見屋內人問:“誰呀?進屋裏來吧!”
兩個人進了屋。正對著大門,便是一張床。床上正半躺著一個男人。蒼白的臉,將發黃的胡須映得有幾分淒惶。孟浩長嘴動了動,卻沒問出話來。倒是丁成龍說了:“我們來找個人”。
“找人?找誰?”男人問。
“李……李光升!”孟浩長道。
“啊,那是我兒子!早晨出去幫窯場上磚去了。馬上應該回來了。你們等等。”男人說:“桌上有茶水,你們自己倒。我這……”他苦笑著。
孟浩長盯著男人的臉,慢慢地就將他同二十多年前跟在李老實後麵的那個年青人重疊起來了。即使那臉色再蒼白,再淒惶,但眉眼和格局不會變。他是個畫畫的人,能看出皮相之中的骨骼。這就是那個青年,隻是歲月將他磨倒在了床上。算起來,他應該比自己年長。當年,這個青年跟在李老實後麵,高巧雲讓孟浩長喊他“哥哥”,而李老實則說:“要不得,直接喊天大就行。你是少爺,不能亂了禮節。”孟浩長其實什麼也沒喊。可他記住了李老實說的這青年叫天大。天大,天大!這名字有意思。是說天真的大?還是說要說比天還要大?
當年沒問。現在自然也不會再問了。孟浩長湊近床邊,仔細地看了看李天大。
李天大卻別過臉。牆壁上畫著一道道的深痕,像一隻被囚禁的蛛網。
丁成龍走出屋子,恰好李光升回來了。李光升剛想同丁成龍打個招呼,孟浩長就出了門。李光升張著嘴,說:“你……你怎麼?”
孟浩長伸出手指擋在嘴唇上,示意李光升不要再說。出了門,他拉著李光升,三個人到了圩埂上,孟浩長介紹說:“這是丁老師,你丁伯伯!”
“丁伯!”李光升說:“剛才我爸沒覺出什麼吧?”
“沒有。”孟浩長說:“我就是拉丁伯伯來看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這樣吧,光升,我也幫不了什麼,這點錢你拿著,給他治治。真治不了,就多弄點營養品。還有你妹妹,讀書也要錢。”
“我不能收!”李光升道。
“拿著!”孟浩長將錢塞在李光升手上,說:“這不是給你的。是給他們的!你替我給他們用就好了。”說完,他又問:“你媽墳在哪?”
“在紫蓬山上。”李光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