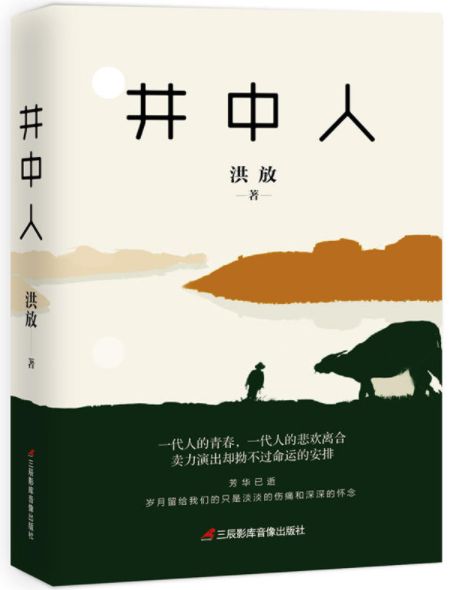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三章 廬州滄海
百花井的拆遷公告上了牆。
公告上說:為提升城市品味,決定對百花井地區進行拆遷重建。所有居民,請在公告發布後一個月內,搬遷完畢。所拆遷房屋,按現行規定,予以補償。
陳健康盯著公告,看了三遍。看完後,他有些興奮。回家後對正在看電視的耿麗萍說:“終於上牆了。百花井真的要拆遷了。”
“真的?看你那高興的。一輩子就這點出息。”耿麗萍眼睛繼續盯著電視,電視裏正播放《紅樓夢》。
陳健康將拐杖放下,坐到沙發上,說:“按現行規定,我們這房子得換兩套。”
“兩套?”耿麗萍回過頭來,說:“哪像丁老師家,不得換個十套八套的?”
“那……也許是吧!”說到丁成龍家的別墅,陳健康心裏就發虛。六年前,丁昌吉不知使了什麼法子,竟然在這百花井大院子建上了別墅。陳健康和耿麗萍起初也想跟著建,可剛一動靜,街道上就找來了,說私自建房,違法,即使建好了,也得拆除。耿麗萍問那怎麼老丁家就能建?街道上人說他家是辦了建房手續的。耿麗萍說那我們家也辦?街道上的人眼睛一橫,說你們也辦得下來?要知道,老丁家那姑娘可是通天的人物。不然,想在這百花井建房子,估計連想也別想。耿麗萍就問那丁昌吉不就是個做生意的女人嘛,哪來那麼大能量?街道上人說這你還真得另眼相看。那丁昌吉可不僅僅是個做生意的女人,她能耐大得很。連市裏領導都得高看她三分。
耿麗萍不再爭了。事後,陳健康問過陳小健。陳小健很不高興,隻說了三個字:“不知道。”
不管怎樣,丁成龍家的別墅還是建了起來。陳健康和耿麗萍有時候看著丁家的別墅,心裏自然不是滋味。現在,要拆遷了。陳健康倒是笑出了聲。耿麗萍問:“傻笑個麼子?撿了元寶了?”
“我是笑丁家那別墅呢,不也要拆了?”
“就這點出息!像你那兒子,一對活寶父子!”
“這跟咱兒子有麼關係?”陳健康想站起來,努力了下,卻還是坐了下去。
“你那兒子不就像你,沒個出息。這一輩子就被那個小混血給吃定了。”耿麗萍私下裏一直叫丁昌吉“小混血”。
“那也未必。”陳健康辯解得一點分量也沒有。
耿麗萍又扭過頭看《紅樓夢》了,電視裏劉姥姥正進大觀園。
陳健康一個從窩在沙發裏。想了想,他拿起電話,開始撥陳小健手機。忙音。再撥,仍是忙音。
陳健康掛了機,嘴裏罵了句:“忙!忙個屁!忙到四十歲了,還光棍一條……”
從前,陳健康也算是百花井地區有些分量的人物。他自從進入百花井,就注定了與丁成龍一家有解不開的緣分。一九五六年冬天,11歲的陳健康跟著父母搬到了百花井。他們的房子就緊挨著丁成龍家的房子。那時,丁成龍已經畏罪逃亡,家中隻剩下胡滿香和不到一歲的大兒子丁抗美。丁抗美這名字是丁成龍給取的,不過,丁成龍並沒有看到大兒子的出生。陳健康一家搬到隔壁,卻很少見到胡滿香和兒子。更多的時候,胡滿香住在娘家。直到五年後,街道上來人將胡滿香家的房子騰空,分配給了新的住戶。那時候,十來歲的陳健康不會想到,二十多年後,這當年住在隔壁的胡滿香,又會重新回到了百花井。而且,是一大家子回來的。而且,又在百花井建起了一座別墅。再而且,陳健康最不能容忍的而且是,他陳健康的兒子陳小健,竟然為著老丁家的小女兒,耗上了大半生時光,甚至到現在仍無著落。
丁成龍從新疆重回百花井時,正是陳健康最風光的年華。三十多歲正當年的陳健康,其時正在街道食品站當站長。計劃經濟時代,食品站的地位,可想而知。豬肉,糖,豆腐,一應副食品供應,都得經過食品站。雖然站長級別不高,可是手裏頭有硬貨,走在街上,不斷有人對他點頭哈腰。晚上,百花巷裏也經常有人來敲陳健康的家門。耿麗萍總是站在門前,送客人時重複著同樣的話:“都老熟人了,客氣個啥?有事招呼就是了。這麼客氣!”來人總是笑著,說:“以後還得請陳站長多關照,多關照!”
陳健康那時候當然還是個雙腿健全的男人。他抽煙,喝酒。但這些活動從來不在百花井這大院子裏。一回到家,他得完全聽命於耿麗萍。耿麗萍在嫁給陳健康之前,曾經是廬劇團的演員。隻是因為身材太小,加上唱功一般,在劇團裏呆了七八年後,便轉到了鋼鐵廠。後來經人介紹,嫁給了陳健康。古話說一物降一物,在食品站裏風風光光的陳健康,一回家卻變成了耿麗萍的靶子。陳健康每個月手頭上私自握著的那些肉票、糖票、豆腐票,都被耿麗萍給搜了過去。最後,這一切終於醞釀成了一場大禍。在陳健康擔任食品站長的第五個年頭,因為克扣供應指標,陳健康被撤職,並被調到街道工廠擔任一般工人。也就在那一年,他的大女兒陳春,上課時突然發病,口吐白沫。那年,她才十二歲。十二歲的孩子吐著白沫,渾身哆嗦,在地上打滾。上課的女老師嚇得當場哭了,好在校長是個有經驗的人,不幸的是他家亦有一個發病起來狀況的孩子。校長讓人拿來筷子,撬開了陳春的嘴,把筷子放在上下牙齒之間。又使勁地掐人中,直掐到陳春安靜下來。校醫通知耿麗萍到學校為領人。校長問耿麗萍這孩子以前發過這病麼?耿麗萍說從來沒有。校長說那以後可就得注意了,這叫癲癇!厲害得很,發作時如果不采取果斷對路的措施,會咬斷舌頭,會死人的。耿麗萍臉色殺白,如土一般。她領著陳春回家。陳健康說這叫半角瘋,得找中醫。從此,陳春便成了百花井大院的藥罐子。中藥的香味,多年來一直飄蕩在百花井。
陳春後來考取了中專,在幼師當老師。似乎是門向招的,她至今仍是單身。如果說陳小健是因為丁昌吉而未婚,那麼陳春的單身卻讓人費解。這麼些年,她除了上學上班,唯一能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中藥。她似乎從不與任何男人往來,在她的世界裏,壓根兒就沒有男人的氣息。
當然,這都隻是陳健康和耿麗萍的猜測。十年前,陳春到幼師當老師後,就搬離了百花井。她幾乎不太回家,也很少打電話。耿麗萍要想知道大女兒的情況,往往得問小女兒陳蘭。陳蘭每隔半個月左右會到幼師去看看姐姐。回來後,會報告說:“姐姐長胖了些”,或者說“姐姐學會一個人做菜了。”
一個五口人的家,假如按照正常的軌跡運行,也許早就應該是九口,甚至十口以上的大家庭了。可現在,依然是五口。未來遙遙無期,前途一點也不光明,這是讓陳健康和耿麗萍在百花井越來越壓抑的原因。直到拆遷公告上牆,陳健康猛拍沙發。耿麗萍罵了句:“神經發了?”
“不是神經,是精神!”陳健康說:“我上半年聽說百花井要拆遷,就找人問過了。我們家小健和春兒,都沒成家,但也老大不小,可以分開,單立戶頭。那樣,拆遷時就可以一人搞一套房子了。”
“有這好事?”耿麗萍挑著眉毛。
“好事要來了,擋都擋不住。明天,我就去找人讓他倆單立戶。”陳健康感到柳暗花明,一片美好。他禁不住哼起了廬州小調。
自從胡滿香去世後,丁成龍就一直住在書房裏。
書房就在樓下,窗子朝南,當年丁昌吉建這別墅時,特意給父親留了這間三十多平米的書房。丁昌吉說:“老頭子一生都糾纏在書上,沒有像樣的書房,不像樣。”她喜歡將“不像樣”三個字掛在嘴上,評論和衡量一件事物好壞時,倘若好,就說“像樣”;不好,自然就是“不像樣。”其它人不明白這說話的來由,但丁成龍清楚:這是從新疆那邊連隊裏學來的。連隊裏的人來自五湖四海,各種方言交錯。方言之間,互相對抗、整合,最後形成了一些獨特的或許隻有個別連隊才說的連隊官話。丁成龍所在的16連,最有影響的官話就是“像樣”與“不像樣”。
丁成龍是連隊裏為數極少的不說這官話的人。他的語言體係本來就駁雜。既有魯北土話,又有豫南方言。五十年代到廬州後,又接受了一些廬州方言。不過,總體上偏向北方普通話。丁昌吉講話其實也是普通話,隻是摻雜著一些連隊官話,便顯出了與眾不同。特別是她到了廬州後,又跟著孩子們學,將“老母雞”讀成“老母zi”。這雖然僅僅隻是在表現在語言上,但卻顯示出了這孩子個性上的特立獨行。
胡滿香在世時,每每跟丁成龍吵嘴,到末了,總要夾上一句:“我知道,你心裏就隻有昌吉!”
丁成龍立即語塞。
丁昌吉是丁成龍這一生的軟肋。這一點,除了胡滿香,隻有丁成龍自己清楚。
丁成龍每天晚上讓保姆回家。保姆住得也不遠,就在杏花公園邊上。她是北鄉人,進城來陪孩子讀書,順帶著做保姆。丁成龍就一個人,吃得簡單,洗也簡單,打掃更是簡單。因此,這保姆算得上是清閑。雖然是個鄉下女人,四十掛邊,一開始來丁家還有些拘謹。慢慢地熟悉了,竟然露出喜歡看書的習性。丁成龍就很喜歡,找了家中他認為能讓保姆看的書,就拿出來,讓保姆自個兒挑著看。這樣,有時候丁成龍在書房看書,保姆就在客廳裏看書,房子裏靜悄悄的。丁成龍喜歡這種氛圍。大概是一生顛沛的時間太長了,他感覺自己就像一隻老龜,越年齡大了,越往身子裏麵收縮。
最近,丁成龍也在做一件他認為很有些意義的事情,那就是編寫《廬州地名誌》。
這件事情的緣趣,還是因為孟浩長。
有天黃昏,也就在上次喝老酒之後不久,丁成龍和孟浩長一道出了百花巷,想沿著淝河走走。路上,就碰見幾個搞畫家。畫家們見了孟浩長,自然恭敬。平時,他們想見他,也不一定能見得著。一見著,馬上就上來,問長問短,特別是問最近孟先生都看了哪些人的畫,又有哪幾位畫家有了長進?孟浩長笑而不答。這其中有位留著大胡子的畫家,叫葉長風的,問孟浩長:“上次托人轉送過來的那幅畫,不知先生覺得如何?”孟浩長瞥著葉長風的大胡子。孟浩長一生畫畫,卻從來沒留過大胡子。他永遠是白淨麵皮。他瞅了很長時間,才問:“是那幅《小南門春早》?”
葉長風諾道:“是。請先生批評!”
“畫且不說。就畫中所畫的風景,並不是小南門,而是水西門。從前的水西門!”孟浩長說著就拉丁成龍走路。葉長風愣在那裏,足足有三五分鐘,才喊道:“孟先生,我是問那幅畫……”
到了淝河邊上,水正瘦。岸邊的柳正瘦。停泊在河裏的船正瘦。
丁成龍說:“孟老師,你剛才那樣說人,是不是有點太過了?麵子上拉不下來。”
“不過。不過。”孟浩長輕輕一笑,接著道:“我倒在想,丁老師你得搞本書,關於廬州地名。免得這些年輕人老是出錯!”
“好主意。廬州的不少古地名,現在已經消失。有些雖然名子還在,但地方發生了變化。搞本書,詳細地記錄和介紹這些,有意義,有意思。我來搞!反正我現在閑著也是閑著,趁老骨頭還能動,就多蹦它幾天吧!”丁成龍竟然有些激動。當天晚上回到百花井,他便在書房裏鋪展開了。
現在,他正寫到《城隍廟》。
寫著寫著,他便又開始行進在五十多年前的廬州城中了。
這本來是一塊江淮衝積平原,五萬人的廬州城,就依在平原的中間,猶如桑葉中心的一枚嫩蠶。淝河就是桑葉的脈絡,而金鬥河是更加細小的血管。城隍廟立在廬州城的中間,高大的廟牆,介於黃色與鐵紅之間。城隍廟前,便是一條一裏路長的前街。街上人煙嘈雜,市聲不斷。
丁成龍隨著部隊進入廬州城時,廬州正迎來它兩千多年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轉折。它剛剛被確定為省會所在地。不斷有人從全國各地調來廬州,一些工廠也開始遷往廬州,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隨即拉開了序幕。
這些從全國各地調來的人群中,部隊人員占大多數。而這些人,將來會成為這座新興城市的建設者,經曆者,見證者。
三條主幹道,一條東西,兩條南北,構成了廬州城的道路格局。丁成龍最初被分配在宣傳辦。雖然他正式的學校生涯也就四年,但後來到了桐柏根據地後,他又上了軍政大學,在部隊裏也算是個秀才了。他負責宣傳簡報的采寫。每天,他奔忙於城市的各個角落。整個城市,似乎也是一個大戰場。東邊,正在興建鋼鐵廠;城隍廟前,金鬥河改造與淝河治理同時進行;而南邊,省委、省政府辦公區正在建設;西邊,電廠和醫院以及三所學校,都已破土動工。這火熱的場麵,真個是“百廢俱興”。丁成龍往往是早晨在南邊,中午卻到了西邊,黃昏時,他卻正在淝河邊上與施工隊長交談。晚上,在宣傳辦的簡陋的辦公室裏,他伏案寫稿。那時他年輕,才二十多歲。激情充沛,精力飽滿。隻有每周的周日下午,他才稍有清閑。這清閑時光,他便交給了城隍廟。
城隍廟裏已沒了供奉。大殿改成了軍管會所在地。
丁成龍偶爾進廟去看看。他喜歡看廟頂的鬥拱,興趣好時,他會從後殿的樓梯上到二樓。二樓是個城樓,站在二樓上,他可以對這個正在興起的城市一覽無餘。他能看見淝河飄逸著,從城北流過,又向城西而去;而在城東,金鬥河從淝河引出,如同一根腸子,蠕動在廬州城中。城裏也有高一些的建築,比如教堂。廟前街一直往東,出口處便是基督教堂,大十字依舊立在哥德式建築的尖頂上;而向南,另一座圓形建築格外醒目。藍色,月形。丁成龍最初也不知其名。他專門跑去看了看,才知那是一座清真寺。基督教堂的尖頂,或許是時下廬州城的最高點。而再向東,還有一座十來層的建築——教會醫院。但是,從城隍廟的二樓上看,教會醫院還是比城隍廟低。丁成龍反複比較,最後認定是城隍廟本身所處的位置較高。這樣,他就看出了這座城事實上是以城隍廟為中心,向四周輻射。製高點在城隍廟的城樓上。城隍廟下,向東是廟前街,向西便是原來的廬州縣治。如今,縣治是臨時政府所在地。他當然也看見了從廟前街往東的那條狹長的小巷百花巷。公主府是一大片建築,被征用後,成了規模最大的宿舍區。不過,住在那裏的都是成家的幹部家屬,像丁成龍那樣的單身漢,隻能住辦公室邊上的集體宿舍。
在城隍廟上呆得時間久了,天色已暗。丁成龍就會到下邊廟前街上吃點小吃。
廬州飲食介於南北之間,以麵食為主,兼有米飯。丁成龍喜歡吃三個包子,外加一碗酸辣湯。興致特別好時,他也切過一兩次貢鵝。鵝肉細嫩,入嘴即化。最初那幾年,他當然還不曾真正的品嘗出貢鵝的鮮美。他懂得貢鵝之所以成為貢鵝,是在認識孟浩長之後。那是他住到百花井後的事情了。
最近,為著寫《廬州地名誌》,丁成龍將大時間都放在跑市區的大街小巷上。他也在家查閱資料,但他更願意做實地調查。很多地方已然消失,隻剩下了地名。有些地方,連地名也改了。往往是,他站在那些地方,恍若隔世。他越發感到了急迫。甚至,他回到百花井,坐在自己的書房裏,他也覺得或許就在不久的將來,百花井這地名也會成了一個曆史和塵封中的地名。那時,與這個地名息息相關了幾十年的生命,又會沉淪何方?
從這個意義上,丁成龍不願意看到百花井的拆遷。
昨天晚上,他給丁石子,也就是丁為民區長打了電話。他問上牆的公告是不是就是最後的通諜?丁為民在電話裏語氣短促而肯定,說就是,一個月後,不同意拆遷的,將強行拆遷。丁成龍說那百花井呢?丁為民似乎有些不耐煩,說井留著,行了吧?丁成龍還是追了句:就留一口井?那這公主府第?丁為民大了聲,說都得拆。就留那口井!
就留那口井!丁成龍放下電話,心裏有些悲哀。他也知道,這拆遷的事不可能是丁石子說了算。留哪裏,拆哪裏,是政府說了算。可是,這偌大的百花公主府第,建在這廬州城已經一千多年了,真的將消失不見?沒有府第,僅僅留一口井,哪能說明什麼?前些年,隔壁省還有文史專家專門考證:百花公主後來從廬州嫁到外地,並且死後也葬在外地。廬州城裏的百花公主府第並非百花公主真正宅第,而是其父吳王府第。為著這個,丁成龍奮筆直書,連寫了三篇文章,論證廬州百花井即百花公主府第所在。他一向做事踏實,這三篇文章自然也是有理有據有節,硬是讓對方落荒而逃。為此,孟浩長還專門送了他一幅畫,名字就叫《百花井邊百花人》。
毋庸置疑,城市的發展大勢所趨。廬州城也從當年的五萬人的小城,發展成了現在的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拆遷,猶如一根魔杖,正悄然指揮著鏟車、挖掘機、推土機,奔向一處一處古老和陳舊的建築。有時,你頭天黃昏還在某一幢老房子前看夕陽,第二天卻發現已是一地塵埃;有時,你剛剛為某一處古建築感懷不已,但過幾天卻再也找不著其蹤跡。城市生長之快,古舊建築消逝之疾,令像丁成龍這樣的老輩人難以適應。丁成長自忖自己也不是個過於守舊的人。如果他這一輩子安於守舊,那麼,或許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就不會選擇逃亡之路,而成了某一處勞改農場中的五類分子。但他沒有!
他選擇了流亡與荊棘,同時也選擇了天山、大漠與胡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