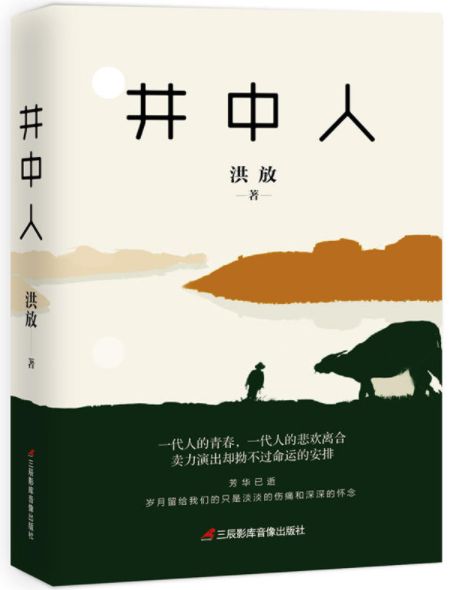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百花井人
孟浩長這一生有三件東西一直不曾離開。
一是書。二是貢鵝。三是百花井。
書是孟浩長來到人世間看到的第一件物品。那書是發黃的長卷,被當軍官的父親放置在臥室的南窗前。他出生第三天的時候,眼睛開始能看見光。光線引著他,看見了那掛在南窗上的長卷。父親喜歡將書籍整理成長卷。這個習慣,一直保存到父親進入法音寺。在法音寺裏,有一年秋天,孟浩長過去看望父親。父親上山采藥去了,但他看見了父親掛在寺裏窗前的那些經書。有些已然發黃,有些開始脫落,然而一旦掛起,光線通過書卷,漫漶不已,則立即有了前塵舊事的幻覺。他站在父親的僧寮裏,黯然無語。
而他自己,這一生幾乎不曾與書有稍長時間的分離。三歲開蒙。五歲家中延請先生為他講經。七歲,他便上了當時廬州城裏最好的小學。廬州城小,雖然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但很少成為兵家駐守之地。前清時,廬州出過淮軍,但淮軍駐在巢湖,後來開到了江南;軍閥割據時,廬州一帶,連年戰爭,但沒有哪一個軍閥在這城裏安營紮寨;日本人來了後,與中國部隊在廬州沿線,形成了長達八年的對峙局麵。日本人也曾三進廬州,但很快就退了出去。廬州因此成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相對比較穩定的一處城池。孟浩長的父親孟雲生是一九四三年調防到廬州來的。按軍銜,孟雲生是上校。然而隻是個名義上的參謀。他的主要工作是為長官提供軍事之外的一切文化娛樂。這是個生來靦腆的男人,喜歡唱戲,吟詩,更多的時候喜歡呆在家裏,翻曬和修補那些舊書。他一到廬州,就讓兒子孟浩長入學讀書。孟浩長的母親從前是天津衛銀行家李樹賢的小女兒。她酷愛唱戲,因之在一次天津衛的私人聚會唱戲的場合認識了孟雲生。一見鐘情,私訂終身,最後幾近私奔,跟隨孟雲生輾轉多地。及至到了廬州,她一下子喜歡上了淝河。她幾乎把所有的時光都放在了淝河邊的赤闌橋頭。流水照花,一九四三年的淝河水,應該是無數次收納和映照了這個叫李晴兒的女人的身影的。
這一生,孟浩長讀了多少書?又經手了多少書?
孟浩長說不清楚。也沒人能說得清楚。他曾經跟丁成龍說過:書就好比頭發,長在頭上,但最後又落了。落了又生,循環往複,誰能記得?
孟浩長喜歡且一生不離的第二件東西便是貢鵝。
吳山貢鵝。僅僅是吳山貢鵝。其它地方的鵝他從來不吃。
吳山是離廬州不遠的一個小鎮子,叫吳山鎮。傳說是當年吳王墓的所在。吳山出貢鵝,貢的也就是吳王。吳山貢鵝的做法,民間傳有三大要素:吳山當地鵝,吳山當地水,吳山當地料,缺一不可。用此三要素做出來的貢鵝,肉嫩,鮮美,有嚼勁,且肥而不膩,爽口清香。孟浩長現在雖然七十二歲了,但他一直記著當年第一次在城隍廟方李記吃吳山貢鵝的情景。那次,穿著旗袍的母親挽著父親的左臂,父親用右手牽著七歲的孟浩長。後麵跟著比孟浩長大三歲的高巧雲。他們一行四人上了方李記的二樓。父親選了個臨窗的位置。彼時,抗日烽火正燃遍大江南北,廬州城卻格外安逸。窗外,一樹香樟,雖是春天,卻落葉。孟雲生讓李晴兒點菜。李晴兒說:“讓浩長點吧!孩子們想吃什麼,就點什麼。”
高巧雲是孟家到廬州後所延請保姆的女兒。保姆姓湯,清絲亮腳,讓李晴兒十分喜歡。女兒十歲,乖巧可愛。有時,保姆會帶著女兒一道來孟家。巧雲並沒讀書,卻能跟著孟浩長背些四書五經。孟雲生尤其喜歡這個女孩,因此出門也帶著。
孟浩長看著跑堂的送來的菜譜。他左看看右看看,總是拿不準。倒是旁邊的巧雲先說了:“就點這鵝吧,聽說這鵝最好吃。”
“那就點鵝!”孟浩長白淨,說話斯文。
李晴兒笑著點點頭,說:“那就鵝。雲生,你再點幾個菜吧!”
那天,鵝一共上了三次。孟浩長除了貢鵝外,再沒吃別的菜。孟浩長並不曾知道:就是這城隍廟中的貢鵝,鎖定了他一生的味蕾。
味蕾決定命運。這當然有些牽強。可是,當八十多歲的孟浩長回首之時,他卻難以對此加以否定。即使在最艱難的那些年內,他甚至僅僅靠一小塊貢鵝,度過漫漫長夜。貢鵝於他,已不僅僅是一種食物,更是一種與精神相通的憑依。
孟浩長一生無法離棄的第三件東西,嚴格說不是他無法離棄,而是他根本離不開。那就是百花井。
百花井是廬州城北的一眼古井。傳說漫長,又與吳山貢鵝的吳王扯上了幹係。百花井之地,當初是吳王府治所在。吳王有女,名百花公主。百花公主命人於院中打井取水,以百花飄於井水之上。井水甘冽,四季不斷。逢上大旱之年,井水供全城汲用。後百花公主故去,百花井仍存。百花公主府第周邊即被稱為百花井。百花井其實也就是一眼小井。青石井台,突出地麵約一尺。井圈上可見數道磨痕,乃長年汲水所致。下井台三米,有青苔數株,長年陰涼,青碧可愛。到一九五0年代,百花井地區已成為廬州城之中心。它東與金鬥河相連,西與城隍廟相接。自金鬥河邊進入百花巷,巷深百米。兩旁高牆,生有爬山虎,連綿蒼鬱。每至初夏,爬山虎開出細碎白花,偶爾風吹,亦能發出微微清香。不過此花開時極短,不到三五日,竟消隱不見。高牆盡頭,豁然開朗。似《桃花源記》所載:初極狹,才通人。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此處亦是豁然開朗。一方約有三畝的空地,靠南亦是高牆,靠西是小學校的後牆。靠北是一長排二層小樓,靠東是老式的百花公主府第,進圓門後,又是一番景象。而百花井,即在這圓門之前,井前有老桂樹一株。此樹年歲不知,根廣數尺,下幹中空,內可藏小兒。七歲那年,孟浩長一家第一次到達廬州城,就入住百花公主府第的第一進。那亦是一座別致的小院子,有瓶形月門,三麵花牆,唯靠北一排五間房屋。上有兩間閣樓。孟浩長一家就住在這五間大房子裏。
一個人的一生也許可以說很漫長,但相對一些老物件來說又實在是短之又短。且不與磨痕道道的百花井相比,就拿這五間老房子來說,孟浩長時常覺得人生不過一芥而已。這一粒芥子,恰如畫家作畫,隨手一丟,正好丟在了這五間大房子裏。七歲那年,他走進最靠裏頭的那間屬於自己的屋子裏,他不可能預見他會在這呆了快七十年。而且,將來還會在這百花井邊終老。不過,作為一粒芥子,他既然紮根在了百花井,那反過來他又成了百花井一切變化的觀照與目擊者。他曾在同丁成龍一次次的喝酒聊天之中,談到這井邊人生,人生之井,結果他們實在無法找出比“滄海桑田”更加適合形容百花井近百十年變遷的詞語。他在六十歲後,給一些同道寫條幅,往往就隻寫這四個字了。別人問何寓意,他亦不作解釋。人生如井,越老越空。又如井苔,越來越寂靜。
這是無法避離的事實!從內心意義上,孟浩長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百花井。三年前,李光升從東大圩過來,要接他去東大圩居住。他側著臉問光升:“你是想我活得長些,還是短些?”
光升自然回答:“長。越長越好。”
“那就讓我繼續居在這百花井。這井水就是我活下去的仙丹。”孟浩長說著,望著窗外的井台。
光升有些疑惑,問:“哪還有井水呢?都被蓋子蓋了。”
“這你就不懂了,井被蓋子蓋著,可是井水的氣息還在往上。每天我隻要在井邊坐上一坐,人就活泛了。”孟浩長又指指北邊,說:“何況這裏還有你丁老伯,陳老伯。我們仨,可是有過約定的。”
“約定?”
“至死不離百花井。”
“哈,這是哪年約定的呢?”
“我六十歲時,他們為我做壽。就是那次,我們在百花井台上喝酒。桂花正香,竟然發出新枝。酒到酣處,便有了這約定。”孟浩長道:“光升,我知道你的孝心。等我哪一天真的走了,你再來百花井接我,把我葬到法音寺旁。”
李光升點點頭。
後來,這三年,李光升每次過來,再沒提接孟浩長去東大圩的事了。
丁成龍回到百花井時,孟浩長剛剛從自己在府前街的舊書店回來。兩個人在百花巷口撞上了。
孟浩長動了動鼻子,他很快就嗅見了吳山貢鵝的氣味。他笑著,說:“我這也有好東西!”
“好東西?啥好東西?不會是一本破書吧?”丁成龍挪揄道。
孟浩長拉了臉,咳嗽了聲,說:“破書?我可沒破書。破書抵萬金。但今天這可真的不是。”
“哪是?”丁成龍興趣上來了,湊到孟浩長身邊,目光盯著他手上的布袋子。
布袋子鼓鼓的,不像是書。看形狀,倒像是一瓶酒。他湊近聞了聞,說:“老窖?”
果然是。陳年的廬城老窖。孟浩長舊書店的一位顧客特意送給他,說是其父親藏了多年的老酒。
酒席就設在丁成龍的屋子裏。丁家住在大院子北邊,樓上樓下一共六間。從前,這房子是連著北邊二層小樓的。六年前,丁昌吉上下疏通,硬是在北邊樓的旁邊空地上,建起了這座上下六間的別墅。那時,丁成龍的妻子胡滿香還在。可現在,就隻有丁成龍一個人守著了。貢鵝,花生米,海帶絲,保姆又臨時炒了三個熱菜,打了個湯。陳健康也拄著拐杖過來了,他是三個人當中年齡最小的,可是身體卻最不方便。十來年前,酒後一場車禍,讓他從此與拐杖結緣。本來,陳健康是跟丁成龍、孟浩長搭不上伴的。可是,住在這百花井的老住戶現在僅剩了這三戶了。緊算慢算,也是近六十年的鄰居。所以,自從陳健康拄著雙拐杖後,丁與孟的二人對酌,變成了三人相酌。
酒是好酒。隻是年份太長了,一瓶酒隻剩了七兩。好在三個人都有節製,七兩正好。一邊喝酒,一邊就談到這鋪天蓋地的拆遷。
陳健康說:“聽春兒說,這次可是動了真格的。百花井也在拆遷之列。”他轉向丁成龍,繼續道:“丁老師應該更清楚吧,據說石子是這次拆遷的總指揮。”
“我不清楚。”丁成龍說的是實話。他也有半個月沒見著小兒子丁石子了。
丁石子是丁為民的小名。丁為民現在是百花井所在的淝河區的副區長。半個月前,丁石子,不,丁為民丁區長曾給父親丁成龍打過一次電話。在電話裏,丁區長語重心長,問及丁老爺子身體,說能吃就吃,能喝就喝,別到處亂跑。然後又說到即將開始的百花井地區的拆遷。他給丁成龍下了道死命令:不議論,不反對,不拖後腿。
丁成龍沒等丁區長說完,就摜了電話。保姆看他黑著臉,便問何事。丁成龍說:“往後這個號碼打電話來,就說我不在。”
眼下陳健康提到拆遷之事,孟浩長也看著丁成龍。丁成龍泯了口酒,說:“我沒看方案。百花井不能拆。我也不搬。”
“那就好。有丁老師這話,我就放心了。”陳健康端起杯子,說要敬丁成龍一杯。丁成龍擺擺手,說:“忘了老規矩?”
“啊,啊,那是。”陳健康放下杯子。他們三個人喝酒,早就定了規矩,不得互相敬酒。酒要平喝,能喝則喝,不能喝則罷。
又喝了一口,孟浩長對著丁成龍小聲問道:“今天在書店還見著一個人,你道是誰?”
“我咋知道?”丁成龍說話一直偏北方方言。
孟浩長遲疑了下,吐出三個字:“馮誌國。”
“馮……別提他!”丁成龍搖著頭。
孟浩長倒是笑著,說:“丁老師也別總記著了。都過去幾十年了。都老了。那老馮現在可是一頭白發。葉紅翠也死了好幾年了。唉。”
陳健康問:“就是原來人大的那個馮主任?”
“就是。丁老師當年戴帽子就靠了這馮主任的舉報。”孟浩長夾起盤子中最後一塊貢鵝,說:“不過那也是那個時代的事,換了現在,他也不會那麼做了。”
丁成龍不語。
丁成龍心想:也許真的是因為那個時代,而不是因為馮誌國的一封舉報信。可是,為著那個時代,為著那封舉報信,丁成龍的人生猛然拐了個彎。這個彎不是一般的彎,是讓他付出了大半輩子生命和心血的彎。不過,好在這個彎道來臨時,他並不曾知道背後有馮誌國的一封舉報信的事情,他僅僅覺得他被裹挾進了一場他無法回頭的運動。他必須離開!他必須重新尋找活路!於是,28歲的丁成龍,成了廬州五七年運動中第一個畏罪潛逃者。
“俱往矣!”丁成龍歎了句。
陳健康又將話題拉回到了拆遷上,說:“這百花井要拆,我倒是喜歡。這房子畢竟太舊了。一下雨,外麵大雨,裏麵小雨。不過,像丁老師這樣的房子,估計……”
“我不拆!”丁成龍又泯了口酒。
孟浩長抹著嘴,其實他嘴裏還在嚼著最後一塊貢鵝。他搖晃著酒瓶,說:“完了。走!丁老師,到我那去,看陳蘭那丫頭畫畫。”
陳蘭是陳健康的小女兒。在陳健康的三個兒女中,陳蘭從小就喜歡往孟浩長家跑。那時,百花井是個真正的大雜院。在丁成龍1981年重回百花井之前,大雜院裏住著近二十戶人家。但到了一九九0年代,百花井被列入省級文保單位後,大雜院裏的居民陸續搬出,現在,前前後後,隻住著五戶人家了。除了丁成龍的小別墅,孟浩長的月形門,陳健康家的四間上下二層樓外,還有兩戶,一戶姓王,一戶姓焦。但平時,這兩戶幾乎都不見人影。穿過百花巷,倘若小學不上課,這大院裏便是一片枯井般的寂靜。
剛走到花瓶門前,孟浩長便唱了句:
“風乍起,問團扇幾時開?
海棠老,問那人,幾時來?”
孟浩長小生嗓子,唱到婉轉處,情不自禁地亮起了蘭花指。丁成龍聽著,這唱詞他聽了不下百遍,這是孟浩長最喜歡唱的一段。他也不曾問過這到底是哪出戲的唱詞,隻覺得這唱詞時時刻刻就掛在孟浩長的嘴邊上。隻要他高興了,或者他不高興了,唱詞都哧溜就滑了出來。這段詞有味兒,有元曲之味。孟浩長唱著,又有院中老桂花被秋雨全打濕了的況味。
丁成龍的腦子裏往往就閃過一個畫麵——
十八歲的孟浩長一臉白淨,站在百花井的桂花樹下。他形如滿月的臉,更像一個女孩子。而那長長的一字眉,猶如弦月;他望著桂花樹影中的那輪明月。明月也似乎在望著他。月與人相對。靜靜的,爾後就是孟浩長往台方向甩出的水袖。接著,就是從嘴邊氤氳而出的唱詞……
而在不遠處,高巧雲正掩麵而立。
那年,丁成龍剛剛從稻香樓那邊搬到百花井。原因很簡單,他結婚了。結婚了,就得有公房居住,不能再住集體宿舍了。他和胡滿香扛著被褥,就在百花井公主府裏有了三間平房。那時,院子更大,連靠北的二層樓房也還沒有。丁成龍跟胡滿香說:“我們也做了公主府裏的人了。”胡滿香隻是笑。胡滿香隻上過幾天識字班,她本來在東北老家,去年春天才隨著她的父母一道調來廬州。她的父親胡仁義是市文教局的副局長,也算是剛剛轉業到文教局當個副科長的丁成龍的頂頭上司。這樁姻緣毫無征兆,卻順理成章。幾乎沒有戀愛,便直接進入了婚姻生活。胡滿香並不懂得公主府第的意思,她前前後後看了一遍這偌大的公主府,然後說:“真不小,跟俺們那邊的大帥府差不離兒。”
丁成龍第一次聽孟浩長唱戲,就在這年的秋天。也就在那之後,丁成龍開始注意起同住在公主府第裏的這個白麵少年。命運總是嚴絲合縫,這一唱一見,卻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如水交情。而更讓他時時不能忘懷的,是那個掩麵站在井台不遠處的女子。三十多年後,他在孟浩長的家裏,第一次聽見李光雪清澈的笑聲時,浮在他腦子裏的就是這個掩麵而立的女子的麵容。隻是他沒有說。一切過往,皆是天機。
陳蘭正在案前畫一片山水。
孟浩長和丁成龍站在畫案前,看著陳蘭勾、提、皴、染,宣紙上雲煙密布。待陳蘭停下畫筆,孟浩長說:“更有神氣了。”
丁成龍點點頭。在廬州書畫界,孟浩長是個隱逸的大師級人物。世事趨向浮躁,那些活躍在各種筆會、展覽和研討會上的書畫家們,人前大紅大紫,道行通天。人後卻最怕見到孟浩長。但他們又無一例外地期待著能得到孟浩長的指點,批評,當然最好是肯定。孟浩長的評價,不僅僅是對一個書畫家藝術的定性,更多的指向其藝術品味之外的道德品味與文化趣味。或許孟浩長也深知其在廬州書畫界的地位與影響,他越發隱逸。這十餘年來,他隻對三位書畫家發表過評論。結果是:其中兩位不得不離開了廬州,而另一位成了當下廬州書畫家的翹楚。
陳蘭是個例外。
陳蘭是孟浩長收下的第一個學生,也是最後一個學生。孟浩長這一生,公開授徒的就陳蘭一人。陳蘭現在廬州一中教書,而這裏也是孟浩長一輩子工作的地方。孟浩長的工作與他的愛好,或者說與他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某種叫人無法理解的反差。他是一個數學老師,大學時期他一開始學的是中文,但到了大二,突然心血來潮,改學數學。數學的嚴謹,加上他對書畫藝術的理解所形成的浪漫,讓孟浩長的人生充滿了不確定的意味。
他正式收陳蘭為學生,已經二十年了。陳蘭八歲那年,在百花井的井台上,陳蘭正用水彩筆畫桂花。孟浩長看見,且笑著,然後他嚴肅而小心地問陳蘭:“願意做我的學生嗎?我是指畫畫。”
陳蘭眼睛明亮,抬著頭問:“為什麼要做你的學生?”
“因為我想你做我的學生。”孟浩長笑著說。
陳蘭想了想,才點頭,說:“你要是真想讓我做你的學生,也行!不過,這事可不能讓我爸媽知道。”
孟浩長又點頭。
從八歲到陳蘭大學畢業,孟浩長隻看陳蘭畫畫,從不指點。陳蘭學的是物理,也與畫畫風馬牛不相及。但孟浩長卻為此欣然。直到她正式工作了,他才開始正式教他畫畫。說是教,也隻是讓她在他的畫室裏自個兒畫。每幅畫畫好了,他會看一眼。然後說上一兩句,都極簡。他堅持認為陳蘭慧根極深,不必太多指點。指點太多反而成了羈絆。果然,這一兩年,陳蘭的山水畫漸成氣候。而孟浩長給她最大的評價是:“是我唯一的學生,而畫風卻與我最不相似。”
陳蘭正在畫上題款。孟浩長用小泥壺沏了茶出來,給丁成龍和陳蘭各倒了一杯。
茶香彌漫。畫紙生煙。丁成龍問陳蘭:“小健呢?最近很長時間沒見著了。”
陳蘭說:“不是去新疆了嗎?您不知道?”
丁成龍真的不知道陳小健去了新疆。
陳小健眼看著也快四十的人了,在陳健康的三個孩子中,他排行老大。他長得像他的娘耿麗萍。耿麗萍在女人中算得上是嬌小玲瓏,臉小,鼻子小,嘴小,眼睛卻大,忽溜溜的。陳小健身材像娘,不到一米七。整個條子看起來,文弱。然而,這文弱的身形之中,卻包裹著一顆堅韌的男兒心。
丁成龍問陳小健,一半是因為遇見了陳蘭,一半更是因為女兒丁昌吉。
陳小健從什麼時候開始愛上了丁昌吉?沒有人知道。陳小健也從來不說。丁昌吉回到廬州時,已經是十三歲的小姑娘了。她睫毛又黑又長,臉形頗似個洋娃娃。皮膚白中透紅,身材嬌小,特別招人喜歡。丁成龍看著十三歲的丁昌吉出現在百花井,他心裏其實是有些說不出來的隱憂的。胡滿香其時正拉著丁昌吉的手,說:“這地叫百花井,從此後咱們就住在這了。”
“我們不回家了?”丁昌吉所指的家顯然是指遠在新疆昌吉連隊的那座前後都是院子的小平房。
“不回去了。我們就在這住了。”胡滿香說:“等過了年,你就在對麵的小學去上學,直接上五年級。”
丁昌吉忽閃著睫毛,問:“那大哥哥呢?”
“他不回來了。他就在新疆了。”丁昌吉所說的大哥哥是丁成龍的大兒子葉抗美。他已經成家,且有了孩子。而他們的二兒子丁石子,早在一年前,已經先行回到了廬州,現在正在讀高二。如同一張網眼太過於疏漏的漁網,丁成龍一生養了三個孩子,年齡差距卻讓人難以想像。大兒子當年出生在廬州百花井邊,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的事情。二兒子卻是八年後,出生在新疆石河子。最小的女兒丁昌吉,出生在昌吉,那是七0年了。
丁昌吉很快就融入了百花井這些孩子之中。她的活潑的天性,使她不僅僅融入了,且成了孩子們的頭。即使比她大一歲的陳小健,也整天跟在她的後麵。每到放學時間,丁昌吉後麵總是跟著一小串孩子。孩子們在百花井前的空地上做遊戲,講故事,跳舞。丁昌吉跳起舞來,如同精靈。而她的哥哥丁石子,卻是另外一番景象。丁石子內向沉穩,而且自從回到內地,他變得比在新疆更加沉默。有時一天到晚,家裏人很難聽見他說上一句完整的話。他整天捧著書,坐在窗前。一開始,丁成龍還曾勸導他多出來休息,勞逸結合。但丁石子隻用一句話就讓丁成龍不敢再說了。丁石子的那句話是:“如果我考不取大學,你來負責?”
負責?丁成龍這一生最沒弄明白的也許就是這兩個字。父親在他出生時,給他的一生定義為“曲折”。曲折隻是人生的一種軌跡,而這個軌跡的運行,推動,方向,與結果,卻必須有人來負責?可是,誰負責了?
當年在淮河大壩上,十七歲的丁成龍被人找到,然後進入了桐柏山。再後來,他隨著工作隊到了廬州。如果說這都是相對正常的人生軌跡的話,那麼一九五六年那個五月之後,他的人生軌跡便不再是正常的,至少不再是按照他的內心來運行的。他常常在深夜捫心自問,卻無法獲得回答。有時,他會坐在百花井邊,任夜露打濕他的白發。他遙望星漢,回想起近半生的浪跡。他痛苦地發現自己從來不曾真正地屬於過哪一塊土地。魯北故鄉的那片沙丘,早已消逝在天邊了。五十多年前的百花井,金鬥河,城隍廟,也已慢慢地進入塵封。在他的腦子裏,出現最多的還是那迢遞逃亡之路。那路懸在天邊,他奮力往上。爬著爬著,往往是夢中驚醒,大汗淋漓。
因此,丁成龍對小兒子的詰問,隻能保持沉默。
丁昌吉是從哪一天開始突然對自己產生了懷疑?為這事,丁成龍曾同胡滿香商討過,胡滿香態度很不友好。胡滿香這一生,除了在丁昌吉這件事情上,敢於同丁成龍發脾氣外,她從來不敢在丁成龍麵前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而丁昌吉之所以懷疑自己,純粹是因為陳小健的一句提問。
那是在桂花樹下,丁昌吉讓陳小健為她收集桂花。陳小健用手掌捧著桂花,看著丁昌吉,吞吞吐吐地問道:“昌吉,你怎麼長得像個維吾爾人?”
丁昌吉一下子愣了。她反過來問:“你見過維吾爾人?”
“學校裏老師們都這麼說。我在書店裏連環上也見過,長得跟你特像。都是長睫毛,大眼睛,高鼻梁,都是……”陳小健的話被丁昌吉伸過來的手掌攔腰斬斷。他手掌裏的桂花也灑了一地。
丁昌吉跑著回家。她問胡滿香。胡滿香驚惶失措,仿佛被人捅破了一個天大的秘密。她背轉過臉。丁昌吉卻不依不饒。胡滿香隻好說:“你是像維吾爾人。那是因為你出生在新疆。你隻是像!你仔細看看,你不也像爸爸和媽媽嗎?”
丁昌吉拿著鏡子,反複地照。最後她半信半疑,說:“我鼻子像媽媽。嘴,像爸爸。”
胡滿香看著女兒,雖然笑著,心裏卻是針紮般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