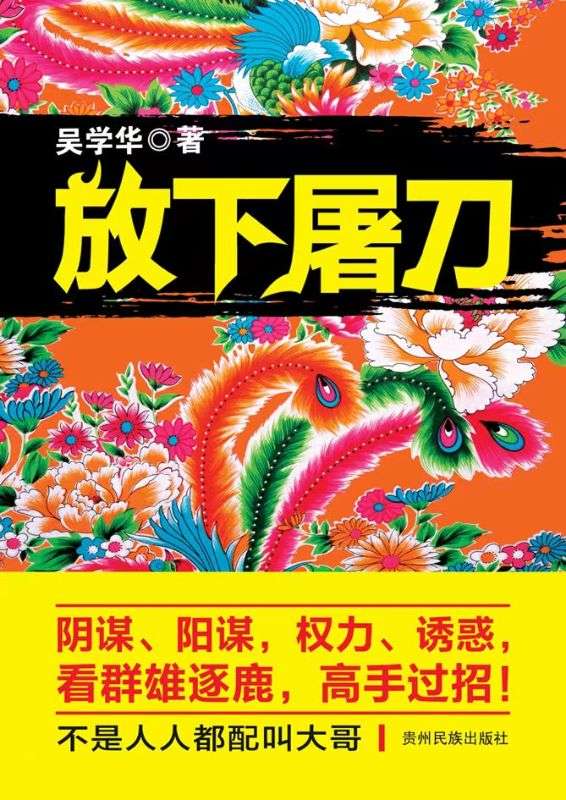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三章 出獄後的老大
第三章 出獄後的老大
縣招商局局長張先華坐在地稅局局長陳建國的下首,他看了坐在香港客人廖先生身邊的沈瑞強,暗暗使了一個眼色。
酒喝到這份上,大家都有了幾分醉意,主賓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融洽。今天下午,以沈瑞強為首的縣談判代表團,和來自香港的國際商人廖先生達成了初步合作的意向。首先,由縣裏出資200萬,委托廖先生的公司,在法國注冊一家貿易公司;其次,公司成立後,廖先生立即投資五千萬,在縣裏建造一座竹木工藝的大型加工廠,產品主要銷往歐洲。產生的利潤,縣裏占四,廖先生那邊占六。
出資200萬,就能擁有投資五千萬的四成股份,隻有傻子才不幹。雖然有縣裏的一些幹部對此事持懷疑態度,可沈瑞強卻一口咬定廖先生是身家幾十億的大老板,隨便做一次生意就賺個幾百上千萬。人家願意到縣裏來投資,主要是看在他的麵子上。
他對身邊的人說,上次去南方考察的時候,廖先生邀請他一個人到香港去玩了一趟,並帶他去了位於中環名門大廈的辦公樓,在那種寸土比寸金還貴的地方,擁有半層商務辦公樓,難道不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
既然沈縣長敢拍著胸脯保證,誰還敢再有半句怨言呢?
廖先生端著手裏的酒,斜著眼睛看了大家一眼,說道:“我和內地的很多朋友合作過,一直都合作得很好。現如今內地的經濟形勢發展這麼好,我們這些做生意的,怎麼會錯過呢?”他喝了一口杯中的酒,望了一眼坐在旁邊的餘愛仙,接著說:“餘小姐,你很漂亮,真的。我在內地也見過不少美女,可她們都不像你這麼有女人味。我在一次酒宴上聽人說過,處女是貢酒,男人都想嘗一口;少婦是紅酒,喝了一口想二口;情人是啤酒,喝了爽心又爽口;老婆是白酒,難喝也得整一口!我不知道餘小姐到底是什麼酒,但是我敢說,你絕對是一杯陳年佳釀,讓每個見到你的男人都醉了!”
按計劃,酒喝到興頭上,大家就要陪著廖先生去卡拉OK放鬆一下,至於接下來發生什麼事,那就不是別人所關心的了。沈瑞強要張先華打電話把餘愛仙叫來陪客,不就是那麼回事嗎?
餘愛仙原來的男朋友,是高雲縣赫赫有名的黑道老大胡誌雄。胡誌雄被抓,她就成了眾多男人互相追捧的目標。自從幾年前被公安局副局長朱玉華叫去陪客時,被人趁她酒醉輪奸並拍了現場照片後,就成了人皆可上的“公共汽車”。
餘愛仙這樣的“公共汽車”,張先華他們幾年前就趕上了趟,現在才不感興趣呢。不過,她那美貌的外表,還是能夠迷住很多男人,有時候用來“招待”外地來的朋友,是最好不過了。隻要他們有權在手,她敢不聽話?
沈瑞強看了看廖先生,提議道:“廖先生,您遠道而來,或許有些累了,不如……”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聽到一陣手機響,原來是坐在餘愛仙下首的廖先生秘書的身上發出來的。那秘書拿出手機,嘰裏咕嚕地說了一大通英語,接著用普通話問廖先生:“老板,那邊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給他們發貨?”
廖先生接著酒意說:“你告訴他,就說我這邊還在談,不急,不急,大不了把錢退給他們!”
那秘書對著手機又嘰裏咕嚕地說了一通,最後把電話掛了。
地稅局局長陳建國是經濟類院校畢業的高才生,英語自然不賴,他聽完那秘書的電話後,頓時露出驚駭的表情,偷偷對沈瑞強說道:“好像是意大利那邊的一個羅百爾特的生意人,給他們打了80萬歐元的預付款,催著他們要貨呢!”
沈瑞強有些興奮地說:“如今國際上對中國的傳統工藝品很看好,我早就覺得這次的招商引資一定能成功。隻要廠子能夠辦起來,其他的都好說!”
廖先生眼光迷離地望著餘愛仙,仰頭一口幹了杯中的酒,舌頭有些打結地說:“有……餘小姐……在身邊……真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
那秘書有些歉意地對沈瑞強說:“沈縣長,實在不好意思,我老板不勝酒力,他醉了!有什麼失禮之處,還望大家多多原諒!”
“哪裏,哪裏?”沈瑞強說:“都說生意人很精,可是我從喝酒上,就能看出廖先生是豪爽的人,像他那樣的人,現在可不多了!”
那秘書說:“沈縣長是說笑了,如今做生意可比不得以前,主要靠誠信的。生意人所謂的精明,要看精明在什麼地方。如果對每個人都那麼算計的話,生意還能做得下去麼?”
沈瑞強連連點頭:“那是,那是!”
看到廖先生已經將頭靠在桌子上,那秘書便提議回賓館。沈瑞強會意,暗示餘愛仙扶廖先生起身。
張先華去酒店的前台簽了單子出來,見沈瑞強的專車已經不見了,幾個喝酒的人當中,也不見了廖先生和餘愛仙。
一輛車子開了過來,陳建國上前開了門。沈瑞強看了大家一眼,也沒有說話,和廖先生的秘書鑽了進去。其餘的人心照不宣,上了後麵的車子,跟著前麵的車子走。
車子在街上轉了幾個圈,駛到臨江的一間茶樓門口。張先華下了車,看了看沈瑞強,見沈瑞強正親熱地與那秘書說著話,便帶頭向上麵走去。
這家茶樓的門口豎著一扇雕花木牌樓,顯得別具特色,牌樓上五彩霓虹燈招牌,並沒有幾個人會去注意。
一行人上了茶樓,並沒有進茶樓的雅間,而是走過二樓的通道,掀開通道盡頭的一張布簾,直接進了與茶樓相隔的一間桑拿沐浴室。
在車上的時候,張先華就已經給了這家桑拿沐浴室的老板打了電話,說他們要來。
社會的經濟上去了,男人的口袋裏有點錢,還不是想出去亂花?如今縣裏像這類的桑拿沐浴室和洗腳城,不都學著很多大城市的樣子掛羊頭賣狗肉?至於裏麵有什麼特色服務,就要看老板的後台有多硬了。
每次縣裏有打黃掃黑行動,一些場所便幹著正當的營生,而風聲一過,各種特色服務爭相上場。
這家桑拿沐浴室的老板是張先華的一個遠房親戚,他中午接到老板的電話,說今天剛到了幾個的妹子,手藝都很不錯。老板是個很有眼光的人,為了留住客人,不惜花重金派幾個人去南方某大城市學了許多招數過來,將每一位客人都服侍得舒舒服服。
所以在吃飯之前,他就建議沈瑞強晚上去哪裏瀟灑了。
幾個人走進去的時候,桑拿沐浴室的老板迎了上來,將張先華拉到一邊,低聲說:“張局長,你們怎麼不早來一點?”
張先華問道:“怎麼了?我不是叫你給我們留著的嗎?”
老板慌忙不迭地說道:“是呀,是呀!之前有好些個客人要點她們,都被我給拒絕了,可是……可是……”
張先華問道:“可是什麼?”
老板看了看沈瑞強,說道:“可是剛才虎爺和萬老板帶著兩個人來了,你知道,我這裏有虎爺三成的股份,再說萬老板是……”老板看著張先華的臉色,接著說:“要不我先安排別人,等會再讓她們上?”
張先華低聲說道:“你也不看看我們是什麼人,哪有吃別人剩菜的道理?”
他說完後,來到沈瑞強的身邊,低聲耳語了幾句,沈瑞強頓時變了臉色,接著對那秘書說道:“對不起,我們走錯了!走走走,去別的地方!”
看著沈瑞強陪那秘書下樓,張先華惡狠狠地對老板說:“連這點事都不會辦,我看你的生意也做到頭了!”
老板哭喪著還未解釋,就見張先華已經轉身離開。
×××××××××××××××××××××××××××××××××××××××
盡管屋裏開著燈,可窗外那皎潔的月光,還是頑強地透過落地窗簾的縫隙,落在黃來德的身上。他這兩天都沒有給劉昌仁打電話,他上次聽了劉昌仁的那些話,回到家細細品位,也覺得有幾分道理。
對於當年縣裏抓獲胡誌雄一事,他也聽說了一些原委,有人說胡誌雄是被人出賣的。胡誌雄被抓後,縣裏的某些領導發了大財。
雖然胡誌雄是有妻子的人,而大美女餘愛仙和他的關係,那是眾所皆知的,他沒有被抓之前,誰都不敢碰她一下。可是這幾年來,她在各種勢力中艱難生存,幾乎變成了人盡可夫蕩婦。這種情況,身在監獄中的他不可能不知道。
作為男人,誰會容忍自己的女人被別的男人玩弄?特別是那些像胡誌雄那樣的男人,又豈會輕易放過那些欺負過餘愛仙的男人?
隻要胡誌雄一出獄,幾股黑社會勢力定然會再次相拚,那些和餘愛仙的有過關係的男人,也會受到一定的牽連。如此一來,縣裏肯定亂成一鍋粥,不管結果如何,對他而言,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用劉昌仁的話說,叫做“渾水摸魚”。
他本想打個電話給朱玉華,可剛撥了兩個鍵卻又停住了,他完全站在高處望大水,沒有卷進去。縣裏期望胡誌雄出獄的幹部,又何止他一個呢?
縣委書記孟金生是當年抓捕胡誌雄的人,原想借此功升上去,可升來升去,也不見有多大的氣色,自從沈瑞強調來後,他好像不太多管事,每次的常委會議上,都是一副老好人的樣子,似乎再也找不到當年的幹勁與魄力,變得有些優柔寡斷。縣委書記當到這份上,也真夠難為他的。
有小道消息傳出來,說孟金生已經向上麵打了報告,想幹完這一屆就提前病退。其實五十出頭的人,離病退還早著呢,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黃來德在官場混了那麼久,自然知道裏麵的一些玄機,整日勾心鬥角,時間長了,確實也身心疲憊,難怪有些人想盡快離開這個是非圈。
但是權力給人的那種刺激,猶如吸食毒品的人,越吸越上癮,令人欲罷不能。不然的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削尖了腦袋都要往上鑽?擁有了權力就擁有了一切,金錢美女社會地位自然不用說,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那些親戚,也會跟著人五人六起來。
不要說身為單位的領導,就是一般的小公務員,也都在人前牛逼哄哄的。這些年的公務員考試,就是很好的證明。
某個單位要錄用一兩個人,而參加公開考試的就有數千人。為了能夠擠進公務員隊伍,那些有點門路的考生,無不施展渾身的解數找門路,以便在麵試的時候能夠順利過關。於是,原本就門庭若市的單位領導的家裏,更加車水馬龍起來。
今年上半年地稅局招錄三個工作人員的時候,局長陳建國處理給某家煙酒專賣店裏的煙酒,就有兩三萬塊,而最終錄用的三個當中,有一個確實很出色,另兩個都是“內定”的,其中一個是該局副局長公子,另一個則是縣招商局局長張先華的侄女。張先華目前是縣裏的紅人,陳建國不敢不給麵子。
陳建國的為人很精明,他是不會讓那些人送了禮而沒有達到目的人懷怨在心的,正式工錄用完畢後,地稅局又招錄了好幾個臨時工。緊接著,他又在某大酒店請了幾桌客,來的都是他那些所謂的朋友。至於請客的費用,自然有人替他掏。
遍觀高雲縣,不要說那些手握實權的人物,就是有一點小權力的人,在請客的時候,又有幾個人是自己掏錢的呢?
見黃來德坐在沙發上出神,老伴泡了一杯茶走過來,輕聲道:“老黃,要注意身體呀!”
黃來德看了看徐娘半老的老伴,心中閃過一絲愧意,身為領導幹部,有時候在一些場合,免不了和別的女人有露水之緣;結婚這麼多年來,由於工作上的原因,也沒能與她好好談談心。而她毫無怨言地扮演著家庭主婦的角色,維護著這個家庭,從來不過問他的工作上的問題,就像一顆粗大的老樹,默默地安慰他,並及時地給予家庭的溫暖。想到其他幾個副縣長都是二婚,而他的還是原配,心中的那意思愧意也就煙消雲散了。那幾個人的老婆無不長得花枝招展,真正下得了廚房上得了廳堂,令他眼饞不已。
他剛要說話,放在身邊的手機響了,一看卻是朱玉華,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手機那頭傳來朱玉華的聲音:“黃縣長,你好呀!”
“哦,你好你好!”黃來德也客套了一下,接著問:“朱局長這麼晚打電話給我,有事麼?”
朱玉華說道:“其實也沒什麼事,你是領導,打個電話問候一下而已!”
黃來德嗬嗬地笑了兩聲,說道:“那我可要謝謝朱局長了,什麼時候有時間一起出來喝茶?”
他雖然認識朱玉華,興許是工作性質的緣故,彼此之間平時也沒有多大的往來,私下的關係也就那樣,好不到哪裏去。他有一種直覺,朱玉華這時候打電話給他,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對他說。
果然,朱玉華說道:“發生這麼大的事,現在縣裏估計沒幾個人有心思喝茶了!”
黃來德愣了一愣,問道:“發生什麼事了?”
朱玉華說道:“黃縣長,你還不知道呀?餘愛仙死了!”
黃來德吃驚不小,連忙問道:“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我怎麼不知道?”
朱玉華在電話那頭嗬嗬笑道:“我也是剛剛得到的消息,還以為有人向你彙報了呢?”
黃來德知道朱玉華是在說屁話,他又不管公安係統,就算要知道,也沒有朱玉華那麼來得及時。當下,他裝作奇怪的樣子說道:“你認為這樣的事,誰會向我彙報呢?”
朱玉華在電話那頭停頓了片刻,接著發出一聲歎息,說道:“我現在向你彙報也一樣哦,下麵的人說,餘愛仙是下班回到家裏後自殺的,我覺得很奇怪,她活得好好的,聽說昨天還陪著萬老板他們一起玩呢,怎麼會突然自殺呢?”
黃來德淡淡地說道:“她到底是不是自殺,那是你們公安局的事,縣裏可管不了那麼多。不過,一個好好的人就這麼死了,總會有什麼原因吧?有些社會性的問題,不得不需要慎重考慮的。”
他那話中的意思很含糊,是讓朱玉華聽完之後,自己去揣摩的。像餘愛仙這種備受非議的公眾性人物突然間自殺,無論縣裏公開什麼樣的調查結果,隻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人們所關心的是導致這個女人自殺的黑幕。誰有本事能夠堵得住悠悠眾口,不讓人們去懷疑和猜測呢?
朱玉華說道:“我也覺得她死得很奇怪,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選在這當兒上自殺。這不明擺著給縣裏添事嗎?”
黃來德問道:“按朱局長的意思,人家自殺還要選時間呀?”
兩人又不鹹不淡地聊了幾句,就掛了,誰都沒有主動提到胡誌雄這個名字。黃來德的老伴把茶放到他麵前的茶幾上,就坐在一旁看電視了。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道:“剛剛是公安局的朱局長來的電話,說電視台那個女的自殺了!”
老伴扭頭看了一眼黃來德,低聲說道:“累了吧,累了就進房休息!”
黃來德深深呼了一口氣,頭往後仰靠在沙發椅背上,閉上眼睛。他確實感到有些累,可是聽了那通電話之後,竟莫名地產生了一絲興奮。
×××××××××××××××××××××××××××××××××××××××
沉重的鐵門在胡誌雄的身後緩緩關上,他站在那裏,扭頭望了望那高牆上的鐵絲網,還有站在鐵門兩邊崗亭前的獄警,臉上微微閃露一抹冷笑。這個生活了8年的地方,他可不想再來了。
他原本被判12年,期間由於表現良好,減刑兩次,每次減一年。半個月前,也不知為什麼,隔壁監舍的兩個囚犯在勞作時發生口角,近而引發械鬥。他在獄警沒有趕到之前,成功地將械鬥平息。
就在昨天,監獄方通知他說,由於他在半個月前那場械鬥中的立功表現,再一次獲得減刑,並提前釋放。
當人們哀歎人生猶如白駒過隙,轉眼就是一年的時候,又怎麼能夠體會得到那些在監獄中服刑的犯人,是怎麼樣掰著手指頭計算自己出獄的時間的。8年的時間,足夠能改變一個人的很多東西。說真的,在裏麵生活了那麼久,對裏麵還有不少依戀,那一個個穿著囚服光著頭的獄友,還有那一排排整齊的囚舍,一切都那麼熟悉。
“老大!”一個聲音從前麵傳來,他定眼望去,見那裏停了幾輛車,汪積德帶著幾個人正快步朝他走過來。
當年那些一同被抓進來的兄弟,先後都已經出獄。道上的兄弟還真夠義氣,每個月的親屬探視日,都有人去監獄探望他。
汪積德接過胡誌雄手裏的包裹,丟給身後的一個人,同時說道:“老大,你辛苦了!”
胡誌雄看著汪積德那油光滿麵的臉和大腹便便的肚子,說道:“當心脂肪肝,人胖了,很累的!”
汪積德嘿嘿地笑了兩聲:“老大,你的身材還是那麼健壯!”
胡誌雄淡淡地看了身邊那幾個人一眼,說道:“你又不是沒在裏麵呆過,我就是想胖也胖不起來呀!”
汪積德親熱地擁著胡誌雄,朝車子走去,來到車前,胡誌雄突然說:“你們先回去吧,我坐公汽回去!”
“為什麼?”汪積德以為自己聽錯了,他瞪著眼睛望著胡誌雄,說道:“大哥,你這是……”
胡誌雄從旁邊那人的手上拿回自己的包裹,顧自往前麵走去,離監獄不遠就有車站,從這裏坐車到市裏,再轉去高雲車就行了。
汪積德緊走幾步,跟在胡誌雄的身後,哀求道:“大哥,你就當給做兄弟的一個麵子,上車吧?”
胡誌雄頭也未回地說:“行,但是你也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汪積德說道:“好,你盡管說。憑我們兄弟之間的關係,不要說一個要求,就是十個八個的,也沒問題。”
胡誌雄一字一句地說道:“從今往後,不允許你們再來找我!”
汪積德愣住了,過了片刻才說:“大……大哥,為……為什麼?”
胡誌雄說道:“不為什麼,我想過點正常人的日子!”
他說完後,轉身上了車。汪積德也上了車,就坐在他旁邊。車子啟動向前行去,將監獄的大門遠遠地拋在背影中。
望著車窗外飛逝的景物,胡誌雄始終緊抿著嘴唇沒有說話。汪積德望著他的樣子,眼中露出憂慮之色,幾次話到嘴邊還是忍住了。
當車子駛入高雲縣境內的時候,汪積德終究還是忍不住,呐呐地說道:“雄哥,有一件事我……我必須要告訴你!”他見胡誌雄微微點了一下頭,便鼓足勇氣說道:“其實……其實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在半個月前,她死了!警方說她是自殺的,我們……”
胡誌雄眼中露出狼一樣凶戾之色,嚇得汪積德渾身一顫,接下來要說的話頓時梗在喉嚨裏,再也說不出一個字。
胡誌雄露出一抹苦笑,將頭轉向窗外,過了片刻,深吸了一口氣,才緩緩說道:“他果然猜中了!”
汪積德驚問道:“雄哥,是誰猜中了?”
胡誌雄往後一躺,顯得有些疲憊,低聲說道:“是我的一個獄友,當過市規劃局的副局長,遭人舉報,查出他貪汙受賄一千多萬,被判了9年。”稍停了一會,他接著說道:“他對我說,他實際不是栽在貪汙受賄上,一千多萬在市裏算不得什麼,比他多的人大有人在。他是栽在人際上,身在官場上,有時候說了什麼話,做過什麼事,自己不覺得怎麼樣,說不定就已經得罪了不少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誰都算不準什麼時候就栽了。別人既然要整他,就有整他的辦法,任他怎麼樣都翻不了身……”
汪積德“嗯”了一聲,官場上的那些貓膩,他也知道不少。
胡誌雄說:“給我一支煙!”
汪積德忙從身上拿出一包軟中華,抽出一支遞過去。胡誌雄接過煙銜在嘴上,讓汪積德為他點上火,深吸了幾口。
汪積德自己也點了一支,車廂內頓時彌漫著濃鬱的煙草香味,待一支煙快吸盡的時候,他說道:“雄哥,要不你去看看她,就葬在火葬場旁邊的公墓裏。”他見胡誌雄沒有反對,便拿出手機,通知縣城裏的兄弟,趕緊定幾個大花圈,直接送到餘愛仙的墳前去。
胡誌雄把吸剩下的煙蒂丟到窗外,沉聲問道:“其實我還有幾個月才刑滿,為什麼急著把我從裏麵弄出來?”
汪積德似乎嗆了一下,咳了幾聲之後,說道:“雄哥,你不是提前釋放的嗎?”
胡誌雄說道:“是提前釋放,可這件事是有人操控的!”
汪積德說道:“我也覺得很奇怪,以前任由我們想什麼辦法‘撈’你,可都沒有什麼用!”
胡誌雄說道:“他對我說,一定是有人想我出來。”他的眼睛始終望著窗外,繼續說道:“要是換在一年前出來,我一定會把高雲縣鬧個底朝天。是他教了我很多為人處世的大道理,人一旦進到那裏麵,接觸不同的人,能學到很多東西。你已經不是當年的醉雞,而我,也不再是以前的雄哥!”
×××××××××××××××××××××××××××××××××××××××
高雲縣的公墓就是火葬場的邊上,那座並不高的小山,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墓碑,有的墓碑上隻刻著死者的名字,而有的墓碑上則有著一張死者生前的照片。
車子到達山腳下的時候,見這裏已經有了好幾輛車,幾十個穿著黑色西服,胸口佩著白色紙花的男子,分成兩排站在公墓的台階上。在另一邊,幾個男子抬著很大的花圈。
胡誌雄下車的時候,一個人從旁邊走過來,站到他麵前,恭敬地叫了一聲:“雄哥!”
他看著麵前的王小虎,見對方那一頭暴發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顆清潔光溜的光頭,他微微笑了一下,說道:“以前別人都叫你大頭虎,現在成虎爺了!”
王小虎嘿嘿笑了兩聲,說道:“在雄哥麵前,我永遠是大頭虎!”他瞟了一眼胡誌雄身後的汪積德,接著說:“我聽說醉雞去接你,所以我就沒去。我猜到你一定會來看她,這不,早準備好了!”
胡誌雄問道:“她真的是自殺的?”
王小虎說道:“我向一個搞刑偵的朋友打聽過了,從現場上看,確實是自殺。活得好好的,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會想不開!”
汪積德說道:“我一直認為,她自殺肯定是有原因的!”
“人都死了,還提那些做什麼?”胡誌雄說完,朝山上走去。有兩個男子在前麵帶路,將他引到餘愛仙的墳墓前,並利索地擺好花圈,點燃香,燒起紙錢。
他站墳前,摸著墓碑上那張黑白照片,凝視著照片上的人。這張藝術照是她那年生日的時候,他陪她去省城拍的,原來擺在她臥室的書桌前,想不到現在居然放在了這裏。
笑容猶存,然伊人已逝。他閉上眼睛,腦海中回憶著往日兩人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有歡笑和快樂,也有痛苦與悲傷。
汪積德點燃了三支香遞給胡誌雄,見他沒有接,隻得自己朝墳墓拜了幾下,將香插在小香爐裏。
王小虎也學著汪積德的樣子上了三支香,而後退到一旁,過了一會,他說道:“雄哥,都怪我們不好,沒有保護好她。那些……那些人都是……都是縣裏的頭麵人物……我們……我們……”
“你們惹不起的!”胡誌雄望著麵前的兩個人,低聲說道:“我並沒有怪你們,大家都是有家室的人,做什麼事都會想一想後果,不像以前那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她原來就對我說過,很多男人都想和她上床……”
汪積德扭頭看了幾眼王小虎,走到胡誌雄的麵前,低聲說道:“雄哥,今天晚上……”
胡誌雄說道:“別忘了你答應過我的話!等會兒你們送我回去,從今往後,我們就當是不認識的人,不要再來找我!”
“雄哥,為什麼?”王小虎說道:“你這一出來,兄弟們還想著重新跟你呢!”
胡誌雄說道:“你們都是做老大的人,又怎麼能重新做小弟呢?我沒別的意思,隻想過幾天安穩的日子,以前的那些,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
王小虎張了張口,沒有再說話。
胡誌雄凝視著餘愛仙的照片良久,用手在墓碑上重重地拍了幾下,算是一種無聲的安慰。他那幾下,猶如拍在汪積德和王小虎的心口,兩人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身子,相互望了望,也沒說話。
“送我回去!”胡誌雄轉身下山。
×××××××××××××××××××××××××××××××××××××××
紅旗茶場在縣城西北麵,雖然距離老縣城2到3公裏路,可幾乎都是連在一起的。茶場成立於上個世紀60年代。七八十年代最紅火的時候,擁有茶園麵積一萬多畝,職工一千多人。受市場經濟的衝擊,從九十年代開始,紅旗茶場的經營狀況如日落西山,盡管茶場的領導用了多種經營模式想挽回舊日的輝煌,可都無濟於事。
1996年,紅旗茶場宣告破產,所屬職工全部下崗各謀出路。昔日機器聲轟鳴的茶葉加工廠房成了鳥雀的居所,茶場擁有的茶園,也被私人承包。
原先職工們居住的宿舍,大多是六十年代建的磚土結構的平房,曆經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已經破爛不堪,成為縣裏有名的貧民區。貧民區最大的特色,就是隨處可見低矮的簡易窩棚,很多從鄉下來的人,在縣城內打點零工,為了省幾個錢,就住在窩棚裏。
2002年,縣委、縣政府興建新縣城的規劃出台後,紅旗茶場一下子成了新縣城的中心點附近的商業區,地皮隨之上漲。茶場那空蕩蕩的廠房和長滿雜草的茶園,被縣裏陸續“開發”,變成了商業用地,並很快成了高檔住宅區。根據縣委、縣政府的設想,要把新縣城打造成花園式的縣城,前期的建設很重要,前期建設好了,將有助於拉動招商引資工作,所以各個部門包括政府在建設新辦公樓的時候都想打造高標準的辦公樓,以吸引企業入駐。
在職工宿舍周圍的茶園被相繼開發後,那些平房被眾多商業大廈和小區包圍著,顯得極不協調。縣裏早就想將那一塊區域的職工宿舍連同原先的城郊居民區一同遷走,由於搬遷資金太大和其他諸多的原因,一直未能付諸實施。
經過這些年的旅遊開發,縣裏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在將修建文化廣場的提案放進日程後,對於文化廣場邊緣那處貧民區的商業開發,也迫在眉睫了。
幾輛豪華小車駛過新修的水泥大道,拐進一條坑坑窪窪的柏油馬路,在貧民區邊上的一個路口停了下來。
胡誌雄背著那小背包下了車,也不看後麵的人一眼,徑直向前麵走去。
在一排低矮宿舍最盡頭的一間屋子裏,走出一個穿著碎花上衣,手裏端著一個臉盆的女人。那女人看上去約莫四十歲左右,雖然臉上布滿歲月滄桑的痕跡,卻不難看出她年輕時候的俏麗。
她剛彎腰在屋子旁邊的水池邊上搓了兩件衣服,就聽到鄰居叫道:“小蓮,那是不是你男人?”
她抬起頭,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影正朝她走過來。她怔了一怔,手裏提著的衣服落在盆子裏,濺起的水花淋濕了她的褲腳。
她望著那越來越清晰的身影,眼睛漸漸模糊起來。二十幾年前,正值花樣年華的她,自從第一眼看到這個男人之後,就深深地喜歡上了他。她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投入他的懷抱,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剛出獄沒多久的街頭混混。他不顧她有孕在身,獨自去南方闖蕩,一走就是幾年,期間沒有給他來過一封信。她為他生下一個女兒,默默忍受著街坊鄰居們的閑言碎語。那年代,一個未婚大姑娘,在沒有出嫁的情況下為男人懷孕並剩下孩子,要忍受多大的精神壓力呀?
後來他回來了,拉著一幫兄弟“打江山”,生意做得那麼大。他想接她一起享福,住別墅開名車。但是她拒絕了,因為她想要的一個名分,他一直未能給她。她知道他身邊不缺女人,更何況,坊間多次傳出他要與高雲縣第一美女餘愛仙結婚的傳言,對她的刺激很大。
看在女兒的份上,他曾經也想和她結婚,可由不得他。她那過早衰老的模樣,看上去比他姐姐的年紀還要大,如果他們結婚的話,他怎麼麵對手下兄弟的非議?
她渴望一個實實在在的男人,時刻嗬護著她,給她家庭的溫馨與快樂。他曾經多次給她的錢,或者以她的名義買一套別墅,想彌補點什麼,可是她什麼都不要。年輕時衝動所導致的苦果,她獨自吞咽,而且毫無怨言。
眼看他們的女兒胡麗麗漸漸長大成人,他也動了心思,不管怎麼樣,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當他想以自己的真誠獲得她的諒解時,他卻再一次出事了。
他在監獄中生活的那些年,她們娘倆從來沒有去看過他,他知道她們恨他。那種恨,是在極度失望與痛心之後才有的,所以他並不怨她們,因為他能理解她們的感受。
胡誌雄走到小蓮的麵前,兩人呆呆望了很久,小蓮用手擦了擦眼睛,並沒有像以前那樣,用掃把打他或是個石頭扔他,而是淡淡地說道:“你出來了?”
“嗯!”胡誌雄應了一聲,他突然覺得眼眶一熱,聲音有些哽咽起來:“對不起,小蓮!”
小蓮勉強笑了一下,說道:“說那些話做什麼?進屋坐吧!”
屋裏很暗,有股潮濕的味道,小蓮開了燈,走到廚房裏間去泡茶。胡誌雄見屋內的陳設還是與原來一樣,隻是牆上掛照片的地方,多了兩張黑框照片,他認出那是小蓮的父母。記得他沒被抓的時候,她的父母還在世的,想必是這幾年過世的。
他走到那套早已經褪了色的木沙發前坐下,見小蓮從裏麵端著一個茶杯出來,放到他麵前的茶幾上。見他望著牆上的照片,便說道:“我爸得的是咽喉癌,你進去的第三年就過了。我爸走了之後,我媽整天都在哭,後來也……”
他望著那兩張照片,頓時百感交集。是呀!他們雖然活得很平淡,但是很恩愛,這就已經足夠了。
他問道:“麗麗呢?”
她在他麵前的地方坐了下來:“在縣一小當老師,去年縣裏公開招錄的時候,考進去的。考了全縣第二名,本來政審過不了關,好在她表舅在教育係統,幫忙說了話,才進去了!”
他知道她有個表哥原先在下麵的一個鄉鎮當老師的,後來調進縣教育局,當個普通幹事。他雖然在監獄裏服刑,可每次有人去看他,都會對他說一些高雲縣的事。那次他聽說他女兒考教師的事,便要汪積德暗中幫忙。他女兒能夠進一小當老師,到底是她那表哥幫忙,還是汪積德使了力,他是清楚的。
她接著說:“她前些天帶了一個小夥子來,說是她的男朋友。我覺得那小夥子不錯……”
他點了點頭,他似乎都忘記了,他們的女兒已經二十多歲了,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
兩人相對望了望,沉默了片刻,他鼓足勇氣說道:“我想……想和你明天去領結婚證……我們……我們……”
小蓮苦笑了一下:“那麼多年都過來了,還在乎那東西,隻要你好就行!”
他凝視著她,良久,良久,喃喃地說道:“這麼多年來,苦了你了!”
小蓮返身進屋,從裏麵拿出一大摞信件出來,放在他的麵前,平靜地說道:“這是你在裏麵給我寫的信,有一些是托人帶來的,都在這裏。麗麗也看了,她說有很多錯別字!”
他“嘿嘿”地笑了幾聲,沒有說話。
外麵人影一閃,有兩個人一前一後地走進來。走在最前麵的是一個長得十分俏麗的年輕女人,後麵跟著一個戴眼鏡的小夥子。
胡誌雄從沙發上起身,有些欣喜地看著那年輕女人,說道:“你是麗麗,都長得這麼大了?”
小蓮笑道:“看你都激動成什麼樣了,這是麗麗的好朋友林薇,那那戴眼鏡的小夥子是她的男朋友小方。”
站在門口的小方說:“路口那邊不知道怎麼回事,站了很多人呢,我們還以為又是那些人來逼拆遷的,剛才還差點過不來!”
胡誌雄對小方說:“麻煩你過去對他們說一聲,就說不要逼我!”
小方狐疑地看了胡誌雄幾眼,見他雖然一副很落魄的樣子,但眉宇間自然有一種逼人的氣勢,猶豫了片刻,還是轉身出去了。
林薇看了一眼胡誌雄,對小蓮說道:“阿姨,麗麗說今天是你的生日,她已經定了飯店,要我接你過去,她和小偉去拿蛋糕了,等會他們直接去飯店!”
胡誌雄望著小蓮,眼中充滿了歉意,嚅嚅著說道:“原來……原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我都沒有……沒有……”
小蓮說道:“麗麗這孩子很懂事,每次都記得我的生日,有時候我自己都不記得了。以前都是在家裏給我慶祝的。唉!買點菜回來吃就行了,怎麼去飯店裏呢?一定是小偉的主意,這孩子也真是的!”
林薇笑道:“阿姨,你就去吧!誰不想討好未來的丈母娘呢?”她轉向胡誌雄:“這位叔叔是你們的親戚吧,要不也一起去?”
小蓮有些難為情地看著胡誌雄,說道:“我看你還是……別去吧?麗麗和我一樣,性格倔強得很,她……”
胡誌雄會意地點了點頭:“沒事,我不去,你們去吧!我去路邊小攤上隨便吃點就行,等會在這裏等你們回來!”
小方回來了,他看著胡誌雄的時候,眼中有些畏懼之色,低聲說:“剛才我還覺得很奇怪,我對他們那麼一說,他們還真的走了!回來的時候,我聽隔壁的肖嬸說,原來……原來你是……”
這時,林薇的手機響了,她拿出來一聽,臉色頓時變了,驚道:“麗麗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