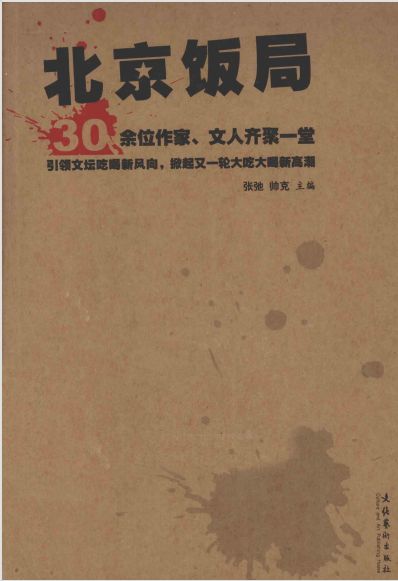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艾丹小記
狗子/文
大約七八年前,因為一本叫《手稿》的同人刊物認識了艾丹,認識了之後,除了一口氣讀完了他的三部作品《東張西望》、《下個世紀見》、《紐約劄記》,艾丹讓我的生活發生的另一個變化就是酒局迅速增多了起來。
那時的艾丹在我眼中是個樂天派,他衣食不愁,體格像頭熊,抽5 塊錢左右的國產煙,喝洋酒啤酒紅酒和二鍋頭,開白色富康,車技老到,經常一邊開車一邊說笑話,有時在擁擠的車流中將車開成蛇行,鑽來鑽去以顯示他的車技。
艾丹酒量驚人,這麼多年來,我就沒見他喝趴下過,據說這與他自小在新疆長大有關。那時艾青在新疆下放,當我們小時候喝粥吃饅頭的時候,他卻在喝羊奶吃羊肉,而且很可能他尚在繈褓之中,他爹艾青就一邊哀歎時代不公一邊用筷子靛著伊犁特喂過他。在酒桌上,因其酒量巨大,所以劃拳時我們贏他十拳,他隻需勝我們五拳,即為不敗。他還有一個絕技就是,據說他曾自學過《麻衣神相》,會點半生不熟的宿命通,能測得某人的前世來生及今生今世結幾次婚生男孩還是生女孩,但此招在酒桌上一般用處不大,偶爾能起到擾亂軍心的作用。
艾丹約酒的方式也與眾不同,在北京,我們這些能喝酒的人約著出來狂喝,從來不說“一起喝酒”,而隻說“一起吃個飯”,或者“聚聚”,或者“一塊坐會兒”,偶爾張弛會小心翼翼地冒出“小酌”這樣的詞,阿堅會慌著半顆心說出“小喝小坐”這樣的話,這些老酒膩子們在約酒時仿佛都很懼怕說出“酒”這個字,更不要說“好好喝頓酒”、“喝大酒”這樣直白豪邁的語言(某些沾酒就暈的家夥們反而愛這麼說),比之於張弛阿堅的兜圈子探口風小心翼翼哆哆嗦嗦,艾丹約酒的風格完全是另一路,他貌似最簡單,通常是這樣——
艾丹:狗子晚上幹嗎?
我:沒什麼事。
艾丹:晚上六點半荷風軒。
我:好吧。
艾丹:別晚了不見不散。
然後就掛了。我說他“貌似”簡單,是因為我覺得他的語速快得有些不正常,完全不帶標點符號,三句並作兩句,而且聲若洪鐘,他平日就嗓音渾厚,但此時分明又高了八度,大概把他早年唱歌劇學的那點腹腔胸腔臚腔共鳴都用上了,而且語氣毋庸置疑,像在發表宣言,而且他電話掛得太快了,讓我覺得他在電話那頭一痛虛張聲勢兼手忙腳亂,他是在不給我猶豫和反悔的時間?尤其有一回,我在他掛斷之前的瞬間多問了一句“晚上都誰呀? ”,他竟對著話筒大吼大叫了起來:“別他媽那麼多廢話一會兒見!”他近乎粗暴地飛速掛斷,我握著話筒愣了會神,這廝是怕我節外生枝吧?
說到歌劇,據說艾丹早年確實苦練過一段美聲,而且還曾在紐約百老彙與帕瓦羅蒂同台獻演過,他扮演一個屠夫,一句詞沒有,還被帕瓦羅蒂噴了一臉唾沫星子。
以前的艾丹一直是以詩人和作家的麵目出現的,我之所以加入中國作協也是因為艾丹的大力推薦,當時我對他的這份熱心很是疑惑,後來得知他多年來一直領著作協的一份工資。他每年的工作任務就是向作協推薦兩名新會員,另外他還有一點小私心就是他覺得以我的筆名很適合當中國作協主席。
這些年,沒見艾丹再寫什麼東西,按他的說法就是“作家兩個字讓我倒胃口”,他說他現在的專業是研究中國古玉,尤其是商代以前的,果然他不久前出了一本《玉器時代》,我翻看了一遍,很長見識,同時麵對書中那些精美的古玉照片(據說都是他收集的),想起這些年他經常在北京神秘消失一段,有人說他是跑外地盜墓去了。確實有一兩回他臨上火車前我們在一起喝酒,他穿了一身不知什麼兵種的軍裝,背著碩大的軍用挎包(那裏麵會不會藏著洛陽鏟之類的家夥什?),很明顯,他的出行肯定與體力活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