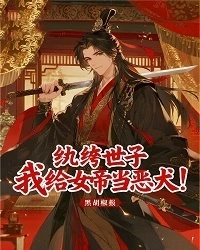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5章
徐恪剛剛將那本《貨殖通錄》的秘密剖開,那股破解了驚天密碼的興奮感還沒來得及在他滾燙的血液裏沉澱,密室的門便被“砰”的一聲撞開。
親信緹騎周七連滾帶爬地衝了進來,一張臉煞白如紙,聲音因恐懼而走了調:“大......大人!不好了!都察院的人......把咱們衙門給圍了!”
“什麼?”趙恪猛地站起身,手已經按在了刀柄上,滿臉的功勞喜色瞬間被滔天的煞氣所取代,“都察院的瘋狗!他們想幹什麼!”
周七喘著粗氣,語速快得像在放連珠炮:“是左都禦史張承!他......他帶著十幾名禦史,還有大理寺的官差,說、說我們懸鏡司濫用職權,無故擾民,指名道姓要您......要您出去回話!”
空氣瞬間凝固。
丞相的刀,終究還是砍下來了。
而且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準,正好卡在他們剛剛取得突破,心神最鬆懈的節骨眼上。
“他媽的!”趙恪怒罵一聲,轉身便要往外衝,“我倒要看看,誰敢在懸鏡司的地盤上撒野!”
“站住!”
徐恪虛弱的聲音不大,卻像一道無形的韁繩,死死勒住了暴怒的趙恪。
他劇烈地咳嗽起來,每一次都牽動著肺腑,帶來一陣撕裂般的劇痛。
一旁的陸時上前一步,默默地為他遞上了一杯溫水。
徐恪接過水杯,潤了潤幹裂的嘴唇,那張蒼白的臉上,非但沒有半分驚慌,反而露出了一絲玩味的笑意。
“大人,”趙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這幫言官最是難纏,我們不如以‘聖命在身,調查機密’為由,先關門不見,把他們晾在外麵!”
“晾?”徐恪搖了搖頭,放下水杯,“他們要的就是我們關門。我們隻要敢把大門一關,明天早朝,一本‘懸鏡司心虛抗法,藐視朝綱’的奏折就能擺到陛下的龍案上。”
他看著滿臉焦急的趙恪,輕輕一笑:“他們要的是程序,是道理。我們跟他們講道理,就輸了。”
“那......那怎麼辦?”
徐恪緩緩從床上坐直了身體,在趙恪和陸時震驚的目光中,下達了一連串匪夷所思的命令。
“開中門。”
“焚香。”
“備最好的茶。”
他抬起頭,那雙因病而略顯黯淡的眸子裏,閃爍著一種近乎妖異的光芒。
“請張禦史和諸位言官大人,入堂‘審查’。”
懸鏡司那扇常年緊閉、仿佛巨獸之口的黑石大門,此刻竟洞開到了最大。
門內香爐青煙嫋嫋,兩列緹騎按刀肅立,竟擺出了迎接貴客的最高禮儀。
左都禦史張承,帶著十幾名年輕氣盛的言官,正站在門外,義正辭嚴地宣讀著文書。
他本以為會吃到一個閉門羹,甚至做好了當場血濺五步,以死明誌的準備。
可眼前這陣仗,直接把他滿肚子的腹稿都給憋了回去。
就在他發愣的當口,一個身披厚重狐裘大氅,麵色慘白如紙,仿佛隨時會被風吹倒的身影,由兩名緹騎攙扶著,緩緩從大堂內走了出來。
正是徐恪。
“下官......咳咳......不知張禦史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徐恪一邊咳著,一邊對著張承拱了拱手,姿態放得極低。
張承愣了一下,旋即冷哼一聲,將手中的文書一揚:“徐指揮使,本官奉旨前來,調查你懸鏡司昨夜濫用職權,縱火擾民一案!還請你配合!”
他身後的一眾年輕禦史,個個昂首挺胸,眼神銳利,準備好了用唾沫星子將這個“酷吏”淹死。
然而,徐恪的反應,再次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他沒有辯解,沒有反駁,反而露出一副“終於等到你”的誠懇表情,上前一步,親熱地拉住了張承的手。
“哎呀!張大人,您可真是及時雨啊!”
張承被他這突如其來的熱情搞得渾身一僵,下意識地想把手抽回來。
徐恪卻握得更緊了,臉上滿是“真誠”的感激:“本官身負皇恩,正愁宵小之輩在坊間散布謠言,擾亂查案視聽。諸位大人能來協助審查,明辨是非,還我懸鏡司一個清白,實乃社稷之福,陛下之幸啊!”
這番話說得是情真意切,大義凜然。
直接把張承一行人從“問罪的敵人”,強行拔高到了“協助辦案的友軍”這個尷尬的位置上。
不等張承反應過來,徐恪便側過身,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諸位大人,外麵風大,裏麵請!咱們升堂,審查!”
張承和一眾言官,就這麼稀裏糊塗地被“請”進了懸鏡司那殺氣森森的指揮大廳。
剛一落座,熱茶還沒端上來,徐恪便拍了拍手。
“來人,把昨夜行動的所有卷宗,都給諸位大人呈上來!”
一聲令下,指揮大廳兩側的偏門被同時打開。
數十名緹騎吭哧吭哧地抬進來一口又一口沉甸甸的大木箱,“哐當!哐當!”地扔在大廳中央,瞬間堆成了一座小山。
箱蓋被掀開,無數的卷宗、文書、圖冊如山崩般傾瀉而出,灰塵彌漫,嗆得幾個年輕禦史連連咳嗽。
張承看著眼前這座文書山,徹底傻眼了。
徐恪裹著大氅,走到那堆故紙山前,用一種無比真誠的語氣,開始了介紹。
“張大人,您請看。這是我們昨夜行動的所有相關文書,分門別類,一應俱全。”
他隨手拿起一卷,攤開:“這是緹騎的夜間巡邏路線圖,精確到每一條巷子,每一更的人員交接記錄。”
他又拿起一本冊子:“這是盤查記錄,昨夜所有被盤問過的更夫、貨郎、乃至暗娼的口供,都在這裏。”
“哦,還有這個。”徐恪指著一摞厚厚的公文,“這是我們向京兆府申請引動水龍會的申請公文,上麵有京兆尹的親筆批紅。以及,這是事後我們委托第三方公估行做的損失評估,精確到燒壞了幾塊瓦,熏黑了幾塊磚,賠償款項一分不差。”
他抬起頭,用一種“你看我多專業”的眼神,真誠地看著已經目瞪口呆的張承。
“為求公正,還請諸位大人逐一審查,找出任何一處不合規的地方。本官與懸鏡司上下,全力配合!”
他頓了頓,又補充了一句最致命的話。
“當然,在諸位大人的審查結束,並出具‘審查無誤’的公文之前,我們懸鏡司絕不進行下一步任何動作,以免......幹擾大人們的工作。”
這番話,如同一記無聲的耳光,狠狠抽在了張承和所有禦史的臉上。
他們被死死地架在了火上。
查?
看著眼前這座比人都高的文書山,他們感覺自己的腦袋“嗡”的一聲。
他們是來搞彈劾的,是來吵架的,誰他媽是來做文書審計的?
這堆破爛玩意兒查到猴年馬月去?
不查?
那你就是無故上門尋釁,藐視皇差,幹擾懸鏡司辦案!
徐恪已經把姿態做足了,把皮球用一種你根本無法拒絕的方式,狠狠地踢了回來。
張承的臉,一陣紅一陣白,精彩紛呈。
他感覺自己像是掄圓了拳頭,結果一拳打進了一堆又軟又黏的棉花裏,有力無處使,憋屈得想吐血。
他被徐恪用“程序”本身,困死在了原地。
大堂裏,禦史們被困在文山會海之中,騎虎難下,隻能硬著頭皮拿起卷宗,裝模作樣地翻閱起來。
一牆之隔的密室內,氣氛卻截然不同。
徐恪、趙恪、陸時三人,正圍著那本《貨殖通錄》,爭分奪秒。
“看這裏。”徐恪指著那條“北地鐵料,臨江船行收款”的條目,對已經徹底服氣的二人,進行了一次跨越時代的經濟犯罪科普。
“這叫‘虛構交易’和‘資金轉移’。鐵料產自北疆,是戰略物資,買賣卻讓一家南方的船行來收款。這就說明,錢根本沒到賣鐵人的手裏,而是通過這家船行這個‘中轉站’,被洗幹淨之後,流向了別處。”
趙恪和陸時聽得雲裏霧裏,但他們抓住了最關鍵的一點。
這家船行,有問題!
“查!”徐恪眼中精光四射,下達了命令,“立刻動用所有情報資源,給我查清這家‘臨江船行’的幕後東家是誰!查他這幾年,與朝中哪些官員有過大額的資金往來!”
他忍不住又咳了兩聲,蒼白的臉上卻浮現出一絲冷笑。
“丞相大人送了我們這麼一份大禮,把這群‘審計官’派來,為我們爭取了寶貴的解謎時間,我們可不能浪費了。”
與此同時,丞相王德庸的府邸。
心腹管家正低聲彙報著都察院在懸鏡司的窘境。
王德庸正拿著一把小巧的銀剪,一絲不苟地修剪著一盆名貴的君子蘭。
他剪去一片枯黃的葉子,動作平穩,沒有絲毫波瀾。
聽完彙報,他沒有生氣,反而停下了手中的剪刀,沉思片刻,然後笑了。
“有趣。老夫本以為他是一條隻會撲咬的瘋狗,沒想到,還是一隻懂得挖陷阱的狐狸。”
他那雙渾濁的老眼中,閃過一絲欣賞,但更多的是冰冷的殺意。
“傳話給張承。”
他拿起噴壺,輕輕潤了潤君子蘭的葉片。
“就說老夫說的,既然是為國審查,就不可操之過急,一定要查得仔細,查得明白。”
他頓了頓,嘴角勾起一抹高深莫測的弧度。
“讓他......就在懸鏡司住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