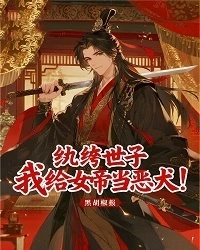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6章
懸鏡司大堂內,氣氛凝重得能滴出水來。
丞相王德庸那句輕飄飄的“就在懸鏡司住下吧”,像一道無形的聖旨,將左都禦史張承和他身後那群年輕氣盛的言官,變成了釘死在這裏的“常駐監軍”。
他們不再是來勢洶洶的問罪者,而是變成了懸在懸鏡司頭頂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他們什麼也不做,隻是每日正襟危坐,翻閱著那些永遠也翻不完的卷宗,用最“合乎規矩”的方式,將整個懸鏡司的行動能力徹底鎖死。
大堂內,緹騎們個個臉色鐵青,手按刀柄,卻連大氣都不敢喘。
這感覺,比跟北疆的蠻子真刀真槍地幹一架還要憋屈。
“大人!這就是個死局!”趙恪在內堂急得像一頭困獸,來回踱步,將地板踩得咚咚作響,“這幫酸儒擺明了就是要耗死我們!不如......不如我等上奏陛下,請她老人家聖裁!”
“請陛下聖裁?”
病榻上,裹著厚厚狐裘的徐恪聞言,劇烈地咳嗽起來,一張臉白得幾乎透明。
他好不容易喘勻了氣,看著滿臉焦急的趙恪,虛弱地搖了搖頭。
“陛下要的是一把能解決問題的刀,不是一把總在喊著‘主人,我被卡住了’的鈍刀。”
他抬起眼,目光越過趙恪,望向大堂上那個正襟危坐、一臉正氣的身影,嘴角忽然勾起一抹蒼白的笑意。
“張大人,你們在這兒幹坐著,也不是辦法啊。”
徐恪的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遍了整個內堂,也傳到了大堂上張承的耳朵裏。
張承聞聲,眉頭一皺,正欲開口反唇相譏。
徐恪卻已由陸時攙扶著,緩緩走了出來。
他走到張承麵前,將一張墨跡未幹的紙,輕輕放在了對方的桌案上。
“本官這裏,剛好有一樁‘疑似’動搖國本的大案,正需要各位‘清流’表率,來為我們懸鏡司的行動,做一個‘公正’的見證。”
張承低頭看去,隻見那張紙上赫然寫著“關於臨江船行與北疆鐵料異常資金往來之初步報告”。
“徐指揮使,你這是何意?”張承的眼中充滿了警惕。
“沒什麼意思。”徐恪坦然地坐到了他的對麵,仿佛不是在跟一個政敵說話,而是在與一位同僚商議公事,“本官懷疑,臨江船行涉嫌資敵,甚至通逆。但你也知道,我們懸鏡司行事,向來被詬病手段酷烈,證據或有瑕疵。若我單獨查辦,事後必有人彈劾我羅織罪名,構陷忠良。”
這番話說得是光明磊落,甚至帶著幾分“自嘲”。
張承冷笑一聲:“既然知道,就該謹言慎行,而非......”
“所以,我才需要張大人您啊。”徐恪打斷了他,話鋒一轉,那雙因病而略顯黯淡的眸子,此刻卻灼灼放光,“但若有張大人您以及諸位禦史大人,全程‘監察’我們的抓捕與審訊,那此案的程序便無懈可擊。”
他向前湊了湊,聲音壓得極低,卻字字如雷。
“查出來,是諸位大人與本官一同為國除奸,大功一件;查不出來,也證明了船行的清白,彰顯了諸位大人明察秋毫。無論結果如何,諸位都立於不敗之地。”
張承瞬間明白了徐恪的險惡用心。
這是一個陽謀!
一個讓他根本無法拒絕的陽謀!
拒絕?
“拒絕”二字一旦出口,就等於他張承,當著所有人的麵,承認了自己“明知有叛國嫌疑卻阻撓調查”。
這個罪名,別說他一個左都禦史,就是丞相王德庸,也擔不起!
同意?
同意,就等於他帶著整個都察院,給懸鏡司這次明顯是“濫用職權”的行動背書!
他將從一個高高在上的“審查者”,瞬間淪為徐恪的“同謀”!
在“瀆職”和“同流合汙”之間,他根本沒有第三個選擇。
他看著眼前這個咳得仿佛下一秒就要斷氣的病秧子,後背卻竄起一股徹骨的寒意。
這哪裏是個人,這分明是個披著人皮的怪物!
良久,張承從牙縫裏,擠出了兩個字。
“......好。”
半個時辰後,京城南街的百姓們,看到了此生最為詭異的一幕。
一隊隊伍,正浩浩蕩蕩地朝著臨江船行的方向開去。
隊伍的後半截,是數百名身著黑色飛魚服、手持繡春刀的懸鏡司緹騎,一個個殺氣騰騰,眼神像是要吃人。
而在隊伍的最前方,引領著這群虎狼之師的,卻是十幾位身穿青綠色官袍、一臉嚴肅,甚至可以說是“生無可戀”的都察院禦史。
百姓們議論紛紛,竊竊私語。
“這......這是唱的哪一出?懸鏡司抄家,怎麼還讓禦史老爺帶隊了?”
“你懂什麼!這叫‘奉旨查案,名正言順’!”
臨江船行門口,一名管事模樣的中年人帶著十幾名護院,囂張地攔住了去路,手中還舉著一塊“東家有喜,歇業三日”的牌子。
“懸鏡司的各位爺,行個方便!我們這兒......”
趙恪正要拔刀,隊伍最前方的張承,那張臉已經黑得能擰出墨來。
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綁上了徐恪的戰車,此刻若有半分退縮,事後被清算的第一個就是他。
他鐵青著臉,從懷中掏出都察院的勘問令,往前一遞,聲音冷得像是從冰窖裏撈出來的。
“都察院聯合懸警司辦案,閑雜人等,速速退避!”
那名管事臉上的囂張瞬間凝固,整個人如遭雷擊,呆立當場。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最大的護身符,竟然成了對方最鋒利的刀!
這一聲,徹底擊潰了船行所有人員的心理防線。
趙恪獰笑一聲,大手一揮,身後的緹騎們便如虎入羊群,在陸時那冰冷目光的指揮下,直撲後院一間隱秘的賬房。
不遠處的街角,一輛不起眼的黑色馬車裏。
徐恪裹著狐裘,隔著車簾的縫隙,靜靜地看著這一切。
他劇烈地咳嗽起來,咳得撕心裂肺,嘴角卻勾起一抹蒼白而滿足的微笑。
他知道,魚兒,上鉤了。
......
臨江船行,後院密室之內。
一個被稱為“錢先生”的中年文士,正不緊不慢地將一封封密信投入麵前的銅火盆。
他聽到了外麵的騷動,但並不驚慌。
他深知懸鏡司的行動模式,更知道都察院那群瘋狗正死死地咬著他們,料定對方不敢有大動作。
“先生!不好了!懸鏡司的人......打進來了!”一名下人驚慌失措地闖了進來。
“慌什麼。”錢先生頭也不抬,將最後一封信丟入火中,“一群莽夫罷了,讓他們鬧。等張禦史的彈劾奏章一上,有他們好果子吃。”
然而,那名下人接下來的話,卻讓他燒信的手猛地一抖。
“可......可是......帶隊的,就是張禦史!他還喊......喊都察院聯合辦案!”
錢先生臉上的從容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極致的驚駭和難以置信。
“瘋了......徐恪這個瘋子......”
他喃喃自語,一張信紙從指間滑落,掉入火盆,瞬間被火焰吞噬。
“他怎麼敢......他怎麼能?”
他立刻意識到,所有的後手和托詞,在“聯合辦案”這個無懈可擊的名頭下,都已化為泡影。
自己,已是甕中之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