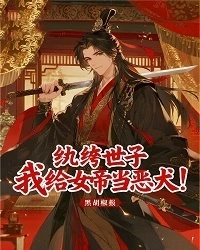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4章
懸鏡司的臨時安全屋內,空氣凝重得仿佛能擰出水來。
親信緹騎周七單膝跪地,雙手高高舉著一個樸實無華的鐵盒,那姿態,仿佛在呈遞一枚傳國玉璽。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這隻盒子上,呼吸聲清晰可聞。
“大人,幸不辱命!”
徐恪點了點頭,正要示意趙恪接過,靜室的門卻“吱呀”一聲被從外推開。
一道身影踉蹌而入,帶著一股濃重的血腥味。
是陸時。
他那張萬年不變的冰山臉此刻蒼白如紙,右臂的飛魚服被劃開一道深可見骨的口子,皮肉外翻,鮮血已經浸透了半邊身子,正順著指尖“滴答、滴答”地落在幹淨的木板上。
“陸都指揮使!”趙恪大驚失色,一個箭步衝上前扶住他,“你受傷了?”
陸時擺了擺手,推開趙恪的攙扶,依舊站得筆直,像一杆寧折不彎的標槍。他看向病榻上的徐恪,聲音因失血而有些沙啞,卻依舊平穩:“屬下幸不辱命,拖住了他三十五息。”
三十五息。
一個聽起來不算長,卻足以讓在場所有人心臟驟停的時間。
陸時沉聲道:“那人......很強,深不可測。”他言簡意賅地描述了那場短暫卻凶險到極致的交鋒,“他的武器是一串佛珠,看似尋常,卻能彈出,每一顆都蘊含千鈞之力。身法鬼魅,若非屬下以命相搏,硬接了他三記殺招,恐怕......十息都撐不住。”
房間內死一般寂靜。
剛剛因勝利而升起的些許喜悅,瞬間被一股冰冷的寒意衝得煙消雲散。
在場眾人,都是在刀口上舔血的好手,他們比誰都清楚,能讓鳳駕親軍都指揮使陸時說出“十息都撐不住”這句話,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眾人第一次如此直觀地,感受到了那個名為“佛見愁”的殺手的可怕。
也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了徐恪那套“避免正麵衝突”的戰術,是何等的正確。
陸時那雙冰冷的眸子,再看向徐恪時,已經從最初純粹的監視與審視,多了一絲軍人之間,對卓越指揮官的敬佩。
徐恪沒有多言,隻是對趙恪點了點頭:“上金瘡藥,請最好的大夫。”
隨即,他將目光移回了那個決定無數人命運的鐵盒之上。
鐵盒被打開,一本泛黃的賬簿靜靜地躺在其中。
封麵上,用工整的楷書寫著四個字——《貨殖通錄》。
眾人立刻湊了上來,連剛剛坐下處理傷口的陸時,也投來了關注的目光。
趙恪小心翼翼地捧起賬簿,翻開了第一頁。
然後,他愣住了。
再翻一頁,他臉上的期待,變成了茫然。
當他一口氣翻了十幾頁後,那張寫滿了“功勞”二字的臉,徹底垮了下來。
賬簿上,沒有一個名字,沒有一行罪證,更沒有什麼謀逆的信函。
滿滿的全是日期、貨物名、數量和銀兩。
“三月初七,入庫蘇繡一百匹,記銀一千兩。”
“三月初九,出茶三百斤,往江南,記銀五百兩。”
“三月十一,購入景德鎮官窯瓷器二十箱......”
這......這不就是一本普通商號的流水賬嗎?
趙恪臉上的肌肉抽搐著,寫滿了失望與不解,他抬頭看向徐恪,聲音都變了調:“大人,我們......我們是不是搞錯了?這東西......這東西有何用處?”
氣氛瞬間跌入冰點。
所有人,包括周七在內,都感覺自己像是被人從頭到腳澆了一盆冰水。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與京城最頂尖的殺手生死競速,最後奪回來的......就是一本無用的廢紙?
徐恪從趙恪手中接過了那本《貨殖通錄》。
他靠在床頭,一頁一頁地翻看著。
起初,他也眉頭緊鎖,似乎在思索著什麼。
整個房間裏,隻剩下紙張翻動的“沙沙”聲。
然而,隨著他翻看的頁數越來越多,那張因高燒而泛著病態潮紅的臉上,卻慢慢地,浮現出了一絲冰冷而興奮的微笑。
那笑容,看得趙恪和陸時心裏直發毛。
“有點意思。”徐恪終於停下了翻動,用一根蒼白的手指,輕輕點在了賬簿的某一頁上。
他抬起頭,環視著滿臉困惑的眾人,開始了他的提問。
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扇在場所有人都看不見的大門。
“你們看這裏,”他指著一行字,“三月初七,‘入庫蘇繡一百匹,記銀一千兩’。就在同一天,下麵緊跟著又有一筆,‘蘇繡折耗,記損三百兩’。趙千戶,我問你,有誰家的生意,是貨剛入庫,連動都沒動,就憑空損耗了三成的?”
趙恪下意識地搖頭:“不可能!除非是掌櫃的自己監守自盜!”
“很好。”徐恪的手指又滑到另一處,“還有這裏,‘購入北地鐵料五百斤’。北地的鐵,運到京城,天經地義。可為什麼收款方,卻寫著南方的‘臨江船行’?鐵從北邊來,錢往南邊走,這錢......究竟去了哪裏?”
陸時那雙冰冷的眸子裏,第一次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最可笑的,是這個。”徐恪的指尖,最終停在了一連串的數字上,“你們看,每一筆超過萬兩的大額支出後麵,都雷打不動地跟著一筆數額精確到三錢七分銀子的小額‘茶水費’。你們不覺得......這太巧合了嗎?哪家的茶樓,喝杯茶還能喝出零有整的?”
一連串的問題,讓在場這些自詡為刑偵高手的精英們,腦子徹底變成了一團漿糊。
他們感覺自己像是第一次學認字的三歲孩童,看著一本明明每個字都認識,連在一起卻完全看不懂的天書。
徐恪抬起頭,那雙因病而略顯黯淡的眸子裏,閃爍著一種看穿一切的、屬於另一個次元的智慧光芒。
“這不是一本賬,這是兩本賬。”
他的聲音不大,卻如同一道驚雷,在眾人耳邊炸響。
“一本,是寫在紙上,給外人看的明賬。而另一本......”他頓了頓,用一種他們從未聽過的詞彙,揭示了真相,“用你們聽不懂的話說,叫‘洗錢’的暗賬,就藏在這些看似合理的流水裏!”
“每一個不合理的‘折耗’,都是一筆被憑空侵吞的黑錢!每一次流向錯誤的‘采購’,都代表著資金的非法轉移!每一筆精準到分的‘茶水費’,都他媽是一個接頭暗號!”
徐恪的眼中燃燒著興奮的火焰,仿佛一個頂級黑客,剛剛破解了世界上最複雜的密碼。
“這本《貨殖通錄》,根本不是燕王的罪證名單!”
他將賬簿重重地合上,發出一聲清脆的“啪”響。
“這是他在京城所有地下勢力的......神經網絡圖!”
......
與此同時,丞相王德庸的府邸,書房內墨香四溢。
這位權傾朝野的老人,正手持一支狼毫,氣定神閑地臨摹著一幅前朝的山水畫,筆鋒穩健,看不出絲毫心緒波動。
一名心腹管家悄無聲息地滑了進來,在他身後低聲彙報了昨夜城南水龍會附近,懸鏡司緹騎以“消防稽查”為名,鬧得雞飛狗跳的全過程。
“懸鏡司......消防稽查?”
王德庸聞言,淡淡一笑,手中的筆鋒沒有絲毫停頓,依舊在紙上勾勒著嶙峋的山石。
“徐恪這條小瘋狗,病得快死了,還不忘齜牙咬人。他搞出這麼大的動靜,可不是為了抓幾個潑皮無賴,而是為了掩蓋更大的動靜。”
他緩緩放下筆,吹了吹畫上未幹的墨跡,那雙渾濁的老眼中,閃過一絲與年齡不符的銳利。
“他想查案,老夫就偏不讓他查得安生。”
老人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口浮沫,語氣平淡得像是在吩咐下人打掃庭院。
“傳我的話,讓都察院的張禦史,帶人去懸鏡司‘坐坐’。”
“就問問我們那位徐指揮使,為何無故擾民,濫用職權。”
他呷了口茶,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病了,就該好好在床上躺著,別總想著出來亂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