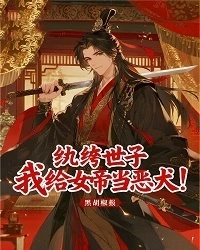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9章
懸鏡司詔獄的靜室內,檀香的餘燼已冷。
戶部尚書宋文淵跪伏在地,這位在朝堂上呼風喚雨了半輩子的二品大員,此刻涕淚橫流,將他那腐爛到骨子裏的秘密,一點一滴地剖了出來。
他貪墨的巨額銀兩,並非全部中飽私囊。其中超過七成,都通過一個極其隱秘、橫跨南北的商路網絡,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了一個地方——北疆。
鎮守北疆的,是燕王。
賬冊上那些看似天衣無縫的“官方采買”與“火耗折損”,實際上都是為燕王私鑄兵甲、囤積糧草打的掩護。
靜室內死一般寂靜,隻有宋文淵壓抑的抽泣聲。
趙恪站在一旁,從最初的震驚,到渾身血液都開始沸騰。
他握著刀柄的手因過度用力而青筋暴起,眼中迸射出駭人的光芒。
這不是貪腐案!
這是通敵謀逆!
是足以將大周江山都捅個窟窿的潑天大案!
狂喜,難以抑製的狂喜瞬間淹沒了趙恪。
他仿佛已經看到,在這份供詞的推動下,懸鏡司將立下不世之功,而眼前這位病弱的指揮使大人,將一步登天!
“大人!”趙恪激動得聲音都在顫抖,“我立刻將這份供詞整理成冊,八百裏加急呈報陛下!此乃......此乃天大的功勞啊!”
這是任何一個大周官吏最本能的反應,忠誠且直接。
然而,由兩名緹騎攙扶著,幾乎是被人架在椅子上的徐恪,卻隻是緩緩地抬起眼皮,那張蒼白如紙的臉上,看不出半分喜悅。
......
半個時辰後,內院病房。
濃重的藥味彌漫在空氣中。
趙恪手捧著剛剛謄寫好的供詞,像捧著一塊燒紅的烙鐵,滿臉通紅地衝到徐恪的床邊。
“大人!您看,一字不差!隻要將此物呈上,燕王......燕王他......”
“現在就報上去,”徐恪虛弱地靠在床頭,聲音輕得像一陣風,卻瞬間吹滅了趙恪所有的熱情,“我們兩個,就都成了催命符。”
趙恪臉上的狂喜瞬間凝固,如同被人迎麵潑了一盆冰水:“大......大人?為何?這可是潑天的功勞啊!”
“功勞?”徐恪低聲咳嗽起來,每一次都牽動著肺腑,帶來一陣劇痛。
他緩了口氣,銳利的目光鎖定在趙恪那張寫滿不解的臉上。
“趙恪,我問你,這份供詞,除了宋文淵的口述,我們有第二份證據嗎?”
趙恪一愣,下意識地搖頭:“尚無......但這可是戶部尚書的親口供詞!”
“所以,這就是原則一:不要給上級‘未經證實’的情報。”徐恪的聲音不大,卻字字敲在趙恪的心坎上,“口供隻是口供,在沒有找到那條商路,沒有查獲一刀一槍之前,這就是孤證。我們拿著一份孤證,去指控一位手握二十萬邊軍、鎮守國門的親王,你猜,陛下是會相信我們這兩個剛辦了件差事的酷吏,還是會為了穩定大局,先砍了我們這兩個‘構陷忠良,動搖國本’的罪魁禍首?”
趙恪的額角,瞬間滲出了一層冷汗。
他隻看到了功勞,卻忘了功勞背後那足以吞噬一切的風險。
徐恪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繼續用那平淡的語氣,拋出第二個問題。
“好,就算陛下信了我們。然後呢?”
“然後?”趙恪被問住了,“然後......然後自然是發兵平叛,捉拿燕王......”
“說得好。”徐恪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原則二:不要給上級‘無法解決’的問題。發兵?錢從哪來?戶部剛被我們抄了個底朝天。兵從哪來?京城衛戍的兵能打仗嗎?我們把一個足以讓大周分崩離析的難題,赤裸裸地丟到陛下麵前,這不是功勞,這是逼宮。我們不是在為陛下解決麻煩,而是在給她製造一個天大的麻煩。”
趙恪徹底呆住了。
他感覺自己的腦子像一團被攪亂的漿糊,那些他奉為圭臬的“忠君”、“辦事”的準則,在徐恪這番話麵前,被衝擊得支離破碎。
“那......那我們該怎麼辦?”他茫然地問道,語氣裏已經帶上了一絲他自己都未曾察覺的敬畏。
“記住,”徐恪的眼中閃過一絲屬於現代精英的、洞悉一切的微光,“原則三:永遠要帶著‘解決方案’去彙報。我們的職責,不是咋咋呼呼地跑去告訴陛下‘房子著火了’,而是要把這團亂麻理順,摘出最關鍵的線頭,然後告訴陛下,隻要輕輕一拉這裏,整個線團就能迎刃而解。我們要上報的,不應該是一份惹事的供詞,而是一份能解決問題的‘方案’。”
他喘了口氣,對已經陷入呆滯的趙恪吩咐道:“筆墨伺候。”
在趙恪近乎石化的目光中,徐恪靠在床頭,用微弱卻清晰無比的聲音,口述了一份足以載入大周官場史冊的奏折。
“第一部分,名為‘已證實事實’。”
徐恪緩緩說道:“隻寫賬冊上能證明的東西。寫宋文淵貪墨巨額官銀,並與身份不明的勢力有長期、大規模資金往來。每一個字,都要有賬冊上的條目做支撐。這部分,是鐵證,是我們的功勞,無懈可擊。”
趙恪一邊奮筆疾書,一邊不住地點頭,冷汗已經浸透了他的後背。
“第二部分,名為‘待證實情報’。”
“把宋文淵的供詞,作為附件。但在前麵,必須用最醒目的字跡標注:‘此為犯官宋文淵單方麵供述,其心可誅,其言待查,懇請聖裁’。明白嗎?我們要把這份情報的真實性,和我們自己徹底撇清關係。它不是我們的結論,隻是我們繳獲的‘戰利品’。”
趙恪握筆的手,已經開始微微顫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第三部分,名為‘初步行動建議’。”
徐恪的眼神變得無比銳利:“基於以上兩點,向陛下提出一個具體的、可執行的、低風險的下一步行動方案。你就這麼寫:臣建議,暫不驚動北疆,以免打草驚蛇,動搖軍心。由我懸鏡司秘派精銳,順藤摸瓜,偽裝成商隊,徹查供詞中所謂的‘商路’。若查實,則人贓並獲,可一擊製勝;若查無此事,亦可證明燕王清白,安定社稷。”
說到這裏,徐恪停頓了一下,加重了語氣,說出了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句話。
“在結尾處寫上:期間一切責任,由臣徐恪一人承擔。”
當最後一個字落下,趙恪停下筆,整個人像是虛脫了一般,呆呆地看著手中那份墨跡未幹的奏折。
他顫抖著,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
他終於明白了自己和徐恪的差距,那不是聰明與愚笨的差距,而是維度上的差距。
他看到的是眼前的功勞,而徐恪看到的是功勞背後的風險,是整個朝堂的棋局,甚至是龍椅上那位女帝的心思。
這份奏折,既呈上了無可辯駁的功勞,又清晰地分析了潛在的風險,還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解決方案,甚至主動將所有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這完美地迎合了一位帝王“掌控一切”的心理需求。
這已經不是一個酷吏的彙報了。
這是一個頂級戰略家的藍圖!
......
相府,書房。
丞相王德庸將最後一頁賬冊投入了麵前的銅火盆,靜靜地看著那一行行觸目驚心的名字和數字,在火焰中卷曲、焦黑,最終化為一縷青煙。
他渾濁的雙眼,平靜無波。
一位心腹門生站在他身後,憂心忡忡:“恩師,徐恪此舉,分明是手握屠刀,意在震懾我等。宋文淵落在他手裏,怕是......”
“他把原件送來,就是要老夫親手燒了它。”王德庸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口浮沫,打斷了門生的話,“他要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規矩’。”
老丞相頓了頓,眼中閃過一絲與年齡不符的精光。
“他要殺的,是像宋文淵這種不守規矩的蠢貨,好給那些守規矩的聰明人,騰地方。這隻小狐狸,是在幫陛下,也是在幫老夫......清理門戶啊。”
他明白,徐恪那近乎“敲詐”的行為背後,是一種殘酷的政治默契。
他決定暫時順水推舟,先借徐恪這把快刀,砍掉自己陣營裏那些早已腐爛、不聽話的爛肉。
......
一份用火漆密封的奏折,被趙恪親自送入了皇宮。
整個懸鏡司都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安靜,所有人都知道,決定他們命運的時刻,已經到來。
這份與眾不同的“三段式”奏折,擺在女帝的案頭時,會掀起怎樣的波瀾?
那位高深莫測的君主,是會讚賞徐恪的深謀遠慮,還是會更加警惕他那洞悉人心、近乎妖孽的可怕智謀?
徐恪主動請纓,將自己置於調查燕王的風口浪尖,這究竟是忠誠的獻祭,還是另一場更宏大、更危險的賭局的開端?
夜色深沉,無人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