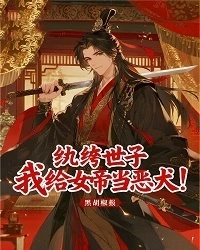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0章
夜深如墨。
懸鏡司後院的靜室內,藥味與檀香混合的氣息揮之不去。
徐恪躺在床上,因傷痛與算計過度而陷入淺眠,眉頭緊鎖,仿佛在夢中也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廝殺。
“吱呀......”
房門被無聲地推開,一道攜著子夜寒氣的身影,悄無聲息地滑了進來。
那股熟悉的、清冷中帶著一絲霸道的龍涎香,讓徐恪的神經猛地一跳,瞬間從淺眠中驚醒。
他費力地睜開眼,看到的,是此生最不想在此時此地看到的人。
大周女帝,李青鸞。
她褪去了繁複的朝服,隻著一件玄色龍紋常服,不帶任何儀仗,僅在一名貼身老太監的陪同下,如鬼魅般出現在了他的床前。
她不說話,隻是靜靜地看著他,纖長白皙的手中,正把玩著那份他用盡心血口述的“三段式”密折。
黑暗中,那雙鳳眸比詔獄最深處的寒冰更冷,比懸鏡司最鋒利的繡春刀更利。
沉默,是帝王最可怕的武器。
這種無聲的審視,像一座無形的大山,重重壓在徐恪的胸口,讓他本就虛弱的呼吸變得愈發困難。
他知道,女帝不是來聽彙報的,她是來剖開他的腦子,看穿他的靈魂的。
不知過了多久,女帝終於開了金口,聲音清冷得不帶一絲溫度。
“你的奏折,很有趣。”
她將那份密折輕輕一揚,紙張在空中劃過一道冰冷的弧線。
“把事實、猜測和建議分得這麼清楚。是在告訴朕,如果查錯了,罪不在你嗎?”
來了。
徐恪的心猛地一沉。
這是第一道陷阱,一道致命的送分題,也是送命題。
她將他的風險規避,曲解成了推卸責任。
他掙紮著想要起身行禮,卻被一股無形的氣場死死壓在床上,連動一動手指都變得無比艱難。
冷汗,瞬間浸濕了他貼身的裏衣。
“臣......不敢。”徐恪的聲音沙啞幹澀,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裏擠出來的。
女帝沒有理會他的辯解,向前走了一步,居高臨下地俯視著他,鳳眸中的審視愈發銳利。
“你主動請纓,徹查燕王。一個小小的懸鏡司臨時指揮使,是什麼讓你覺得,你有資格把一位手握二十萬邊軍的親王,當做你的目標?”
第二問,接踵而至。
這個問題比前一個更加惡毒,直接質疑他的動機,暗示他不知尊卑,野心過大,想要借機染指國之重器。
徐恪的呼吸一滯,高燒和巨大的心理壓力讓他眼前陣陣發黑。
他咬著舌尖,劇痛讓他勉強維持著清醒。
不等他想好說辭,女帝那冰冷的聲音,便拋出了最後的,也是最致命的一問。
“這份奏折,寫得滴水不漏。既為朕解決了眼下的難題,又為你自己鋪好了所有的退路。徐恪......”
她緩緩湊近,吐出的氣息都帶著冰碴子。
“你究竟是忠於朕,還是忠於你自己的這一身智謀?”
轟!
這最後一問,如同一道九天驚雷,在徐恪的腦海中轟然炸響!
它徹底撕碎了所有公事的偽裝,將矛頭直指“忠誠”二字。
這是帝王對臣子最根本的拷問,答錯了,便是萬劫不複。
徐恪知道,這是他的生死關。
他用盡全身的力氣,雙手撐著床沿,在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後,終於勉強坐了起來。
他沒有直接辯解,那隻會顯得蒼白無力。
他抬起頭,迎上女帝那雙仿佛能洞穿一切的鳳眸,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聲音虛弱,卻異常清晰。
“回稟陛下,臣不是刀,更不是劍。”
他喘了口氣,在女帝微微蹙起的眉間,一字一頓地拋出了那個全新的概念。
“臣,願為陛下手中的‘手術刀’。”
女帝的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訝異。
徐恪沒有給她思考的時間,立刻開始闡述自己的理論,這是他賭上一切的自白。
“手術刀之用,在於精準。”他迎著女帝的第一道質問,不卑不亢地解釋道,“何處是腐肉,比如宋文淵的罪證,這是已證實的事實;何處是肌理,比如那份未經證實的供詞,這是待查的情報;何處可以下刀,比如臣提出的徹查商路,這是具體的行動建議。三者必須分毫不差,因為臣知道,若不分清,魯莽一刀下去,毀掉的便是陛下的江山社稷。臣......不敢不慎。”
這番話,完美地將“推卸責任”的指控,升華為了“為國盡忠”的高度謹慎。
女帝的目光閃爍了一下,沒有說話,示意他繼續。
徐恪的呼吸急促了些,繼續道:“而手術刀本身,沒有資格選擇要切除哪個部位。決定權,永遠在執刀人的手中。”他直麵那關於“野心”的第二問,姿態放得極低,“臣的目標從來不是燕王,也不是朝堂上任何一位大人。臣的目標,永遠是陛下您用目光指出的任何一處‘病灶’。”
最後,他深吸一口氣,直麵那最致命的忠誠拷問。
“陛下,手術刀的忠誠,不在於它會思考,而在於它的所有鋒利和思考,都隻為了執刀人一個目的——根除病灶,讓肌體恢複健康。”
他的目光變得前所未有的坦誠和炙熱。
“臣的智謀若不能為陛下所用,便一文不值。若有半分私心......”他停頓了一下,每一個字都擲地有聲,“甚至......罪該萬死!”
話音落下,靜室內死一般寂靜。
“手術刀”理論,如同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完美地解答了女帝所有的疑慮。
它坦然承認了主角的智慧與危險性(鋒利),但又將其牢牢地限製在了“工具”的範疇內,並將最終的決定權和榮耀,全部歸於龍椅之上的執刀人。
這是一個既展現了自身無與倫比的價值,又表達了絕對服從的、天才般的回答。
良久,女帝那萬年不化的冰山臉上,終於勾起了一抹奇異的弧度。
那笑容裏,有欣賞,有玩味,更有了一絲更深的忌憚。
她被說服了。
“好一個‘手術刀’。”她緩緩點頭,隨手從腰間解下一塊通體漆黑,上麵隻用金文篆刻著一個“敕”字的玄鐵令牌,隨手扔在了徐恪的床頭。
令牌落在被褥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卻仿佛重逾千斤。
“朕給你便宜行事之權。”女帝的聲音恢複了慣有的冰冷,“懸鏡司、地方官府、乃至軍隊驛站,見此令如見朕親臨。調查所需錢糧,可直接從內帑支取。”
這是前所未有的授權!
是足以讓任何一個臣子都為之瘋狂的恩賜!
徐恪的心臟狂跳起來,但他還沒來得及謝恩,女帝的下一句話,便如同一盆冰水,將他所有的興奮都澆得一幹二淨。
“但你傷勢未愈,身邊需要人手。”
她輕輕拍了拍手。
房門被再次推開,一名身穿飛魚服,身形挺拔如鬆,麵容冷峻如冰的青年將領,邁著沉穩的步伐走了進來。
他單膝跪地,動作幹淨利落,沒有發出一絲聲響。
“這是朕的鳳駕親軍都指揮使,陸時。”女帝淡淡地介紹道,“從今日起,他與他麾下的一百鳳駕親軍,歸你調遣,負責‘保護’你的安全。”
“保護”二字,被她刻意加重了語氣,像兩座無形的山,壓在了徐恪的肩上。
恩賜與枷鎖,同時降臨。
陸時,既是他最精銳的保鏢和助手,也是女帝放在他身邊最直接、最致命的監視者。
......
與此同時,相府書房。
夜色已深,丞相王德庸卻毫無睡意,靜靜地撚著一枚冰冷的棋子。
一名身著夜行衣的黑影如鬼魅般出現在他身後,單膝跪地,低聲彙報:“......陛下出宮,隻帶了陸時,去了懸鏡司,逗留了約莫半個時辰。”
王德庸撚動棋子的手指微微一頓,雙眼微閉,仿佛睡著了一般。
不知過了多久,他才緩緩睜開眼,那雙渾濁的老眼中,已無半點睡意,隻剩下洞悉一切的清明。
“知道了。”他淡淡地吩咐道,“備一份厚禮,明日一早送到燕王府上,就說,老夫恭賀王爺......喜得麟兒。”
身後的心腹門生聞言一愣,滿臉不解:“恩師,燕王妃並無身孕,府中也未曾聽說有哪位側妃有喜啊?”
王德庸將手中的棋子輕輕放回棋盒,答非所問地悠悠道:“有沒有,不重要。”
他抬起頭,看向窗外那深不見底的夜色,嘴角勾起一抹高深莫測的笑容。
“重要的是,讓王爺知道,京城裏有人‘惦記’著他有沒有子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