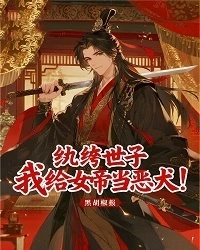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8章
懸鏡司詔獄,京城裏能讓小兒止啼的凶地。
傳聞中,這裏常年陰暗潮濕,牆壁上滲著洗不淨的血跡,空氣裏飄蕩著冤魂與黴菌混合的惡臭。
任何被押進來的官員,不等用刑,光是聽著刑具架上那些玩意的名字,就足以嚇得魂飛魄散。
戶部尚書宋文淵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他準備好了麵對酷刑,準備好了痛斥酷吏,準備好了慷慨陳詞,上演一出“忠臣蒙冤,士可殺不可辱”的千古名場麵。
然而,當他被押入詔獄最深處時,卻愣住了。
沒有想象中的陰暗與血腥。
他被關進了一間幹淨得過分的“靜室”。
地麵鋪著幹燥的木板,牆壁粉刷得雪白,角落裏甚至還點著一爐上好的安神香,淡淡的檀木味驅散了所有的汙穢氣息。
室內陳設簡單到極致,隻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
定時送來的飯菜,是精致的四菜一湯,還冒著熱氣。
宋文淵所有的腹稿,都卡在了喉嚨裏。
這感覺,就像你憋足了勁要跟人拚命,結果對方不僅沒亮刀子,反而客客氣氣地請你坐下喝茶。
巨大的預期反差,讓他渾身難受。
第一個時辰,無人審問。
第二個時辰,一名麵生的緹騎走了進來,一言不發,隻是為他空了的茶杯續上熱水,然後便退了出去,關上門。
宋文淵從一開始的倨傲冷笑,逐漸變得坐立不安。
他最強大的武器——二品大員的身份,朝堂辯論的規矩,在這裏完全失效了。
舒適的環境和絕對的安靜,像一把無形的刀,正在一層層剝離他“尚書大人”的身份外殼,將他從一個高高在上的政治符號,打回一個必須孤獨直麵自己內心的凡人。
他開始焦躁,額角滲出了細密的汗珠。
“吱呀――”
靜室的門終於再次被推開。
北鎮撫司千戶趙恪大步走了進來,將一本厚厚的賬冊,“啪”的一聲,輕輕放在了宋文淵麵前的桌上。
宋文淵瞳孔一縮,那是他的賬冊。
但他旋即冷哼一聲,將頭扭向一邊,擺出了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態。
趙恪沒有看他,隻是自顧自地坐下,翻開了賬冊。
他沒有念宋文淵的罪證,反而像是自言自語般,念起了別人的名字。
“兵部右侍郎王之渙,收受北地鐵礦幹股三成,折銀二十七萬兩......嘖,胃口不小。”
宋文淵眼皮跳了一下,王之渙是他最鐵的盟友。
趙恪仿佛沒看見他的反應,繼續翻頁。
“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李茂,於江南鹽引案中,為其門生行方便,得銀八萬兩......”
宋文淵的呼吸開始變得急促。
趙恪合上賬冊,端起茶杯,吹了吹熱氣,用一種閑聊的語氣,不經意地說道:“哦,對了。王侍郎已經被我們請來喝茶了,他很合作,說所有事都是您在背後主使的,他也是一時糊塗。”
宋文淵猛地轉過頭,死死盯著趙恪:“你胡說!王大人與我乃生死之交,豈會構陷於我!”
“是嗎?”趙恪笑了,那笑容裏帶著一絲憐憫,“李禦史也托人帶話了,說他深受您蒙蔽,險些釀成大錯。如今幡然醒悟,明日便要上奏,彈劾您結黨營私,穢亂朝綱。”
這些話,半真半假。
賬冊是真的,但王侍郎和李禦史的“背叛”,卻是徐恪憑空捏造的謊言。
可這些謊言,建立在真實罪證的基礎上,便擁有了以假亂真的恐怖力量。
宋文淵是官場老手,他比誰都清楚“大難臨頭各自飛”的道理。
趙恪這番話,如同一柄重錘,狠狠砸碎了他心中最後一點僥幸。
他堅信,自己已經被整個文官集團當成了棄子,連丞相大人都保不住他了。
他不再是“我們”中的一員,他成了一個孤零零的、即將被所有人分食的“我”。
他的心理防線,從外部開始,寸寸崩塌。
看著宋文淵那張瞬間失去所有血色、變得灰敗的臉,趙恪心中對那位病榻上的指揮使大人,生出了近乎神明般的敬畏。
就在宋文淵心神俱疲,即將崩潰之際,靜室的門再次被推開。
一股濃重的藥味湧了進來。
徐恪由兩名緹騎攙扶著,緩緩走了進來。
他麵色蒼白如紙,嘴唇毫無血色,裹著厚厚的裘衣,仿佛一陣風就能吹倒。
他每走一步,都伴隨著一陣壓抑的低咳,整個人看起來比階下囚宋文淵還要淒慘。
宋文淵抬起頭,看著這個將自己逼入絕境的始作俑者,眼中充滿了怨毒與不甘。
徐恪在趙恪的攙扶下,慢慢坐到了宋文淵的對麵。
他沒有看宋文淵,甚至沒有理會他那能殺人的目光。
他隻是虛弱地靠在椅背上,對身旁的趙恪輕聲問道,仿佛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家事。
“去江南查的那個‘遠房表侄’,有消息了嗎?”
宋文淵的身體猛地一僵。
徐恪繼續用那平淡的、不帶一絲波瀾的語氣說道:“派人看好他,別讓他出什麼意外。宋大人倒了,他一個無依無靠的讀書人,在江南那種地方,可別被人欺負了。”
“遠房表侄”這四個字,如同一道九天驚雷,在宋文淵的腦海中轟然炸響!
這把最鋒利的刀,瞬間刺穿了他所有的偽裝,精準地紮進了他內心最柔軟、最恐懼的地方。
那個所謂的表侄,根本不是什麼遠親,那是他的私生子!
是他此生唯一的牽掛和軟肋!
他貪墨斂財,費盡心機地往上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給這個見不得光的兒子,鋪一條錦繡前程!
這個秘密,他自以為埋藏得天衣無縫。
可眼前這個仿佛隨時會死的病秧子,卻輕描淡寫地,將它挖了出來。
徐恪終於緩緩抬起眼皮,第一次正視著眼前這個失魂落魄的戶部尚書。
他的聲音不大,卻字字誅心。
“尚書大人,朝堂上的事,到你為止,可以結束了。”
他頓了頓,虛弱地咳了兩聲,眼神卻銳利如刀。
“但有些事,才剛剛開始。”
“你選吧。”
“是當一個保全了兒子前程的罪臣,還是當一個......絕後的烈士?”
宋文淵看著徐恪那張年輕卻仿佛能洞穿一切的臉,眼中第一次充滿了極致的恐懼。
他意識到,對方不僅掌握了他的罪證,看透了他的靠山,甚至連他埋藏在人性最深處的秘密,都挖得一清二楚。
他所有的驕傲、官威、城府,在這一刻,被擊得粉碎。
“噗通”一聲。
大周朝堂二品大員,戶部尚書宋文淵,雙膝一軟,從椅子上滑了下來,跪倒在地。
他伏在冰冷的桌沿上,老淚縱橫,哭得像個孩子。
“......我說。”
“我全說。”
......
深夜,紫宸殿。
女帝李青鸞隻披著一件玄色外衣,烏黑的長發如瀑般垂下,襯得那張絕美的臉龐愈發清冷。
她靜靜地看著桌上那本由懸鏡司呈上來的賬冊副本,鳳眸中閃過一絲滿意之色。
一名心腹老太監悄無聲息地滑了進來,在她耳邊低語了幾句。
“哦?”
女帝撚動書頁的手指微微一頓。
“賬冊的原件,他送去丞相府了?”
老太監連大氣都不敢出。
女帝沉默了許久,寢宮內安靜得能聽到燭火燃燒的“劈啪”聲。
忽然,她那清冷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長的冷笑。
“這隻惡犬,不僅學會了咬人,還學會了自己劃分獵場,甚至懂得用獵物去和別的狼群做交易了......”
“有意思。”
她的語氣裏沒有憤怒,反而是一種混雜著欣賞和警惕的複雜情緒。
她欣賞徐恪的能力,這正是她需要的;但她也警惕這種能力,已經開始超出“工具”的範疇。
她對身旁的老太監淡淡吩咐道:“告訴徐恪,讓他好生養病,朕的刀,要時刻保持鋒利。”
隨即,她又補充了一句。
“再告訴王德庸,讓他明早上朝,把頭抬高些,別讓朕覺得他老了,連路都走不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