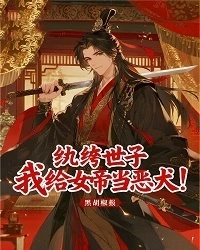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7章
女帝的鳳駕如同一片沉默的烏雲,悄然離去。
隨之而來的,是數名提著藥箱、神色肅穆的太醫,他們魚貫而入,整個懸鏡司後院瞬間被一股濃鬱而名貴的藥香所籠罩。
指揮權,第一次完全落在了北鎮撫司千戶趙恪的肩上。
他站在院中,聽著內室傳來太醫們壓低聲音的交談和銀針刺破皮肉的微響,又看了一眼天邊那抹即將被黎明吞噬的殘月,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
空氣中,還殘留著女帝離去時帶來的、那股令人心悸的龍涎香。
“所有人,點兵!”趙恪的聲音不再有絲毫猶豫,變得如鐵般堅硬,“目標,戶部尚書宋文淵府!”
“千戶大人,是否需要卑職帶一隊弟兄,先破門立威?”一名百戶摩拳擦掌,滿臉都是嗜血的興奮。
“破門?”趙恪瞥了他一眼,腦海中卻浮現出徐恪那張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的臉,和那雙仿佛能洞穿人心的眼睛。
他想起了那匪夷所思的“交叉審計”,想起了那駭人聽聞的“病榻驗屍”。
不,不能用老法子了。
指揮使大人的手段,是殺人,更是誅心。
“不。”趙恪緩緩搖頭,眼中閃過一絲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精光,“傳我命令,將尚書府圍起來,圍得一隻蒼蠅都飛不出去。”
他頓了頓,補充了一句讓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指令。
“但是,後門那條巷子,留出來。一個人也不要放,讓它看起來......像是我們疏忽了。”
眾緹騎麵麵相覷,滿腹疑竇,但看到趙恪那不容置疑的眼神,還是轟然應諾。
一時間,懸鏡司緹騎傾巢而出,無數道黑色的身影如鬼魅般融入京城的夜色,悄無聲息地將一座燈火通明的府邸,圍成了一座鐵打的囚籠。
戶部尚書府內,夜宴正酣。
宋文淵端坐主位,與幾位心腹同僚推杯換盞,談笑風生。
“諸位放心,周平那條線已經斷得幹幹淨淨。徐恪小兒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休想在天亮前找出半點證據。”宋文淵撚著酒杯,臉上是智珠在握的從容,“待天一亮,我等便聯名上奏,彈劾懸鏡司構陷朝臣,濫用酷刑。屆時,看陛下如何收場!”
“宋公高見!”
“我等附議!”
一片阿諛奉承聲中,宋文淵愜意地眯起了眼睛,仿佛已經看到了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黃口小兒在西市被千刀萬剮的場景。
他正欲將杯中美酒一飲而盡,府外,卻隱隱傳來了一陣不同尋常的騷動。
一名管家連滾帶爬地衝了進來,臉色煞白:“老......老爺!不好了!懸鏡司......懸鏡司的人把咱們府給圍了!”
“慌什麼!”宋文淵嗬斥一聲,強作鎮定地放下酒杯,“一群隻會動刀子的莽夫罷了。傳令下去,關閉府門,護院家丁各就各位!我倒要看看,沒有陛下的旨意,誰敢闖我二品大員的府邸!”
他篤定,懸鏡司不敢冒著與整個文官集團開戰的風險強攻。
他還有足夠的時間,銷毀那些真正致命的證據。
府邸外,趙恪站在暗影中,靜靜地看著那扇緊閉的朱漆大門。
“千戶大人,對方有防備,要強攻嗎?”
“不急。”趙恪擺了擺手,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讓他們燒,讓他們藏。給他們希望,再親手掐滅,那才有趣。”
他對著身後一名神射手低聲吩咐了幾句。
片刻後,一支利箭劃破夜空,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精準地落在了尚書府的庭院中央。
箭頭上沒有威脅的信函,隻有一個用油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
正在後院書房內,將一封封密信投入火盆的宋文淵,聽到庭院裏的驚呼聲,皺著眉走了出去。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支插在地上的箭。
解開油布,一股熟悉的、烤得焦香四溢的魚味,猛地鑽入他的鼻腔。
那是一條“銀鱗刀魚”。
魚身下,還壓著一張小小的紙條,上麵隻有八個用血寫成的大字。
“陛下問,魚,好吃嗎?”
宋文淵的瞳孔,在一瞬間縮成了針尖大小。
他隻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衝天靈蓋,渾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這一刻被凍結了。
他踉蹌著後退兩步,撞翻了身後的石桌,整個人癱軟在地。
完了。
對方不僅知道他殺了人,還知道得一清二楚!
這種被徹底看穿的恐懼,遠比千軍萬馬的衝擊,更能摧毀一個人的意誌。
就在宋文淵心理防線徹底崩塌的瞬間,府邸外,趙恪那被內力催動、清晰傳入每一個角落的聲音響了起來。
他喊的不是“投降不殺”,而是另一種更惡毒的誅心之言。
“指揮使大人有令:主動獻出宋文淵貪腐賬冊者,賞銀千兩,既往不咎!”
聲音頓了頓,陡然變得森寒。
“窩藏證據者,一律同罪!”
這番話,如同一顆投入蟻穴的火星,瞬間引爆了尚書府內部的混亂。
原本還算忠心耿耿的管家、師爺、賬房們,眼神瞬間就變了。
老爺......已經完了。
自己是跟著他一起死,還是拿了那千兩賞銀,換一條活路?
求生的本能和對金錢的渴望,讓他們在短短幾息之內,就從“守衛者”變成了互相猜忌、瘋狂尋覓的“尋寶者”。
“賬冊在我這裏!”
“胡說!老爺明明交給我保管了!”
小規模的騷亂和爭搶,很快在後院爆發。
最終,宋文淵那位最心腹的老管家,死死抱著一本厚厚的、用油布包裹的密賬,趁亂衝向了那條看起來無人看守的後門小巷。
他以為那是生路。
然而,當他一頭衝進巷子,看到的,卻是趙恪那張似笑非笑的臉,和數十名早已等候在此、手按刀柄的緹騎。
片刻之後,尚書府邸那扇緊閉的大門,緩緩打開。
失魂落魄的宋文淵,已經換上了一身嶄新的二品朝服,自己走了出來,仿佛不是去投降,而是去參加一場最後的朝會。
趙恪上前,沒有給他上鐐銬,隻是平靜地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宋大人,指揮使大人在懸鏡司的大牢裏為您備了茶。”
他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有些關於‘魚’的話,想和您聊聊。”
......
懸鏡司,內院病房。
一股精純的藥力在四肢百骸中化開,徐恪猛地咳嗽一聲,從死亡線上掙紮了回來。
他睜開眼,視線從模糊到清晰,看到的是床邊焦急等待的趙恪。
“人......抓到了嗎?”他的聲音沙啞得像是被砂紙磨過,“賬冊呢?”
趙恪臉上露出發自內心的敬佩,將整個抓捕過程一五一十地稟報了一遍。
聽到趙恪完美地複刻並執行了“心理戰”,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尚書府和關鍵賬冊,徐恪那張蒼白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絲虛弱的微笑。
他喘了口氣,隨即下達了第二道,也是更具政治智慧的命令。
“把賬冊......抄錄一份副本,立刻送進宮裏給陛下。”
“原件......”他眼中閃過一絲與他此刻病弱模樣完全不符的狡黠,“送到丞相府上。告訴他,我懸鏡司隻想查殺人案,對賬上的‘朋友’,沒興趣。”
他停頓了一下,補充道:“但這......取決於丞相的態度。”
......
深夜,當朝丞相王德庸的府邸,書房內燈火通明。
王德庸須發皆白,麵容清臒,正在燈下與自己對弈。
當聽聞宋文淵府邸被圍時,他隻是淡淡地落下一子,對身邊的門生說:“意料之中,垂死掙紮罷了。待天明,老夫自會在朝堂上,為文遠討個公道。”
他以為,這不過是女帝與懸鏡司的一次示威。
然而,當一名懸鏡司的密探,如鬼魅般出現在他的書房,將那本沉甸甸的賬冊原件,輕輕放在他的棋盤上,並原封不動地轉達了徐恪的話後。
王德庸那隻撚著白色棋子的手,第一次,停在了半空中。
他緩緩翻開賬冊,看著上麵一個個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和那一筆筆觸目驚心的銀錢往來,良久,一言不發。
最終,他將手中的棋子,緩緩放回了棋盒。
棋盤上,他那條眼看就要屠龍的大龍,因為這一子的撤回,瞬間變得死氣沉沉。
“告訴徐指揮使,”他抬起頭,聲音蒼老而疲憊,“老夫......知道了。”
“朝堂之上,不會有雜音。”
棄車,保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