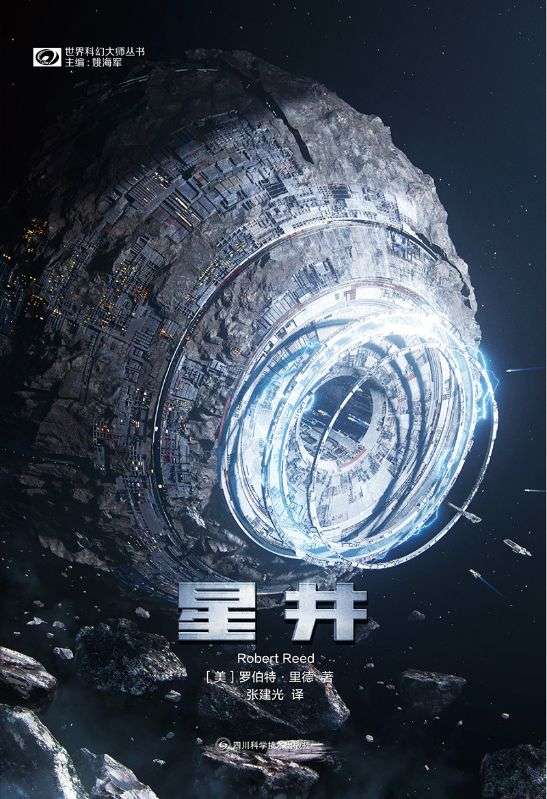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七
洛克一直是個寡言多思的男孩。作為兩個最雄心勃勃的船長誕下的唯一孩子,他遺傳了他們的外貌,綜合了他們高超的智力,卻沒有繼承領導他人的內在渴望。吃著髓星的堅果和烤昆蟲,他長成了一個中等個頭的青年男子,各個方麵都很健康,卻又顯著且永久性地不同於父母。他強壯且優雅,長著父親的眼睛,靈動、明亮,總是顯得十分專注。他的臉更像母親,也遺傳了她的自信。但他完全沒有控製任何組織或操縱任何事業的興趣,不管這些組織或事業有多了不起。經過長期觀察,母親斷定這並不是因為他缺乏這方麵的能力,基因的混合並沒有偷走任何天賦。他也不缺乏有關鼓動、宣傳技巧的教育。都不是。在包括他父母的他人看來,偉大、崇高的事業是抽象的,有時甚至讓人有些懷疑。但洛克卻很容易把這些事業當成縹緲、美好的王國,夢想與理論在其中交織,創造出無限複雜、矛盾的方程式。
作為一個青年,洛克愛上了違望者的信仰。他們的主要信條之一就是在遙遠的過去,當宇宙仍處於渺小和年幼之時,有建造師創造了巨艦,還有被稱為“荒涼”的勢力試圖偷走它。後來兩者都暫時死去。宇宙變成了不毛之地,不斷向外擴張,巨艦則在其中最深、最寒冷的地方遊蕩。然後,荒涼重生,他們找到了巨艦,將它據為己有。違望者聲稱人類就是荒涼。當然,如果你碰巧是個在髓星上孕育的人類,那你就變成了重生的建造師。你的任務、你唯一的使命,就是重新奪回巨艦,既為自己,也為了自己偉大的祖先。
作為這個崇高使命的追隨者,洛克成了違望者。但可怕的一刻降臨了,必須做出不可能的選擇:他的母親遇到致命危險,唯一能拯救她的方式就是殺死攻擊她的人。懷著巨大的悲傷,但完全沒有猶豫,洛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隨後他用母親的銀手表標記了他的埋葬地。後來,他努力讓自己看上去仍然是一個忠實的違望者。但洛克是個充滿負罪感的兒子,每當審視自己的信仰,他看到的都是缺陷和殘酷。隨後他找到了幫助母親的第二次機會,他不僅盡最大努力幫助她,還背叛了違望者。1
浣生就是他的母親。
戰爭結束後不久,有傳言說洛克將獲準加入船長的行列。浣生說過這話,亞斯林和其他一些髓星任務的幸存者也說過。但帕米爾明確地警告說,那個年輕人看上去仍然像個違望者,說話也像。好幾個世紀裏,他追隨他們那奇異的使命,無怨無悔。還有,一副為自己那個曾經叛逆的孩子說情,讓他取得不應有的地位,能給大船帶來什麼好處?
“你覺得他不配嗎?”浣生問道,聲音嚴厲,帶著些慍怒,“是的話,直接說出來。”
“我不是已經說了嗎。”帕米爾笑了。
但洛克自己終結了這個可能性。他聳了下肩,溫和地說:“母親,”那恍惚的目光看著遠處,他向她、也向自己坦白道,“我缺乏成為船長的必要技能。更重要的是,我也沒有這個願望。”
浣生很難過。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他的誠實打動了她,她也終於放下了望子成龍的重擔。她輕聲問洛克:“你有什麼願望?”
他又聳了下肩,溫和地說:“我還算聰明,在一些小問題上,我有很深的見解。還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很奇特。另外,我剛剛拋棄了我一生之中唯一的信仰體係,頭腦脫離了一切束縛,同時一片空白。”
這樣的失去是什麼感覺?喪失了使命感和立身之所——浣生無法想象。
但洛克卻覺得幸運。
“我一片空白,”他重複道,“沒有方向,沒有指引。我的靈魂急需找到新的信仰。希望這一次能找到真正值得信仰的東西。無論我朝哪裏看,我都能隱隱約約看到某種偉大和真實的東西。”
“什麼東西?”
帶著輕鬆自如的神態,他說:“我有個觀點,母親。”接著,他用極其平實的語言,平靜地詢問:建造師們是否隻建造了這艘船;或者,他們還製造了整個宇宙,巨艦隻是其中的一個小秘密,它外麵還有數之不盡的一層層船殼,一層層包裹著它。
大船的使命與意義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人們製造、培養了一組人工智能,不管別的,專門思考這個問題。經過近一千個世紀的苦苦思索之後,它們沒有得出任何實實在在的結論。但洛克的小觀點令它們很感興趣。違望者和他們的神話也同樣令它們著迷。最後,該怎麼做已經是明擺著的事了。機器和這兩個人得出了同一個必然的結論。“加入它們,”浣生敦促自己的兒子,“學習必要的物理學、宇宙學和高等數學知識。可能的時候幫助它們,要是你喜歡的話,也可以獨自工作。”
“我現在正在這麼做,”洛克露出淺淺的、略帶疲倦的笑容,“大多數時候都在學習,自己做研究。”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浣生急切地問。
“從我們俯視髓星的那一天。”
通往髓星的通道被新生的超異纖維封閉之前,他們最後一次去了大船的核心。
“我沒注意到,”浣生坦承,“我為什麼沒注意到?”
“你太忙了,母親。”
確實。
“你總是在忙別的。”他指出。
“還總是很累。”她又加了一句,“但是,說真的,我們必須經常交談,把它當成一件大事。從現在開始!”
但一副終究是一個異常忙碌的職位,即使在輕鬆的日子裏。戰爭雖然結束了,但仍有大量的維修工作要做。他們還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民間憂慮和經濟上的障礙。必須安撫和教育數目龐大的乘客,必要時轉移他們的注意力。還要重新訓練和鼓舞士氣低落、狐疑不定的船員,關注全新構成的船長這個團體——新船長們需要學習各自的崗位職責,這些事情沒有哪個學校可以教會他們,更別提教成熟練工了。在這一切之上,是為墨水井做好準備。這個需求始終存在,下一段航程就會麵對它了。作為一個障礙物,寒冷的星雲會帶來無休無止的麻煩。塵埃和斷斷續續出現的彗星會考驗飛船的防護罩和激光。即便最安全的航線也會讓他們的防禦係統防不勝防。船殼將再次遭到打擊,讓它坑坑窪窪,變得難看,變得虛弱。這就是浣生堅持開展維護的原因,盡管所有係統都已經修複完畢。在她的命令下,建造、安裝了新的激光,加強了防護罩,大型望遠鏡陣列每時每刻都在掃描墨水井的深處。然而,即使他們能戰勝大自然的殘酷——沒有頭腦的冰、岩石和偶爾的遊蕩行星——仍有一個簡單的、無法逃避的問題:究竟是誰,或是什麼東西,生活在那片寒冷的黑色物質裏?他們想從大船上得到什麼,假如他們想的話?
浣生被工作淹沒了。在大批紐聯器的幫助下,她製訂宏大的計劃,精心安排長期項目,盡量讓兩者相互配合。為了保持頭腦清醒,她也睡覺,但隻是在碎片時間,而且隻是當帕米爾或亞斯林能夠接手工作的時候。看兒子是難得的事。很長一段時間,她認為兩人長期不見麵的原因是她的工作太忙,以及她不夠自律。但她還能怎麼辦呢?與洛克輕輕鬆鬆吃頓晚飯,意味著她隻能換個時間研究打開大船引擎的問題,意味著推遲兩場與工蟻人和雷莫拉人的會議,意味著必須推遲安慰某個居民物種的演講、推到一個不那麼合適的時間,或者她必須又一次放棄睡眠,比預期更多地消耗自己。和洛克說說話真是太難了。有時,她好幾年也見不上他一次。是的,他們會交換信息和全息,通常每周一次。但沒有哪項技術能夠媲美輕鬆晚餐的親密與高效。總算能一起吃頓飯時——通常是在間隔很久之後——整個晚上都在努力重拾上次中斷的話題。
如果他們是在她的住處見麵,食物的風格總是簡單而精致,很可能是附近社區的禮物。不管它的製作者是人類還是其他物種,都是浣生熟悉的風味。如果在洛克的住處,他們就會吃烤錘翅鳥、甜岩漿堅果和其他髓星出產的珍品。這些都是未遂的征服者帶上大船的樣本,再經她的兒子培育。他在一個私人洞穴內——幾千米長,寬度幾乎跟長度一樣——製造了一個微型但逼真的髓星模型,有四處飛濺的熔化鐵水,漸漸變暗的天色。他的食物和這裏的天空讓他看著像是個違望者:煙灰色的皮膚,眼睛裏流露出一絲饑餓的神色。不過,至少在母親麵前,他穿得像個守法的乘客,簡單的褲子加薄外套。隻要有可能,浣生會將她的製服留在別的地方,穿著打扮配合他的休閑口味——這位忙碌且熟練的管理者就是這麼關注細節。
她常常談論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中最大的問題,談得未免太多了些。
當洛克目光遊離到遠處、看著肥胖的錘翅鳥在人造天空下翱翔時,她會停下,即便她的話才說到一半。隨後,她會帶著真摯的歉意說一聲,“對不起。”
剛開始,洛克會點頭,說“沒關係”。
然後浣生會堅持,“我想聽聽你的工作。你在做什麼?”
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繁文縟節之後,兒子決定直接跳過她的道歉以及之後的老套。浣生在回憶一個她本人以為相當有趣的故事,可能跟一個奇怪的物種有關,她如何處理與他們相關的緊急事件……她說到一半時,洛克會脫口而出,“我的工作還算順利。”
這是他的信號,又過了幾十年後,浣生不再感覺受了冒犯,或是覺得尷尬。
“我仍然在學習科學和數學。”她的兒子會解釋。他在髓星接受過完整的教育,但那是艱難的時光。在髓星上,孩子對宇宙的廣袤沒有清晰的認識。“我還有很多要學的地方,”他接著說,“學完了也隻能到人工智能天生就懂的程度。至於做有意義的工作……怎麼說呢,可能永遠都實現不了。誰知道呢?”
“但你已經學到了很多。”她會提醒他。
洛克會點點頭,和氣地笑一笑,為自己的學業受到承認而高興。隨後他可能會告訴母親一個冗長、曲折的故事,關於六個關鍵的大一統理論之一的某個奇特之處。日常應用中其實隻有一個理論。它的應用範圍很廣,也很簡潔。它似乎能解釋宇宙的一切,從無限小之中誕生,到無盡的擴張,從相對寧靜的現在,到不斷積聚的黑暗、嚴寒和最終無法避免的死亡。隻有某些特殊領域的專家才會執著於其中的不協調之處:超宇宙的基本特征是什麼?時間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平行宇宙真的存在,還是隻是為了數學上的便利?在這個連續體內的某處是否存在能被稱為“靈魂”的東西?
出於簡便,這些更具體的、通常相互矛盾的理論被打包成了六個同等的類別。
作為工程師的女兒,後來又受訓成為艦上的一名船長,浣生受到的教育說這六種理論都是有效的,也都不夠全麵。沒有方法能對它們做個一對一的測試,至少在這個宇宙內不行。但它們那複雜艱深的數學演算總是會得出同一個結論,即浣生們旅行於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中——也就是所有偉大的方程式演算之後得到的現實。對於船長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判斷乘客相信這六種之中的哪一種。每一種都有自己的魅力和誘惑,也有不協調之處。大多數物種會擁抱隨便哪種可以讓他們睡得更踏實、活得更舒服的理論,或是能以最低程度的抱怨接受自己的存在。通過他們的信仰,可以窺視他們的本性。有時,當洛克提起其中某個理論時,她會隨口說上一句,“嘎魯人也不相信時間”,或是用嚴肅的口吻警告洛克,“哈魯薩魯討厭平行宇宙的說法。隻有一個現實,而且他們理所當然地居於它的正中央。”
洛克會耐心地點點頭,可能會露出一絲笑容。他並不特別關心哪個物種的審美,包括他自己的。他向往的是坐在一個高處,不帶任何傾向地看著風景,看到所有等待著被看的一切。
離違望者戰爭已經過去百年的某次午餐中,他開始描述一種新的數學。剛開始,浣生仔細地聽了,自信理解了它的核心。但在他的大段獨白進行到某個點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完全無法理解進入耳膜的聲音。和往常一樣,洛克在講述之前給了她文件——他自己記的說明和示意圖——便於她查看。她一頭紮入這些文件,隨後又抬起頭,像快淹死的人從深不見底的冰洋探出頭來似的竭力喘息著。
“你在說什麼?”她脫口問道。
但她兒子已經不說了,可能在幾分鐘之前就停止了。
“我一點兒都不懂。”她向他坦白,同時也像抱怨。隨後,她自嘲地笑了一聲,說道:“扔個救生圈過來,親愛的。”
“救生圈?”這個比喻對他沒有意義。
終於,她的頭腦裏蹦出了一個古老模糊的記憶,道:“等一下,”沒等兒子進一步解釋,“我想起來了。”
“什麼?”
“我母親,還有幾個老師……他們有時會提起……什麼來著……?”她閉上黑色的眼睛,苦苦回憶,“大統一場的第個理論。非常奇怪、非常簡單……沒人相信過它……”
洛克微微聳了聳肩,點了下頭,以示回應。
“我對第七種理論一點兒都不懂。”她再次請求幫助。
但洛克隻是聳了聳肩,坦承道:“我知道的並不比你多。”沉默許久之後,他又補充了幾句,“它是一係列討厭的等式。真的,甚至人工智能——我的老師加同事——他們也討厭第七種理論,討厭它的各個方麵。它太醜了,太別扭了。要不是它有其神秘之處,我懷疑他們根本不會看它第二眼。”
三十年之後,在又一次午餐中間,浣生再次問道:“課上得怎麼樣了?”
他笑得很燦爛,有點兒奇怪。
笑完後,他聳了聳肩膀說:“我現在取得了一些成就。沒什麼了不起的。但至少我搭建了一個框架,為我一百萬年後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他是認真的。說起如此漫長的時間時,他的口吻異常寧靜,令人敬畏。他幾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時間跨度的可怕。懷著隻有狂熱者和瘋子才有的獻身精神,他露出一個深邃、純粹和歡欣的笑容,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終於,浣生問道:“你在做什麼工作?”
“一點兒小事。”他說道。
她等待著。
“我製作了一張清單。”他說。有那麼多可用的材料,他卻選擇了銅蠅那巨大的翅膀。許久之前,當船長們困在髓星上時,他們最早就是用這種材料來充當羊皮紙。“一張小清單。”
“好的。”她隨口附和了一句。
他沿著天然的褶邊打開翅膀,還將它微微卷起,隻有他的眼睛能看到他寫的字。
“什麼樣的清單?”她問道。
“都是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他回答道。
“例如?”
“顯而易見的問題。”他重複了一句。他長著和他父親一樣靈動的雙眼,但他的沉默卻令浣生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每隔幾年,浣生就會意識到洛克和他的外祖母是同一類人。區別隻在於,那位老太太畢生都在從事工程師的工作:要求精確、總在趕進度。還有,工程師永遠在已知領域內工作。
“顯而易見的什麼?”她追問道。
“我相信你也問過這些問題。我敢說至少不下幾千次。”
“給我看看。”
他考慮了一下這個請求,隨後卻開始把堅硬的紅色翅膀重新疊起來。“還沒到時候。”
“就看一眼,行嗎?”
他搖了搖頭,把翅膀收進看不到的地方。
“可以嗎?”她不想放棄,“我想看看你到底問了什麼。”
但兒子是由更加固執的材料組成的。他微微搖了搖頭,重複道:“你自己也問過這些問題。但要是你沒問過……那樣的話,母親,就算現在讓你看了也沒什麼用……”
1 以上情節出自《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