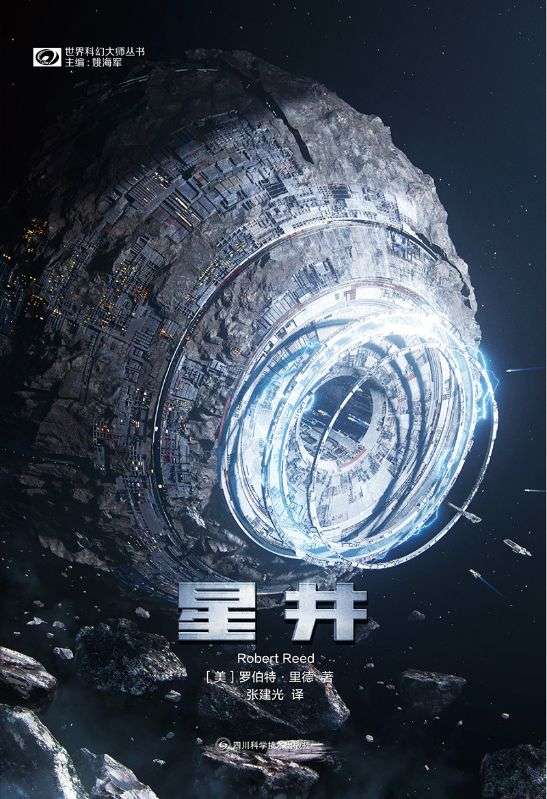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二
地球人類起源於脆弱的猿猴,但早在千萬年前,他們就用人造基因和生物陶瓷大腦填充了自己的身體,創造出了比任何岩石的裸露表麵都更加持久的生命。這座玄武岩的山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統治開始的第一天,首領船長和她的高階官員就在這個地方會麵。在她的任期內,海岸線的侵蝕情形清晰可見:原先的黑色巨石已經被風化成礫石,被亙古不變的海浪悄悄吞沒。開始時那座傲人的高山今天已顯得十分普通,首領船長本人亦是如此。乍一看,她似乎和眾人期待的形象一樣:身形高大,威嚴,麵色冷峻。但在違望者之戰中,她的敵人重創了她。她的身體最近剛完成再生,在頭顱陷於昏睡的狀態中再造了金色的肌膚、強健的骨骼。新鑄的網絡紐聯器植入體內,她的身體因此而拓展,其意識能與最偏遠的係統及傳感器互聯相通。從嚴格意義上說,她仍是之前的那個她。然而,盡管她於千鈞一發之間脫險——的確,她能活著已經是個奇跡了——她還是變了。甚至可以說轉化了。她坐在傳統的黑色椅子上,椅背很高,塗了厚厚的漆,由一整根卡蘭柚木雕刻而成。然而,除了表麵的權威和自信,眼前的這位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從寂滅的邊緣重建,再造重生的過程中曆經上千種改變。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副首領都是新近提升的,許多人甚至連船長都是剛剛升任不久。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人類,這是事實,但並非全部。居然有了非人類的副首領,這種事從前誰能想到?一對暴脾氣的哈魯薩魯大大咧咧地坐在石頭上,一位穿著注水保護服的鰓人一本正經地站著,一個小個子工蟻人正和一個雌雄同體的雙麵人熱切地談論著戰爭。這些有機生命的行列中還夾雜著三名非有機體,它們是人工智能團體的代表,藏身於人造麵龐和人形身體裏。外星人和機器如今也穿上了船長專屬的鏡麵製服,佩戴著象征最高頭銜的肩章。這是他們幫助打敗違望者之後獲得的榮譽。但比他們外表更奇特的是他們的情緒。在過去的會議上,首領會定下基調和討論內容的核心。她的命令通常在之前就下達了,坐在這裏的山頂上隻是一次優雅的表演,一種雄心、驕傲與傳統的展示。然而,在今天明亮溫暖的光線之下,重生的首領卻顯得沒那麼自信。手下的官員自顧自地交談,很多時候用的還是非人類的語言,而她緊緊地握著兩隻大手,新生的臉龐幾乎變得透明,空洞的目光注視著遠方。她用勉強能蓋過海浪的聲音問道——聲音裏有明顯的緊張,也沒對著任何人——“我排名前兩位的副手在哪裏?”
“快到了,”一個新的副首領回答道,“浣生好像走錯路了。”
說話的人是一個名叫康拉德的雷莫拉人。說實話,幾乎算不上人類。雷莫拉人生活在大船的外殼上,身體永久地密封在超異纖維織就的防護服內。由於暴露在真空及射線之中,他們一直在變異,患著各種奇怪的癌症。但雷莫拉人不僅接受了這種傷害,還利用了它。每一次癌變都是一次再造,充滿了潛力和可能性。對一個真正的雷莫拉人來說,身體隻是意識的容器,理當不斷重塑,就像一塊完美的畫布,正該在上麵任意揮灑,塗抹出各種各樣的精彩。1
康拉德的獨眼看著像人類眼睛,隻是長在一根肌肉發達的眼柄上,能夠四周轉動。他對同伴們擠了擠眼,開玩笑道:“這可不是好兆頭,連一副都迷路了。”
首領瞪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
“要不,”有個人工智能拉長聲音道,“別等他們了?”
金色的女人搖了搖巨大的腦袋。考慮到自己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她不得不開口說話:“不行。我們要等。我們必須等。”
一切都跟過去不一樣了。
一切。
這兩位尚未出現的船長正走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信步朝黑色岩石的方向走去。帕米爾的笑容流露出少有的好心情。他朝執勤的安全部隊點了點頭,帶著假模假式的笑臉,問道:“你能猜一下嗎?假如我們走進這個城市裏的每一所房子,會找到多少個逃兵?”
浣生沒有搭話,心裏想著其他事情。
“十到十個不中用的家夥。”帕米爾主動給出答案,然後真正笑出聲來,補充了一句,“消失一直挺簡單的。”
“我們要把它變難嗎?”她問。
帕米爾在逃亡方麵經驗豐富。他在船上的很長一部分時間都在躲藏,以不同的方式躲藏。隻是因為大赦,才讓他從自我放逐中走了出來。給他機會的話,他會第一個承認,自己升任二副的概率其實遠遠低於在浣生兒時的廚房裏發現一個醉醺醺的、不起眼的罪犯。
“應該把消失變得更難。”他表示讚同,又笑著補充了一句,“隻是為了剔除業餘選手。”
走上山頂之時,他們仍在笑。首領依然保持著坐姿,其他高階官員則站著。浣生笑了笑,敷衍地點點頭,說道:“長官好。大家好。抱歉遲到了。可以開始了嗎?”
首領一臉冷峻的沉默。
事實上,浣生是故意遲到的。僅僅通過這一次遲到,她就能向同事展示新的秩序。首領無權指責她的拖拉。浣生和帕米爾拯救了她的生命和權威。她之所以還能統治,隻是因為他們允許她那張金色的圓臉——那張大家十分熟悉的臉——繼續代表巨艦講話。
“歡迎。”那張臉說道。
人類點頭示意,所有人都重複了這個詞,“歡迎。”
浣生和帕米爾先後坐上最後空著的兩張椅子,分別位於首領船長的兩側。
“我們先從彙報開始,”金色臉龐接著說道,“康拉德,請吧。”
這個雷莫拉人的新肩章釘在他的超異纖維肩膀上。眼柄之上的獨眼透過鑽石麵罩逐一打量每一位和他一樣剛獲得晉升的同事。隨後,用一張十分靈巧的大嘴,他描述了大船外殼的狀況。“情況糟透了,”他通報道,“激光和防護罩失效後,我們遭到了沉重打擊。我們還要修補幾個非常大的撞擊坑。防護罩和激光的能量才恢複了不到一半。還有,由於望遠鏡和其他傳感器被撞成了碎片,我們幾乎是在蒙著眼飛行。需要好幾年時間才能修複我們的眼睛,再加上幾十年時間才能補好撞擊坑。這還不包括那個巨型撞擊坑,修複它需要整整一百年的辛勤勞作。”
戰爭打到最激烈的時候,防護罩和激光突然間失效。一顆大彗星撞上了大船,速度達到了光速的三分之一,讓冰塊、瀝青和碎石形成了一個熾熱的等離子氣體球。船體遭受的巨大衝擊,超過了超異纖維所能承受的極限,它的一部分被迫熔化,形成一個臨時湖泊,向外掀起一千米高的巨浪。
“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真正的爛攤子。”康拉德道,“彗星砸在一個舊傷疤上,那正好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傷疤。大概五十億年前,一個月球大小的家夥撞在那地方。當然,你們也知道測量超異纖維的種種特征有多困難。要考慮它的年齡,或者它是什麼時候受損的,等等。總之,我的祖先以盡可能快的速度修補了那個舊傷疤,用的是最高等級的超異纖維……但我們的運氣實在太糟了,這次新撞擊讓舊傷複發……”
“有船體破裂的風險嗎?”首領問道。
“假如有一個柯伊伯級的天體以最壞的角度高速撞擊,是的。這種可能性很小,但後果嚴重。船體可能會被打穿一個洞。”
但這種風險概率極小。通過紐聯器,康拉德提供了整份報告,給大家留了一些時間來消化他粗略的估計和手繪的示意圖。出乎大家意料,圖還畫得挺漂亮。跟它古老的前輩相比,新的撞擊坑就像個小小的指環。但它與中央撞擊區剛好重疊,裂縫一直深入船體深處,讓那個由更古老、更遙遠的撞擊造成的弱點更加脆弱。
“當然,我們可以加快進度,”康拉德保證道,“但雷莫拉人的人手不夠。”他提醒大家,戰爭損耗了大量人口——好像有人已經忘了似的,“需要好幾千年時間和大量嬰兒才能恢複之前的人口分布。至於最近幾天發生的事,更是需要幾百萬年的時間,才能把它們拋到腦後。”
首領保持著沉默。盡管對他的語氣感到不滿,但首領沒有說出口。
浣生扭頭看著另一位新晉的副首領。“亞斯林,”她說道,“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亞斯林負責整個工程師隊伍。她是前往髓星的船長之一,而且和有些人不同,她仍舊忠於大船。她站起身,向人類露出一個溫暖的微笑,給哈魯薩魯一個凝視(哈魯薩魯喜歡這樣),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她解釋了向幾十億乘客與船員提供能源的引擎和反應堆的狀態如何低下。然後,她真心誠意地提醒大家,“別忘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奇跡之中,一個在設計與製造方麵都堪稱天才的作品。不管大船的建造者是什麼人,他們在創造這部機器時都預見到了它一定會經曆維修和翻新,必要時還會加以改造。我可以在八個月內讓所有反應堆恢複到滿額功率,十八個月內修複所有的引擎。然後我的工程師就可以去幫雷莫拉人。”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雷莫拉人不接受外人的幫助。大船外殼是他們的領地和責任,也是他們唯一的家。所以,康拉德竟然嘟囔了一句“歡迎任何好手加入”,讓大家不免吃了一驚。
船殼的毀壞到底有多嚴重?
沉默之中,其他副首領焦慮起來,開始重新審視報告。小小的工蟻人舉著尾巴,興奮地說:“我的物種也能幫忙。隨時可以開始。”
獨眼先是閉上,隨後又睜開。
“歡迎,”雷莫拉人說道,“謝謝。”
幾天前,浣生與總工程師、康拉德還有工蟻人單獨見了麵。剛才那一刻就是先前那次溝通會的成果。船殼已被削弱,不管今天做出什麼決定,未來幾十年內都會維持這種狀態。但船體不是關鍵。浣生的計劃是在這些差異巨大的物種之間打造合作精神,並讓他們服從於她個人的權威。她必須在尊重他們傳統習俗的同時達成這兩個願望。
現場的情緒有了些改善,盡管隻改善了一點兒。
浣生讚賞地點了點頭之後,請首領再次講話。
“安全部隊,”重生的女人說道,“我想聽聽你們的彙報。”
占據這個關鍵位置的是一個哈魯薩魯,名叫奧斯米姆。這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型兩足生物慵懶地坐在一塊崎嶇的灰黑色岩石上。通過呼吸嘴,他大聲描繪了仍在進行中的對殘敵的掃蕩,還報告了如何重新建立值得信賴的安全部隊。講述中間他停頓了一會兒,他從腳趾很長的腳上的一隻皮口袋裏掏出一個形狀奇特的淡金色幹果,送進他的進食嘴。然後,他用低沉沙啞的嗓音宣布:“我希望繼續保留禁止新乘客上船的禁令。我還希望當局能通過必要的措施,給我足夠的權限。”
這個種族竟然坐進了這個小圈子,最讓首領反感的莫過於此。哈魯薩魯是個難以打交道的物種,有暴力傾向,像小孩子一樣易怒。沒錯,他們在拯救大船上有功。但他們太暴力,太容易發火,簡直就是人類身上最糟糕元素的綜合體。在她看來,幾乎所有物種都比哈魯薩魯強,就連人工智能都不例外——她完全可以接受它們進入船長的序列。但是,新任安全首領要求更多權限的話卻讓首領暗暗讚賞。這才是真正的紐帶。她和這個異種都明白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隻要宇宙存在,權力都是第一位的。
“但現在根本不會再有新乘客。”另一個哈魯薩魯直截了當地反駁她的同伴,“我們偏離了航線。大船上發生了內亂,受到了嚴重傷害,而且再過幾千年,我們可能會徹底離開銀河係。哪個乘客願意冒這種風險,除非他是個傻子。”
“同意。”首領說道。
浣生沒有說話。
首領差點兒看向她的一副,隨即卻肉眼可見地抑製住肩膀肌肉的扭動,接著說了下去:“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該放鬆對外移民的控製。假如有乘客想離開,隻要我們和他沒有財務方麵的分歧,一兩次例外也是可以的。”
帕米爾往前探出身子。
“長官。”他說道,簡單的一個詞,卻流露出不同尋常的尊重。他緊接著解釋道,“昨天,我對乘客和船員做了一次普查,用了多種方法,我清點了每一個人。大船上現在總共有一千多億個生命。也可能遠大於一千億,取決於你對自主意識的定義。”他的大腦袋點了點,擠了擠眼睛,“普查之後,我還對這些意識做了一番測算,想搞清這些意識的總體情緒——”
“怎麼測的?”首領問道。
“隻能測個大概,”他承認道,“我在三個不同的物種之中開展了三種不同的調查。我記錄了顧客對各類逃跑遊戲和心理藥物的喜好程度,還有交配室的流量。更重要的是,我直接征詢了意見。我製作了一個我本人的全息,在一個小時內采訪了將近一百萬個居民。上述所有研究都得出同樣一個醜陋的結論:我們這兒有一大批驚恐的、憤怒的家夥。一千億居民中的大多數都希望能在明天下船。或是今天。老實講,他們更希望幾年前就已經離開了……在髓星或是該死的違望者出現之前。”
現場出現了短暫凝重的停頓。
隨後,一個人工智能開口提醒大家:“但我們缺乏星艦。”藏在人造麵孔後麵的是一個極其微小的自主意識—— 一個基於量子計算機的思維,比指甲蓋還小。這張麵孔給出了現存星艦的確切數目,以及它們十分有限的容量。所有大船乘客中,機器生命是最微小的,但即使是它們,即使將它們像沒有意識的沙子一樣堆在一起,也沒有足夠的位置讓它們安全離開。
“謝謝,”首領打斷道,“知道了,救生艇數目不夠。我們知道這個嚴峻的事實,謝謝。”
它說錯什麼了嗎?沒有,它的話裏沒有事實錯誤。其他副首領也沒有提出進一步的意見。人工智能聳了聳假肩膀,生氣地噘起了嘴,表現得未免過於像人類了。
“有些人已經逃走了,”帕米爾接過話頭,“在戰爭爆發後、我們衝向那顆古老的恒星的時候。當時看來,大船好像會撞上那個黑洞,於是引發了小規模的逃離風潮。根據我的統計,我們少了兩艘高速飛船和十三艘慢速交通艇,差不多能裝載五萬名乘客。還要再加上一萬一,或者一萬二三個乘救生囊逃生的。”救生囊是從船殼上發射的超異纖維口袋,隻配備了報警信號和最低級的循環係統,乘客所能依靠的隻有發射時的初始軌道,以及他人的憐憫。“救生囊裏的那些膽小鬼都完蛋了,”帕米爾彙報,“我們正在穿越的是太空中的空曠區域。空曠是指友好港口數目稀少。如果他們趕在我們改變航線之前逃走,可能還會沒事。按照原來的航線,再過一百年左右,我們就會進入一個行星稠密區域。但這些混蛋中的大多數是在我們改變航線之後才離開的,飛行軌道隻稍稍偏離大船的現行軌道。也就是錯誤的軌道。”高速飛船可以轉動矢量噴口,改變航向;隻要有足夠的耐心,慢速交通艇最終也能抵達合適的區域。“在它們可能的航向扇麵上,恒星的數目不會超過五十個,”他繼續道,“多數是M級矮星。已知隻有六個世界存在技術級別的生命,四個經過地球化改造,兩個自然形成。或許,它們中有幾個有能力伸出援手,抓住幾個救生囊。隻是或許。但是,想讓它們從整體經濟中劃出一大塊資源來救援一群烏七八糟的難民……這麼說吧,我知道世界上有運氣和善良這種事,但顯然不夠這群混蛋用的。”
帕米爾停頓了一會兒,從椅子上向前探出身子。椅子後腿離開裸露的岩石,結實的木頭吱嘎作響。他的語氣平緩,其中卻飽含焦慮,“我們需要所有剩下的星艦。正如我的同事提醒的那樣,我們港口的泊位上一共才停了一萬七千多艘。一旦條件成熟,我們應該生產更多飛船。更快、更大、更好的飛船,隻要情況允許。還有,我們不能批準任何人離開,一個都不行——除非我們能確保飛船還能飛回來。最好還能帶來重要的貨物。”那張長相平凡的臉提醒大家,“我們剛繞著紅巨星和黑洞完成了一個八十度急轉彎,正在飛往未知的區域。一個我們從沒關注過的區域。假如我們無法或者不願返回舊航線,不太多的幾個世紀之後,我們就會進入星係間的太空。恒星會變得稀少,偶爾才能碰到有生命存在的行星,更別提有什麼能幫助我們的文明了。”他眯起眼睛,射出巫師般攝人心魄的目光,“別問我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有這種感受,這種直覺——”
“——覺得我們需要所有的星艦。”首領替他說完。
“對,”帕米爾答道,“但星艦之外,我想得更多的是乘客。有些乘客,或是所有乘客——在這場亂子結束之前,我們會發現,擁有這麼多的乘客是我們的幸運。”
每一位副首領都有權發表意見,他們中的大多數也確實發表了。投票開始,三位最高指揮官做出了最終的決定。當所有的議題都結束時,天已經快黑了。人造太陽落在遠處的海平麵上,夜鳥開始飛翔。大船的規定中新添了兩個重要決定:第一是幾乎全麵禁止對外移民,第二是征用所有適合於長途航行的私人飛船。對於習慣長時間一成不變的機構而言,這是異常繁忙的一天。雙麵人同時用雌雄兩張臉看了看太陽,問道:“接下來呢?飛過這幾個太陽之後,等在前麵的是什麼?”
答案很顯然。副首領、船長、甚至大批乘客都知道大船的航線前方是什麼。但雙麵人問的是更高層麵、更深刻的問題。“接下來呢?”是時候為未來考慮了,“等在前麵的是什麼?”這是一個請求,希望能有人來描述那無法避免的命運。
浣生開啟了她的一個紐聯器,隨即眾人麵前出現了一張星圖。巨艦是穿行於幾個小恒星之中的一個特別標記出的小點。恒星和它們的行星都顯示在圖上,恒星間的太空和偶爾的初生黑洞也標上了導航標簽。這一片星河不大,厚度隻有七十光年。過了那些恒星之後,能看到一大片平滑的、廣袤的、黝黑的星雲表麵。星雲由寒冷的氣體和惰性塵埃組成,夾雜著冰塊和幾個可能已燃燒至半途的太陽。在違望者出現之前,大船偶爾派出的勘察隊已經窺視過那個深邃永恒的黑暗,找到了奇怪的熱源和微弱的無線電聲音——標誌著高等技術正在蓬勃發展。
浣生沒有提醒大家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使大船今晚就點燃尚能工作的引擎,接下來的兩百年間,他們的航程也不會發生實質上的改變。他們會在過於遙遠的距離經過每一個恒星,無法形成有用的彈弓效應,最終會飛到星雲麵前。因為燃料即將耗盡,他們別無選擇,隻能鑽進黑色的塵埃與晦暗的氣體之中。他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吝嗇地利用他們的氫氣海洋,抓緊時間維修防護罩和激光,尤其重要的是始終做好計劃,然後做更多的計劃,最後再放棄所有這些聰明的備用方案,激發出新的想法,趕走那些流於表麵的、無用的點子。
但浣生什麼也沒說。
很長一段時間內,她都沒有開口,而是站起了身。一位令人欣賞的女人,優雅的外表下麵充滿力量;一位穿著完美無瑕的鏡麵製服的船長,這身製服似乎是為她一個人量身定做,而不是為了別人。她眺望著開闊的水麵,回想起孩提時代在這個小小海灘上度過的歡樂時光。一些隱約的、已然淡忘的記憶纏繞著她。這是她今天第二次想起了父母。三個人坐在一起,說著話。說的什麼呢?她還是想不起話題,可能永遠都記不起來了。算了吧,她對自己說。隨後,保持著表情、站姿和智慧的沉默,她依次看著自己的同伴。她發自內心地喜愛這些人。帶著微笑,她開口了:“發生什麼,就是什麼。”
她停下了,和開始時一樣突然。
就連異種和思維敏捷的機器都感到好奇,耐心地等待著她再次開口,或是改用肢體語言表達。
“發生什麼,就是什麼。”她重複了一遍。隨後,她點了點頭,道:“我想,未來將是綿延不盡的奇遇。但願是驚喜吧。”
聽眾中泛起讚同的漣漪。
每一個坐著的人都準備站起。
除了首領船長。她依舊牢牢地坐在椅子上,金色的臉孔迅速打量她的新任副首領們。雖然隻是名義上的領袖,她還是保持著相當的威嚴。帶著一絲過去那個她的精氣神,她清了清嗓子,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我能提個建議嗎?”她說道。
浣生立即轉身看向她,“當然,長官。”
首領走下黑色的椅子,兩條腿分立,穩住身形。“我們每個人都要想象十種不同的未來。”她提議道,她的身材甚至讓哈魯薩魯都顯得矮小,“十種可能的、可怕的未來。精確地描述它們,徹底地模擬它們。然後,我們將交換彼此想象出來的未來,作為訓練。在下次首領宴會之前,我們中的每個人都要拯救大船十次。”
讚許地點了下頭之後,浣生說道:“是,長官。”
“隻是作為訓練,”古老的女人重複道,“大家不必想太多。”
“當然。”
隨後,以一種已經消失了不知多少年的魅力,首領承認道:“我知道我現在是什麼。完全清楚,我明白我的新角色。盡管我不喜歡,但這是我應得的。”看不出滄桑的臉笑了一下,悲傷混合著幾乎是孩子氣的放棄,“但是,如果你允許的話,浣生,能否賜予我這個小小的榮譽,由我來宣布本次會議結束……可以嗎?”
1 關於雷莫拉人的故事,請參閱《科幻世界》(譯文版)2022年第五期《雷莫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