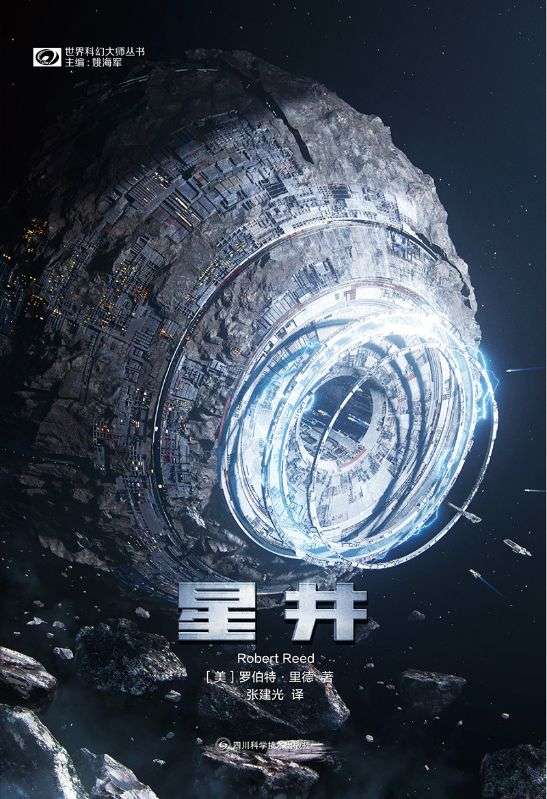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一
“這個聖地在哪兒?”帕米爾問道。
兩人剛從輛沒有標誌的密封車上下來。浣生略微怔了一下,在人造太陽的強光下眯起明亮的黑眼睛。“在那邊的石頭上。”她朝一塊長長的、伸進藍色大海中的玄武岩示意了一下。她是個身材修長、舉止優雅的女人,很可愛,喜歡笑,但笑容隱藏不住她內心的自傲,“椅子在等著我們。”
“我能看到椅子,但我問的不是這個。”
“那你在問什麼?”
“你原來的家。”帕米爾解釋道,低沉沙啞的嗓音裏透著不耐煩,“你談起過幾千次。在這裏,我們走著就能到。既然還有時間,不如你給我看看你小時候的家?”
為什麼不呢?浣生想。
然而,緊接著,她卻顯得有些無措。上一次去那地方是幾個世紀之前的事了。在她離開期間,城市已經改變了模樣。所有街道都換了位置或是重新鋪過,兩旁的房子要麼翻蓋了,要麼幹脆就消失了。當然,也有可能一切還跟她之前見過的一樣,隻是她不記得了。活了一千個世紀之後,即使最聰明的人、在最機敏的日子裏,也隻記得她所見和所做的一小部分。
要解決這個疑惑,最好的方法就是向植入式網絡節點詢問地址與地圖。但浣生抵抗住了這種誘惑,等待自己的靈光一現,卻一直沒能等到。她決定先走走看,於是領著她的同伴走上一條看似可能的路,希望它能通往正確的山頂。
他們所處的這個空腔在大船上屬於中等大小,融入黑色玄武岩的走勢之中。深埋的超異纖維大梁和加強筋牢牢地支撐著空腔頂部和遠處的岩壁。當初,在勘察小組首次來這裏繪圖時,整個空腔仍被水冰填滿,其中還摻雜著氮氣和甲烷的雜質。因為空腔的相對較小——最寬處隻有一千千米——也因為它接近大船的艦橋和阿爾法港,於是這裏成了第一個被轉化的居住點。工程部門將附近的六個反應堆從漫長的沉睡中喚醒,逐漸把冰融化成依舊寒冷卻可以馴化的液體。隨後,他們抽幹了空腔。作為實驗的一部分,每一滴液體都過濾了兩次,並由一係列傳感器加以分析。沒有發現生命曾經存在過的絲毫跡象——跟船上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水遠談不上純淨。古遠的冰中有礦物和鹽分,還有幾個構造簡單的有機分子,但沒有指示性的脂質膜碎片,也沒有DNA和RNA那種永恒的螺旋體結構,或是任何細胞,可以追溯到人類或是他身上攜帶的細菌。
大船上到處分布著巨大的泵和虹吸管,其唯一的用處應該就是這個。一聲令下,機器開始將水抽回山洞。裝到半滿之後,工程師們關掉了泵,封上了泄水孔。其他小組開始擺弄環境控製,設定日夜循環和季節更替,模擬被戲稱為地中海式的氣候。新的海洋鹽分恰到好處,又加入了鐵元素。全息投影儀繪出明亮的藍色天空,晚上換成黑色,古老的星空在頭頂上方緩緩轉動。然後,一批簡單的微生物和浮遊生物被釋放到風中,光禿禿的平地厚厚地鋪上一層由儲備的碳氫化合物製成的黑色土壤。從地球帶來的方舟中釋放出了魚和烏賊;粗壯的橡樹和橄欖樹紮根在黑色的海岸;物種並不豐富的鳥類突然間變得到處都是。大船的首個城市就建造在這片土地上,城裏居住著乘星艦前來的工程師和其他船員。另有二十二塊土地和淺水區被劃定為未來的居住區。但是,即使過了一千多個世紀之後,這些計劃中的城市也隻開發了一半,而且大多隻有幾所房子立在規劃好的地方。大船的廣袤讓蓬勃的開發顯得微不足道。既然空腔的數目比乘客還多,那麼為什麼不住在你自己的天堂裏呢?況且這裏是大船上第一個地球化的小角落,多少有點粗糙,因為工人的專業本來是維修星艦引擎。其他地方的海更優雅、更漂亮、更古怪或是更獨特。大多數乘客都有這種勢利的想法。但浣生沒有。她在這個怪石嶙峋的黑色海岸邊長大。此刻,盡管尚不清楚方位,她發現自己輕易就回想起了甜蜜的時光: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裏,作為一個兒童數目極其稀少的世界裏的孩子,在這艘偉大的飛船曾經最美的城市裏忙碌地生活。
一直在上坡的街道很寬,玄武岩地磚鋪成傳統的類晶體形式,接縫處嵌入紅色的碳納米管砂漿。道路兩旁種著粗壯的橡樹,樹齡可能是兩百年,也可能是兩萬年。在他們左麵,藍色的大海慵懶地拍打著岩石和高聳的懸崖。在右麵,房子和小商店創造了真實的鄰裏間的溫馨氣氛。偶爾有居民看到浣生和帕米爾經過,但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兩人已經走進了斑駁的陽光。真的沒眼花嗎?真的是打敗違望者的那兩個船長?話很快就在小巷子裏傳開了。地球人和其他物種都急忙跑出門外,看著這兩個穿著鏡麵製服的神奇人物肩並肩地走在最普通的道路上。沒人相信自己竟有這麼幸運。他們隻是全息投影嗎?不是,顯然不是。一個無畏的男孩走上前,還未開口,臉上先洋溢起笑容,“您真的是一副,長官?”
“是的。”浣生回答道。
“您是二副,長官?”
“算是吧。”帕米爾嘟囔道。
兩位船長最近剛升任副首領。提升背後的原因很複雜,甚至還有些齷齪,不免令人唏噓。但在這個孩子看來,故事很簡單。違望者是壞蛋,是一群危險分子,來自那個秘密的世界,髓星。浣生和帕米爾則是大英雄,打敗了敵人,他們的肩章是靠著他們的勇敢和對巨艦的滿腔忠誠換來的。首領船長本人對此十分感激,並給這兩副久經考驗、結實可靠的肩膀添加了新的重擔。現在,大家都能睡個安穩覺了。
“你們來這裏開會?”男孩問道。
他走在浣生的身旁。他們組成了不尋常的一對:一個是留著短發、體形矮壯的小男孩;另一個是漂亮臉蛋、身材修長的女人,長長的黑發挽成一個發髻。浣生點了點頭,低頭瞥了一眼這位同伴,故意裝出一副冷漠的樣子,“你住在附近嗎?”
“在那邊。”他回答,指了指前方隆起的山包。
“想找個本地的導遊?”帕米爾開了個玩笑。
浣生沒有搭理他。
男孩用驕傲的語氣宣稱:“這裏是巨艦上最古老的城市,所以我們叫它阿爾法城。也可以叫第一城,或者直接叫阿爾法也行。”
“我知道。”浣生柔聲應道。
“首領船長總是在那兒召開最最重要的會議,在那邊的大石頭上。”
“我聽說過。”
“你參加過這種會議嗎?”
浣生搖了搖頭,“應該沒有。但也可能是我忘了。”
“那你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這是個好問題。”浣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因為我們迷路了。”緊跟在她與剛交的好朋友身邊的帕米爾替她解了圍。
其他路人都笑了,但笑聲有些緊張。男孩似乎並不在意。他皺了皺眉,隨後決定提醒浣生,“那上頭沒啥重要的,什麼都沒有。”
“你真這麼想?”
這個問題是陷阱嗎?男孩遲疑了一下,隨後又提醒了一次,“那是個老居民區。不讓把房子拆了,隻能等它們自然倒塌。但它們不會倒,因為每個人都必須好好維護它們。”
“因為它是一個曆史保留區。”浣生朝男孩眨了下眼睛,解釋道,“那些房子是第一批登上大船的人蓋的,所以它們有特殊意義。而且,據我所知,有一兩位船長就出生在那裏。”
男孩很吃驚,“哪幾個?”
“都是低階船長。”浣生說道。
“我也要當船長。”她的朋友宣布。隨後,他緊張地抬頭看了看浣生,發現她露出讚許的神色,便又扭回頭對二副強調了一句:“我很快就會當上船長。很快。”
帕米爾是個氣勢逼人的大高個。不怎麼英俊,脾氣也不怎樣,對保持微笑或是魅力毫無興趣。那張棱角過於分明的臉十分擅長在任何時間、因為任何細小的原因、對任何船員或是乘客皺眉。但因為眼前是個孩子,或者是因為新的製服和頭銜,他這次的表現得體多了。不管出於哪個原因,總之他決定避開赤裸裸的事實。“有可能,”他隻是簡單地回了一句,“祝你好運。”
緊接著,通過一個私人的、重重加密的紐聯節點,他對浣生說道:“前提是還有船隻可供駕駛。”
即便在看似尋常的散步時,兩位副首領依舊關注著日常工作和突發事件。植入式網絡紐聯節點使之成為可能,他們的頭銜也讓他們無法擺脫責任。按照緊急方案,大船巨大的引擎正在進行維修和翻新。保安部隊仍然在搜尋最後的違望者成員。乘客與船員需要鼓勵、保持溝通,這要用到一係列公關措施,每一個都是定製的,以便符合特定物種獨有的文化。還有,一定要通過完全公開的方式揭露和粉碎謠言。要說浣生最擔心什麼,那就是謠言的傳播速度和誇張程度。哪怕是一件誕生於各式各樣的誤解或半真半假之中的小事,一旦開始在公眾中間傳播,它就會不斷地變化、誇大。正如此刻,在她平靜地徜徉於古老社區的同時,她仍在處理一個異常頑固的謠言:船長和他們的家人正打算棄船。這個謠言誕生於違望者被打敗的那一刻。盡管采取了各種措施證實它是錯的,但它依舊有很強的生命力。
今天傳播棄船故事的是一個不知名的物種,他們使用的是一種氣味標記和熒光尿液組成的語言。麻煩剛一露頭,一個由人工智能和外星生物學家組成的小組就開始著手製定反擊策略和傳播方式。浣生也收到了通知,在腳下的路變得越來越窄的同時,她檢察並否決了其中的六七種方案。“太正式了。”這是她的總體感覺,“要自然一些。”這是她的要求,“找個船長將真相尿給公眾。”這是她的建議。隨後,她抬起頭,驚喜地發現眼前有一處熟悉的景象等待著她。
前方是一片看不出樹齡的橡樹和核桃樹果園,占地大小剛好給人一眼望不到邊的感覺。粗壯交錯的樹枝和肥大的綠色葉子製造出一片茂密的陰涼。陰涼如此強勢,隻有喜陰灌木才勉強得以在黑色礫石的土地上存活。樹蔭唯一的缺口在一座低矮房屋的上方。這座裝飾著雕花玄武岩和人工鑽石的建築顯得很牢固,重心穩定,隻是略顯單調,顯然是出於工程師的設計。火星式框架和羅馬式拱門顯示著力量和不經意間的典雅。人造陽光灑在屋頂,令它有一種不真實的莊嚴。前門關著—— 一扇厚重的白色大門,由智能塑料和黃銅飾條組成——看上去似乎沒人在家。浣生打了聲招呼,但她沒聽到門去提醒裏麵的住戶,也沒有對她做出回應。這房子大概沒人住吧,她想。如果它是空的,她會買下它。她花了點兒時間考慮這個決定,短暫地想象了一下再次住在這裏的情景,馬上就後悔了。她不屬於這裏。曾經住在這裏的女孩已經離開了,不切實際的幻想是愚昧的。
男孩依然留在附近。她轉身看著他,問道:“這是誰的家?”
“反正肯定不是空的。”他信心滿滿地脫口而出。
緊接著,一扇鑽石窗口的後麵出現了一張臉,浣生如釋重負。
“看吧。”男孩又加了一句。
然而,那張臉奇怪地迅速消失了,門依然靜靜地緊閉著。沒了耐心的帕米爾走上前,掄起大拳頭使勁砸門,直到門鎖變成液體,流進門柱。門不滿地開了。剛才在窗口窺視的那張臉原來屬於一個身材矮小的地球女人。此刻她現身於門縫之中,用近乎耳語的聲音說道:“來了來了,先生。來了,女士。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浣生接口道,“我以前在這裏住過,僅此而已。”
男孩笑了,立刻跑開,把這個他剛剛探知的秘密告訴別人。
“不麻煩的話,”副首領接著說,“我想很快地看一眼裏麵的樣子,可以嗎?”
女人嚇了一跳。她的好幾百個鄰居和所謂的朋友站在樹蔭下,看著眼前的一切。她盯著他們,臉上露出氣呼呼的表情。緊接著,她隱藏了自己的憤怒,用幹巴巴的聲音嘟囔了一句:“我沒法擋住你,不讓你看。”
她這種態度有傳染性。浣生猶豫了,“我知道這有點兒強人所難,女士。如果你跟我們說‘走開’,我們會離開的。”
這個承諾讓女人嚇了一跳。她深吸一口氣,扭過臉,對一個看不見的人低聲說了幾句。隨後,因為不相信浣生——沒有哪個小小的乘客能阻擋副首領——她順從地低下頭,慢慢地讓出門口,允許兩位偉大的船長進屋。
根據法律,房屋的內部結構必須以曆史為標準,維持原狀。也因為這個麻煩,住戶得到了豐厚的財務補償。浣生先入為主地猜測這裏沒有照章辦事。女人不願讓他們進去,原因就是這個。然而事實上,房子裏即使有不符合標準的地方,肯定也隻是在細節部分。不去訪問舊的數據庫的話,浣生根本找不到什麼差異,除了有幾個小房間做出了小小的改動,以便讓某些外星物種能生活得更舒適一些。
房子的占地麵積隻有一公頃,參觀一遍隻需幾分鐘。她和帕米爾逛了逛娛樂室、社交室,還有老式的圖書館,薄薄的鑽石擋板後麵塞滿玻璃書和紙質書。一個室內池塘喚醒了她的回憶。“我就是在這裏學會的遊泳。”浣生指了指它。隨後,她帶帕米爾挨個參觀了三個從前歸她所有的房間,分別屬於孩提時代的三個不同階段,最後一間離父母的房間最遠。最終,他們走進古老的大廚房,在那裏,如果她有興致的話,可以自己做飯,不靠機器人或是智能餐食幫忙。緊挨牆邊的是一個大到足以喂飽一群人的灶頭,很久未用,但一直處於待命狀態。鋼和超異纖維製成的鍋碗瓢盆掛在從天花板垂下的銅管上。房間中央,一個陌生人坐在一張簡單的木頭桌子前。他是個小個子男人,正從一杯熱騰騰的、濃稠的麻醉飲品中喝下最後一口。副首領進入房間時,他驚叫了一聲。他們倆看到他時,他丟下杯子,抽泣起來。他的臉埋在桌上,鼻子頂著黃色的木頭表麵,半遮住的嘴巴發出一聲哀求:“請原諒我。”
女人站在另一個門廊裏。還有五十來位好奇的鄰居站在院子裏,眯著眼從窗戶往裏窺探。
“非常對不起。”小個子男人低聲說道。
帕米爾笑了。
聲音柔和卻掩飾不住恨意,他回了一句:“你還有臉說?我們是不是該把你活活打死?”
男人戰抖著,說不出話來。
浣生在他對麵的一張椅子裏坐下。她有些摸不著頭腦,但聽到的已經足以讓她開口下令了:“告訴我們,”她並攏雙手,看著空空的掌心,“把整個經過告訴我們。”
男人幾乎一口氣就供出了整個來龍去脈。他這一輩子都是個技術員,在阿爾法港工作。違望者來的時候,他逃離崗位,躲了起來,買了新麵孔和新身體。戰爭爆發,隨後結束,他又換了兩次臉,打造了一個新身份。一切本該完美,但顯然不是。他住到了姐姐這裏,現在看來是個錯誤。不過,找到他的並不是保安部隊。不是,誰能想到呢?一副和二副竟然會來到這種地方。這肯定意味著出於某種重大的原因,他被當作了一名嚴重的罪犯。
帕米爾笑了。一連串的巧合導致了這意料之外的一刻,讓他有些吃驚。
但浣生幾乎沒在聽他說。她合攏的雙手分開了,放下了曾經攏住的“空無”。她歪著腦袋,看著它滾下桌麵,仿佛在傾聽一個幾乎和她一樣年長的回音。
“站起來。”帕米爾命令道。
技術員一下子跳了起來,差點兒摔倒。
“清醒點兒,”二副下令,“回到你的崗位。今天就回去。假如你可以做到兩件事——清醒和工作——假如你還記得怎麼工作,我會向首領船長求情。明白嗎?”
“你會為我去求情?”
“我這麼做不是為了你。是為了大船。”利用紐聯節點和個人權限,帕米爾找到了這個女人的身份,追查到了她失蹤的弟弟,清除了檔案中的不利記載。技術員很寶貴,尤其在當下。這個人並沒有加入違望者,這是個很有利的加分項。況且,如果把這個罪犯就此關押起來,眼前這一刻就沒那麼有趣了。
“謝謝,”心懷感激的技術員說道,“謝謝長官。”
浣生往後推開椅子,站了起來,木頭在地板上發出刮擦聲。她仿佛沒有聽到最後幾分鐘的對話一樣,隻調整了一下鏡麵頭盔的角度,帶著淡漠的笑意,問道:“你在這裏住了多久?”
女人咽了口唾沫,承認道:“最近十七個世紀都住這裏,女士。”
浣生點了點頭。
思索一陣子之後,她說了句,“比我住在這裏的時間長了十倍。”接著,她又笑了笑,還眨了下眼睛,“現在這是你的房子了。你想怎麼處理都可以。重新裝修,推倒重建。無論你怎麼打算,都可以。”
“女士——?”
“但假如你發現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任何古老奇怪的東西……請把它送到我那裏去,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