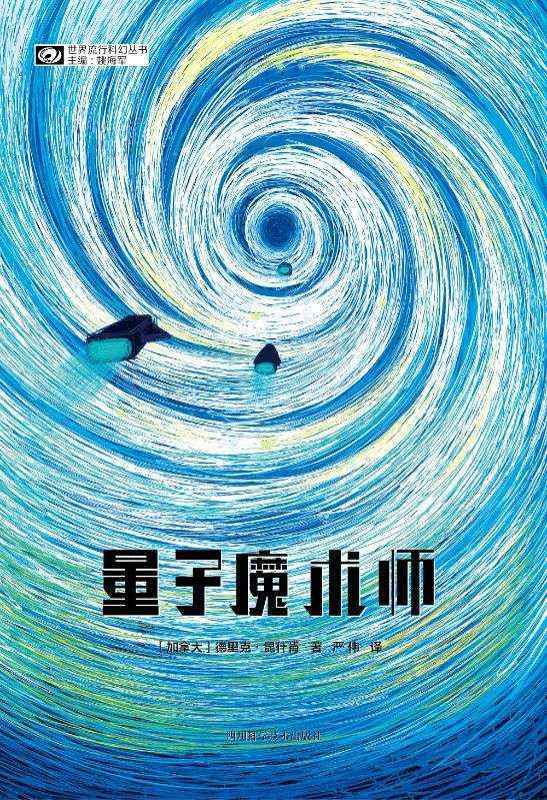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十四
薩格奈或許隻是一座省城,但它誌存高遠。薩格奈站的拉努瓦賭場敞亮、喧鬧,勝於貝利撒留記憶中的樣子,四處洋溢著燈光和生活氣息。這裏得不到聚合政府的“老”錢,卻另開財源,憑借其競爭力十足的造船廠及附屬供應鏈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在聚合社會,形成階級和地位分別的不是金錢。光靠有錢是不能成為“本地”人的,這稱謂隻保留給最古老的金星血統。不過有錢總不是一件壞事。耍錢有贏有輸,是一項運動,而拉努瓦則是個很好的競技場。
貝利撒留正站在天花板很高、鋪著紅毯的接待區裏,接受身體掃描,等待進入賭場大廳。從他開始頻繁光顧,賭場就應該給他建了專檔。X射線肯定再次發現了他身上的電肌塊,甚至也許還有他體內一部分的納米碳微管網絡。六個聯網的福爾圖納A.I.馬上知道了他是量人,可能會安排一些額外的監視,但也不會太多。
貝利撒寄存好大衣,又刷了刷他的黑色羊毛晚裝。這裏還提供陪玩的人,可以選個男人、女人或雙性人陪他逛賭場。他選了一個身著藍色晚禮服、魅力十足的女人。他們挽著手臂,走進第一個大廳。
“貝爾!”她用法語8.1低聲說道,“好久不見!你長大了。”
“你過獎了,瑪德萊娜。”
“你都去哪兒了?”
“到處轉轉,”他說,“現在我在自由城做收購偶人藝術品的生意。”
“真的嗎?那門生意怎麼樣?”
“要多煩人有多煩人。”
她調皮地碰了碰他的胳膊,“你應該多來這裏,找點樂子。”
“很不幸,我已經好久沒玩兒這個了,而且我現在正在工作。”
她轉了轉眼珠子,“這話聽著不太像我過去認識的那個貝爾啊。我到現在還記得你和威廉在大廳後麵的酒吧打的那場架呢!想不到你居然會……”
“那都是舊聞了,”他敷衍道,“我現在做的是藝術品買賣。”
她慢下腳步,指給他看輪盤賭那邊的一個空位。他搖了搖頭。他們手挽著手在賭場繼續閑逛。她從一名經過的侍者那裏拿了兩杯蘇格蘭威士忌,那侍者竟是一名真實的人類。拉努瓦真是誌存高遠。
“藝術聽起來很無聊。”她若有所思地說。
“我一直都很無聊的,瑪多。回憶都是經過美化的事實。”
“哈!直到現在,俱樂部裏一些人在吹噓誇張故事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叫你魔術師呢。”
“所有的故事都是經過誇張的,瑪多。”
她笑了,“你說你正在工作,那又是什麼?”
“我在找一個醫生,名字叫作安東尼奧·德爾卡薩爾。”
瑪德萊娜掃視整個房間,臉上笑容依舊,但眼睛裏閃爍的微光說明她正在讀取角膜顯示器上的來賓名單。
“他是個遺傳學家?你想要幹什麼?想加點兒增強模塊,還是要移除?”
“也許他知道誰想買藝術品。”
“你大老遠到薩格奈來,就為這個?”
“你要是知道現在有多少人想要偶人藝術品,肯定會大吃一驚。”
她盯著貝利撒留的眼睛。她有雙漂亮的眼睛,古老的北歐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她的皮膚,幾乎和他的一樣黑。但隨著她從網上檢索偶人藝術品的信息,這妙目之中卻開始跳動著微弱的懷疑目光。她皺起了眉頭。“哎喲——”然後眉頭皺得更緊了,“他媽的!”她咒罵道,“這些人這又是什麼毛病?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毛病,我是說。”
“他們有毛病你很意外嗎?”
“倒也不意外。”瑪德萊娜顫抖著,眼裏的光芒也消失了,“噢!這下我可忘不掉了。”
她陪著他,漫步走進第一大廳中央,經過輪盤賭、花旗骰、二十一點和百家樂區域,來到了樓梯旁。這是一段樹皮光滑且並不很粗的樹幹,上麵纏繞著非常細的藤蔓,向上攀緣。每隔一定的間距,藤蔓上就冒出透明如薄紗的新葉。這些葉片台階顯得如此脆弱,貝利撒留覺得自己站上去肯定會壓彎它們,但瑪德萊娜領著他走上那些葉片。她腳踩到每一級樓梯的時候,葉片就會發出熒光。
貝利撒留跟在後麵,他的大腦剖析著這樓梯的工程構造:基因改造過的植物細胞可以生長出碳納米微管,可能以此加強木質部和韌皮部,達到可以媲美鋼鐵的強度。而生物能夠發光的菌落則在植物細胞內生長,在壓力作用下就會亮起來。漂亮的設計。
“德爾卡薩爾在夾層的撲克室裏。”她說。
一條淺溪沿夾層流淌,清澈的水底泛著氣泡。水麵上露出一串腳印形狀的石英玻璃步道,通向一連排的高頂房間。那裏就是撲克區。
貝利撒留掃視著牌桌的海洋,一張張牌桌上正進行著五張牌和七張牌的梭哈、抽牌以及更加奇特的玩法。這裏共有三間屋,每個屋裏有六十張桌子。四下裏短促的對話聲傳來,讓貝利撒留心底的渴望複燃。在這個賭場,他曾經擊敗過很多人。
賭場遊戲自19世紀末期以來就沒有太大的變化了。技術改變了很多人,但並沒有改變這項遊戲,不過人們也增加了一些反製措施,以保護遊戲的純淨。拉努瓦的牆壁裏裝的法拉第籠(1)或許比英西銀行裝的還要多。到處都有低白噪聲發生器在工作:天花板上麵、牆壁裏,甚至地板下麵。非視覺頻譜的部分則由電磁幹擾引擎負責,特別是熱和紫外線。和偶人穿越他們蟲洞的運輸生意一樣,賭場的興衰也依賴於能否讓顧客確知這裏是誠實可靠的。
“他在第三室。”瑪德萊娜說。最高賭注區。
“你就陪我到這兒吧,”貝利撒留說,她失望地看著他,“談生意之前,我想先觀察觀察他。”
她的肩垂了下來。貝利撒留把一大筆小費和酒杯都塞給她。
“你要是還有什麼別的需要,就告訴我,”她不那麼純潔地微笑著,“我喜歡你長大了的樣子,貝爾。”
“我一定會的。”
他的謊話讓她笑了。他穿過中等賭注室,進入了高賭注區。
安東尼奧·德爾卡薩爾坐在一台五張牌桌旁,正看著別人出牌。和貝利撒留一樣,德爾卡薩爾的血統往前追溯很多代,也是起源於哥倫比亞。不過,貝利撒留從自己先祖那裏繼承的是加勒比黑人和土著的混血,而德爾卡薩爾則擁有殖民者的淺色皮膚,隻有黑色的眼睛和頭發多少顯示出拉丁與印第安的混血痕跡。
貝利撒留走到房間邊緣的一排椅子處,觀察著牌局。
撲克牌遊戲擁有一種純粹性。從表麵上看,概率的平均性具有一種柏拉圖式的純潔。在概率麵前,政治、暴力、愚昧、貧窮和財富全都毫無意義。與他的量人本質正好契合。於是,賭博的感覺就像回到了家裏。
而且,撲克牌還擁有一種超越時間的穩定性。16世紀的時候,類似現代撲克牌的遊戲已經在歐洲流傳。其最終形式,也就是四種花色各十三張牌,到了19世紀就已成型。那之後,就像蜥蜴、鯊魚和蛇,它們不再改變了。不是因為這樣最有魅力,而是因為模因選擇已經實現了對它們的完美改造,使其與社會學意義上的生態位正好吻合。能夠成為這種穩定性的一部分,這令他感到心安。這種穩定性讓他對智能與意識的本質有了某種了解。
智能是生命的意外產物,同樣地,受控概率的遊戲也是智能的意外產物。智能是一種適應進化的結構,使人類不僅可以在空間上感知世界,更可以在時間上預測未來。概率遊戲就是對這種預測機能的測試——如果以受控概率的遊戲作為區分意識跟無意識的手段,甚至遠比圖靈測試都要來得更為有效。
貝利撒留從不信任圖靈測試。該測試的理論基礎是如果能足夠好地模仿意識,那就有可能騙過有自我意識的生命。但意識生物其實很好騙過,從而導致圖靈測試得出與事實相悖的誤報。貝利撒留曾經在牌局中對付過電腦,甚至是像聖馬太那樣的A.I.。隻要是優秀的玩家,遲早都會發現程序員預先訂下的規則,而貝利撒留是個非常優秀的玩家。隨機改變風格,甚至隨機產生用於做出決定的閾值,這些都隻是掩蓋深層規則的表麵工作,而且隻能掩蓋一時。牌桌上的對手如果是一台計算機,甚至往大了說,就算是一個神遊中的偶人,都無非是一套可以解讀的算法而已。
德爾卡薩爾起身走到樓上的酒吧裏,找了張桌子坐下,俯瞰著主廳。貝利撒留緊隨其後。輪盤賭的哢嗒聲、下注聲、發牌員的叫牌聲,以及歡呼聲和歎息聲,嘈雜地傳到酒吧上來,與經久不息的背景白噪聲混在一起。
“醫生,我一直想跟您談談。”貝利撒留用英西語說道。
德爾卡薩爾審視著貝利撒留。德爾卡薩爾的眼睛裏肯定有增強模塊,卻看不到那種標誌性的微光閃爍。他裝的一定是最昂貴的那種,可以無須視網膜中介,直接輸入信號到大腦的視覺皮層。他的眼睛微微眯起。
“阿霍納,”他說,“我上次在賭場見到你的時候,你還不過是個孩子。我不記得跟你說過話。”
“您說得不錯。”貝利撒留從侍者那裏要了一杯酒,走近德爾卡薩爾的桌子。
“你是個量人,”德爾卡薩爾說,一邊眉毛因為好奇而揚起,“不過不算一個好量人,因為你跑到這裏來,跟我們這些人在一起。”
貝利撒留向醫生敬了一杯酒,說道:“量子神遊裏麵有諸般妙處,卻唯獨缺了兩樣:蘇格蘭威士忌和女人。”
德爾卡薩爾笑著舉了舉自己的酒杯。“神遊能幫你打牌嗎?”他問道。
“各種量子感知彙總在一起,經常會給出反直覺的結果,所以你沒有看到投資者擠破了閣樓的門檻,衝進來朝我們大把砸錢。”
“那我想知道,你幹嗎還在這兒跟我講話呢?”德爾卡薩爾慢慢地說,“十年前,你跟威廉·甘德是搭檔。”
“你的消息很靈通。”
“為了找到對路的情報搜集服務,我花了不少錢。”
“我有一陣子沒跟甘德合作了。”
“他現在在監獄裏,”德爾卡薩爾說,“我猜他騙錯了人。”
“我現在做非主流藝術品生意。”
“是嗎?”德爾卡薩爾說,“可我不覺得你來這兒是要賣給我藝術品的。”
“我很仰慕你的工作。我手頭有一個項目,可以發揮你的技能,而且我付的報酬要遠超市場行情。”
“好的遺傳學家多得是。”德爾卡薩爾說。
“沒有能做我這個活兒的。”
德爾卡薩爾眯起眼睛。“也許我們應該找個安靜的地方,”他說,“我在賭場有一間長租房。”
貝利撒留跟著德爾卡薩爾走出大廳,經過幾家餐館,來到一處小橋流水的所在。水中的睡蓮和魚兒都能生物發光,熒光點點,炫耀著主人的財富。貝利撒留的大腦開始探尋各種模式。閃爍的生物光對力學擾動沒有反應。植物和魚類在不同顏色的小瀑布中發著熒光。這些圖案很漂亮,但也充滿了信息。這個生態係統中隱藏著簡單的信號轉導,不過在其他的旅遊者眼裏隻是一個燈光秀。這肯定是德爾卡薩爾的作品。其中隱含的信號是什麼呢?
兩人來到一座花園,裏麵都是如水銀般閃耀的透明植物,沿著一個燒結風化壤堆成的小斜坡向上攀緣。另有一個裏麵栽種著硬葉植物的樓梯井,通往一個陽台。
“你的作品?”貝利撒留問道。
“拉努瓦的目標是成為全文明頂級的賭場之一,”德爾卡薩爾說,“所以需要有獨一無二的美景。”
“這些葉子,”貝利撒留用手指輕輕撫摸葉子,測試其硬度,“是玻璃做的?”
“我插入了嗜極細菌(2)的基因,它們能分解矽酸鹽,”德爾卡薩爾說道,“我還照搬牡蠣用來生長殼和珍珠的方式,設計了矽酸鹽承載係統和礦物沉積通路。這些東西脆弱而美麗,但沒有像量人那麼複雜。”
“你是量人項目的崇拜者嗎?”
“我崇拜的是項目中體現的技術,”德爾卡薩爾說,“而不是項目的目標。”
“這一點我跟你想的一樣。”
貝利撒留沒有再問那些沿樓梯栽種的銀色植物。那些植物閃爍著另一種微光,一路通向德爾卡薩爾的房間。德爾卡薩爾打開門走了進去。天花板上並沒有頂燈,取而代之的是螢火蟲發出的一排排柔光,點綴在頭頂,仿佛天穹上的星辰。德爾卡薩爾走到房間的另一邊,從架上抽出一瓶紅酒。貝利撒留關上門,靜立在房間裏。
“這些也是你的作品?”他問道。
“如果客戶想要美觀,我會把東西做得漂亮點。不過自然才是首要的考慮,而自然充滿了血腥的尖牙利爪。”德爾卡薩爾一邊說,一邊拔掉酒瓶上的軟木塞。
貝利撒留兩邊的牆上貼著的像是仙人掌皮,但上麵的刺很長,有手指粗,一根根都指著他。
“這些牙可真夠長的。”貝利撒留說,“是動物嗎?”
德爾卡薩爾倒了一杯酒,卻空著另一個杯子。他喝了口酒,轉過身來。
“都是植物,”德爾卡薩爾說,“我增加了能夠捕捉紅外線的感光器,這樣它們就能夠追蹤……目標。每根刺底部的球狀部位是加壓水囊,這個設計模仿某些植物用來釋放種子的爆炸室。當然我設計實現的壓力值自然界裏沒有植物能夠達到。你可以想想毛瑟槍,就能大概知道那是什麼樣子。”
“用什麼來觸發?”
德爾卡薩爾伸出一根手指,點了點自己的腦袋,“我自己的思想,通過神經增強模塊發出無線電信號。這些球狀部位裏包含了無線電天線,按分形模式生長,可以減小尺寸。它們隻會對一個特定頻率做出反應。剩下的,在它們看來,都是不斷轉導的信號。”
“很有意思的待客之道。”
“時不時地你就得需要這個。好了,告訴我吧,阿霍納,你來這裏做什麼?你可不是什麼藝術品經銷商。”
“我接了一個活兒,一個大活兒。這個活兒需要個遺傳學家。”
“遺傳學家有很多。”
“他們有誰能複製你在元神領域所做的那些工作?”貝利撒留問道。
德爾卡薩爾一動不動地注視著貝利撒留。長時間的沉默。“我得誇一下你的線人。你在醞釀什麼秘密計劃,阿霍納?”
“我想潛進皇城,還有斯塔布斯港的幾個安全設施。”
“怎麼進去?”
“我需要你幫我改造一個人,好讓他聞起來像個元神。”
他這話聽起來像在罵人。元神是整個文明世界裏被唾罵得第二多的人。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德爾卡薩爾說。
“我知道你一直在封閉野生元神後裔體內的信息素。”
“我已經能夠減少那些信息素了,主要是通過破壞代謝中間產物。但我還沒能完全治愈任何人。”
“我想找你再試試。我還可以給你提供特別的資源,”貝利撒留說,“一個真正的偶人,他是個流亡者。”
“我還以為流亡者隻是一群無法檢測到元神信息素的基因突變者。”
“我也希望他不要改變。他要幫我們穿過偶人的防禦設施。”
德爾卡薩爾喝了一口酒,“要糾正偶人的遺傳缺陷,還要製造一個假元神。你大老遠地跑來,該不會不知道你的這些要求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吧?這兩件事,最多也隻能做出個贗品而已。最初的設計者創造了全新的亞細胞細胞器,它們具有獨特的分子和遺傳結構,以及新式的共生微生物組,從而可以改變其生物化學、免疫和神經反應。即便你給了我貨真價實的樣本,元神也好,偶人也罷,我都沒法複製。”
“我知道,”貝利撒留說,“你就當成一次生物工程擬態的練習好了。你覺得你的贗品能近似到什麼程度?”
德爾卡薩爾眯起眼睛。他緩緩晃著酒杯,看著杯壁上掛著的酒液。
“付的錢越多,”德爾卡薩爾說,“買到的東西就越好。凡事都是如此。但我懷疑你是不是能付得起錢,哪怕隻是為了一個希望渺茫的方案。”
“報酬有七位數,法郎。我的財力會讓你大吃一驚。”
德爾卡薩爾眉毛一揚,臉上的表情十分滿意,“果真如此的話,想殺掉你的人肯定也會讓我大吃一驚吧?”
“所有宗主國都沒有任何理由會注意到我。”貝利撒留說,“我不僅僅是跟一個突變偶人和一個假元神合作。我的團隊裏還有兩個量人。那可是一個很大的基因模型庫,可以用來學習。”
德爾卡薩爾略有些著迷地看著貝利撒留,“要是能親手對量人做些修改的工作,這事兒我或許會覺得很有意思。”
“這事好辦。”貝利撒留說。
“可惜你的團隊裏沒有雜種人,不然你就有全套的人類大家庭了。”
“你這話可真巧了。我正準備跟你談完就出發去見一個雜種人的。你去過‘文明最深大餐廳’嗎?”
(1)由金屬製成,用於電磁屏蔽。
(2)可以在極端環境中生長繁殖的細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