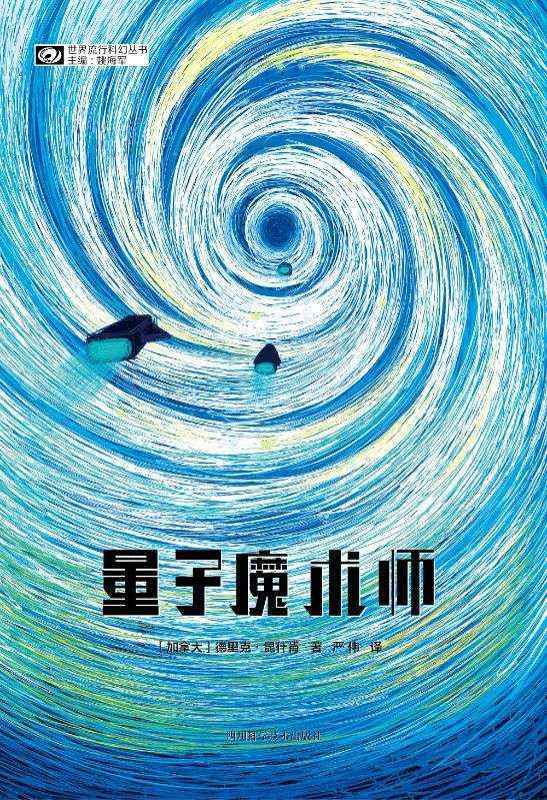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五
貝利撒留不知道是否應該接受這份工作,但現在還不急著答複。伊坎吉卡領他來到走廊,那個憲兵還在那兒守著。貝利撒留探手想去握住梯級,但動作不太利索。他抓了個空,驚慌失措地張開手臂,不知怎麼就在走廊中間旋轉起來,夠不到任何一堵牆壁。他歎了口氣。
“好久沒在零重力下生活了。”他說,“誰能幫我一把?”
憲兵露出厭惡的表情,伸出他的手。貝利撒留摸索著抓住那隻手,仿佛緊握著一條救生索,總算攀上了牆上的梯級。他小心翼翼地跟著他們穿過走廊,周圍褪色的碳聚合物牆壁讓人感覺冷冰冰的,很壓抑。要是裝幾個小彩燈,也許會讓飛船更溫暖些。伊坎吉卡停了下來,將手掌按在一部傳感器上,一道艙門向下打開。裏麵顯露出一間陰暗的房間,大小差不多能放下幾口棺材。
“我們讓一位軍官搬到主營去了,這樣在你逗留期間可以有貴賓的感覺。”伊坎吉卡說道。貝利撒留覺得她的話裏應該是沒帶諷刺意味。他在偶人自由城房子裏的淋浴間都比這個房間大。
他飄進屋子,轉身麵對她。她棕色的眼睛挑釁地盯著他。“你們不可能擊敗聚合政府的,”他最後說,“他們哪怕是打個噴嚏,其他宗主國都會提心吊膽,更別說你們了。”
“你隻管施展你的魔術,剩下的交給我們。”
她犀利的目光直直地瞪著他,然後又稍稍軟化下來。
“我對你這個人沒什麼意見,阿霍納,”她說,“但沒人願意在壓迫下生活。你嘮叨了半天,不過是些人們重複了幾十年的老生常談。我們不是自己家園的主人(1)……”這句老話,她隻說到一半就沒再繼續。
牆壁內的自動門再次升起關閉。借助天花板上一隻方頂燈的弱光,能看到四麵年久褪色的灰棕色碳纖維牆壁。其中一麵牆上綁著一個零重力睡袋;另一麵牆上有隻手柄,拉開是一個小水槽和配套的水龍頭。空氣中摻雜著汗水的氣味。屋子裏肯定有攝像頭在監視著他。撒哈拉以南聯盟的激情顯而易見,他們的偏執也同樣如此。他小心翼翼地打開睡袋鑽進去,把自己綁好。他關上燈,閉上眼睛,腦中的思索卻還停不下來。
撒哈拉以南聯盟在籌劃一場反對文明中最強大力量的獨立戰爭。他們需要一個騙子,來幫助他們把秘密武器運到一個可能讓他們化為齏粉的地方。這麼看起來,這任務可不那麼吸引人。
更重要的是,伊坎吉卡還隱瞞了什麼事情。她撒謊的技巧十分拙劣。某個聯盟科學家僅憑一己之力,突然搞出了一個新型推進係統,這件事的概率可算是微乎其微。他們的新武器——暴脹子驅動器——是從哪兒得到的?他得好好想想。
量人大腦已經過十一代的升級改造,不斷強化其算數和幾何能力,再加上極為清晰的記憶力。這些能力足以培育出智商驚人的孩子,但想要解決宇宙中最艱深、最抽象的問題,量人還需要進一步強化自身。
仿照電魚的DNA改造,使得每個量人的肋下都有電肌塊,那是一組肌肉,作用類似電池。貝利撒留從自己的電肌塊發送了一股持續的極化微電流到他的左顳區——大腦中與感官輸入和語言相關聯的區域。片刻之後,他的大腦對語言和交際的細微之處進行辨識的能力減弱了,嗅覺、味覺和觸覺也同樣被抑製。與此同時,大腦右前葉的活性大大增強,跟數學創造性有關的腦神經連接不斷擴增,幾何思維能力也上升到超越天才的水平。量人稱這個狀態為“白癡天才”。
貝利撒留從電肌塊又發出了另一股電流,讓他的磁小體——肌細胞中含有微型金屬線圈的細胞器——帶電。他的身體周圍展開了一個弱磁場,能夠讓他感受到“木塔帕號”施加在他胳膊和腿上的電場和磁場。天花板格上連接到隱藏式水槽的金屬鉸鏈讓他的磁場產生了失真。那台沒打開的電腦顯示器後麵連著的金屬線纜也是如此。這間狹窄客艙某個角落裏嵌著的那部攝像機也有同樣的效果。他調整了自己的磁場,重點感應那部攝像機所導致的失真。攝像機沒做出反應,說明它不是現代化的靈敏機器,隻能監控圖像。
貝利撒留轉身背對攝像頭,把腦袋鑽進睡袋,裝作在睡覺的樣子。在睡袋的黑暗中,他掏出剛才從憲兵手背上摘下來的膠貼。很久都沒幹過從別人身上“揀”錢包、硬幣或是芯片的活計了。他一度擔心自己沒準兒會失手。
這膠貼是一片透氣的碳絲織網,上麵有半導體納米電路。柔軟貼身,隱約有光澤,由身體的運動能供電。他把膠貼貼在左手背上。上麵的細小數字和字母亮了起來,發出微光。貝利撒留白天曾經讓伊坎吉卡好多次旋轉全息圖,這樣他就能觀察她是如何操縱膠貼的。她當時的動作自信而熟練,而他現在隻能試探著操作。一個簡略的全息影像浮現在他的手背上方。膠貼沒有設置密碼鎖定,這意味著飛船上的所有設備可能都是這樣。
如果讓聯盟的人發現他正在他們的網絡裏亂轉,他可能會被處以極刑。現在隻能寄希望於這支第六遠征軍使用的量子計算機還是十多年前的老東西。貝利撒留的大腦具備全套的量子處理能力,但他卻十分緊張。通常他接活兒都不會把自己置身於這樣的險境之中。但是,他必須了解聯盟,才能搞清楚自己是否應該接受這份活計,甚至是這活兒到底有沒有可能做成。
有個叫甘德的騙子曾經告訴過他,世上隻有三種賭局:
第一種:你是玩家,你玩的是牌。
第二種:你是莊家,你玩的是玩家。
最後一種:你就是隨便扔個骰子都能撞大運。
他侵入了聯盟的網絡。手背上亮起幾格標準樣式的黃色圖標:通信、共享存檔、科研、電力係統、武器裝備、狀態儀表盤,以及保密文件。接著出現了一幅認證圖案,閃爍著等待輸入。這應該是一道量子密碼驗證程序。
周圍的世界變得模糊不清,因為他的思維方式已經切換成量子邏輯的模式。他的頭腦並沒有變得不精確,而是采取了另一種態度,不再那麼重視精確度。多重的互動和關係變得比單一的身份和狀態更加重要。周圍的物體變得模糊,包圍在閃動著的光環之中。聲音也變得更加深沉豐富,被幾不可聞的旁白幹擾影響,時而增強,時而減弱。可稱為“當下”的那部分時間,輕輕地擴展開來。
他用自己的視覺增強模塊把認證圖像放大到巨細靡遺的程度,發現其中的加密算法用得十分高級。貝利撒留的頭腦繼續保持在白癡天才的狀態,然後用量子處理的方式,艱難地試圖破解密碼。時間花得很長:十秒、二十秒、三十秒,他甚至覺得自己肯定已經觸發了警報。沒有。那些全息圖標變成了綠色。
他觸了一下懸浮在空中的“動力係統”圖標。該目錄下包含暴脹子驅動器那令人咋舌的加速和散熱功能描述、最大耐受度閾值以及詳細的維護說明,但沒有藍圖或基礎理論。這些信息可能單獨存放在隔離係統內。此路不通。
他又點進了“研究”目錄。他的大腦開始進行模式嗅探,專注於搜尋數學公式以及與之相關的物理學理論,哪怕僅僅是隻言片語。怪異的是,遠征軍並沒有掌握什麼暴脹子理論,隻是對一個耳熟能詳的概念——蟲洞物理——做了些修補,以此作為他們改造工程的基礎。跟貝利撒留自己在十幾歲時就已經掌握的蟲洞物理知識比起來,他們的理論體係缺乏嚴謹性,相應的預測和分析能力也就削弱了。遠征軍的理論淩亂破碎,看上去就像是某位非主流藝術家的作品。也許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沒有什麼部隊會隨軍帶上理論物理學家。
他的大腦停在了這些研究內容的日期上。研究報告的日期有的重疊,有的偏早。與第一代試驗相關的研究文件的日期開始於2499年,可是卻有四組不同的第五代試驗顯示其文件開始於2476年。僅僅一年後,遠征軍就失蹤了。按說第一代試驗應該早於第五代試驗,對不對?
難道早在他們離開之前很久,聯盟就已經在從事非法的研究?假如聯盟軍隊定期出入聚合世界主軸的蟲洞,並且始終處於隨船政委的監視之下,他們又是怎麼一直保持自己的秘密研究不為人知?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離開之前,他們並沒有開始這些研究工作。
他又快速掠過另外一些參考資料和注釋。聯盟的這些研究大部分似乎都涉及蟲洞物理學,其中一些觀察結果隻有根據進出蟲洞的經驗才能得出,而且還必須是組成先驅者世界主軸網絡的眾多永久性蟲洞之一。遠征軍一定是發現了一個這樣的蟲洞。
真要那樣的話,那可是一個價值無法估量的寶藏。擁有世界主軸網絡的永久性蟲洞,這是宗主國成其為宗主國的專屬特權。藩屬國沒有永久蟲洞。另外,根據聯盟與聚合政府簽訂的宗主-藩屬條約,新的世界主軸蟲洞一經發現,必須移交給他們的宗主國。這就是導致遠征軍失蹤的原因。
對貝利撒留個人而言,這一發現也有非常特殊的意義。他們的觀察結果如果是正確的,那就開辟了一片研究的新天地。多年以前離開家園的時候,他不得不放棄了那樣的天地。過去的回憶不斷湧現,和模糊的渴望壅塞在一起。他努力壓抑著種種情感,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
混亂的文件時間戳依然令人費解。對於前期發現所做的調查並沒有順理成章地帶來新一波的調查研究。許多複雜的發現似乎在那四十年的初始階段就已經得出。
就在這時,他看到了一個叫作“研究協調中心”的目錄。協調中心過去三年一直處於休眠狀態,但在那之前,它曾經是一個巨大的研究成果交易中心,彙聚了各類新發現。在這裏,人們先提交研究工作中碰到的問題,之後會有人交付問題的答案:蟲洞物理、武器研究、防禦技術、傳感器技術、推進技術和計算需求。數十年的研究一下子得到解答。正是在這些結果傳遞給不同的研究單位的時候,日期發生了混亂。
貝利撒留調整了一下全息顯示,以更好地適應他的大腦。他想要幾何顯示,最好有至少四個維度,以及從試驗指向其結果的因果矢量,這樣才能追查到這些結果是在何處嵌入下一組試驗的設計之中。全息顯示屏聽話地做出了調整,呈現出一個超維纏繞,憑借人類的肉眼和大腦很難解開。
眼前出現一幅噴泉形狀的圖形,噴泉由六束流光組成,時間沿著光束垂直向上,指向未來。試驗和問題的開端位於噴泉底部。試驗結果由遠征軍的研究人員推動著向上升,保持在各自離散的時間流裏,並不與其他的研究路線發生交互。在第一批試驗結果的基礎上,迅速向上生發出進一步的試驗,得到新的試驗結果,接著又是新的試驗……如此直到2487年附近,也就從最初的試驗開始剛過十年的時候,試驗結果消失了。它的下一次出現,是在相鄰光束的底部。
在底部。
那裏是2476年。
時光倒流了十一年。
貝利撒留沒法相信這樣的結論。他反複檢查了日期標記。眼前這些時間光束的模式如此規整有序,絕無可能存在日期不一致或是數據庫錯誤的問題。他的大腦經過改造,就是為了識別這個世界中的各種模式。問題是遺傳工程師們把這項能力增加得太過強悍,讓他常常發現一些其實並不存在的模式。他得時常對自己的直覺觀察進行事後的印證分析,才能讓眼前的這個世界顯得還算符合邏輯。
這一次看來也是如此。
不過,與其自己一個人整晚做這種印證分析,還不如痛快地接受另一種可能性:遠征軍找到了向過去發送信息的方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些有關研究的信息流就是特意設計成分隔開的狀態,這樣就能分隔開不同的知識,以避免違反因果關係。第一股時間流中的研究人員在2487年的時候絕不會看到自己的試驗結果從2498年發回來。這些結果去了第二股時間流。同樣地,第二股時間流的結果又去了第三股事件流的過去。就這樣,結果走遍了每一個研究時間流。然後以十一年為周期,如此循環往複。
多麼精巧的設計,大氣恢宏。這樣一來,聯盟就有了一部可以實現時間旅行的裝置。
借助這種手段,在四十年之內,他們完成的不僅僅是四十年的研究,其價值也許抵得上四個世紀!聯盟的起點遠遠落後,然而現在他們或許已經成功地超越了所有其他國家。不過,一旦他們擁有時間旅行手段的消息傳出去,所有的宗主國,哪怕是在天涯海角,也將不惜為之一戰,前來討伐他們。如果他接受了這份工作,結果可能會觸發一場整個文明都會卷入的戰爭。這件事千頭萬緒,一時間很難想清楚。
接著貝利撒留發現了一組文件,裏麵包含了時間旅行技術裝置的數學公式描述。理解這些公式的過程大費周章,令人沮喪,不過花費了幾分鐘之後,他終於發現文件描述的是兩個成對的蟲洞,相距隻有數十米,部分地相互關聯,形成了一座橫跨十一年的單向時間橋。聯盟發現的不隻是一個先行者蟲洞,而是兩個,因為某種軌道力學的偶然事件而粘在了一起。一對結合在一起的蟲洞將會放射出各種量子級別的幹擾,他在靠近艦隊的時候感覺到的電磁場異常也許就來自於此。那對蟲洞可能就在附近。突然間,貝利撒留恍然大悟:這對蟲洞的直徑或許僅有區區十幾米。
遠征軍隨身攜帶著一對蟲洞,就在他們的某一艘飛船上。
他想起了跟隨伊坎吉卡和巴貝迪一起登上艦隊的時候感覺到的那股信號。他開始回溯檢索,計算著信號源可能的位置,又讀取了艦隊編隊的記錄,來進行交叉比對。他登上艦隊、感受到那個結構怪異的磁場時,場源附近隻有一艘飛船,“林波波(2)號”。但是他跟那艘飛船相距兩百多公裏,實在太遠,沒法做出任何觀察。那麼近,卻又那麼遠。
貝利撒留關閉了飛船上的文件,又退出了白癡天才狀態。
他從手背上揭下那張可以成為罪證的膠貼,握在手心。他的電肌塊發出一股電流,通過一組絕緣碳納米微管線路,湧向他的指尖。膠貼燒焦皺縮,成了一小團。他將那一小團塞進睡袋接縫的一個破口裏麵,為了保險起見,還將它揉得粉碎。
(1)原文是法語,語出弗洛伊德。
(2)南非的一個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