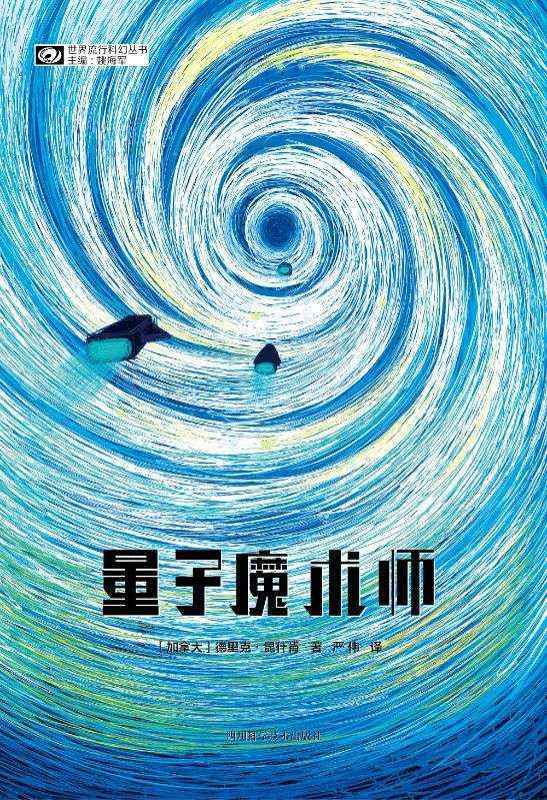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六
第二天早上,貝利撒留仍然沒有決定接受還是拒絕這份工作。不管他成功也好,失敗也罷,都會有人——也許是很多人——丟掉性命。第遠征軍說不定會因此全軍覆沒,傷亡還可能不止於此。但聯盟顯然已經下定了決心,不管有沒有他的加入,他們都要放手一搏。真正的戰爭即將來臨,這可不僅僅是一直伴隨在所有人生活中的冷戰。對於偶人,他的確相當了解。除了偶人自己,外人的了解最多也隻能到這種程度。蟲洞他也了解一些。可對於如何做成這件事,他還是毫無頭緒。但盡管如此,他仍然知道,自己是最佳人選。他想不出來還有誰能比他更好地幫助聯盟實現這一計劃。
一名憲兵進來,把他帶到了另一個房間,牆壁上掛著幾套宇航服。伊坎吉卡少校已經穿上了一套。“你想看看遠征軍的表現,”她說,“我已經得到授權,這就帶你去看看。”
在零重力下,貝利撒留手腳亂舞著飄向牆壁扶手,取下一套看上去跟他身材相仿的宇航服。由於沒有重力,他很花了一些時間才穿上宇航服。他還在穿褲子的時候,那名憲兵已經穿戴完畢了。他想用兩隻手扯下襯衫的一個紐扣,結果身體卻開始在空中打轉。伊坎吉卡的耐心終於消耗殆盡,伸手搭住他的胳膊,幫他擺正姿態。他不好意思地把那顆紐扣放進宇航服的一個外層口袋裏,然後繼續穿衣服。
“我沒問題的。”他封好宇航服的密封口,說道。
三個人依次通過密封艙門,進入了外麵的高度真空。他的內心感到一陣失落。他喜歡星星,卻討厭太空,特別是巨大到讓人反胃的宇宙中那片幽深的黑暗。貝利撒留的肌肉感受到微弱的磁場拂過,那是十分之一光年外的斯塔布斯脈衝星。僅憑人類的天然肉眼,他也可以看見四千顆星星。繁星之間,是浩瀚無垠的虛空。如果打開視覺增強植入模塊,開啟望遠模式,他能看見的星星數目會是現在的五倍。但星星之間的空間也將被放大,平添許多杳無人跡的虛空。看著這整個宇宙,感覺就像在神遊:你不僅僅是知道它乃是一片虛空,而且自身就是這片虛空的一部分。
他用戴著手套的手指從口袋裏掏出那枚紐扣,讓它飄浮在巋然不動的“木塔帕號”飛船旁邊。
“木塔帕號”上耀眼的探照燈光打在他們身上,將宇航服的手和胳膊部分照得雪亮。數公裏之外,太空中停泊著另一艘戰艦,艦首正對著“木塔帕號”艦身中部。伊坎吉卡少校和那個憲兵一人抓住他的一隻上臂,從“木塔帕號”上一躍而出。三個人飛身縱入虛空,貝利撒留的胃劇烈收縮,拚命忍住才沒大叫出聲。
沒有往返飛行器,沒有導索。什麼都沒有。
伊坎吉卡和那名憲兵就這麼徑直躍了出去。他已經嚇到動彈不得,因而倒也沒有幹擾他們的前進。他的身體一直繃得緊緊的。那兩個人用冷凍氣體噴射器修正著飛行路線,他能感受到輕微的推力。估計還得有個幾分鐘,他們才能到達對麵那艘戰艦。他飛翔在太空之中,除了自己粗淺急促的呼吸聲,耳畔隻有那兩人的宇航服跟他的宇航服相互摩擦發出的嘎吱聲。
這是些什麼人啊,竟然在太空船之間跳來跳去?他想不出有什麼必要非得做這樣的機動動作。不可能是為了在他麵前炫耀,他們沒有那麼把他當回事。也許這是一種新式的軍事機動動作,或者是艱苦條件催生出來的新戰術。或許這隻不過是一種純粹為了與眾不同、出人意料才發展出來的戰術動作。既然第六遠征部隊有了新式的武器係統和推進技術,在戰鬥中引入新的戰術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你要對付的是牌手,而不是他手中的牌。
他們正在接近對麵那艘戰艦。他們飛向一個暗淡燈光映照下的小船塢,聚光燈一直跟著,照在他們身上。他感覺到幾股更大的力道,身體隨即開始倒轉過來,雙腳朝向目的地。下方出現了一個強磁場。
“彎曲膝蓋,阿霍納,不然你的腳踝會骨折的。”頭盔無線電中傳來伊坎吉卡的聲音。
他照做了。腳下的飛船以駭人的速度變大。他明白自己身體攜帶的動能並不多,僅僅來自於開始的那一跳。但內心本能的恐懼仍舊難以抑製。視野中無垠的太空漸漸被飛船遮蔽,他們的腳撞在了船體上,緊緊卡住。耳邊是自己粗重的呼吸聲,膝蓋顫顫巍巍。
“見鬼,阿霍納!”伊坎吉卡喊道,一把將他推進密封艙門,“怎麼好像你從來沒有進過太空一樣!”
貝利撒留臉上一熱。他們依次通過了密封艙。
“這就是‘瓊萊(1)號’,”她一邊對貝利撒留邊說著,一邊脫下頭盔,“一艘很棒的戰艦,可以代表遠征軍的飛船水平。”
他們雙手攀緣著向艦橋移動過去。貝利撒留行進緩慢,但好在沒有發生什麼事故。他們見到了“瓊萊號”的指揮官魯辛迪上校,一位年近四十的女人,皮膚黝黑,額頭上有六道橫著的疤痕。艦橋居然有重力,在普遍的零重力環境中顯得十分突兀。六個棺材大小的加速艙以一定角度斜立在艙壁上,上麵還有覆蓋著厚玻璃的小窗戶。如果加速艙裏有船員的話,小窗應該就是他們朝前看的位置。魯辛迪在艦橋中間調出一幅全息顯示圖。貝利撒留腳上穿著磁力靴,隻能笨拙地拖著腳步靠近,凝視著全息圖。
“能讓我看看外麵的景象嗎?”他問道。
上校手指劃動,全息圖縮小了,“瓊萊號”變成隻有一個圖標那麼大。圖上隻有一艘其他飛船:“木塔帕號”。
“範圍請再擴大些,”貝利撒留說,“讓我看看整個遠征軍艦隊。”
上校又動了動手指,全息圖中心的兩個圖標繼續縮小,新的圖標出現在圖像邊緣。遠征軍艦隊的左翼是懸浮在太空中的指揮巡洋艦“尼亞力克(2)號”,旁邊是“朱巴(3)號”“戈布德維(4)號”以及“巴特布奇(5)號”。幾艘戰艦成編隊排列,在圖上顯示為橙色的圖標。艦隊的右翼艦隻顯示為淡黃色:裝甲巡洋艦“林波波號”、下轄“奧姆卡馬(6)號”、“法紹達(7)號”和“坎帕拉(8)號”。艦隊的中軍是戰列艦“木塔帕號”,周圍拱衛著“瓊萊號”“恩登(9)號”和“皮博爾(10)號”。
一股微電流從他的電肌塊發向大腦,觸發了白癡天才模式。語言和情感的微妙之處被幾何和數學解讀的疾風暴雨衝刷得一幹二淨。用量化的方式看世界讓他自在安心。隻是身邊這些人的存在讓他很不舒服。他們不喜歡他,也許吧。之前他感受到的那些情感線索、社交關係已經退到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幾何與數字方麵的洞見,如暴風雪般襲來,徹底吞沒了前者。
全息圖上的遠征軍艦隊變成了一張由動量、距離、質量和光速等信號組成的網絡。“林波波號”“木塔帕號”和他放出去飄浮在真空的紐扣,三個點的位置正好形成了一個狹長的三角形。貝利撒留頭腦中閃過各種數字。從“林波波號”到“木塔帕號”,二百五十公裏。
他吞吞吐吐地說:“我需要了解你們的飛船是怎麼利用蟲洞的:飛船打開一個黑洞有多快?在黑洞裏能走多遠?穿越黑洞有多快?穿越之後重新出現時,飛船係統恢複工作又有多快?”
貝利撒留發現無人回應他的目光。在白癡天才的狀態,與他人目光接觸,就好像盯著一盒子拚圖碎塊看,讓他大腦中的模式功能變得超級活躍。對方的麵部表情仿佛在飛速變化,從反對到讚成,不斷循環,攪成一個極速旋轉的旋渦。上校的手指動了動,飛船隨即嗡嗡作響。腳底下的重力猛然增加。
永遠渴求著邏輯推理與抽象分析的貝利撒留的大腦開始解析“木塔帕號”這個艦名。腦中植入的百科全書增強模塊可以給他提供各種資料,他想要多快就能多快給他。木塔帕,由大津巴布韋的一位王子創辦的中世紀王國。木塔帕王國很快就超過了它的鄰國,甚至其母國,強大的形象,強大的象征。他希望能夠對此做出量化分析。
聯盟挑選了一些好名字。比如奧姆卡馬,那是一個王朝的名字,統治烏幹達直至19世紀。這個王朝沒有被現代化的曆史巨輪碾碎,而是隨之滾滾前進,因而擁有強大而深遠的文化影響力,甚至一直延續到撒哈拉以南聯盟形成的時代。用一個具有強大象征意義的文化資產來給一艘戰艦命名。這種象征意義強大到值得去犧牲嗎?他不想讓他們犧牲。
他要怎麼才能量化這種象征效果?應該有專供社會學使用的邏輯算法。他應該編製一種這樣的算法。文化傳統推動著遠征軍,在全體國民身上烙上了它的印記。他們被自己的文化傳統包裹著,由此生出無限的自信。連貝利撒留也隻能羨慕這種自信。
恩登,這是19世紀丁卡人(11)的一位先知。丁卡人的創世神名字叫作尼亞力克。巴特布奇則是中世紀一個圍繞大湖(12)地區而建的帝國。戈布德維是南蘇丹著名的阿讚德王的名字,字麵意思是“把人的腸子扯出來”。
強大的形象,強大的象征。聚合政府怎麼就沒想到呢?聯盟的戰艦身負這些名字已經好幾十年了。這也是數學,這是關於人的物理學。情感和愛國的能量倍乘在一起,就產生了精神上的動力。
伊坎吉卡推了推他,他卻呆立在原地。
“要不要這個,阿霍納?”她說了好幾次。
一個計時器,一部數字計時器。她拿著一部數字計時器,在她的手中,她的手在他麵前。他在白癡天才狀態下。記得要有禮貌。
“謝謝你,”他說,“我能清晰感知時間。我不需要這個。謝謝你。”
他沒有看她的眼睛。她已經走開了,邊走邊搖頭。重力在增強。
“我們的飛船現在就是由暴脹子驅動器在推進?”他問道。
“是的。”伊坎吉卡說。
他沒有察覺到磁場發生任何變化。這意味著暴脹子驅動器不與電磁力相互作用。
“我們現在的重力低於半個g(13)。”貝利撒留說,“暴脹子驅動器能加速到什麼級別?十個g?二十個g?”
軍用級核裂變推進導彈的加速能力可以保持在四十個重力加速度,而且能在這種情況下跟蹤並命中做出躲避動作的目標。
“還要大得多。”她說。
快到導彈也追不上?但就算有精神動力和高速飛船,最終還是無關緊要。聯盟一共隻有十二艘飛船。聚合政府的一個中隊就擁有那麼多艘戰艦,而聚合政府有好幾百個中隊。數學總是這麼無可否認,令人安心。而且遠征軍除了暴脹子驅動器技術之外,其他技術大都是半個世紀以前的過時貨。悲哀啊,為聯盟感到悲哀,但這是他們自己想要的,文化傳統的動力推動著他們一往無前。
“瓊萊號”停止加速,旋轉了一百八十度。重力一下子變得像要把人壓扁,貝利撒留的膝蓋止不住顫抖起來。他一個踉蹌撞在牆上,努力不讓自己暈過去。因為無法再度集中注意力,白癡天才的狀態變得時斷時續。伊坎吉卡和魯辛迪正站在那裏笑話他。他的內心燃起了怒火——不是對她們,而是對他自己。
“這才剛到1.5倍的重力加速度,阿霍納。”伊坎吉卡說。
他不想失去剛才腦海中的那些數字。從“木塔帕號”到“林波波號”,坐標,以秒計數的時間,重力加速度。記住那些坐標。他蹲下身子,靠牆坐住,把頭埋進雙膝之間。他不在乎別的人會怎麼看他。
34.7秒後,巨大的壓迫停止了。嗡嗡聲停了下來,重力也一下子消失了。“瓊萊號”已經跟“木塔帕號”拉開了一段距離,現在足夠安全,可以打開蟲洞了。魯辛迪上校手指連彈,加速艙中的值班人員關閉了飛船的係統。
“你想躍遷去哪兒?”魯辛迪用口音很重的法語問道。
“朝銀河係南的話,你們能跳多遠?”他問道。來上這麼一次傳送,他就能知道遠征軍打開的蟲洞的距離和精度了。
魯辛迪默不作聲,又做了幾個手勢,給出命令。貝利撒留拖著腳上的磁力靴,笨拙地湊上前去。全息圖上,外部全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內部係統的各種圖形。圖上可以看到“瓊萊號”的磁線圈正從艦首向外擴展。貝利撒留雖然身處飛船內部,都能感覺到那磁場的牽引力。磁場強度上升到了九千高斯(14),一萬,一萬四千,二萬一千。
貝利撒留感覺手臂和胸部一陣刺痛。
六萬,十萬,二十八萬高斯。
已經超過了工業和醫療用的磁場強度。
強度達到四十萬高斯的時候,電磁場和引力場就會開始以奇妙的方式相互作用。隻要能恰當設置磁場方向,就可以讓時空本身開始“嘎吱作響”。讀數在五十五萬高斯的地方停了下來,穩住。
飛船的正前方,一個時空口袋鼓脹出來,跟空間的三個維度都成直角。半熔化的時空腫脹得像隻探出來的手。磁場的形狀和焦點推動著這根時空管道,橫跨那些聽任自己被卷曲的空間維度。這隻手落了下來,手指環繞,把一段空間握在手中,一架狹窄而不穩定的橋隨即出現,伸向遙遠的銀河係南的某個地方。指示燈變成了綠色。他們打開了一個蟲洞。
接下來是有危險的部分。“瓊萊號”六百米長的艦身裏麵擠滿了核聚變和核裂變電力係統,以及那台暴脹子驅動器。飛船上所有能夠移動的部件都不得不固定起來,因為在人工打開的蟲洞裏,意外隨時可能發生,就像一支筆尖朝下立著的鉛筆隨時可能倒下一樣。黑洞跟絕對零度之間的溫度差處於不確定性原理的範圍之內。無論與周圍的環境發生何種相互作用,都很可能會導致這個環境的徹底崩潰。這跟通天軸那種永久蟲洞十分不同——即使發生了人為錯誤,永久蟲洞也絕不會將穿越其中的飛船吞噬掉。
“瓊萊號”的主係統和備用係統都關閉了,儀表盤上顯示戰艦外麵的溫度為105開爾文。遍布船身的紅外輻射儀打開了,它們的作用是對“瓊萊號”的黑體輻射進行處置,將其冷卻至幽冥般的低溫,從而不會幹擾到蟲洞。他的腳感覺到十分之一個重力加速度的壓力,時間持續了2.31秒。“瓊萊號”推進到了黑洞的史瓦西喉(15)。
然後,飛船裏又變成了失重狀態。貝利撒留屏住了呼吸。蟲洞會在他們身後關閉。儀表指示燈又變成了綠色,一記鐘鳴聲響起。軍艦顫抖著,各種係統又上線工作了。全息戰術圖跳了出來,從上麵看不到周圍有任何其他飛船。圖像邊緣出現了各種數字。
“三分之一光年。”魯辛迪上校讀道。
正是顯示在全息圖底部的數字。
“這是‘瓊萊號’的躍遷極限嗎?”貝利撒留問道。
伊坎吉卡走了過來。他盡量不去看她的臉。
“這是船員敢於躍遷的極限,哪怕是在最緊急的情況下,”她說,“那三艘主力艦可以稍微跳得遠一些。”
“我想再問一次:‘瓊萊號’需要準備多久才能進行穿越飛行?”貝利撒留問道。
“主係統和備用係統都要上線,來做星際定位、戰術評估、目的地最終望遠勘察。在整個係統關閉之前,這些都要完成。”少校解釋道,“如果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船員隊伍,可以在五到十分鐘之內做好準備。”
“如果盲躍呢?”他問道。
“什麼意思?”伊坎吉卡說。
他低頭注視著腳上的磁力靴,同時凝神感受著靴底的磁體。
“沒有確切的定位,”他說,“隻靠推測來規劃目的地。”
“那太愚蠢了。”
“如果你們是倉促之中,時間來不及呢?”
他等待著。伊坎吉卡走了過來。
“看著我。”她終於開口說道。
他等待著。少校伸出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服。白色的衣服襯托出她黝黑的皮膚。力道十足。她晃了晃他,然後猛地將他拉近,“我說看著我,阿霍納。”
“我做不到。”
“你在搞什麼鬼?”她喝問道。
“我不能看著你。做正經事情的時候,量人需要花費巨大的數學能力。我們可以通過關閉大腦的其他部分來打開天才級的數學能力,比如語言、感官輸入、社交。這是一個權衡取舍的過程。我現在已經進入了白癡天才的狀態。”
他站著不動,沒有看她,卻在默默計算著全息圖上顯示的各種數字信息。三分之一光年——並不是三分之一,應該是0.32977145光年。如果再做更多的望遠觀察,數值將更加精確。
“你說什麼?”伊坎吉卡追問道。
“我不能看著你,”他原樣重複了剛才的回答,“做正經事情的時候,量人需要花費巨大的數學能力。我們可以通過關閉大腦的其他部分來打開天才級的數學能力,比如語言、感官輸入、社交。這是一個權衡取舍的過程。我現在已經進入了白癡天才的狀態。”
她嫌惡地鬆開了他的衣襟。“你當不成騙子,”她說,“也當不成戰士。”
“我的確是個糟糕的戰士,”他說,“但我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騙子。而且,我也許可以幫助你們穿越偶人主軸。”
“怎麼幫?”她喝問道。
“盲躍的事怎麼說?”他問道。
“上校?”伊坎吉卡揚了揚手,“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魯辛迪上校穿著磁化鞋側身走了過來。“你想知道些什麼?”她問。
貝利撒留不耐煩地重重噴出一口氣,“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不做星際定位,‘瓊萊號’穿越到指定目標地點的能力又會如何。用推測的手段、航位推算法?”
貝利撒留覺察到上校有些不耐煩,甚至生氣。也許還有其他情緒,他搞不清是什麼。在白癡天才的狀態下,如此之多的社交信息仿佛瘋長的雜草,讓他無法穿行。魯辛迪環抱著雙臂——那個姿勢代表什麼意思來著?
“‘瓊萊號’當然可以不做星際定位就打開蟲洞,”魯辛迪說,“但那樣做沒有什麼意義。到了需要撤退的時候,指揮官肯定已經有了完整的星際定位。鑽進打開的蟲洞,從另一頭鑽出來——撤退行動就此完成。在後麵追擊的敵人不太可能也打開一個蟲洞口,離我們還非常近,處於交火距離。這種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計。”
全息圖底部顯示的數字令人昏昏欲睡。貝利撒留用這些數字算了又算。幾處舍入誤差讓他明白了“瓊萊號”導航軟件的設置情況。
“我想讓‘瓊萊號’關掉導航望遠係統,然後再打開一個新的蟲洞。”他說。
“為什麼?”上校問道,接著又用另一種語言說了些什麼。他一直在想他們的口音。他們彼此之間說話的時候,講的是紹納語(16)嗎?語言的變換給他的大腦帶來了一個新謎題,他仔細琢磨著,就像麵對的是一個密碼學問題。要開發一套“文化代數學”理論也許並沒有那麼難。伊坎吉卡站到了他麵前。
“這樣做我們能得到什麼,阿霍納?”她喝問道,“我覺得你是在耍我們。你的所謂魔術不過是揮手比畫幾下,耍點花招而已。” 她明明白白地表達了她的感受。貝利撒留喜歡這樣,能夠幫助他理解。原來如此:她揮手的姿勢意味著惱怒。“你要我們打開蟲洞,到底去哪兒?”她問。
他扯掉外套上的一顆紐扣,那顆紐扣被全息圖照映成五顏六色。
“之前我穿上太空服的時候,揪掉了一顆這樣的扣子,”他說,“我把它丟在了‘木塔帕號’外麵,然後跟著你們來到了‘瓊萊號’。那顆扣子裏有一個磁阱,可以屏蔽熱振動。磁阱中是幾十個粒子,與這顆扣子裏的粒子構成量子糾纏。”
伊坎吉卡的手比他還大,伸到他的手腕旁邊,握住那枚紐扣,舉在他的麵前。她的臉也湊了過來,臉上複雜的表情讓他不由得向後退縮。緊接著,一支手槍的槍管頂到了他的眼前。
“你在‘木塔帕號’上留下了跟蹤裝置?”
她怒不可遏,怒火在她身上彙聚,幾乎就要噴了出來。他不喜歡離人如此之近。豁出去了,說就說吧。
“它們隻是糾纏的粒子,”他說,“並不是什麼跟蹤設備。除非我特意那樣使用它們。從來沒有人嘗試過那麼做。我想看看能不能不借助你們的導航係統讓‘瓊萊號’回到遠征軍駐紮的位置。”
“還有誰有這些東西?”她喝問道。
“沒有誰,”他說,“它們是糾纏粒子。隻會成對出現。”
她放下槍,輕彈貝利撒留外套上的其他紐扣,“這些都是糾纏粒子?”
“一對對的都是。”他說。
“還有誰擁有這種追蹤技術?”
“這不是什麼追蹤技術,”他說,“我甚至不知道這辦法是不是行得通。”
她放開了他,發出憤怒的聲音。
“你說你想要魔術。”他說。
“我想要的是到偶人主軸的另一端去!”
“那就別耽誤我做事。”
伊坎吉卡和魯辛迪用紹納語交換著意見——他覺得她們講的是紹納語。伊坎吉卡走過來,脫下了貝利撒留的外套。這樣一來,除了手裏的那一顆之外,他再沒有紐扣了。
“我好不容易才做的這些扣子。”他說。
“你打算怎麼做?”她問。
“量人在神遊狀態下能夠感知量子場,也包括那些鏈接糾纏粒子的量子場,”他說,“也許我可以循著這種糾纏鏈接,以此為導向,穿越蟲洞。”
“你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她問。
“誰也沒試過。現在,你們可以關閉導航係統了嗎?”
主顯示屏與上麵眼花繚亂的數字一起熄滅,隻留下飛船內部狀態儀表板還亮著。
“你能把飛船開起來嗎?”他問道,“我知道我們在哪兒。”
“不看導航顯示,你不可能知道。”上校說。
“在你關掉它之前,我已經全都記住了。”
上校彈彈手指,重力加速度又回來了。一半,四分之三,全部。伴隨著飛船角度的變化,他們在三維空間裏做出各種旋轉、加速動作。想讓他迷失方向。增加難度。無所謂,他擔心的不是這個。
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得進入神遊狀態,完全不做自己。他已經快要進入不是自己的狀態了。白癡天才關閉了各種認知功能,通過暫時削弱他的大腦功能,令他不再是他。但進入量子神遊狀態,意味著不做任何人。他已經逃避神遊很多年了,還為此背井離鄉。他的手在顫抖,他把手夾在胳膊下麵。大家都在看著他。看著他。別看著我。
“我需要蟲洞磁感線的數據顯示圖,越詳盡越好。”他輕聲說道。
眼前的儀表板消失了,代之以一組圖表,衡量著磁場的強度、形狀和質地。
“我能改改設置嗎?”他說,“我需要讓數據顯示得更有邏輯性。”
“瓊萊號”的電腦為貝利撒留臨時創建了一個有限訪問賬號,他開始重新配置顯示圖設置。改動之後,顯示圖達到的信息數量級遠超飛船導航員所需。磁感線的溫度、曲率、磁極化、電阻和表麵自由電荷密度的模式,通過複雜的幾何結構相互反映。
重力再度消失,相對速度為零。伊坎吉卡站在他身旁。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阿霍納?”她問。
“我需要你們耐心等待,起碼在我要求你們這樣做的時候。”見伊坎吉卡氣呼呼地哼了一聲,他又補充道。
在量子理論發展的早期,科學家和哲學家曾經激辯過量子波函數的含義,想搞清楚量子態疊加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一個電子可以同時通過兩條狹縫,這意味著什麼?原子級別的現實世界很不確定。這種不確定性最著名的體現就是薛定諤的貓,那隻糾纏在量子世界不確定性之中的貓,其命運取決於觀察者的觀察動作。有些人認為,假設那隻貓真的同時處在雙重狀態——既不死也不活——那麼它就變成了量子世界的一部分,因為量子就是這樣的雙重狀態。還有人認為,是實驗本身創造了新的多重宇宙,其中一個宇宙裏的貓死了,而另一個宇宙裏的貓還活著。這兩套理論都附帶了太多的條條框框,誰也無法最終勝出。如果真的有一方已經勝出了,那麼量人和貝利撒留可能就永遠不會被創造出來了。
人們發現,意識是造成量子係統坍縮成明確結果的元素。量人項目因此而誕生。作為主觀具有意識的生命,人類永遠無法直接觀察量子現象。隻要他們一看,貓要麼是死的,要麼就是活的;電子在實驗中要麼通過這條狹縫,要麼通過那條狹縫。隻要人類一靠近,疊加和重疊的可能性就會消失。人類的意識將可能性轉變成了現實。量人項目的目標,本來是通過改造,讓人類能夠隨心所欲地舍棄自己的意識和主觀,從而避免量子現象因為人類的觀察而坍縮。
在貝利撒留看來,進入量子神遊狀態的過程仿佛是站上一麵跳板,獨自站在水麵之上,投下自己的倒影。自我的熄滅和消融就在水中等待著。向下一躍,就變成了環境的一部分,變成太空、星星和虛空,不再是具有體驗能力的主體。向下一躍,就意味加入那樣一種類事物的行列:隻是一係列規則和算法的集合,而沒有心智,就像昆蟲和細菌。進入神遊狀態,自己就變成了包含在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之中的無數事件之一。他的胃一陣痙攣。他已經站在了跳板上,凝視著自己在水麵上的倒影。已經有十年了,他沒有從跳板上躍下過。
能夠進入神遊狀態的量人屈指可數,還要付出巨大的艱辛才行。對於他們來說,嘗試進入神遊狀態就像在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崖。經過改造的本能可以幫到他們。遺傳學家已經加強了模式識別和好奇的本能,通過一代代基因工程改造,讓這類本能變得像自我保護的本能那樣強烈。
在貝利撒留身上,他們超越了原本的目標。他對學習和理解的渴求,跟他的自我保護意識一樣強烈。他不能依賴自己的本能,它可能讓他送命。無法預料當意識熄滅之後,他的大腦會做什麼。神遊對他來說是危險的。但是,此時此地,已別無選擇。他需要一個正常運作的量人,而身邊除他自己之外再沒有另一個。他引發了神遊狀態。就像關掉了一個開關,貝利撒留這個人不複存在。
(1)南蘇丹的一個省。
(2)非洲丁卡人的造物主。
(3)南蘇丹的一個省。
(4)曆史上的南蘇丹國王。
(5)非洲大湖區王朝。
(6)曆史上的烏幹達王朝。
(7)在今蘇丹。
(8)烏幹達首度和最大城市。
(9)非洲丁卡人先知。
(10)南蘇丹城市。
(11)南蘇丹的主要族群。
(12)東非大裂穀中和裂穀周圍一係列湖泊的總稱。
(13)地球表麵重力。
(14)磁場強度單位。
(15)黑洞位於視界之內的部分會與宇宙的另一個部分相結合,這個彎曲的視界就是史瓦西喉。
(16)剛果語係班圖語族的一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