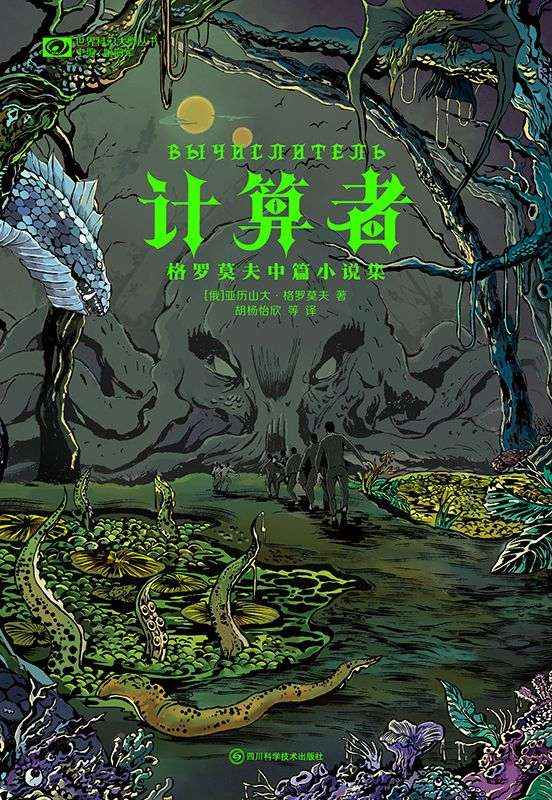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十一章 二
到了早上,喬布的身體已經所剩無幾:隻餘皮膚、骨頭和衣服的碎布,大半個身子被拖進了沼澤裏,覆著一層薄薄的褐綠色。顯然,再過幾天,便隻剩長條狀的土墩標記著這個安靜的、因不為人知的罪行被判決的書記員的葬身之地。
這種肉食性的蘑菇並非隻有一個,似乎還有很多隱藏在前麵,並且並不是每一處都有土墩這樣的標記。厄溫把繩子纏在斷了的木杆上,像投擲魚叉一樣地往前一扔。無論木杆是刺進沼澤地還是漂浮在沼澤麵上,每當有白色的細絲纏上它,他就要及時地把繩子往回拉,以免失去木杆,即使它隻剩下半截。半天過去,兩個旅人向南繞了一大段彎路,終於成功地繞過了危險的地帶。
更糟糕的是,颶風弄亂了沼澤原來的模樣,原本一眼便知藏不了野獸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冒著沼氣的新的一片爛泥地。水藻一動不動地鋪在沼澤上,被冒泡的淤泥帶分割成一片片區域,像是緊密相鄰的浮冰群。他們行動遲緩,不得不尋找或多或少更結實些的地方作為跨越不同區域的渡口。他們常常停下來,像棋手一樣提前好幾步計算要走的路。
“不過,很快就能知道哪裏是薄弱點了。”厄溫安慰道。
而當克莉絲蒂在看似堅固的地方突然沉下,一路陷到胸口時,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若是沒有那半截木杆,她已經從頭到腳整個陷入沼澤。
兩隻蝌蚪就是他們今天所有的收獲,他們老老實實地均分了。克莉絲蒂試著去抓水藻裏亂竄的小蝦,但它們的味道極為令人作嘔,幾乎無法入口。
他們一天沒走多遠。在厄溫的懷裏入睡前,克莉絲蒂已經平靜地想象著,饑餓會在幸福群島顯現在天邊的迷霧中之前,將他們殺死。又或許,地圖是故意騙人的,馬尾藻沼澤根本不是通向群島,而是直通開闊的海洋?誰能弄明白,為什麼沼澤沒有被海洋衝刷幹淨呢……
第二天,他們很走運。當天空被第一縷曙光映紅時,厄溫碰見了曾遠遠見過的一種敏捷的群居動物的窩。他在這隻生物一躍而起、飛跑離開之前成功用刀殺死了它。
他們在日落前停下休息了很久,因為他們又遇到了灌木叢。厄溫設法點燃了一小團篝火,勉強把他們的獵物微烤了一下。到了晚上,兩人終於享受到了鮮嫩多汁的肉。他們飽受折磨:經常需要進食但每次隻能吃到一點點,吃下之後,胃也仍會如刀割般疼痛得痙攣起來。
次日,他們在原地度過,把抓到的獵物吃了個精光,仔細地將含有幾丁質的外殼也刮了個幹淨。他們似乎連骨頭都不願剩下,可惜這種生物沒有骨頭。
然後他們相擁而眠,在睡夢中敏銳地傾聽著沼澤的一舉一動。厄溫從女人身上解下囚服的碎布時,克莉絲蒂幫了他一把。他們瘋狂地愛撫著彼此,在一片冒著泡的黝黑水窪裏翻來覆去。兩人交纏的身軀將沼澤的浮毯壓得凹陷,他們的下方就是無盡的深淵,他們吸食著沼澤腐爛的毒瘴卻對此無知無覺,隻有一件事讓他們對自己感到驚奇:他們兩人竟然還有性愛的精力和欲望。
“我們會到達幸福群島的,對嗎?”
“對。剩下的路程不多了。”
“之前我不相信……現在我信了。聽著,我想問你一件事……隻不過你要誠實回答……”
“什麼事?”
“首先,你要保證你會誠實地回答。”
“我是個誠實的刑犯。”
“停下……”
“然後是誠實的兩棲動物。再在水窪裏睡兩晚,我們都要長出鰓來了。”
“你別開玩笑,你認真地保證……”
“我保證。你想問什麼?”
“你從頭到尾都在撒謊,對嗎——從最開始的時候?那些關於你是強大的計算者的事情,你是怎麼做出最理想的計算的……你是想安撫我,對嗎?”
她等待著回答,但沒有等到。
“為什麼不說話?你是在可憐我嗎?”
“是。”厄溫悶聲說,“我都是胡說八道的。你生氣嗎?”
“不,你在說什麼呢。我很高興。愛上一個可以計算出你的愛並且把它納入方程組的人,很可怕,不是嗎?”
“是。”
這個夜晚異常美妙:晴朗,而又溫暖。沒有來襲的蛇,沒有顯示舌怪靠近的微微顫動的泥沼。這天夜裏,他們明白了,沼澤也可以是慷慨的。
早上,克莉絲蒂問:“我要像之前一樣走前麵嗎?”
“這樣比較安全。”厄溫歎了口氣,回答道,“即使我不是計算者,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不過如果你想的話,我們就輪流帶頭。”
“好吧。”克莉絲蒂擺擺手,笑道,“你就在後麵慢悠悠地走著,欣賞我的彎腿。”
“是直的……”
越往東走,沼澤裏的生物就越少。有好幾天,他們沒有碰上任何活物。尋找蝌蚪讓他們疲憊不堪,卻沒有任何收獲。就連黏液團,也隨著帶狀水藻的消失而離他們遠去了。隻有灰色的飛禽像之前一樣在高空盤旋,緊追不舍,等待著自己夢想成真的一刻。
離開腐爛淺灘的第十九天,克莉絲蒂開始抱怨自己的鞋子擠腳。看來,饑餓和鹽水開始讓她的腳腫脹起來。厄溫費勁地將她的鞋子脫了下來,藏在了更像是一團泥的背包裏。第二天,他感覺自己也開始發腫了,他脫了鞋,然後,為了不負擔多餘的重量,把兩雙鞋都扔進了最近的水窪裏。
“最好還是赤著腳,這樣才能活下去。”他解釋自己的舉動。
第二十天,一隻巨大的舌怪在離他們大約五十步的地方炸開了沼澤的表層。它高高揚起的紫色觸手跟電視塔一樣高。當它拱起浮毯,橫掃自己周圍的沼澤時,在藻毯上揚起了如同風暴的巨浪。逃跑毫無意義。“別動!”厄溫喊道,盡管他還沒開口,克莉絲蒂就已經被嚇得渾身僵直。觸手摸索了一圈,在比克莉絲蒂高一些的地方揮過,碰到了靜止不動的厄溫,並將他按下了沼澤,但沒抓住他。也許,在靠近自己核心的地方,它的感覺不是那麼靈敏。
他們爬出了危險地帶,爬出來時,一邊顧忌著浮毯的輕輕搖晃,一邊因腐爛水藻的微微顫動而感到害怕,常常停下來,靜止很久。當他們成功爬到安全距離的時候,舌怪察覺到獵物一個不剩,狂怒地朝四麵八方揮舞觸手,瞬間便將沼澤的浮毯變成了難以越過的泥潭。他們逃過一劫,久久地躺在溫暖的鹹水水窪中,沒有力氣起來繼續上路。
“你還記得我們那晚嗎?”克莉絲蒂的聲音幾不可聞。
“當然。”厄溫沙啞地說,“難道能忘掉嗎?”
“沼澤將它投給我們,就像是扔下一點施舍。我們再也不會有那樣的夜晚了。”
“也許吧……至少在沼澤裏不會再有。再等等,等我們到了幸福群島……”
“到了那裏我就變醜了,到了幸福群島,我會腫成醜八怪。即使我洗幹淨身上的汙泥,也會有膿皰。你會連看都不想看我一眼。馬尾藻沼澤不想放過我們。每晚,我都會因為噩夢而尖叫。”
“你會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在我看來,這些汙泥永遠不會被洗淨……”
“一切都能被洗淨,相信我。我們會忘記過去,就像忘記一個愚蠢的夢。而沼澤會是我們第一個遺忘的,我向你保證。”
“我不能。”克莉絲蒂搖搖頭,“你也不能。”
“誰知道呢。無論如何,我們都盡力了,不是嗎?”
第二十一天,一株不認識的肉食性植物把克莉絲蒂從身邊放了過去,卻猛撲向厄溫。它看起來更不像植物,而像是一團纏結在一起的藍黑色的蛇。他成功地割下身上的藤須,鬆開了顯然被植物當成了美味獵物的背包。
也是這天,厄溫發現了一株鞭藤並將它割下一段,與此同時卻失去了匕首——它被勃然大怒的斷裂藤蔓扯進了沼澤——還差點失去了手腕。他並沒有多惋惜:隻有從來沒蹚過馬尾藻沼澤的人會認為刀比鞭子珍貴。
第二十三天,厄溫發現用四肢爬行似乎要比兩條腿走路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他為什麼沒有早點知道呢?……隻是不可思議的意誌力讓他強迫自己站起來,靜待自己眼前的黑暗散開,然後從黏稠的泥濘中撕下水鞋的碎塊,在一天內,他將無數次重複這個動作。
吧唧。吧唧。吧唧。
饑餓性的昏厥以可怕的規律性重複著。當克莉絲蒂倒下時,厄溫意識到了這個事實,但仍然繼續往前走,直到被四仰八叉的克莉絲蒂絆倒,自己也倒了下來。當厄溫倒下時,克莉絲蒂會試著向前走一段時間,但拽繩子毫無用處,然後她隻能不樂意地走回來。他們相互攙扶著站起來,想著,如果沒有相互支撐,他們恐怕沒法自己起來。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想離開彼此。
也許,隻需一條饑腸轆轆的蛇,就能毫不困難地殺死他們兩個。但沒有蛇。隻有禿鷲,在晴朗明媚的天空中不停地盤旋。
“好了。”克莉絲蒂停下來,喘息著,她沒有倒下僅僅是因為她撐著一截木杆,“我不行了。就讓我們這麼死了吧,這樣更好……”
“我們還能走。”厄溫呢喃道,煎熬地忍受著雙腿的交替移動,“我們不會死……”
“我不想活了,不想!”克莉絲蒂無聲地哭泣著。
“你聞到了嗎?”厄溫問道,他動了動鼻子。
“沒有。我該聞到什麼,你說?是什麼?”
“海的氣息。外海的空氣,不是馬尾藻沼澤的。是自由的氣息。生命,堅實的土地,一定還有食物。隻剩下最後一點路了。”
“你出現幻覺了。”克莉絲蒂絕望地搖了搖沾滿冰淩的頭發。但她的聲音很冷。
“我告訴你,剩下的路程不多了。一天,或者兩天。很快就到了。”
“你真的相信嗎?”
“當然。如果空氣透明度高一些,我們現在已經能看到群島之巔了。那是火山口和山巔。”
“而在我看來,這片沼澤沒有盡頭。”
“會有的。我們會一路順風順水。如果我們像第一天那樣精力充沛,本來今天就能到了。現在這樣——得明天。”
“你確定?”
“嗯,或許是後天。這是最糟的情況。好了,走吧……”
“如果後天沒有……”克莉絲蒂深吸了一口氣,往前邁出步伐。
她來不及說完,也來不及尖叫。她腳下薄薄的一層狀似結實的沼澤植毯的植被膜破裂了。克莉絲蒂迅速地陷下了沼澤,像是一塊被扔進水裏的石頭。
這一猛墜濺了厄溫一臉的泥。他打滑了,設法用腳底刹住,雙手緊緊攥著潮濕而滑膩的繩子。在絕望的泥潭的“窗口”,悠悠晃動著泛著油光的水。
“堅持住!”他低聲說,祈禱繩子不會勒破彎曲的植毯,“我在拉!我在……”
他覺得自己在一點點地從沼澤那裏奪回它的獵物,盡管實際上他正被一點點拖向沼澤的陷阱。然後,在泥潭深處,有什麼猛地拽了拽繩子,像是有一尾體型巨大得難以想象的饑餓的魚咬了鉤,然後斷繩輕易地被拉出了泥潭。
有好幾秒鐘,厄溫遲鈍地看著那截斷繩,直到他意識到自己沒有必要逃跑。沒有什麼未為人知曉的泥潭居民,也沒有誰在這裏設下陷阱。由很多段碎布連成的繩子並沒有被咬穿——隻是一個綁得笨拙的繩結鬆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