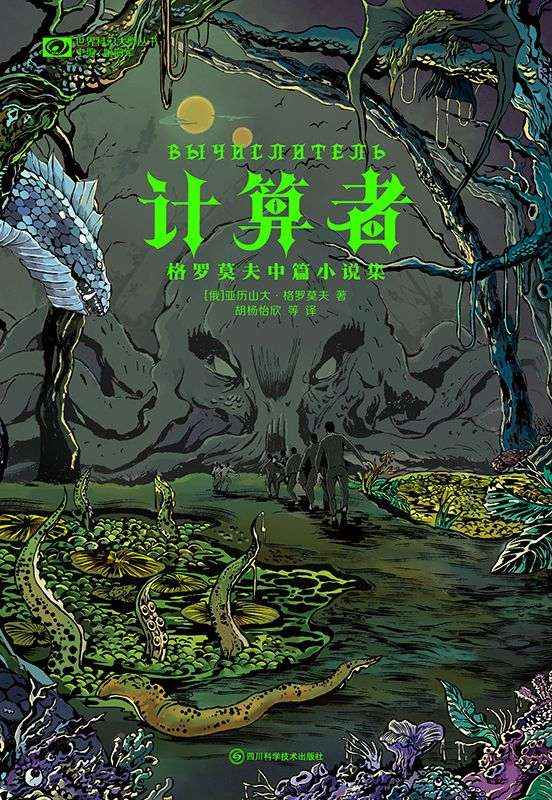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十章 三
一隻灰色的翼獸蹲在小島的邊緣,關切地觀察著幾個人類。厄溫用嘶啞的嗓子喊了一聲,它不樂意地展翅回到空中。它的五個同族懶洋洋地劃過小島上方高高的蒼穹。
厄溫的喊聲吵醒了克莉絲蒂。在更像是餓暈過去的半睡半醒中,她覺得自己好像看到了幸福群島。她從來沒有見過它,但她相信,那就是它。那裏碧海翻波,雪白的細沙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還有海藻,散發著碘味,而不是腐爛的氣息。難道一定要經過跋涉,才能到那裏嗎?隻要閉上雙眼就已足夠……
“你是不會被餓死在這裏的,別指望了。”厄溫挖苦道,毫不憐憫地粉碎了她的美夢,“這些禿鷲不會等我們死透,對它們而言,我們沒有反抗能力就已經足夠下手了……”
又過了兩個晝夜,之前的風浪才又趕著小島往水麵的西邊漂。夜間,三人都沒有入睡,不管小島上的狀況多麼淒涼,他們幾乎全程迎著潮濕的風,敞開自己身上臟兮兮的破布,隻為給小島增加哪怕那麼一點“船帆”;白天,他們睡覺,或者麵朝下地趴著。
第三天的黎明降臨時,他們靠岸了,沼澤地在他們眼裏就像是堅實的大地。他們禁不住想手舞足蹈,想撫摸和親吻腐爛的水藻。喬布又哭又笑。甚至連剛一登陸就被兩條巨蛇攻擊也沒能熄滅他們狂喜的心火:一條蛇被厄溫一鞭抽斷,像根軟爛的麵條;另一條被克莉絲蒂插在尖利的木杆上,她怒喝一聲,將它抖落到那連狡猾的野獸也會被吞沒的窟窿裏。
“幸好來的隻有兩條,而不是五條。”厄溫緩了緩,搖搖頭說,“不然就是它們收拾我們了。”
人們開始恢複理智。漸漸地,他們混沌的頭腦裏浮現出同樣的念頭:相較於剩下的路程,已經獲得的勝利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幸福群島依然無跡可尋,而若非堅持到底,所有的努力都會付諸東流。
克莉絲蒂避開了他的目光。喬布吐了口唾沫,絕望地搖了搖頭。
從欣喜若狂到心如死灰,不過一步之遙,而這一步他們絕不能跨出。
“還剩多少繩子?”厄溫嚴厲地問道,“隻剩下這些了?太少了。斷了的有嗎?把它們綁在一起。我們走成一列。喬布,你走前麵。克莉絲蒂,把木杆給他,然後拿上刀子。我有鞭子就夠了。”
一整天都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他們不得不靠指南針指路,隻希望指南針在此處還能依稀指出方位。這天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因此他們堪堪填飽了肚子:淺淺的水窪裏滿是肥美的蝌蚪。灰色的野獸被甩在身後,未曾碰見舌怪。時而有蛇來襲,但它們連三人的汗毛也沒碰著,沒有造成任何損失。
第二天如同昨日,唯一不同的是,夜幕降臨前,他們終於碰上了幾叢直接長在沼澤上的幹枯的灌木。他們停下來過夜,盡管被雨淋著,但至少不是在水窪裏了。還有一個打火機能用,但篝火沒能生起:濕透的枝條顯然不想被點燃。
就跟昨天一樣,厄溫和克莉絲蒂相擁而眠。兩步之外是咳嗽著、不時發出呻吟的喬布——他今晚第一個值夜。沼澤泛著微弱的磷光。四千萬人踏上這個星球的唯一一片大陸,又將自己的遺骸投入沼澤化的邊緣海,而微小的發光生物對此毫不在意。全能的沼澤甚至能讓他們活得更久,以供自己消遣。
“想起來很好笑,”厄溫低聲說著,撚走克莉絲蒂耳後頭發上粘著的冰淩,她的頭發已不如往昔紅亮,“有時我會覺得這是對的。”
“嗯?你指的什麼?”
“放逐出社會,深淵星的慣例。社會學家至今仍在爭論審判的意義是什麼:是懲罰,還是對其他人的警示;是贖罪,還是反思的機會;又或者,不過是社會對個人的庸俗報複。雖然很奇怪,但社會保障一直很合我的心意。沒有了罪犯——保護了社會免受其侵害,而罪犯究竟去了哪裏,實質上並不那麼重要……實話說,用幸福群島一遊替代光束槍的背後一擊,我過去覺得,這簡直是高尚的人道主義行為!我不是在開玩笑。”
“那現在呢?”克莉絲蒂冷漠地問。
厄溫久久地沉默。
“說說你是怎麼殺掉自己的市政監察員的。”
“你問這個做什麼?”
“隻是想知道。”
“用刀……他鬼哭狼嚎得像頭豬似的……你不想知道為什麼我要殺他嗎?”
“我知道。他把你帶到深淵星,許以金山銀穴、社會地位,實際上是把你送進墮落腐化的魔窟,最後還把你拋棄了,或者送給了別的什麼人。對嗎?”
“你都是從哪兒得知這些的?”
克莉絲蒂覺得,厄溫在回答前似乎笑了笑。“再怎麼說,我終究是個計算者……”
“你算出我們還能堅持多久了嗎?”克莉絲蒂咽著委屈的淚水,問道,“一天,兩天?我不信能撐一星期。”
“我們總會走到的。”他說,“我想去那裏。我們經曆了那麼多,已經足以為過去和將來所有可以想象的罪過贖罪。如果所有的這些都白費了,一切就會變成屈辱,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克莉絲蒂啜泣道。
“你這是怎麼了,小家夥?”厄溫溫柔地撫摸她的頭,“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一切都會好的,你會看見的……”
在連綿不絕的雨中,他們又走了三天,他們用僅剩的碎繩子將彼此綁到了一起,一路上吃蝌蚪、趕蛇、將陷入沼澤的人拖出來。不知怎的,他們在這裏沒有遇見過舌怪,也許是因為沼澤很深,又或許是因為——厄溫不確定地猜測道——底下的軟體動物迎來了某種季節性的“齋戒期”,比如說,可能與繁殖相關。有一次,就在旅人們背後大概五十米遠,眾人剛剛走過的地方隆起了他們十分眼熟的小丘,它在震耳欲聾的聲音中漲破,然而,劈啪作響地衝向天空的不是紫色的觸手,而是褐色的淤泥噴泉,噴了三人一身,浮毯上的洞在剩餘沼氣的作用下,還咕嘟作響了許久。
第四天,蝌蚪變少了,到了第五天,它們完全消失了。值得高興的是,蛇也銷聲匿跡了,還有在水域對岸就十分稀少的鞭藤,在這邊完全不見蹤影。沼澤似乎很堅實。如果不是因為饑餓、虛弱、發炎又難以結痂的傷口……每走一兩百步,他們就停下來,等待眼前搖曳的黑色消散,等待心臟停止狂跳。
克莉絲蒂感覺到自己正在變得遲鈍,而奇怪的是,這並不讓她感到害怕。喬布已經失去了所有對命令提出異議的能力,他順從地走在前麵,沒有換班,日複一日,他的咳嗽愈發嚴重,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呻吟。厄溫沉默,隻偶爾用嘶啞的聲音簡扼地發出稍微往左或往右的命令,擾亂腳下原本整齊規律的腳步聲。
啪嗒,啪嗒。撲哧,撲哧。吧唧,吧唧。
綠藻。褐藻。生機盎然的水藻和衰朽腐爛的水藻,交錯如密密織成的吊床,鬆軟似細細擀開的毛氈。一串串複果——還未成熟的、已經拋出孢子的、已經腐爛了的,像是一個個舊浴球。開裂的水鞋下滿是黏液和氣泡。
沼澤在身前,沼澤也在身後。沼澤在左,沼澤在右,還在腳下。隻有上方——低懸著愁雲慘霧和淒風苦雨混成的湯粥。
傍晚,雨水斜落,風力驟強。這鍋雲雨粥湧動起來,像是有個巨人在用一隻虛幻的湯勺攪動著。平靜了幾分鐘,又突然刮起急驟的狂風。
厄溫第一個停了下來。克莉絲蒂沒聽到他的話,他不得不拽緊繩子拉住她。
“怎麼了?”她喊了一聲。
一陣狂風推得喬布直往後退。
“我們要留在這裏了!”厄溫指著自己腳下,大聲喊道,“這次好像是來真的!”
克莉絲蒂躲避著狂風,指向了前方,那裏沒有漣漪交雜的水窪,而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土墩帶,看起來似乎更幹燥和結實。
“也許那裏更好?”
“我不喜歡這些土墩!”厄溫朝她耳朵喊道。
百依百順、對一切都無動於衷的喬布被他們用繩子拽倒,跟他們一起躺下。天很快暗了下來。夜幕降臨在馬尾藻沼澤,與之相隨的是愈強的風。人們變得難以呼吸。天空中轉瞬間黑雲傾動,濃雲密布,層雲就如團團汙泥。雨水橫斜,劈頭蓋臉地打下。
能做的隻有等待,還有期望風力不會無止境地變強。但風變得愈為猛烈。已經接受在劫難逃事實的人們隻得相互在對方耳邊大喊:“堅持住——風可能會把我們吹走……”
“我在堅持……這颶風是從哪裏來的?從海裏嗎?”
克莉絲蒂聽不清厄溫的回答,但根據他點頭的動作明白了,厄溫的回答是肯定的。
“也就是說,它掠過了幸福群島上空?”
“沒錯。甚至在幸福群島時比在這裏更強。”
“我明白了……隻是活著、能呼吸、走在堅實的土壤上——就已經是一種幸福了,對嗎?”
“沒錯。”
再然後他們連說話也做不到了。狂風的怒號遮蓋了所有的聲音。颶風拔出叢叢灌木,席卷至沼澤上空,劈頭蓋臉地扔下亂七八糟的水藻碎塊和水珠。道道閃電劈在沼澤之上。
這讓人難以忍受,但他們必須忍受住,緊緊地相互依偎,以免凍僵或死去。
狂風持續了整夜,直至早上才開始平息。黎明時分還出現過一次增強的趨勢,但很快就偃旗息鼓,到了中午,攻勢減弱至正常風力。一輪紅日從烏雲中探出頭來,但處於半昏迷狀態的三人仍久久地躺著,一動不動,或者虛弱地動彈幾下,無力起身。
克莉絲蒂第一個注意到了在天空中盤旋的黑色生物。很快,它的周圍就聚集了它的十幾名同族。這些猛禽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從颶風中平複,徐徐降落,搜尋獵物。
不知從哪裏來了幾隻巨大的灰色飛獸,將黑色的生物給趕走了。食腐動物們準備第一個拿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它們用菱形的翅膀捕捉著上升氣流,它們耐心地等待著,似乎毫不懷疑,自己並不需要等待多久。
厄溫呻吟著坐到了水窪裏。緊接著,他嘗試站起來,他成功了。
“站起來……”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讓克莉絲蒂站了起來,然後在她的幫助下拽著喬布站了起來。喬布看起來仿佛隨時就要直直地撲倒在地,像根木頭似的。書記員失焦的目光裏隻表達出:都走開,不要拽著我,我這樣安安靜靜地就很好,為什麼要把我拖去別處呢?
“他不能走了。”克莉絲蒂聲音沙啞地說道,絕望地搖頭,“我暫時也是……需要休息。”
“我走。”喬布夢遊般地嘟噥著,打了個趔趄。
“你看見了嗎?”克莉絲蒂尖叫道,“看見了嗎?”
“我看到了。我們明天早上出發,現在先找個地方過夜。喬布,我們該去那邊,看看那裏。”厄溫用手指了個方向,“那裏,我覺得更幹燥一些。我和克莉絲蒂再收拾點東西。”
喬布機械性地點點頭,鬆開了繩子,他呆愣凝滯,像個機器人似的開始踩著啪嗒啪嗒的步伐走過水窪,往布滿土墩的地方走去。厄溫纏著繩子,目光緊隨其後,一刻不離。
“我的頭疼得像是要裂開了。”克莉絲蒂抱怨道。
“因為氣壓驟降……當然,還有營養不良。第一點會過去的。第二點也是……總有一天。”
“你還指望這個嗎?”
“我相信會的。”
喬布繼續笨拙地、啪嗒啪嗒地朝土墩直直走去。
“為什麼你昨天說,你不喜歡這些土墩?”克莉絲蒂低聲問道。
“因為那裏明明更幹燥,但不知怎麼,卻沒有灌木生長。”厄溫小聲解釋道。
“那可能……”克莉絲蒂欲言又止。厄溫的意圖清晰至極,也隻有因疲憊和饑餓完全喪失思考能力的人才會不明白他的意思。為什麼她會覺得厄溫是個卑鄙的家夥呢?他隻是理智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可卻是完全正確的。隻有這樣,才能在這裏前行——用鮮活的探測器來探測腐爛的沼澤,選擇最弱的人來扮演這一角色,反正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有見到沼澤邊緣的那一天。隻不過厄溫很早就明白了這一點,而她剛才才恍然大悟……
一切都發生在轉瞬之間。離最近的土墩隻剩最後幾步,一圈圈小噴泉攪動了水窪,某種白色的絲線在喬布麵前突然炸開,一瞬間纏上了他的手腳。喬布被猛地一拉,站立不穩,胡亂地掙紮和尖叫起來,聽起來他與其說是害怕,不如說是很驚訝。克莉絲蒂忍不住叫出聲來。
在奔跑中——如果在沼澤裏遲鈍拖遝的邁步可以算作跑的話——厄溫揮起了鞭子。響亮的一擊揮打在白絲上,但並沒有能將它們打斷。第二擊落空了:細線俘住了鞭子,無比輕易地將它從厄溫手中奪走,扯入沼澤。
喬布大喊起來,聽起來更多的是出於恐懼,而不是疼痛。他很快變成了一個白色的繭。他漸漸停止了掙紮,呻吟起來,又抽搐了兩下,最後陷入靜止。
“他……死了?”克莉絲蒂咽了口唾沫,問道。
厄溫點點頭。他們佇立著,看著那些白絲從沼澤地毯裏爬出來,準確無誤地向犧牲品延伸,觸碰他後,似乎就此靜止不動了。
“它們會直接在他身上生長。”厄溫陰著臉道,“他現在是它們的培養基了。”
“植物?”克莉絲蒂想要背過臉去,但她不能。
“我覺得是菌類。這些絲線是它的菌絲。是個菌絲體。”
他們沉默地後撤到安全距離,找了個地方過夜。西斜的落日久久不願落下,似是怕把自己弄臟。兩鐮彎月若隱若現,天空斟滿了濃稠的藍色。
“喬布救了我們。”克莉絲蒂幾近冷漠地說道,“不然我們明天會直接往那邊走……”
“是。”厄溫低沉地應道,“有這樣的可能。那麼喬布就會在明天救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