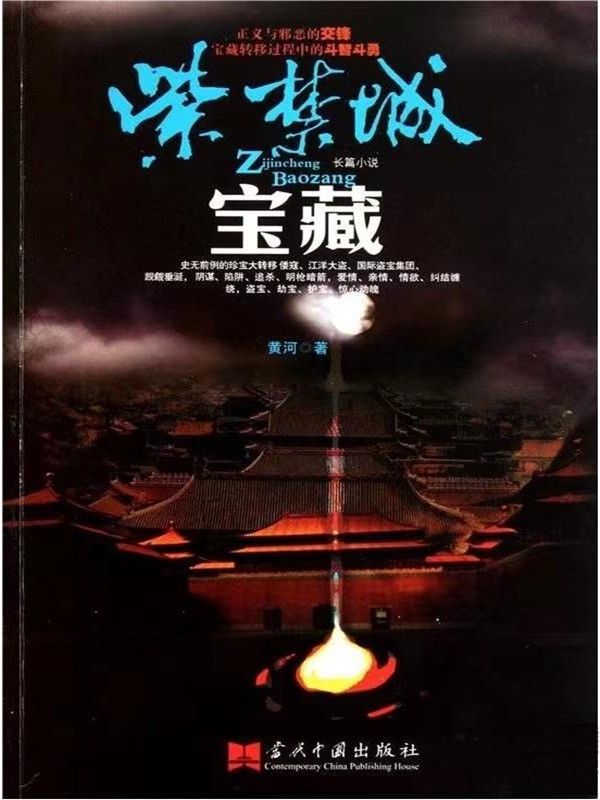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十一、賣藝街頭實乃負仇之人 救危扶弱真正俠肝義膽
京城天橋鬧市,肩搭布褡褳,頭戴遮陽涼帽富商打扮的馬家田慢慢走來。街上行人如織,街道兩旁鑲牙的、治蟲的、賣老鼠藥的、賣糖人兒的、賣小吃的……吆吆喝喝,吵吵嚷嚷,好不熱鬧。
一個穿石青團花綢衫的漢子若即若離尾隨著馬家田。
馬家田在一賣紙扇的攤兒前站下來,挑挑選選,目光無意中往後一掃,著石青綢衫的漢子趕緊縮人堆後。
馬家田忽被旁邊一人堆兒裏傳來的賣藝聲所吸引,放下紙扇走了過去。他鑽人堆裏一看,見圈兒裏一個穿水紅緊身衣靠、模樣俊俏的姑娘,倒提一口柳葉刀抱拳揖了一圈,朗聲說:“初到寶地,人地兩生,沒來得及到諸位府上請安,小女子這兒有禮了!”說著,抱拳揖了一圈,接著道,“遭逢戰亂,有家難歸,賣藝糊口,各位父老兄弟、大哥大嫂就是我等衣食父母!我這裏先給大家獻上一趟祖傳刀法,一來向前輩行家討教,二來討碗飯錢!各位,有錢的幫個錢場,沒錢的幫個人場,替小女子站個圈兒,助個興兒……”
馬家田將那女子細細一瞧,一顆心陡地提到了嗓子眼上,趕緊往前頭擠去。
姑娘道罷,又抱拳揖了揖,道聲“討教了”,唰地展刀亮了個門戶,單腳一踮,柳腰一閃,一聲嬌吒便追風逐電地耍起刀來。
馬家田嘴巴張了張,想要招呼那女子,礙於人多眼雜,不好唐突,隻得耐著性兒人圈裏立了。
姑娘舞到酣處,擰腰一個晴空霹靂騰空翻身劈刀,觀眾一齊鼓掌喝采。不料就在姑娘即將落地之時,從人堆裏滴溜溜飛來一物,端端地打在姑娘手腕上,姑娘手中刀當啷落地。場子裏敲鑼的老者和一個紮紅兜肚、八、九歲的男孩,一齊驚叫著撲上去。老者看了看姑娘傷處,回身四麵打躬作揖,低聲下氣說:“我等初來乍到,禮數若有不周之處,還望海涵。不知冒犯了哪位老爺,何必跟我等吃壩壩飯的一般見識?有何見教,敬請當麵點撥……”
那姑娘口氣可就強硬得多,氣哼哼睜圓杏眼人堆裏搜索著說:“若是何方高人要指教小女子,何必暗中下手,盡可站出來說話呀!”
“何方高人,不知道是嗎?本少爺就是了!”隨聲人群中走出個公子哥兒模樣的人來,身後又跟著兩個穿對襟排扣短衫的打手。
一個黑且粗壯的打手搶前一步:“哪來的?討飯還要看個街口,跑船也得拜個碼頭,挖個茅坑兒也有土地爺管著哩!也不問問,這地段姓甚名誰歸了哪個堂口就來練攤找吃!哼!這點規矩都不懂,跑啥江湖!”
小男孩:“誰叫你們不問青紅皂白就動手傷人!”
老者喝:“小鐵蛋,不準多嘴!”老者將小鐵蛋拉身後,連連作揖打躬道歉陪笑。
另一個暴著大黃牙的打手上前指指身邊那公子哥兒,神氣活現地:“這是我們盧少爺,老東西,你也不稱二兩棉花紡紡(訪訪),在這天橋地界,提起咱盧少爺的名頭呀,那是數九寒天打炸雷,嚇你不死也得嚇你一褲子尿!”
小鐵蛋拾起腳邊一物事,遞給方才耍刀的姑娘:“紅姑姐,是個鐵核桃!”
暴牙打手見了撲上去搶,鐵蛋縮手躲過,暴牙一巴掌抽鐵蛋臉上,奪過鐵核桃,又罵罵咧咧抬腿照鐵蛋踢去。紅姑柳眉倒豎,一掌虛攻暴牙麵門,一掌結結實實打在他胸上。暴牙摔出丈餘,鐵核桃飛向空中。黑漢打手見了凶凶地撲向紅姑,老者怕事兒鬧大,陪笑勸阻,被黑漢子一腳踢翻。
空中的鐵核桃朝馬家田落下,馬家田不動聲色伸指一彈,鐵核桃流星般射向盧少爺,端端打在他腮幫上,頓時牙碎血流,哇哇鬼叫:“誰?誰他媽背裏暗算?有種的站出來?”
黑漢同紅姑纏鬥起來,盧少爺同暴牙張牙舞爪在人堆裏找暗中下手的人。身材粗壯穿石青團花綢衫的漢子讓盧少爺盯住了。盧少爺捂著腮幫慢慢走過去,冷不防一個黑虎掏心一拳打向漢子胸窩。漢子腳不挪窩身不晃,手一招,不知怎麼就叼住了盧少爺手腕,一送一牽將他摔出丈遠,跌倒對麵人牆前。
盧少爺跳起:“反啦!反啦!打!打!都給老子上嗬!”喊叫著從懷裏掏出把二號櫓子指著穿石青團花綢衫漢子。人群大亂。
忽有人喊:“偵緝隊!偵緝隊來啦!”人群炸窩,一個個作鳥獸散。
螳螂張率四五個偵緝隊員跑來,同紅姑打了個照麵,略一楞怔,掏出張畫像看了看,隨即大叫:“刺客!刺客!她就是大鬧石川交通團的刺客!”
紅姑扶著老的拉著小的在人群中奔跑。馬家田一擰眉頭,追上去挾起老者在前飛奔。紅姑一怔,亦挾了鐵蛋飛身跟上。穿石青團花綢衫的冷麵漢子亦尾隨跟來。
螳螂張瞅著紅姑背影大著“刺客!刺客”猛追。
螳螂張倒底耳目眾多,顯然已有人向他報了信兒。馬家田和紅姑等人衝出天橋鬧市,專挑僻靜街巷鑽,螳螂張一夥緊追不舍。
一胡同口,穿石青團花綢衫的冷麵漢子突然從天而降,雙腿連踢,踢翻兩個追在前頭的偵緝隊員。雙腳落地的同時,探掌抓住一個偵緝隊員腦瓜將其扳倒,另一隻手從腿下一抄將那倒黴蛋托起,擲麻袋樣擲向要朝他開槍的螳螂張。螳螂張見頭頂掉下個煞星,早嚇得慌,舉槍就打,到發覺不對勁兒想要收槍已經遲了,槍響處,那倒黴蛋應聲落地。
螳螂張抬槍想再打,哪料那漢子已跟著落到他麵前,一把扭住了他手脖兒,兩眼前後一掃,湊他耳邊陰沉沉咕噥了幾句,一掌將他掀翻,飛身而去。
螳螂張爬起來,揉著跌得生疼的腦勺,招呼幾個欲追上去的弟兄:“還追個屁!別追了,都給我回來!”
一個手下不解,問:“隊長,咋啦?咱拳腳功夫打不過可有槍呀!”
螳螂張沒好氣地:“有槍咋的?不要腦袋啦?”
一家夥喪氣地嘟噥:“媽的,又遇上惹不起的了!不知這回是哪路神仙……”
京城某破落王府。馬家田挾著老者飛身躍上王府高牆,回頭朝紅姑點點頭,落到院內。
王府大院,荒草滿庭,門窗破損,了無人跡,一副破敗荒涼景象。紅姑挾著小鐵蛋飛落院內,小鐵蛋驚疑地打量王府庭院屋宇,仰臉問:“紅姑姐,這是啥地方呀?”紅姑不答,遊目四顧,眼裏也滿是警戒疑惑。
馬家田扶著老者向正殿走去,回頭示意紅姑跟上,紅姑略一猶豫,扯了小鐵蛋大步跟來。
馬家田扶著老者轉過正堂,繞到側後通閣樓的樓梯間,回頭衝紅姑笑笑:“姑娘放心,這兒絕對安全。老爹受傷似是不輕,應好好靜養陣兒。”
紅姑上前兩步:“這位大哥,多謝出手相助,敢問高姓大名?”
馬家田:“在下馬家田。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姑娘不用客氣。”說著,扶了老人上樓。
上到閣樓,紅姑立門邊一看,見樓內堆滿雜物,蒙滿灰塵蛛網。閣樓一角,草草收拾了個地鋪兒,顯然就是這位姓馬的眼下的棲身之所了。就尋思這馬某的身份來曆該是頗費猜詳了,但看他為人行事,又定非雞鳴狗盜之徒,卻不知他是哪條道兒上的,又為何獨自躲這地方來,該不是這王府的後人吧……想著,就上前抱拳道:“多謝馬大哥相救,大恩大德,容當後報!不過……我等鄉野草民,皆無受王府庇護的福氣,也不好再叨擾馬大……唔,或許該稱馬公子才對。小女子等這就別過……”
馬家田聞言嗬嗬笑道:“姑娘誤會了!這是座沒人住的空宅子,我隻是無處棲身,暫借此處落腳,哪是啥王府公子,嗬嗬!老人家被踢傷了心脈需要將息醫治,且不可再奔波顛跛。”
紅姑回身跪地鋪前,抓著老人手:“叔,你沒事吧?”老人搖搖頭說沒沒事兒。小鐵蛋撲上去“爺爺,爺爺”地叫著哭起來。老人吃力地欠了欠身子,終於沒能坐起來,撐起半個身子朝馬家田說:“馬家兄弟,多虧了你,要不,今兒怕是……怕是……唉,老了,沒用了……”
馬家田趕緊讓老人歇著,說不必客氣不必客氣。老人喘了陣兒,又問:“馬家兄弟,聽口音你不是這京城人呢,北邊來的吧?何故落腳在這種地方?”
馬家田:“在下正是從關外來的,到京城尋個故人,誰料數月過去,蹤跡渺無,而囊中卻日漸羞澀,故隻得暫且棲身在此。”說著,嘿嘿一笑,上前將老人枕頭弄弄正,說,“老人家,你快歇著吧,啥話兒日後再嘮,我先給你弄點兒藥吃。”道罷,從枕下扯出個長長的包袱兒,解開,卻是幾件衣衫裹住的一柄古劍,並沒見有藥瓶兒。
紅姑對他似仍有戒心,她身上本藏有跌打丸,但她並沒掏出來,袖手旁觀,她要看看這姓馬的有何作為。
馬家田找來個碗兒,又從一個豬尿脬裏倒了些水在碗裏,持劍懸於碗兒之上,拇指在劍柄龍鼻處一按,龍口張開,再輕彈劍身,就有黃色藥末兒從龍口裏吐出。馬家田將碗兒端起蕩了蕩,遞給紅姑:“給老人家喝了吧,這藥雖不是仙丹,治跌打損傷卻很是靈驗。可惜沒酒,若用酒吞下更是管用。”
豈料紅姑卻如中邪,兩眼直勾勾盯了馬家田隨手放鋪邊那柄古劍,對他遞過來的藥碗兒視而不見。小頃,又突地扭頭盯了馬家田,激動地湊前一步道:“就是你……你就是那夜街頭出手相救小女子的恩人?”
馬家田淡然一笑:“給,替老伯喂藥要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姑娘又何必掛在心上。”
紅姑接過藥碗,目注馬家田,心潮起伏地:“真是不好意思,屢次有勞馬大哥援手相救,受人滴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這叫小女子如何……如何……”說著過去替老人喂藥。
馬家田拉過小鐵蛋,摸摸他腦袋:“叫鐵蛋是不?啃不動砸不爛的鐵蛋蛋嗬嗬!硬氣!硬氣!長大一準是條好漢!”
鐵蛋:“長大我一定要作馬叔叔這樣的人,專打抱不平,專幫窮苦人!”
紅姑咯地一笑:“沒羞!能趕上你馬叔叔一個腳趾丫兒就阿彌陀佛了,還包打天下不平呢!”
鐵蛋噘了嘴,指著紅姑衝馬家田道:“叔叔,紅姑姐可小心眼兒了,別跟她好,嗬?她有槍,真正的手槍!比飛鏢暗器狠多了!就是不給人家玩兒,摸一下都猴急得什麼似的,哼,小氣鬼!”
紅姑臉色陡然陰沉,叱:“鐵蛋!再亂嚼舌根兒看我咋收拾你!”
老人也掙了掙身子,喝:“你個小東西,胡說些啥?”
鐵蛋叫了聲爺爺,委屈地湊他爺跟前去了。馬家田心想,此中必有人家不便言及的隱私,遂變了個話題兒,衝躺鋪窩兒裏的老人和站旁邊的紅姑拱拱手道:“嘮了這半天,還沒請問老伯和姑娘高姓大名……”
紅姑趕忙還禮:“小女子姓柳,名紅姑,這是我叔,那小頑皮蛋你已認識了。”
馬家田:“恕馬某多言,姑娘和老伯以賣藝為生,為何偏偏與日本人為仇?化裝踩點於前,性命相搏於後……”
紅姑:“馬大哥,實不相瞞,小女子來京,專為尋殺父仇人。而今仇人雖已找到,可恨大仇難報……”
馬家田:“這麼說,姑娘的殺父仇人定是日本人了,隻是不知因何同日本人結此深仇大恨的。”
紅姑唉氣搖頭道:“此事說來話長,不說也罷!不說也罷!”
馬家田關切地:“姑娘真是藝高人膽大呀!你到八寶胡同一攪,整個京城都鬧動了,竟還敢在天橋鬧市拋頭露麵!現今日本人和京城的警察、偵緝隊都在繪影圖形地抓你呢!可得千萬小心,萬不可再如此逞膽氣兒了!”
紅姑忿忿地:“拿賊拿贓,我額頭上也沒刻字,他們憑啥說是我幹的?”
老人在鋪窩兒裏撐起半截身子,喘咻咻道:“馬家兄弟,此舉雖是未免冒失,但也是出於無奈。為探仇人行蹤虛實,她喬裝打扮充闊人,盤纏花光了;再者,父仇未報,她寢食難安,想以此將仇人引出來……我這侄女就是好逞強,又是個急性子,從小不習女紅愛刀槍……”
紅姑不好意思地:“叔,誰讓你專撿人家短處說!”
馬家田忽閃到門邊,厲聲喝:“誰?站出來!”
門外隨聲跨進個人來,正是那剛才奮身斷後的著石青團花綢衫漢子。漢子不語,衝幾個抱了抱拳。馬家田同紅姑一齊詫異地:“是……好漢。”
柳老伯用手肘撐起上半截身子說:“多謝好漢出手相助,不知好漢到此,失禮!失禮!”
馬家田和紅姑將漢子讓進屋內。紅姑衝漢子抱拳一禮,道:“好漢對我等有相助之恩,還望留下大名,以便小女子日後圖報。”
漢子仍是不語。紅姑同馬家田互換眼色。漢子指指自己喉嚨,搖搖頭不堪言說的樣子,又比比劃劃地唔嚕幾聲。馬家田同紅姑相視一笑,頓時釋然:“噢,原來如此!好漢是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足為謝是吧?”
漢子點點頭。紅姑大奇,衝馬家田問:“馬大哥,你咋懂得……你們認識?”
馬家田搖頭道:“素昧平生。”
紅姑:“那你咋……”
馬家田嗬嗬笑道:“猜的呀!此乃套話呀!但凡好漢英雄,逢此情況莫不如此回答,嗬嗬!”
那漢子聽了頻頻點頭,又指指樓下,指指閣樓裏幾個,比比劃劃,唔唔嚕嚕。紅姑覺得很有意思,含笑瞅了馬家田,意思讓他猜猜漢子說了些啥。馬家田笑道:“他是說他怕有人追來,我們在這兒沒提防,方才他在外頭替我們望著風兒呢。是嗎?”
漢子又點點頭。紅姑和柳老伯又一齊稱謝。紅姑又問漢子高姓大名,漢子拿指頭憑空劃了劃。馬家田凝眉猜度道:“王……王什麼來著……”
紅姑咯地一笑:“怎麼?這回不靈啦?咯咯!”
漢子咧嘴一笑,屈膝用指頭在滿是灰塵的樓板上劃了個“逍”字。
漢子衝幾個抱了拳轉身大步而去。紅姑追到門邊:“王大哥留步!壯士留步!”
漢子頭也不回,竟自去了。
馬家田等人奔窗前,從窗口望著王逍穿過庭院,逾牆而去。
柳老伯閉了眼躺鋪窩裏喚道:“紅姑,我們走吧。多謝馬家兄弟了!”
馬家田詫異地:“老伯,你這是咋啦……”
柳老伯擺擺手,艱難地支起半個身子,緩緩說:“我已好多了,援手之恩,賜藥之德,一並留等日後圖報吧,老漢等就此別過了!馬家兄弟,我看你最好也換個地方才是,這兒不是久留之地呢!”
紅姑:“叔,你是說那姓王的……”
柳老伯搖頭:“倒不是專指他。這兒雖是幽靜冷清,但我等穿街過巷飛逃至此,難保沒有閑眼旁觀。青天白日的,有何秘密可言?一時疏忽,千古遺恨啦!”
馬家田略一沉吟,道:“老伯說得在理兒,既然這樣,我也不留各位。”說著,走到鋪窩邊,從枕下扯出個錢袋兒,往紅姑手裏一塞,“我雖非富豪之人,尚有幾個零錢,就送給老伯抓藥養身子吧!”
紅姑推拒:“這咋使得,這咋使得。馬大哥,這錢我等說啥也是不能收的!”
馬家田轉身將錢袋兒塞鐵蛋手中,鐵蛋推開,閃身躲柳老伯身旁。柳老伯在紅姑的扶助下站起來,連連搖手道:“馬家兄弟,你的盛情我們領了,錢卻是無論如何不能收的!”
馬家田一急,抄起地鋪上當作枕頭的包袱,抓起已用長衫裹好的古劍,將錢袋兒往紅姑腳前一摜:“姑娘,你扶老攜幼,擔子不輕,天橋被人識破行藏,暫時不便拋頭露麵,馬某此舉,全為老伯和鐵蛋小弟,這錢,你不收也得收!馬某先走一步,後會有期!”道罷,從窗口躍下,飛竄而去,轉眼沒了蹤影。